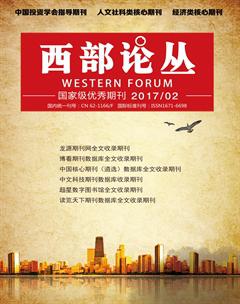淺評石黑一雄作品《被掩埋的巨人》中的 “記憶痛覺”描寫
田悅
摘 要:石黑一雄作為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一出就吸引了文學界的目光。本文將從該作品的人物和敘事線索多重分析,選擇其最具獨創性和升華意義的文學特點,評價架構于石黑一雄多重文化之上的“記憶”與“痛苦”塑造的成功之處。
關鍵詞:石黑一雄 記憶 痛覺 書評
作為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近期新作,《被掩埋的巨人》目前被稱為是顛覆了西方奇幻既有模式的神奇作品。但由于奇幻的文學形式終未被完全模具化,自然也不能以固有形式去看待這本《被掩埋的巨人》。
痛苦僅僅是肉體的應激反應,但感覺卻是更為綿長的一種記憶。石黑一雄是不直接寫痛的,在這本書中的受傷、饑餓、寒冷,甚至死亡,都不過是一種表現;他是以更加沉郁的方式表現在文中的孩子、騎士、武士和夫婦的記憶里。
一、對于個體人物的記憶痛覺塑造
人物是小說的精髓,不僅是作者表意象征的發泄點,也是讀者感同身受的體驗點。本書的“痛覺”是由五個人物和兩條主線來體現的。而“人”之中,最特殊的則是:圓桌騎士高文。小說在第三人稱的敘述中,用獨立的兩個章節,以第一人稱視角細述了高文的獨白。可以看出,高文之痛在于兩點:一是正面形象與反面形象的對撞;二是信仰之心和自我意識思考的扭曲;前者是痛楚的瞬間,后者是感覺的蔓延。
擁有著亞瑟王的首席騎士身份,高文樂于聽到人們對亞瑟的贊美和稱頌,這也是為自己騎士形象給予了絕對的肯定。但巨龍出現后,情況發生了逆轉。當年輕的軀體被歲月摧殘,亞瑟王的輝煌也僅變為閑談,高文便不再是簡單的護衛騎士,而成為一個理想化的爭辯人。石黑一雄一直以高位者的態度敘寫故事,他賦予守龍人與滅龍人的對峙,但并未劃分出他們的對與錯,使得書中少了一個絕對憎惡的敵人,而多了一位矛盾的高文爵士。
而在作者一貫擅長的自我內心對話的操控下,高文的兩次浮想深化了人物矛盾,即讓他代表了一種“痛苦符號”。符號學家諾伯特·威利結合了皮爾斯提出的“我-你”和米德的“主我-客我”對話理論,提出了一種更為全面、多維的模式“客我-主我-你”[1]。在本書中,高文更具有這種時間線性下的符號特色,即為古騎士的精神內涵(過去客我)——在時間變化中的思維沖突(現在主我)——寄予在作者傾向下的現世意義(未來你),由此成為了一個多重身份者,則是以建立起“忠貞、服從、安貧”騎士模型中,裂變出順從亞瑟理想政策和察覺仇恨根系命運的矛盾體,最后以代表著真相掩埋者和無力變革者的身份走向死亡。
可以看出,這個隸屬于亞瑟王的古典騎士,作為記憶和真相的擁有人,孤獨地建立起了過去的戰爭與現在和平的聯系。因此,高文的痛苦是更加深刻且至死不滅的。
二、對于夫妻共有記憶的痛覺描寫
石黑一雄在這部小說中以老年人的視角來寫愛情和死亡,這要比他之前任何一部作品都飽含哀傷,雖然他此前的作品常會觸及人生的遺憾與生命的逝去,但《被掩埋的巨人》帶著其眾多作品中從未有過的陰郁色調,在這種愛與死亡交織下的記憶失復,為書中角色,以至于年輕的讀者們都帶來一點痛苦的味道。
除去群體的記憶以外,個體的記憶依舊在本書中成為石黑一雄探討的重點,這里尤其是夫妻間的記憶成為了關注點。正如他在《日經新聞》采訪中所說的:“愛這個東西真正的重要性是什么?是不是基于分享了共同的記憶呢?”在書中,石黑一雄借比特麗絲的口吻回應了對痛苦的記憶的看法:“我們也愿意讓壞的記憶回來,哪怕會讓我們哭泣,或者氣得發抖。因為,那不就是我們共同度過的一生嗎?”
我們往往認為痛苦記憶的存留是一種殘忍,所以選擇去抹去而免受生活的傷害,但何曾想正因為這種應激的痛覺,才能警醒身體不再重蹈覆轍,去對之后的錯誤作以規避,更及時地對生活進行挽救。
三、民族記憶和集體記憶的創新表現
小說以亞瑟王時代的不列顛人和撒克遜人戰爭之后的偽和平為大環境,將普通的年老夫婦尋找兒子的旅途與民族的復仇記憶喚醒的兩條線索融合,形成獨特的雙線敘述,這種選擇使得本作看似魔幻,又具有現實意義。由于這本小說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作者首次將個人或是部分群體的記憶提升為整個的民族記憶問題,所以對于以復仇聯動的痛覺內涵,也應是對于更大群體的探討。
作為被津津樂道的騎士王傳奇塑造者,凱爾特人的歷史命運與本書不免有幾處共同之處。如今的凱爾特人,已經不存在一個完整、單一的凱爾特民族了,然而過去的他們則是歐洲早期重要的民族之一,其延續的血脈在英國被后來的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和北愛爾蘭人所繼承。古凱爾特人寧死不屈、誓死捍衛民族尊嚴的精神到如今已經演變成強烈的民族認同感[2]。有需談及此,是因為小說中的一位撒克遜武士,他帶著撒克遜人的堅毅和果敢,邁入不列顛人的領土,希望去殺掉令族人失憶的巨龍,喚起族人被屠殺的過去,進行對不列顛人的復仇。可以看出,在戰爭與和平內涵之外,小說塑造出民族的存在且不能用失去記憶而同化的根源性意義,即是來自于有歸屬感民族的集體無意識。
瑞典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認為,人的無意識有個體和非個體的兩個層面,后者包括人在嬰兒之前的根源,即祖先生命的殘留,它的內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帶有普遍性。小說中的愛恨情仇都來自于祖先根源的血性與記憶,不能依靠遺忘而消除過去的痛苦。石黑一雄在自己的親生經歷里看到過遭遇二戰之后的塞爾維亞人仍然被世代教導不可忘記對波斯尼亞族伊斯蘭教的仇恨,二戰之后的歐洲謀求的和平似乎更加引人深思。
四、總結
痛苦本是一種令人難受的過程和感受,但反映痛苦內容的作品在審美層面卻有著其獨特而持久的藝術魅力。也正因如此,這本《被掩埋的巨人》在石黑一雄高超的寫作技術處理方式下,將那些盤踞在痛苦之上的痛覺,細細挖掘出來,殘留在人物的命運和故事的字里行間里,刺痛著閱讀者的神經。
參考文獻:
[1] 穆詩雄.文學符號學--一種新的文學理論[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34(2):92-96.
[2] 周巧紅.略論英國社會中遺留的凱爾特民族特征[J].社會科學輯刊,2006(4):17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