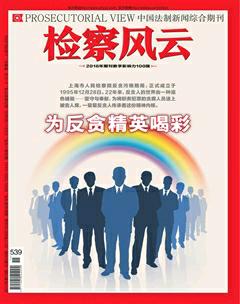制度套利與市場亂象整治從房地產兩則新聞說起
黃偉
近期房地產市場又出現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一是銀監會查處了信托公司對房地產的融資業務,二是上海市發布了整頓上海商住房的政策。除了都發生在房地產領域,這兩件事似乎并沒有直接的顯而易見的聯系。但細究其背后的邏輯卻不難發現,無論是房地產融資的貓捉老鼠游戲,還是商住房的擦邊球,都是監管政策不一致催生的制度套利案例。市場中的漏洞和亂象千千萬,如果我們的立法和執法僅僅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恐怕很難真正地起到規范市場的作用。釜底抽薪式地抹平制度落差,降低市場主體的套利空間,才是法制建設的題中之意。
房地產市場向來是最熱鬧的話題之一,也是最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之一。在中央政府“供給側改革”的基調下,過去的半年多時間可以說是房地產行業的多事之秋。本文中,我們將從房地產市場的兩條“新聞”說起,談談制度套利對房地產業態的影響,以及從規范監管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立法和執法應當如何應對。
房地產去庫存下的房企融資收緊
第一則新聞是今年5月銀監會向各地銀監局印發了關于信托公司現場檢查的通知。這份通知的亮點在于,把違規開展房地產信托業務列入2017年信托公司現場檢查要點,例如信托公司通過股債結合、合伙制企業投資、應收賬款收益權等模式投向房企融資規避監管要求。
眾所周知,房地產行業是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房企對于融資有著極高的需求。傳統上看,房地產企業和項目的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上市和發公司債。但隨著監管部門對這些融資渠道的逐漸收緊,非標融資逐漸成為房地產重要的資金來源。所謂非標融資,是銀行資金借道信托計劃、券商資管計劃這些資管產品投入到房地產開發環節、為房地產企業輸送資金的融資方式。過去幾年,非標融資一度成為房地產企業最重要的融資方式。
另一方面,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大新的挑戰是去除龐大的房地產庫存。為此,中央政府在2015年底特地提出了“供給側改革”,而房地產去庫存就是“供給側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個背景下,證監會系統開始收緊非標融資這個一度飆漲的房企融資通道。今年2月14日,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發布了私募資產管理計劃投資房地產開發企業和項目的備案管理規范,文件全稱叫《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計劃備案管理規范第4號-私募資產管理計劃投資房地產開發企業、項目》。這個《備案規范》對證券公司、基金子公司這些證監會管轄的資管機構發行的私募資產管理計劃參與房地產融資做了嚴密的限制,各種創新型的融資模式都被列進了負面清單。但是《備案規范》只適用于證監會體系下的各類資管機構,例如證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貨公司等等,而不及于銀監會管理的機構,例如信托公司。所以在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資管計劃被限的情況下,房企紛紛求諸信托公司,以至于招致銀監會的重點檢查。
“商住房”的前世今生
第二則新聞是近期上海市針對商住房發布了整頓政策,對違法違規的商業辦公項目和企業做了清理。上海住建部門強調,為進一步維護好購房人的正當合法權益,對已實際成交并完成銷售合同網上備案的,購房人要求退房的,支持購房人依法維權,開發企業必須積極配合;購房人希望繼續履行合同的,可交付使用,相關信息記入房屋交易登記系統。
此前,北京市政府已經出臺過對于商住房的整頓政策。今年3月26日,北京市住建委等五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商業、辦公類項目管理的公告》,對“商住類”房產作了限購:對于個人購房者來說,之前不限購的商住房,現在不僅限購,而且只能買二手商住房,商住房購房人必須滿足在京無住房和商辦類房產記錄,且在京已連續五年繳納社會保險或者連續五年繳納個人所得稅。此外,即使有資格買商住房的個人,也無法跟銀行申請房貸,必須全款。
所謂商住房,是指開發商將依法批準的商業、辦公建設用地改作居住土地使用,并最終以商務公寓、酒店式公寓或者LOFT的產品形式推出的住房。相比真正的住房,商住房有不少明顯的不同:比如商住房的土地出讓年限一般是40和50年,而住宅為70年;商住房一般不強制要求設計學校、商業、居委會等配套設施;購買商住房的貸款利率比較高,并且不能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等。
一個城市的規劃,會綜合考量住宅、商業、辦公、基建等多種功能的布局,特定的土地性質需要被用于特定的用途。例如我國《城鄉規劃法》將建設用地規劃性質分為10類,包括:居住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工業用地、倉儲用地、對外交通用地、道路廣場用地、市政公用設施用地、綠地、特殊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商住房這類產品實際上是對土地使用制度和城市規劃布局的一種變相突破,也是這些年房地產價格飆漲熱潮下出現的市場亂象之一。
監管標準差異下的制度套利行為
信托公司對房企的違規融資和商住房似乎只是房地產市場的兩處彼此獨立的灰色區域,但很大程度上它們揭示了市場亂象背后相同的行為邏輯。
為什么今年以來,房地產企業大量選擇了通過信托公司進行非標融資呢?前面我們交代了中央政府近期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態度,就是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出發,對房地產進行去庫存,同時在房價恐慌性地攀升時,通過限購、限售和限制房企融資等手段調控房價。正是基于這樣的政策考量,證監會和基金業協會對轄下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的房地產融資業務進行了清理。證監體系通路的封鎖,使得房地產信托產品重新煥發了生機。盡管信托計劃的融資成本相對較高,但為了渡過難關,房地產企業還是義無反顧選擇了信托融資。所以,這里的邏輯應當是清晰的:證監會收緊資管機構房地產融資業務,但銀監會并未要求銀行業機構統一步調,從而產生監管標準的不一致和市場主體進行制度套利的空間,最終資金紛紛涌向了制度洼地尋求收益。因而,想要真正限制社會資金盲目流入房地產企業,一行三會必須統一行動,從傳統的“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升級,這也是我們的金融監管部門正在積極實踐的方向。
這個邏輯同樣適用于商住房的案例。之所以開發商和投資者大量涌入商住房,并希望落實“商改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監管標準的不一致,同時這種不一致存在灰色和模糊區域,存在制度套利的空間。實際上,如前面所說,商業房產的成本比住宅房產的成本更高,例如前者貸款利率更高、稅費減免更少、物業保暖等費用更高等,但依然有眾多投資者買入商住房。其原因在于,目前很多城市紛紛縮減了住宅用地的供應,而對于商業用地的供應并沒有收緊。另外,商業用地使用年限為40年,如果其能轉化為住宅用地,使用年限可以直接變為70年,是巨大的收益增長,這也成為眾多開發商和投資者“搏一把”的重要動力。在當前住宅價格節節攀升,而商業利潤逐漸走低的大環境下,投機者通過商住房進行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而言,當前部分城市住宅用地的供不應求也是商住房快速興起的重要原因。但居民住房需求的滿足,應當通過完善住宅用地市場供需機制,而非突破土地使用性質、尋求制度套利。
統一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是市場走向理性的必由之路
房地產市場的亂象絕不僅限于違規融資和商住房項目,現實社會的亂象也不僅僅限于房地產市場,立法部門和執法部門作為經濟秩序的維護者和社會利益的平衡者,勢必要對這些亂象做出回應。以往我們的立法、執法部門更多的是走在了市場亂象的后面,當出現違法違規的行為時,出臺針對性的法律法規,或者直接對違法行為進行取締。但這種“就事論事”式的管理方式無疑很難完全覆蓋市場的所有角落,也很難稱得上高效完善。
市場的監管似乎更應當從“動力學”的角度去開展。為什么投資者紛紛購買上不了戶口裝不了燃氣的商住房,為什么房企選擇成本高昂的信托計劃進行融資?如果監管部門能協調立法和執法,例如對所有資管產品的房地產融資業務都進行一致把控,不論是證監會體系下的資管計劃,還是銀監會體系下的資管計劃,甚至保險資管計劃,資金恐怕便不會挖空心思尋找監管洼地了。同樣的,如果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審批、使用是涇渭分明的,并不存在商業用地向住宅用地隨意轉變的可能,開發商和投資者可能也不會想在這兩種土地間尋求套利。
監管標準的統一并非簡單的在立法上做到一致,它同時也要求執法在執行上確保法律法規能得到一致對待,司法部門也需要做到一視同仁。沒有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支持,立法也可能流于紙面。以房地產非標融資為例,一行三會監管標準的統一是資管行業房地產融資業務規范的前提,但各個監管部門協調行動,例如共享各類資管產品底層資產信息等,則是統一監管得以奏效的保障。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