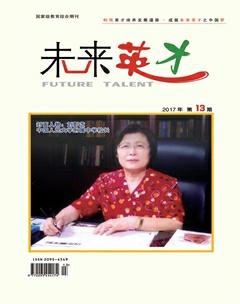守望、妥協還是遺忘
朱嵐高娃
摘要:20世紀的流散文學在流散現象全球性普及的背景下應勢而生,《追風箏的人》便是反映此類流散現象的當紅之作。小說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全球讀者的普遍熱議與熱烈追捧。引發讀者熱議與深思的不僅僅是阿富汗動蕩不安的政治局勢、傳統的風土民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更多的是作為流散者的主人公阿米拉在守望、妥協抑或是遺忘中對精神家園的守望與追尋。
關鍵詞:《追風箏的人》;探析;身份流散;精神守望與追尋
詹明遜說過,“第三世界文學是一種民族寓言,許多第三世界流亡作家都用個人史或家庭史來抒寫民族史,在他們眼里個人漂泊與民族苦難互相對應,形成了隱喻關系”[1]。《追風箏的人》就是在阿富汗人民的悲慘境遇之中植入了主人公阿米拉的個體流散體驗,折射出了阿富汗整個民族前途未卜的命運。
一、身份迷離下的流散與漂泊
在小說中最讓人慨嘆的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漂泊感,這種找不到歸屬的漂泊感是當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種生存狀態,也是作家卡勒德·胡賽尼作為流散漂泊者身份一直堅持的自我救贖的最主要方式。在《追風箏的人》中,無論是生活上的居無定所,抑或是精神上的無所歸依,處處都流露出作者作為一名流散者、作為一名漂泊者的痛苦與無奈、焦灼與不安。
對于流散者或者漂泊者來講,固然闊別故土流落到新的國度、新的異鄉,身體和精神上臨時有了新的故土、新的精神支柱,可是內心深處仍然無法割舍對故土、對家鄉的思戀,刻在靈魂深處的民族印象和個人印象始終無法跟著身體的流散與飄泊而獲得消解。他們常常無法取得所在國度主體文化的認同,也找不到自己本身的文化歸屬,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愈來愈迷離,精神愈來愈無所歸依,在這種狀況下,流散者或者漂泊者愈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作為生活在他國的強有力支撐,這仿佛真的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二律悖反。
如果促使主人公阿米爾走上流散道路的起源是童年的自我認同感的缺失,那么在異國的生活,則使其身份迷離的困惑感和危機感更加強烈。作為被美國主體文化邊緣的流散者或者漂泊者,一方面,他國文化讓阿米爾的文化視野得到了較為徹底的拓展與深化,另一方面,阿富汗傳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意識又深入其骨髓,對其進行著潛移默化地影響,無奈的他只能在異國和阿富汗雙重文化的夾縫中負重前行。當戰爭打破了阿富汗昔日的寧靜,仇恨開始蒙蔽民眾的心,人性被欲望抹殺殆盡,“追風箏”的優秀民族精神蕩然無存,尊嚴、文明都損毀殆盡,民族的前途與命運變得捉摸不定時,對于客居他鄉的流散者或者漂泊者來說,家鄉近在咫尺卻無法真正回歸其中,他們與新環境格格不入,也無法與舊環境徹底隔離,家園故土已不再是靈魂的最終歸宿,這種徘徊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無歸屬感,使阿米拉和整個阿富汗民族都陷入了困惑和迷離之中,在流散漂泊命運的背后,也反映出人民普世性的歷史深思和文化思考。
二、流散漂泊狀態下的守望與追尋
在流散過程中,流散者避免不了會產生諸如焦慮感和困惑感等負面情緒,這種負面情緒在陌生的異域會顯得尤為深重。即便現代交通非常發達便利,但在流散者心理卻仍會產生故鄉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的感覺。交通的四通八達并沒有削弱流散者或者飄泊者對故土的思念之情,在全無熟悉感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謀生,面對迥異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流散者或者飄泊者一面苦苦堅守母國的傳統文化,一面又必須面臨異國或者他鄉文化的全面浸染和離鄉背井的悵然若失。
在《追風箏的人》中,流散者或者漂泊者對于自己的混合身份也有著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流散并不一定必須悲天憫人,不一定非要感傷于世,而是要抱著開放的心態,接受陌生國度的新思想、新觀念、新的生活方式及風土人情。融入其中有諸多益處,如可以拓展流散者或者漂泊者的文化視野,帶來更加新奇、豐富、多姿多彩的生活體檢;在雙重甚至多重文化的浸染下,流散者或者漂泊者可以更加全面地思考人生,能夠更好地思考民族甚至未來的走向;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流散者或者漂泊者可以毫無畏懼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隨心所欲地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對于流散者或者漂泊者的身份問題,確屬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就像小說中著意刻畫的代表人物一樣,大多數人把“我是阿富汗人”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對陌生的環境選擇逃避、選擇無奈,只能在個人的回憶當中才能找到阿富汗人的影子,才能撥動那根民族的琴弦。有些人卻與之相反,這些流散者也懷念故土,也懷念阿富汗的人文情懷,但是他們用更加開放的心態,努力地融入到異國他鄉的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當中,將自己的理想和他鄉異國緊密聯系起來。這種態度,并沒有真正讓他們陷入僵化、一成不變的身份定位之中,而是真實又自然地被不同的文化所感染,在兩種文化所構成的生命歷程中自由地行走。還有一種流散者始終堅定地認為無論自己身在何處,他們始終是阿富汗人,因為那是他們的根之所在,這種立場,盡管會讓他們免于陷入混合身份所帶來的種種困惑和迷離當中,但是客觀的外在環境卻卻無時無刻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但不管如何,這些都是流散者們做出的自我身份追尋,就像主人公阿米爾竭盡所能想消除在阿富汗的個人記憶一樣。阿米爾看似隔斷了與阿富汗的種種聯系和牽絆接受了異國文化,已經融入到異國主流社會當中,但是小說卻用近一半的篇幅講述阿米爾自己救贖的過程。如果說阿米爾童年的遭遇屬于個人悲劇,那么在種族沖突嚴重、宗教文化激烈碰撞、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的情況下,他被逼無奈選擇離鄉背井并因此作為流散者對自我身份的不斷追尋,則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痛苦的印象已經深深地烙印在阿富汗難民心中,自我身份的困窘與追尋在這種不斷的流散漂泊過程中日益加深,悲劇已經開始超出了個體范疇,演變為一種集體的、難以消除的民族悲劇。從這種意義上說,《追風箏的人》主人公阿米爾的流散之路就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主人公阿米爾的身份追尋與重構之路,表達了作者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阿富汗人民的無限憐憫與同情,以及對戰爭發動者的強烈譴責和抨擊,這也賦予了小說更加深厚的內涵和價值,使其具有了更為廣泛的普世與濟世意義。
參考文獻
[1] 付煜.論《追風箏的人》中的身份認同與價值重建[J].名作欣賞,2013(28):87-90.
[2] 李丹.放逐靈魂的流浪——解讀卡勒德·胡賽尼《追風箏的人》[J].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11,32(5):71-7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