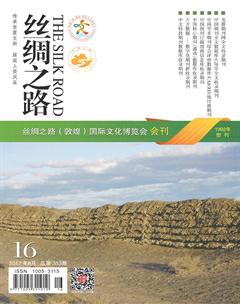裕固族東遷與玉門
[摘要]裕固族的東遷,與今玉門市轄境有密切關系。關西數衛的東遷和安置,是裕固族形成的重要因素,經歷了一個長期、多次甚至反復的過程。今玉門轄境,是裕固族東遷的出發地之一。赤金蒙古衛遺眾是構成裕固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玉門;裕固族;赤金蒙古衛;民族融合
裕固族的東遷,與今日玉門市轄境有密切關系。如欲理清裕固族的東遷細節,必須對有明一代在今玉門轄境生活過的各個殘元部落有一個較為詳細的了解。而這些部落,后來即是裕固族之組成部分。有關赤斤衛部眾東遷及安置與裕固族的關系,筆者曾著文《赤斤蒙古衛、罕東左衛部眾內徙、安置與裕固族各部關系探》。1今再申前述,對當時居處玉門境內各部來龍去脈稍加細說。
關西數衛的東遷和安置,是裕固族形成的重要因素。而關西數衛的東遷,是一個長期、數次甚至反復的過程,其出發點又非一地。由于有“西至哈至”民歌的流傳,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似乎裕固族的東遷,只是從一個或兩個地方出發,也就是說只是從“西至哈至”(大多學者已經認同西至、哈至為沙州、瓜州的觀點)東遷。其實,關西各衛部落的東遷,其出發點各不相同,東遷的時間也不盡一致。如當時活動于沙州的沙州衛、罕東衛、罕東左衛的東遷,活動于西寧周邊及以西的安定衛、曲先衛部眾的輾轉往肅州遷徙,包括哈密衛一部分的東遷等。其中,長期生活在今玉門轄境的赤斤衛部眾的東遷,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今玉門轄境,也是裕固族東遷的出發地之一。
今之玉門轄境,大多地方明代屬于赤斤衛。
蒙元時期,今玉門轄境為豳王家族所統治。有關河西西端的這段歷史,《肅鎮華夷志》卷一“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記載頗得要領:“理宗寶慶元年,蒙古鐵木真代夏,并有其地。元至元七年,置肅州路,隸甘州行中書省,哈昝達魯花據守。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討平之,哈昝掠人民遁入沙漠。二十八年,開設肅州衛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后五所。永樂三年,裁革威虜衛,歸并本衛,為中右、中中二所,共七千戶,所隸陜西行都司。”2
洪武五年(1372),宋國公馮勝下河西,河西蒙元勢力多不戰而逃亡。但明軍沒有繼續西進,而是據嘉峪關而守。大軍還后,逃散的前元殘存各部,陸續返回故地,歸順明政府,罕東衛、沙州衛、赤斤衛,正是在此背景下相繼設立。赤斤衛的設立史料記載頗詳。
《殊域周咨錄》卷14謂:“赤斤蒙古……元時為瓜州,地屬沙州路。本朝永樂二年(1404),故元韃靼丞相苦術子塔力尼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人來歸,詔建赤斤蒙古千戶所,賜誥印,尋升衛,以塔力尼為指揮。”:3“永樂二年九月,有塔力尼者,自稱丞相苦術之子,率所部男婦五百余人,自哈剌脫之地來歸。詔設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為千戶……八年,詔改千戶所為衛,擢塔力尼指揮僉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4
這些歸順的前元部落被安置在赤斤一帶耕牧,時間較早,還不能將其歸入“東遷”。
有關赤斤衛后來分裂為三部分,與部眾由兩種成分構成有關,筆者在《赤斤蒙古衛、罕東左衛部眾內徙、安置與裕固族各部關系探》一文中已有詳細論述。
赤斤建所、衛后,其部眾不可能只有500余人,而是不斷有逃散者陸續歸來,這些歸來者有兩種成分:撒里畏兀爾(史料稱作“西番”)和蒙古族,衛眾因此發生了分裂,牧居于不同的地點。根據《邊政考》記載,早在弘治年間,一部分就東遷至肅州討來河磁窯山口住牧:“赤斤蒙古衛,都督鎖南束,頭目他力把爾加等,原在關西紅泉地方住牧,弘治年間安插肅州討來河磁窯山口住牧,見有部落男婦一千二百九十名口。”5
“關西紅泉地方”,蒙玉門市博物館王璞館長告知,應即《重修肅州新志》“山川”目下“紅泉”條:“紅泉,在赤斤東南一百四十里”。6這很可能是因衛眾分裂后“至是阿速勢盛,欲兼并右帳,屢相仇殺。鎖合者不能支,訴于邊將,欲以所部內屬”7后的內徙。
其余部眾在今玉門轄境主要集中住牧于以下數處:苦峪、王子莊、赤斤城、騸馬城、柴城兒、川邊、回回墓、大草灘(大草灘今屬嘉峪關市管轄)等處。
有關這些部落主要住牧地、何時東遷乃至東遷原因,《肅鎮華夷志》載之甚詳。
細審《肅鎮華夷志》和《邊政考》,以住牧地來命名的各部落有如下:
苦峪衛(苦峪城)的情況稍稍復雜。苦峪城最早受哈密衛管轄。“本朝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來朝,且貢馬,因封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眾居苦峪城。”8哈密衛凡有變故,則其眾東向,皆逃于苦峪。因此,苦峪城或苦峪衛(即苦峪城、下苦峪城)分別生活著赤斤衛和哈密衛部眾,甚至沙州衛遺眾破散后一部分也依從在此9。
“苦峪衛,不知何代建立為衛。都督卜剌召,乃肹卜兒加之父,與也先革同宗,今朵爾只之祖也,指揮管卜兒加、舍人綽兒吉搔宗,以上四族聞皆指揮茍骨班之男,今無遺種矣。又皆沙州迤北之部屬也,若王子莊則住哈峪兒,亦都督也,子曰喃上兒,乃今川哥兒之祖。”10
此苦峪衛,應為下苦峪城,即楊富學先生所論今“西域城”。11
這里有個問題,就是下苦峪城本為安置哈密衛遺眾,包括忠順王族、王母弩溫答失里等,何以又出現了都督“卜剌召”呢?原來,正統九年(1444),哈密衛“被土魯蕃酋鎖檀阿力虜王母及金印以去,國人離散。王母外甥畏兀兒都督罕慎率眾逃居苦峪、肅州。”12這是哈密衛被吐魯番阿力殘破后,遺眾第一次東逃苦峪和肅州。王母及金印則為阿力所虜去。赤斤衛卜剌召、肹卜爾加一支應該住牧于苦峪城而非“下苦峪城”。
“肹卜爾加族原系苦峪城苦術之部屬。嘉靖初年肹卜爾加投來肅州地方,已死,今有子曰朵爾只是也,見為頭目。狡詐貪殘,殆難信懷者也。總牙子肹束爾加乃其婿也。朵爾只見滿哥虎力等強壯膂力,恐伊老勢孤,見婿與革力哥失有隙,遂定計將滿哥虎力等十二人誘殺之,令肹束爾加收帳房,其被害諸夷雖歸部下,心中無不仇恨朵爾只也。今朵爾只晝則乘馬往來,夜則披甲獨臥,亦恐其害己也。部落帳房約有六十余頂,男婦二百有余,牛羊馬駝一千余只匹。羈留一人,即朵爾只子名倉爾失加,終非成服之夷也。萬歷中有頭目阿卜束統束。”13endprint
由上,“肹卜爾加族”顯然非哈密衛遺眾,而是苦術支脈。其部落從永樂二年(1404)來歸,被安置在苦峪一帶居住,直到嘉靖初為土魯番所逼,東遷肅州周邊而被安置,在苦峪及其周邊生活了約百年之久。其安置情況如下:
“苦峪族,頭目朵爾只等部落,帳房九十九頂,男婦四百七十一名口,安插白煙墩南空堡。今頭目阿卜束部落,帳房二百五十頂,男婦三百名口,安插煖泉莊。”14
“白煙墩”在今金塔縣境。此部分后來又被安置到了“煖(暖)泉莊”。關于此部分,筆者在《明代東遷關西諸衛部眾在金塔的安置與流散——以<肅鎮華夷志>為主》15《裕固族人口量變初探》16兩文中已有論說。
與苦峪的肹卜兒加血緣關系最近的是革力哥失部眾。
“革力哥失族 亦系赤斤蒙古衛都督苦術枝派。正德間,父也先革預知有西夷犯邊之機,先投來肅州近地,后果西夷犯邊,游擊芮寧戰沒,也先革以為幸。當時有歌曰:先革馬上微微笑,拍著馬鞭敲。先革乖也先革乖,領著部落先回來。不是先回來,頭上回回禍放來。由是觀之,則當時回夷與諸番相通之情路可驗矣。萬歷中頭目怕剌宛沖統束。”17
革力哥失,又寫作“革力箇失”,其牧居地主要在赤斤城周邊,故稱“赤斤頭目”云云。該部落從永樂二年到正德期間(大致正德七年(1512)的一百余年間,一直牧居于赤斤城周圍。“頭目也先革即今個力個失之父。此夷常自擬曰:我乃元平章之人也。可見為達種。”18“其余部落自正德八年以后,屢被回賊搶殺,俱各投來州來臨縣城四傾堡住牧,離城五里。”19游擊芮寧戰死于正德十一年。則也先哥東遷或為正德十年(1515)。
革力哥失是赤斤衛人口最多、持有赤斤衛印信的一支。
“革力個失弟可洛縱一枝部落,帳房七十八頂,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安插舊八里墩堡。”20也可能在東遷前,可洛縱已經與其兄分立,自率一支。但史料未揭示可洛縱一枝牧居地點。
還有一支,由于有預知吐魯番東侵而先期逃往肅州的經歷,又被稱作“逃軍番”或“逃軍族”(“他爾加族 原系赤斤蒙古衛左所千戶賞不塔兒之后別種,來附肅州之前,他爾加祖曰松林,先從赤斤逃來肅州近地,后各族至肅州,見松林皆笑曰:逃軍是也。因此,又名曰“逃軍族”。部落頗守法度,事耕牧焉。”21)《邊政考》也有記載:“逃軍族,番僧頭目普耳咱結思冬,部落男婦一千一百九十名口,住牧肅州迤南紅山口。”22既言其“逃軍”,則先于其他部落東遷。
“川邊族,頭目察黑包等部落,帳房二十七頂,男婦一百一十四名口,安插王子莊墩堡。今頭目搶爾加奔部落,帳房一百二十頂,男婦一百六十名口,安插老鸛窩莊。”23為之建堡,名“哥力哥什堡”。24
“察黑包族亦苦術之部屬,分住川邊,與肹卜爾加同歸肅州,乃朵爾只之弟兄也。察黑包死,子曰滿哥虎力,繼為頭目,近被朵爾只與肹束爾加謀殺,部落帳房四十余頂、男婦一百有零,今皆屬革力哥失,朵爾只欲屬之,夷眾心不愿隨,俱力服而已。以上三族,萬歷中止有頭目一名搶爾加奔統束。”25
則察黑包與朵兒只為從兄弟。從川邊東遷時間與革力哥失同,被安置在今金塔縣,為其建堡,名之為“察黑包堡”。26其子滿哥虎力為朵兒只設計殺害,其部落為朵兒只吞并。
“川邊”地名,所處不詳。《肅鎮華夷志》載《西域疆里》有“赤斤西二百里至苦峪城……苦峪西一百二十里至王子莊城,……莊西八十里至卜隆吉河,俗名川邊河。”27則當時卜隆吉兒河也俗稱“川邊河”。但《肅鎮華夷志》又有“一種熟達 即赤斤蒙古衛等地之番,原系都督苦術部落,亦前元之達種也,先在赤斤迤北川邊,各分頭目,散處住牧。后因土魯番搶掠,窮迫陸續歸附肅州,各有頭目枝派”28的記載。“赤斤迤北川邊”應即今日花海子一帶。察黑包部落可能一直生活在花海子一帶。作為苦術枝脈,其大小頭目都居住地不是很遠。
還有一名之為“柴城兒”的部落,據說其頭目與革力哥失、肹卜爾加同宗:“卜木爾加族,亦苦術之后,分居柴城,與革力哥失、肹卜爾加同宗。嘉靖初年卜木爾加父曰帖木兒,來歸肅州,部落百人,今卜木爾加懦孤,不能頭目,同部屬十余人俱投革力哥失與朵爾只部下矣。”29
柴城兒,在《秦邊紀略·西域土地人物略》中有“嘉峪關西八十里為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西四十里為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冢,故名。迤北缽和寺,寺西五十里為柴城兒,墓西四十里為騸馬城”字樣,30則柴城兒在回回墓迤北缽和寺西四五十里。據王璞先生判斷,應即今下溝一帶,此處有數個城障,命名為下溝一墩、下溝二墩、下溝三墩。
還有一支是騸馬城部落。
“牙蘭族 原系關外騸馬城之番,亦蒙古衛之部屬也,乃指揮頭目總失加之孫,先年投順肅州,今在兔兒壩地方住牧,牙蘭已死,其子為頭目,居住平川,每月近[進]城貨賣,守法安分,部落男婦不過五十余人。以上番族俱垂髻達語,時人謂之熟達也。萬歷中頭目卜牙爾加統束。”31這個“牙蘭”與屢屢代表吐魯番向東進犯赤斤乃至肅州的“牙蘭”(有時也寫作“牙木蘭”)不是一個人。筆者以為,“牙蘭”或“牙木蘭”,皆“aslan”即“獅子”的意思。西域各民族中,以此為名者很多。生活在騸馬城的這部分赤斤衛部眾,其東遷的時間應該也是正德期間。
另一支即牧居于王子莊的部落:“川哥兒族,亦赤斤、王子莊苦術之部落也。嘉靖初年投來肅州地方,膂力過人,騎射貫便,曾隨兵備副使陳九疇隨操演射,與伊置蓋房舍,常給糧賞,后因嗜酒無厭,將馬牛羊并妻子變賣盡絕,部落見其不能為頭目,遂四散不服。已死,有子曰把卜罕,二人亦勢孤,不能頭目,終日乞食而已。余番有者,屬朵爾只矣。”32王子莊在苦峪城西北五十里處,筆者曾親往考察,在《明代苦峪衛、苦峪城考索》一文中已有考證,認為“二道溝(今柳溝)附近可能是王子莊廢城垣所在地。”33《西域土地人物路》中有缽和寺、柴城兒、苦峪城、王子莊等處方位圖。
苦峪、川邊及革力哥失三部,有相同的血緣關系。其祖上為蒙元平章,血統高貴,故一直做頭目。三部原屬赤斤蒙古衛,自明初投順、設赤斤蒙古所,后升為衛,一直生活在苦峪、赤斤、川邊一帶,支脈綿延,歷時百年。如以諸衛受亦不剌殘破和吐魯番東侵壓迫作為東遷的起始原因,則其主體部分的東遷,始于正德八年到正德十年,東遷的出發地為各自的牧居地,具體說來,就是先是流散到肅州周邊,后被明政府安置在今金塔縣威虜、王子莊等地,為其建堡。但后來又流落到肅州及甘州南山。有關從金塔南遷入祁連山,在《明代東遷關西諸衛部眾在金塔的安置與流散——以<肅鎮華夷志>為主》一文中有詳細揭示。36endprint
應該說,在吐魯番東侵前,生活在境內的赤斤衛各部,雖然不時受到“北番”野乜克力或瓦剌等的侵擾,但沒有出現大規模內遷。
上表內容,出現在以表解方式的《西域土人物略》當中,可知,張雨記錄這些材料時,赤斤衛諸部還生活在原來的牧居地。
《邊政考》是時任甘肅巡按御史的張雨在其任時,奉都察院“每三年一次,該巡按御史閱視各鎮軍馬器械,體察將官賢否,同畫圖具奏,并檄本部查照施行”38之命而成。是知完成時間為嘉靖二十六年。其材料主要依據都察院每三年一次的匯報,包括畫圖。因此,不僅材料可考,且其取材當早于嘉靖二十六年。與《肅鎮華夷志》對比,則知上表材料,早于正德期間赤斤衛各部落陸續東遷前。
由上,可知赤斤衛部眾從永樂二年投順明朝后,設立赤斤所,旋升為衛,部眾在今玉門轄境的苦峪、王子莊、赤斤城、柴城兒、川邊一帶分散住牧,前后相對穩定的住牧生活約有百年。直到正德年間,受吐魯番東侵的逼迫,才陸續東遷肅州周邊。因此,玉門也是裕固族東遷的重要出發地。在東遷過程中,部眾當中還發生了諸如也先哥事先東遷的民謠,以及“逃軍番”這樣反應東遷的有意義的名稱,還有住牧大草灘的巴郎一部,在東遷后,帶領其妻前往兵備道處討要胭脂這樣有趣的事。
筆者在《裕固族人口量變初探》39一文中較為詳細地統計了東遷后安置的各部落人口數量,在表3《邊政考》所載所有關西八衛遺眾人口數量的18183名口中,屬于赤斤衛遺眾者為5148口,幾乎占到了1/3。可見,赤斤蒙古衛遺眾是構成裕固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1高啟安:《赤斤蒙古衛、罕東左衛部眾內徙、安置與裕固族各部關系探》,《甘肅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第31~44頁。
2[明]李應魁著,高啟安、邰惠莉點校:《肅鎮華夷志校注·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頁。
381219[明]嚴從簡著、余思黎校注:《殊域周咨錄》,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66頁、第412頁、第415頁、第467頁。
47[清]張廷玉等:《明史》卷330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556頁、第8557頁。
5223738[明]張雨《全陜邊政考》,《續修四庫全書》第738冊,上海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57頁、第157頁、第148頁、第2頁。
6[清]黃文煒纂修、吳生貴、王世雄等校注《重修肅州新志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71頁。在該志“關隘”、“烽堠”目中也有記載。“青頭山口:東至紅泉口嘉峪關交界,西北至赤斤所一百三十五里。”(第578頁)“紅泉口:在嘉峪關西南,所城東南。”(第579頁)。
9《明史·西域傳·沙州衛》:“明年又為哈密所侵,且懼瓦剌見逼,不能自立。乃率部眾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且令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眾而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560~8561頁。
10《肅鎮華夷志·屬夷內附略》,第276頁。
11見楊富學《玉門“西域城”即“下苦峪”考》,為“玉門、玉門關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尚未發表。感謝以初稿見示。
1314171820212252728293132《肅鎮華夷志》,第285頁、第58頁、第285頁、第276頁、第57~58頁、第287頁、第58頁、第286頁、第58頁、第281頁、第286頁、第286頁、第285~286頁。
15242636高啟安、邰惠莉《明代東遷關西諸衛部眾在金塔的安置與流散——以<肅鎮華夷志>為主》,《金塔居延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27~534頁。
1639高啟安《裕固族人口量變初探》,《河西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第1-19頁。
30[清]梁份著、趙盛世等校注:《秦邊紀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頁。
33高啟安:《明代苦峪衛、苦峪城考索》,楊永生、李玉林主編《火燒溝與玉門歷史文化研究文集》,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656頁。
34《肅鎮華夷志》,第317頁,復制于《嘉靖陜西通志》。
35李之勤:《西域史地三種資料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頁復制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