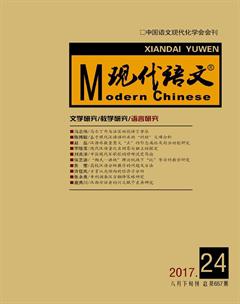方言從眾傾向的經濟學分析
摘 要:語言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人類社會勞動的產物。方言是語言的變體,具有從眾傾向,人們偏好使用人口相對較多的語言,這樣的選擇主要是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量。隨著社會的發展,方言將逐漸向普通話靠攏。
關鍵詞:方言 從眾傾向 經濟利益
方言是人們常說的“地方話”,是某一地區居民普遍使用且與其他地區有著明顯差異的同一語言在不同區域上的分支,是民族語言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分化出來的具有區域性的異變體。方言的產生與變異,與人們生活的區域有關,是長期歷史沉淀的結果。方言與方言之間的差異,與人口遷徙和分化有著直接的關系;人口的流動性,對方言變異產生明顯的影響;影響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因素。古代家庭大都是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物質交換十分有限,人們之間的交往也只在有限的區域內活動,加上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①,久而久之,演變成了各具區域特色的方言。
一、方言的從眾傾向
方言的從眾傾向是指一個人會受到他身邊多數人所講方言的影響,自覺地學習、模仿他們的方言。因此,使用人口少的方言會受到使用人口多的方言影響,使用人口多的方言會受到通用語的影響。根據人口流動的規律,經濟條件較差地方的人口自然地向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流動,人們自然就要學習當地的語言,這樣才能適合當地的生活。對于我國來說,農村方言受到周邊小城市方言的擠壓致使說農村方言的人口減少②,小城市方言往往受到周邊大城市方言的擠壓,致使說小城市方言的人口減少,全國各地方言受到普通話的擠壓,致使說地方方言的人口減少,說普通話的人口增加。這種影響和擠壓的程度,通常表現為人們減少所使用方言的時間和機會,甚至完全拋棄過去所講的地方方言而選擇普通話。這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農村人要模仿周邊小城市人說話,小城市人為什么要模仿大城市人說話,大城市人群為什么要模仿北京人說普通話,全國人為什么都傾向于說普通話了。
方言的從眾傾向與人口的流動性有關,在人口流動性大的地區表現十分突出。改革開放以后,偏遠地區農民進城務工,他們開始學說外地方言,以適應當地人的生活。如廣東,早期外來務工人員要學說白話,有的是先學一些白話后才來廣東務工的。隨著外來務工人口的增加,有的地區出現了外來人口多于本地人口的現象,如東莞市戶籍人口189萬人,常住人口832萬人;深圳市1979年建市之初只有31萬人,到2016年實際管理人口2000多萬人,絕大多數是外地人。人口結構的變化,通用語言的選擇也發生了變化,外來務工人員不用再講白話,反而廣東人在學講外地話,大家都講起了普通話。
方言的從眾傾向,不僅是個人自覺,也是政府自覺。我國古人十分重視語言的統一,周朝時就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古代通用語——雅言。《辭海·雅言》條說:“雅言,古時稱‘共同語,同‘方言對稱。”孔穎達在《正文》中說:“雅言,正言也”,“正言”指的是通用語,相當于現在的普通話。據史料記載,“雅言”是以周朝國都豐鎬地區的語言為全國通用語,各地語言相對于豐鎬話來說都是方言。孔子在魯國講學,他的弟子來自四面八方,孔子就是用大家都能聽得懂的雅言來講學的。《論語·述而·第七》中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元朝時,統治者考慮到語言不通,下令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話為標準音的“天下通語”。明朝皇帝朱元璋下旨編纂《洪武韻》,頒發全國。到了清朝,雍正皇帝率先對官員使用“官話”,在方言最難懂的福建、廣東設立了“正音書院”,讓讀書求仕的人學習官話,否則就不許參加考試,讓各級官員在執行公務的時候,一律使用官話,以免因各地語言不通,耽誤政事。新中國成立后,200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
普通話的推廣和使用,擠壓了各地方言的生存空間。浙江金華市曾經做過關于金華方言的調查,在6歲到14歲孩子中,幾乎所有人都會說普通話,其中52.03%的人完全不會說金華方言,能用金華方言較好交流的僅占22.65%。方言的從眾傾向,使現在的孩子一代比一代少講方言,他們從托兒所、幼兒園開始就接受普通話教育,回家看的是普語動畫片,游戲及任何來自書面或者媒體的信息都用普通話。方言的瀕危狀態早已是學界的共識,特別是在經濟落后地區,表現尤其明顯。
二、方言從眾傾向的經濟因素分析
方言的從眾傾向不僅是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分析,首要是把個人當成“經濟人”,每個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一個人的行為選擇,符合他的效用最大化法則,否則,他就不是理性的經濟人。因此,人們對語言的選擇包含著經濟因素,選擇哪種語言不僅僅是從眾心理需要,更主要的是語言背后經濟利益優化的結果。人們選擇使用哪種語言,放棄哪種語言,都是通過經濟上的比較,從而做出的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區域優勢,特別是在語言發源地或者講這種語言的人口占多數的區域,它是這一地區的主流語言。講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生活工作更方便,這是主流語言的比較優勢。
語言是一種人力資本。掌握一種語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它是以放棄許多機會成本為代價換取的,如果一種語言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大于機會成本,那么他就會選擇這種語言,否則,就不會學習也不會使用這種語言。對于掌握多種語言的群體,大家會自然選擇多種語言下的通用語言,這樣能降低交流成本。眾多語言會朝著單一語言方向過渡,語言選擇是收斂的。
語言能改善人們的自身經濟條件,語言技能對經濟收入有著重要影響。機會成本、語言群體邊界的溢出收益、語言歧視以及非主流語言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邊緣化,這些都是語言使用者考慮的經濟因素。使用人口較少的方言的就業機會少于使用人口較多的方言,使用人口較多的方言的就業機會少于使用通用語的機會,使用本國通用語的就業機會少于世界通用語的機會。當學習一種生活上及工作上都用不上的語言,這種投資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學習的動力和效果大為減少。
對于語言相異的兩個地區,如果一個地方的生活環境優于另一地方的生活環境,人們會自覺地進行語言方面的投資,學習該語言。主流語言能幫助使用者尋找收入更好的工作,從經濟上來說是合算的。比如,早期不少農民學說白話來廣東務工,學說上海話到上海務工,現在大家都講普通話在國內找工作,就是這個道理。當今不少人學習英語或其他外語,移民到美國等發達國家找工作,主要還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條件比國內好。
語言選擇相對于個人來說是市場化的,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通過比較某種語言對自身利益的改善程度,自覺地選擇那種能對自身帶來收益最大化的語言。同樣道理,有些地方以保護民族方言為由而排斥通用語,最終也是徒勞的,這不符合語言學自身發展的經濟規律。從國家層面上講,推行一種統一語言和文字,從經濟上講,減少各族人民之間的交流成本;從政治上講,對于促進經濟發展,增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加強各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有著重大作用。
我們以此來分析國內的英語教學。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生活上不說英語,工作上不用英語,投入的成本相對于預期收益來說是不值得的,這是中國人學不好英語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日常生活、工作都離不開英語,需要經常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程度,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選擇學習英語而不需要外力來強制。
三、結語
我國有55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語言非常豐富。據統計,我國正在使用的語言有80多種,除回族和滿族一般使用漢語外,其他53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有的民族語言有兩種以上,如裕固族分別使用東部裕固語和西部裕固語,瑤族分別使用勉語、布努語和拉珈語。各語種分布區內,存在著眾多區域性的方言,方言數量多到難以統計。
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方言之間、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差別其實就是在通用漢字的基礎上語言要素(語音、詞匯、語法)上的差別,是同一古老語言歷史發展和分化的結果。各地方言之所以會產生、發展以至衰亡,除了受自然環境影響之外,還要受到個人的從眾傾向影響,這種從眾傾向最終取決于經濟原因。個人選擇哪種語言,取決于這種語言能給自已帶來的機會。經濟越發達的地方聚積的人口就越多,大家自然而然地選擇講通用語。現在大家重視說普通話,是因為普通話是全國通用語,由此導致的方言萎縮以致衰亡,是語言發展規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注釋:
①陳鼓應注譯:《老子注譯及評介》,中華書局,2006年,第473頁。
②從人口數量上看,農村人口是比城市人口多,但人口轉移不是集
體行為,而是個人行為,相對于一個人口眾多的城鎮,還是個量。
參考文獻:
[1]陳方.普通話與漢語教學研究[J].教學與管理,1988,(6).
[2]汪丁丁.語言的經濟學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1,(6).
(許佳嵐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