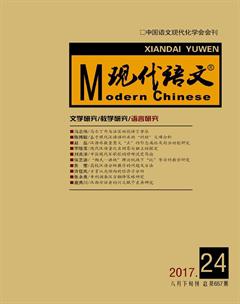英漢親屬稱謂語義場差異及其文化闡釋
摘 要:親屬稱謂是反映人們之間親屬關系的語言符號體系,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構成了特定文化的親屬稱謂體系。本文將英語和漢語中的親屬稱謂詞(背稱)作為研究對象,采用義素分析的方法來考察英漢親屬稱謂語義場的差異,繼而意欲探尋差異背后所蘊含的不同文化內涵。
關鍵詞:親屬稱謂詞 英漢對比 語義場 文化闡釋
20世紀80年代,呂叔湘(1984)曾對“cousin”一詞作過這樣的表述:“如果你翻譯一本小說,遇到主人公有一位“cousin”,你譯作‘表弟,后來發現他是女性(代詞用“she”),就改作‘表妹,后來又發現她年紀比主人公大,又改作‘表姐,再翻下去又發現原來她不是主人公母親一邊的親戚而是他父親一邊的,又只好改作‘遠房姑媽……”[1](P140-141)
從“cousin”一詞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英漢親屬稱謂詞的差異和不對稱。“cousin”年齡大小、性別界限相當模糊,可以被用來稱呼堂(表)兄弟姐妹中的任意一人。這種情況在漢語世界里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每個人的角色都配備有一個精確的親屬稱謂詞。目前,英漢親屬稱謂詞在翻譯互譯、社交語用等領域研究相當豐富,不過將詞匯對比與文化分析結合起來的著作為數不多。鑒于親屬稱謂有背稱、面稱之分,面稱容易受地域、語境等不同因素制約,故為了便于對比分析,本文著重闡述英漢親屬稱謂背稱語義場的差異,并進一步探尋差異背后所蘊含的不同文化內涵。
一、英漢親屬稱謂語義場比較
分析親屬稱謂語義場時,本文采用義素分析法,即引入“男性”“直系”“輩分”“血親”“父系”5個義素標準,并用符號“+”和“-”表示親屬稱謂詞是否具有某一特征。在對比輩分時,主要遵循“以自己或本人為軸心,向上下左右不同側面延伸”的原則,平輩用符號“=”表示,上一輩記為“+1”,上兩輩記為“+2”,下一輩記為“-1”,下兩輩記為“-2”。另外,這里選用的15個英語親屬稱謂詞主要參照了英國社會語言學家特魯吉爾(1974)的提法。具體分析如下:
grandfather=[+男性][+直系][+2][+血親] 祖父=[+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外祖父=[+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grandmother=[-男性][+直系][+2][+血親] 祖母=[-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外祖母=[-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father=[+男性][+直系][+1][+血親] 父親=[+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mother=[-男性][+直系][+1][+血親] 母親=[-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brother=[+男性][+直系][=][+血親] 哥哥=[+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弟弟=[+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sister=[-男性][+直系][=][+血親] 姐姐=[-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妹妹=[-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son=[+男性][+直系][-1][+血親] 兒子=[+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daughter=[+男性][+直系][-1][+血親] 女兒=[-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grandson=[+男性][+直系][-2][+血親] 孫子=[+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外孫=[+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granddaughter=[-男性][+直系][-2][+血親] 孫女=[-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外孫女=[-男性][+直系][-2][+血親][-父系]
uncle=[+男性][-直系][+1] 伯父=[+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叔父=[+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姑父=[+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姨夫=[+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舅父=[+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aunt=[-男性][-直系][+1] 伯母=[-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嬸母=[-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姑母=[-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姨母=[-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舅母=[-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nephew=[+男性][-直系][-1][+血親] 侄子=[+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外甥=[+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niece=[-男性][-直系][-1][+血親] 侄女=[-男性][-直系][-1][+血親][+父系]
外甥女=[-男性][-直系][-1][+血親] [-父系]
cousin=[±男性][-直系][=] [+血親] 堂兄=[+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堂弟=[+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堂姐=[-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堂妹=[-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表兄=[+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表弟=[+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表姐=[-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表妹=[-男性][-直系][=][+血親][±父系]
(注:表兄弟姐妹,若是姑表兄弟姐妹,父系項記為“+”;若是舅(姨)表兄弟姐妹,則記為“-”。)
通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英漢親屬稱謂詞存在的共同之處有:(1)劃分不同輩分,都有祖父母輩、父母輩、兒女輩、同輩,且采用了不同的稱呼。如英語祖父母輩grandfather—grandmother,漢語祖父母輩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2)性別界限分明。是否具有“男性”這一義素內容,英漢親屬稱謂詞大部分都做了嚴格區分,“cousin”是個例外。(3)直系旁系之別。英漢親屬稱謂對直系旁系都有明確劃分,凡是標明“+”的均是直系,“-”的均為旁系。
從總體來看,二者呈現出來的差異更多一些,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宗族關系的差異
英語親屬稱謂語義場對父系母系親屬未作出明確區分,如:“uncle”未標明“父系”,它對應的是漢語中5個不同的稱謂詞:叔父、伯父、舅父、姑父、姨夫。“aunt”也是如此,它囊括了漢語里的伯母、嬸母、姑母、姨母、舅母。這些英語稱謂詞不僅父系母系不分,就連血親姻親也難以辨別。相反,漢語親屬稱謂詞的父系母系、血親姻親界限分明,例如,姑姑—姑父區分血親姻親,孫子—外孫區分宗族非宗族,姑母—-姨母區分父系母系。
需指出的是,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英語親屬稱謂詞也會借助一些輔助手段來區分宗親。高素珍[2]指出,英語常用“paternal、maternal、on my fathers side、on my mothers side”等修飾語來說明宗親或非宗親關系,用同位語“my uncle John”等來補充說明,用后綴“-in-law”構成派生詞來表示姻親關系。但事實上,這類表達方法在背稱系統中使用頻率極低,即便是用于面稱,人們也多是對非直系親屬成員直呼其名。
(二)語義特征的差異
英語稱謂詞的語義較為模糊,漢語稱謂詞則相對精確。前文提到的“cousin”就是有力的例證,單從詞本身,很難確認這位親屬的身份,它不標明是父系還是母系,是直系還是旁系,以及長幼順序,這些語義信息統統都比較模糊。而在現代漢語中,每一類不同的親屬都有一個明確的稱謂,所以才出現了1個“cousin”對應8個不同漢語親屬稱謂詞的情況,而且若要進一步切分的話,還可以細分為“(叔伯)堂兄、弟、姐、妹”“姑表兄、弟、姐、妹”“姨表兄、弟、姐、妹”“舅表兄、弟、姐、妹”。這樣以來,“cousin”對應的就是16種親屬關系。同樣,“uncle、aunt”等親屬稱謂詞的指稱也是很籠統很寬泛,除了輩分外,親疏、內外、長幼都不太看重。
(三)親疏程度的差異
親屬稱謂有核心與非核心之分,“核心親屬稱謂”即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姊、妹等與本人關系密切的親屬稱謂詞,“非核心稱謂”則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伯/叔/姑/舅父(母)、公婆、岳父母、兒媳、女婿、嫂子、弟媳、堂(表)兄弟姊妹等諸多詞項
事實上,英語非核心親屬稱謂詞的數量極為有限,且大都采用復合組詞的方式,例如,father-in-law(公公、岳父)、mother-in-law(婆婆、岳母)、son-in-law(女婿)、daughter-in-law(兒媳婦)、brother-in-law(姐夫、妹夫、大伯、小叔子、大舅子、小舅子)、sister-in-law(嫂子、大姑子、小姑子、大姨子、小姨子、弟媳)。相反,漢語非核心親屬稱謂詞數目繁多,并且分出不同的子語義場,如旁系子場與姻親子場,這可從上文“直系”“血親”中提取很多相關的稱謂詞,符號“-”代表的義項分別可納入旁系子場和姻親子場。同時,漢語親屬稱謂非常講究內外之別,如稱呼自己父親的父母為“祖父/祖母”,稱呼自己母親的父母為“外公/外婆”。由此可見,漢語親屬稱謂十分重視血緣關系和親疏遠近。而在英語親屬稱謂系統中,它更多的是集中在核心稱謂詞上,親屬關系相對簡單,親疏之別不太明顯。
總的來說,現代漢語親屬稱謂嚴格區分父系與母系,血親與姻親,強調年齡輩分、男女有別、長幼之序、親疏之分,而且幾乎所有的親屬身份都有一個固定且唯一的稱謂,所以語義呈現出精確性的特征[3]。相比之下,英語親屬稱謂系統則沒有那么鮮明的特征,不僅數量少,指稱寬泛,而且還呈現出一定的模糊性。
二、英漢親屬稱謂的文化闡釋
薩丕爾在《語言論》中曾經說過:“語言有一個底座。……語言也不脫離文化而存在,就是說,不能脫離社會流傳下來的、決定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和信仰的總體。”“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系的。……語言的詞匯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4](P129-136)如此看來,英漢親屬稱謂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差異,與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念、民族心理、倫理道德等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必然影響著人們對親屬稱謂的制定和選擇。
(一)漢語親屬稱謂與中國宗法制度
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一直強調家族在社會中的基本作用,并在家族中遵循著以血親意識為主體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宗法式的倫理道德。親屬關系如此精密化,反映在親屬稱謂詞上也就十分豐富,于是親屬稱謂詞也就相應地嚴格區分父系母系、血親姻親,特別講究輩分等級、男女有別、長幼有序。
這一點在《紅樓夢》中就有非常鮮明的體現,據肖家燕、劉澤權統計,僅前十二回所使用的親屬稱謂詞就有31個,出現次數多達166次。[5]而且,人物的對話也足以說明宗法制度在親屬稱謂中的嚴格執行,如第三回王熙風牽著黛玉的手,對賈母說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日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一個嫡親的孫女兒……”
不可否認的是,漢語親屬稱謂這套繁雜的體系,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文化背景中逐步發展起來的。這還可以從前人的史書記載中找到證據。許巧云,打西阿且(2007)考證指出,《爾雅》“釋親”篇縱向以“己身”為軸心,往上推及四代,往下推延一共有“八代”,包括自己一共有“父親—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子—孫—曾孫—玄孫—來孫—晜孫—仍孫—云孫”十三代稱謂詞,橫向每個層次有男族、女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稱謂。[6]這種開辟專章記錄親屬稱謂的做法一直延續了下來,到了清代涌現出了一大批關于親屬稱謂的專著,如梁章鉅《稱謂錄》32卷,僅親屬稱謂就占了8卷,并細分為7個小系。所以說,現代漢語親屬稱謂系統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中的,是帶有漢民族特有的文化特性的。
(二)英語親屬稱謂與核心家庭模式
從家庭結構模式的傳統來看,英語國家的家庭模式和中國宗法制主導下的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是截然不同的。通過前面語義場差異的比較可知,英語親屬稱謂詞主要是核心稱謂詞,非核心親屬稱謂詞數目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英語國家核心家庭模式占據主導地位。所謂“核心家庭”指的是家庭結構簡單,通常只包括一對成年夫婦及其未成年子女,最多不超過三代人。
之所以出現這種家庭模式,是因為受到了西方工業革命的影響。18世紀60年代,西方工業革命爆發,城市化進程加劇,人口流動變得頻繁,生活節奏快速運轉,這樣的巨大變化促使以人為主體構成的家庭結構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變革。對此,美國學者威廉·古德指出:“無論在什么地方,工業化使經濟膨脹,都會使家庭改變,擴大的親屬關系紐帶被削弱了,血親組織解體了,朝著夫婦式家庭普遍的方向發展——就是說核心家庭是最為普遍的家庭形式。”[7](P6)換言之,核心家庭是工業化的產物,更能滿足工業化城市職業流動和地域流動的需要;這樣一來,家庭規模變小,親疏程度弱化,進而勢必造成親屬稱謂的簡化。所以,是否區分血親姻親、父系母系,在英語親屬稱謂詞中不是那么重要,這也是“cousin、uncle、aunt”等詞出現指稱寬泛的原因所在。
三、結語
任何一種語言現象,絕不是孤獨的表象,它的背后是有文化因素蘊含在內的。假如忽略了這一點,僅僅將眼光局限于語言的微觀結構,如語義的對比,那么看到的只是一片樹葉,而非整個森林。趙世開(1990)說過:“僅僅對比語言的微觀結構還不足以真正認識和運用這些結構。語言跟社會、心理等方面有密切的聯系。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對微觀結構作更深入和普遍的對比研究,而且還要擴大對比的領域,或者說有必要加強宏觀的對比研究。”[8]本著這樣的精神,唯有將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將詞匯特征與文化內涵關聯起來,交際對象在運用親屬稱謂詞的過程中才不會發生交際失誤,翻譯者在英漢文本互譯的過程中才能做到融會貫通,對外漢語教師在二語教學課堂中才能更好地幫助學生理解目的語中的親屬稱謂詞。
參考文獻:
[1]呂叔湘.由“rose”和“玫瑰”引起的感想[A].楊自儉,李瑞華.英漢對比研究論文集(1977-1989)[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0.
[2]高素珍.英漢稱謂的情感體現[J].山東社會科學,2002,(2).
[3]馮勇.英漢稱謂語對比研究[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與教學),2010,(8).
[4][美]愛德華·薩丕爾.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M].陸卓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5]肖家燕,劉澤權.被扭曲的中華稱謂——《紅樓夢》尊他敬語五種英譯之比較[J].外國語文,2009,(6).
[6]許巧云,打西阿且.漢彝英親屬稱謂詞所反映的民族文化探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6).
[7][美]威廉·古德.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
[8]趙世開.對比語言學的發展和展望[J].世界漢語教學,1990,(3).
(許漫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