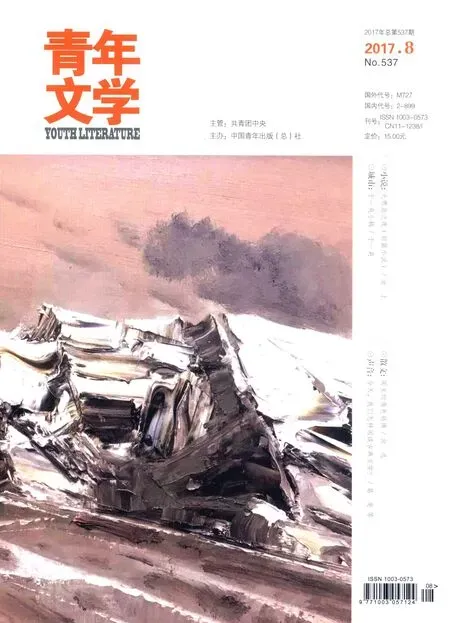開往寒冷地帶
⊙ 文 / 于一爽
開往寒冷地帶
⊙ 文 / 于一爽
一
“我離婚了,”
看見杜楊發來這四個字的時候,呂紅正拖著自己已經摔壞的行李箱在雪地上費力行走。但是她有個習慣,如果短信響起來,她一定要看一下。雪沒到了小腿,如果不是還在行走,她以為已經失去了小腿。就算行李箱沒有摔壞,也一定會很費力,這里的雪太大了,天還很黑,六點的火車,她五點就要到車站,現在已經快五點了,沒有人幫她。她想象裹在大衣里面的自己這么普通,誰會幫她呢?年輕的時候她就很普通,現在年齡大了一點,這種普通反而成了一種保護。接下來,她頭腦中帶著這四個字和一個逗號繼續拖著自己已經摔壞的行李箱在雪地上費力行走,她的當務之急是走到車站,這樣她才有更多的時間安靜下來,或許可以好好盯著手機看一會兒。雖然只有四個字和一個逗號,她的心情說不上來。事已至此,她也沒什么心情了。如果說她和杜楊是什么關系,有一個比喻倒是適合兩個人,也正像這樣的天氣,是從同一片天空中掉下來的兩片雪花吧。
頭頂的天沒有完全黑也沒有完全亮,而是像一些深紫色的玻璃,飄著一些白色的雪花。
到車站的時候,已經五點過了五分,車站很小,看上去像兩個世紀之前建造,這讓呂紅心情大好,感覺自己的離開不是空間而是時間。有一些游客都像她一樣裹在大衣里,沒有身材可言,也看不出男女。這是一輛開往極地的觀光小火車,觀光項目是極光。呂紅曾經在照片上看見過,像一團又一團的鬼火,毫無道理地燃燒在冰冷的天空中。
小火車只要提前五分鐘上車就可以,她坐在候車室,摘下手套,打開手機,“我離婚了”,只有四個字,呂紅把手機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就像某些拼貼處會吃掉一些字一樣。但,什么都沒有。
可,你把石頭扔進水里,總會泛起一點皺紋。尤其對那些一直盯著水面的人來說。直到小火車啟動前的最后兩分鐘,呂紅才上車。
小火車一共只有兩節車廂,第一節坐了一些藍眼睛的人,她坐在第二節,她報了一個當地的旅行團,導游小姐是臺灣人,還有幾個人,如果說他們有什么關系,大概就是沒什么關系。車廂散發著一股保溫瓶的味道。這讓呂紅一坐下來之后心情就變化了。車廂很空,可以隨便坐,她想等其他幾個人坐下來之后再坐,這樣她就可以離別人遠一點。來到這么遠的地方,她并不想再看見誰。她站在車廂的連接處想,杜楊到底要干什么?
和她一起站在連接處的,還有一個鵝蛋臉的中國女人。應該是中國女人吧。她看了一下鵝蛋臉,想點點頭,鵝蛋臉沒有看她。
杜楊沒有說自己的名字,呂紅想,就是說,杜楊一定確定自己沒有刪掉他的電話,后面是一個逗號,這是杜楊一貫的風格,他的逗號從來不表示沒說完,有的時候,表示的正是說完了。但,這就說完了?杜楊的電話已經不在手機里了,十一個數字呂紅背在了腦子里肚子里,像一個密碼一樣,一個已經不那么重要的人依然在你記憶的邊緣,這可能是人體設計里面最大的bug。她覺得很悲哀。
她把自己的手掌伸開,褪去毛茸茸的手套,手掌很小,掌紋很亂,她把手心翻下去,因為不想看見這樣亂糟糟的掌紋而讓自己胡思亂想,她發現指甲有點兒長了,里面可以藏住泥了,她用大拇哥的指甲摳了摳,又用牙齒刮了刮,做完這些之后,又檢查了另外一只手,然后重新滿意地戴上手套,她用兩只手互相摸了摸,就像在和自己握手。
火車很快就要啟動了,廣播里讓所有的人回到座位上,廣播里這樣說的時候,鵝蛋臉正在點一根煙,呂紅想,她肯定抽不完了。呂紅在短信里打了一個“哦”,可猶豫了一下,她沒有點發送,她覺得這個字就像一個嘴巴長成圓形的人,看上去傻頭傻腦的,她可不喜歡杜楊覺得離開了他的自己傻頭傻腦,雖然他們認識的時候,她就是這樣的人。傻頭傻腦,形容年輕的姑娘還不錯,他們認識的時候,呂紅二十七歲,還處在年輕的尾巴上,自然比現在擁有更多傻頭傻腦的優勢。
二
呂紅拉開玻璃門,只有兩男兩女,看上去像是夫妻。一對胖一些,一對瘦一些。但都沒有夸張到需要讓你記住的地步,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都不覺得十分的胖或者瘦,但是也許他們認識,也許僅僅是剛認識,放在一起的話,竟然看上去更胖或者更瘦了。車廂很短,兩對夫妻坐在前面,他們一定以為前面的景色更好。他們一定是出來看景色的,呂紅羨慕地想。鵝蛋臉還沒有進來。
坐下來之后,隨著一聲汽笛響,火車咣當咣當開動了。
呂紅想,也許一會兒就要沒有信號了,于是打開了杜楊的朋友圈,她很久沒看了,她現在竟然還在尋找蛛絲馬跡。第一張圖是排骨燉豆角。兩個小時之前發的。呂紅把照片放大,豆角有些切得很細,有些切得很粗,有些看上去,像是杜楊隨便撕出來的。四周還有八角、香葉、肉蔻、肉桂、丁香,散落在一個小盤子里。看到這些,她都沒有心情繼續看下去了。她把“哦”字刪掉,又想了一下,把杜楊的這條短信也刪掉了。她想到杜楊原來挺愛說的一句話——生活就是這么回事兒。大概就是豆角有些切得很粗有些切得很細,有些看上去像是隨便撕出來的。但生活要真像這么回事兒就好了。
杜楊一直喜歡做飯,理論上,這是一張來自過去的照片,中國比這里早十幾個小時,十幾個小時之前的杜楊正在做排骨燉豆角。又過了幾個小時之后,他給自己發了一條短信,寫著——我離婚了,而且那樣輕松地,寫了一個圓滿的逗號。
不知道他那個可愛的兒子歸誰了,呂紅關掉手機之后閉上眼睛,想到了這樣一個叫人難過的事實。甚至是唯一叫人難過的事實。
導游小姐一上車說了很多話,之后就可以不再說話了,她的工作就是這樣,導游小姐嘴很大,像一直到耳朵都裂開了一樣。呂紅不愿意多看。看多了有些恐怖。她可不希望這樣美好的旅程伴隨這樣的印象。
導游小姐說,情侶在有極光的時候求婚,一定會很幸福的哦。所以現在大家開始祈禱吧。
類似這樣的句式,呂紅聽過很多:情侶在大海面前求婚,一定會很幸福的。情侶在高山面前求婚,一定會很幸福的。
她想那兩對夫妻應該這么做,不然他們一定不會幸福。呂紅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么不善良,這么粗俗。也許僅僅是因為她是一個人,所以很自卑。尤其是聽見祈禱這兩個字,呂紅想能不能到另外一節車廂去。因為如果祈禱真的管用,她寧可祈禱一些不幸福的事。
很快,導游小姐走過來問呂紅,怎么一個人出來呢?

⊙ 廖偉棠· 攝影作品選2
她問得這么溫柔,呂紅都不好意思罵她了,于是她從自己的狗嘴里吐出了一顆珍貴的象牙,她說,有一個孩子,離婚了。
狗嘴里當然吐不出象牙。并且呂紅根本找不出一個理由為什么不能羞辱自己……但是有一個孩子,離婚了,就算是羞辱嗎?如果這樣就算,那杜楊做的正是羞辱自己。
導游小姐說,出來換個心情啦。
呂紅說,心情挺好的。
好像她這種人天生就會為這種事情心情好一樣。
導游小姐拍了拍呂紅的肩膀,似乎有一句話想說又不好意思說出來一樣,就是“加油耶”。
呂紅把臉望向窗外,因為剛剛的這些都打擾不到她,隨著小火車從一片白色拐進另一片白色,很快就化為烏有。當然,除非你有足夠的愿望,否則無法區分這一片白色和那一片白色。
前面兩個女人的聲音很大,呂紅想,也許都是胖女人制造的,胖是女人最大的過錯,所以她應該承擔所有的過錯。
她隱約聽見胖女人說,世界這么大,就應該走走,哈。
瘦女人說,趁身體好的時候,出來走走,哈。
胖女人又問瘦女人,你有孩子嗎?
瘦女人說,已經不和我們出來了。
胖女人說,長大了,哈。
瘦女人說,是呀管不了,哈。
呂紅把耳機插上,她用手擦了擦車窗,她覺得不夠干凈,雖然是雙層玻璃,她把耳機調大,連咣當咣當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她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拍照片。她不想打開手機的拍照功能,她不想打開手機,因為手機里面裝了一個特別煩的世界。比如杜楊,會不會再發一條短信過來呢?如果再發一條短信過來,是不是證明杜楊又可以重新打擾到自己了呢?呂紅摸了摸褲兜里面的手機,拍了拍,就讓它在那里好了。鵝蛋臉一直沒有進來。呂紅想,在車廂的連接處,如果一直在抽煙的話,那真是很浪費煙。搞不好過兩年她就要得肺癌死掉啦。還有,她可以站那么久,都不會冷嗎?
火車就這樣,開出了大概兩個小時,呂紅的脊椎骨因為坐了很久,很不舒服。還有八九個小時的路程。這個時候,鵝蛋臉才進來,她在連接處站了那么久,鵝蛋臉進來之后坐在了她的對面,她們中間隔著一個原木面的小桌子。
這么多空位,她為什么非要坐自己對面?呂紅想換個地方,但是覺得也許可以過一會兒再換更體面。于是她沖鵝蛋臉點了點頭,鵝蛋臉還是沒有看她,呂紅望向走道。
走道里可以看見胖女人的鞋尖正在晃動,想到胖女人的五個腳趾頭擠在這樣的尖鞋里,她覺得人活著怪不容易的。瘦女人戴著干凈的薄片眼鏡正在吃餅干,坐在胖女人對面,她們的老公分別在里面的座位。呂紅想,很快,瘦女人的屁股下面就全是餅干屑了。就像一個盛滿了餅干的小肥皂盆。想到這兒她笑了一笑,沿途太無聊了,除了嘲弄這些和她完全無關的普通人,她想不到還應該做點兒什么。她接著想到,要是這個時候有杯烈性酒就好了,而且還需要一點冰塊,哪怕在這么冷的地方她依然需要冰塊。回憶那些閉著眼睛聽冰塊融化在酒里面的時刻,呂紅感覺自己真的是一個很過分的人。難怪杜楊會離開她,難怪她會離開杜楊,因為兩個人都越來越承擔不起這些過分的局面了。
窗外,所有的植物披了雪掛。看不出時間,大概快中午了吧。白茫茫一片,想不干凈都不行。這讓呂紅想到和杜楊看過的一部電影,講的就是未來世界,也許是更大的一次冰河期到來之后,地球都凍上了,于是聰明的人類,就在地球上修建了一個無限循環的鐵軌和一輛永動的火車,所有的人都在火車上,如果不望向窗外,沒有人會懷疑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他們就應該在上面出生和死亡,戀愛和分手,而對他們一生最大的懲罰就是從車窗拋出去。
就在呂紅想到這些的時候,列車長過來了,說要給大家出一道題。這毫無道理,也許僅僅是為了活躍死氣沉沉的車廂氣氛,但事實上并不一定能達到那樣理想的效果。那道題說的是關于這列小火車每年要撞死多少只駝鹿。
駝鹿是這個地區最多的一種大型動物,但并不是圣誕老人騎的那款。呂紅隨便想了幾個數字,她并沒有猜對或者猜錯的愿望。這只是一周一次的小火車,她想,一年有五十次,如果每次都撞死一只,那就是五十只,她在想,這個概率是不是太高了。
列車長說,二百五十只,去年撞死了二百五十只。然后,就走了。
呂紅想,那也許是一次撞死五只,或者是,有一次,撞死了二百只。難道是這些鹿想集體自殺?
前面的兩對夫妻也發出不可思議的語氣。鵝蛋臉毫無表情。呂紅想,是老處女吧。
列車長走后,呂紅依然搞不明白為什么他要來,為什么要說這些,她想到杜楊給自己講過一些關于火車司機的事情:
火車司機最忙的時候是開車前,因為各種各樣的準備工作,火車真的叮叮當當啟動之后,他們就再也什么都不用忙了,他們只需要每隔半個小時,或者更短的時間,把吵醒他們的鬧鐘按一下,這樣他們才不會真的在火車上睡著……其實每次坐在火車上,呂紅都不確定是不是一個已經睡著的人在駕駛。車窗外有很多駝鹿走過的大腳印。如果真的是一個睡著的人在駕駛,撞死這么多駝鹿就可以解釋了。
這個時候她聽見前面的瘦女人說,鹿夠傻的。
胖女人說,那它踩你一腳,你也得死。
火車已經籠罩在了濃濃的白色中,它發出的轟隆的聲音也是唯一的聲音。車廂中籠罩著一些傻乎乎的對話。火車有的時候跑得快,有的時候跑得慢,遇到值得一看的景色,就跑得慢一些。
呂紅想,這也太不嚴肅了。總之,就這樣不嚴肅地在寒冷的阿拉斯加州境內穿越。透過車窗,遇到拐彎的時候,呂紅正好可以看見被車燈照得發亮的鐵軌。就像兩條銀線,平鋪在這片冰冷的荒原上。手機一點反應都沒有了。沒有人會在這樣的地方鋪設網絡。可,那樣的疑問又出現了,杜楊為什么要告訴自己這個消息呢?只是證明一個道理嗎,證明他說到的事情做到了?兩個人已經分手一年多了。
好吧,就算他做到了。呂紅想,那又有什么了不起。
再后來,她困了。或者僅僅是不想將這些問題想下去。難道還指望想出什么結果?半睡半醒中,她還有另外一件想不明白的事情,列車長有什么用呢?火車有軌道,怎么會走丟?更不會忽然發瘋闖進下面的雪地里,和那些巨大的駝鹿撞在一起……進而呂紅想到一些更無聊的事情,比如人生為什么不能有軌道呢?如果人生有軌道,像杜楊這樣的決定,是不是就是脫軌了?
她感覺自己真的好像睡著了。醒來的時候,她聞到了一些很香的味道——列車員已經把她要的漢堡放在了小桌子上,可看上去放了很久,有些堅硬了。她想到杜楊朋友圈里的菜。漢堡有兩種,她上車之前就已經在車站預約了,有牛肉漢堡和鹿肉漢堡,鹿肉是特色,點了特色之后,現在看,就有些后悔,她憤怒地咬了一口。竟然不難吃,她又咬了第二口。咬到第三口的時候,她的眼淚差點兒出來,因為她忽然想到一個事實:來到這么遠的地方,吃這么堅硬的漢堡,也僅僅是因為杜楊的一句話——活著就去看看北極光吧。杜楊說,那不是光,那是一種能量。
杜楊很多年前說過這種話。他自己一定都忘了。呂紅也不能肯定,自己來是不是因為這句話,因為杜楊已經對她不構成壓力了。但是如果不構成壓力,她還是來了,她覺得自己應該管杜楊要回程票。這趟行程如此昂貴。
是啊,沒有壓力,就沒有控制,其實是已經沒有關聯了,但她竟然還是坐了十個小時的飛機,現在繼續坐十個小時的火車。分手一年之后,呂紅終于要承認這成了賭氣之旅。于是她就像賭氣一樣,又咬了幾大口鹿肉漢堡。至少這樣,不用感覺冷。鹿肉漢堡像一個小地球一樣圓,一些菜葉落在外面。落在外面的部分直挺挺的。
這個時候呂紅聽見胖女人說,和四季飯店的蟹肉漢堡很像……
瘦女人說,像嗎……她說這句話的時候,顴骨看上去隨時會掉下來,這兩塊漢堡加起來的油都比瘦女人多。
要是有三文魚多好。胖女人又說。
是啊,阿拉斯加狗拉雪橇的狗都吃三文魚。瘦女人接著說。
呂紅不知道她們到底點了什么,于是她又咬了一口自己的漢堡,反正她也沒吃過四季飯店的蟹肉漢堡。她甚至不如一只拉雪橇的狗。
一個人生活的一年多,就像窗外的景色一樣,自始至終都很一致。雖然也不能說完全一致,可是誰會有興致區分這一片白色和那一片白色呢?你甚至會得出簡單的結論——火車并沒有移動。大體來說,都是白色就對了。和杜楊分開的一年中,她一個人吃了九百多次飯,一個人睡了三百多次覺,或者只有八百多次飯。她有時候不禁會想,先是食欲的消失,然后很快就是性欲的消失。果真如此的話,屆時她的人生,會有一多半的事情都不會再困擾到她。但是現在,她依然被那些重復的欲望折磨。這讓她看不起自己,她開始忽然羨慕起對面的鵝蛋臉,雖然對她一無所知,但就是那樣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像個死人一樣端坐著,她又想到了自己眼前悲哀的事實:
自己已經三十幾歲了,一個三十幾歲的人,隨便走在街上,碰見一個你能湊合的人,這種概率已經不多見了。而那個人如果還能湊合你,那兩個人就應該馬上沖到民政局結婚。但是自己大概都沒有什么機會結婚了。也許過不了幾年,就會變得像鵝蛋臉一樣,溫馨又從容吧。
三
就在這個時候,小火車路過一個小站,做了短暫的幾分鐘的停留,這里小到都不能算作一個站。幾座彩色的小屋子沿著鐵路排列開來。這些彩色的小房子就像一些彩色的垃圾袋一樣分布在積雪覆蓋的地面上。屋子前面站了三三兩兩的人,他們看著小火車成百上千次路過,而自己只會見他們一次,呂紅不禁想,一輩子安安靜靜地生活在這個小小的環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把屋子刷成彩色的。
停站的時候便有了信號,呂紅看了手機,什么都沒有,自己和杜楊在一起的七年,他都沒有離成婚,才分開,他就離婚了。呂紅簡直不是委屈了,她開始覺得憤怒。前排的兩對夫妻說個不停。從那些彩色的小房子,又說到京市的房價問題,呂紅承認,他們說的都對,生活就是這么回事兒。
和杜楊在一起的七年中,兩個人見了三百天,因為他們只有周六或者周日可以見面,杜楊就像一輛移動的小火車,周一到周五停在家中,周末開到別人家中,杜楊比呂紅大十二歲,再過幾年,就真的成小老頭兒了。看著窗外,呂紅忽然覺得很難過。
站臺上有人向自己揮手,她不知道這是不是也是旅行故意安排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他們為什么要向自己揮手呢?可是很快,揮手的人,漸漸變成了一個小點,小火車伴著長長的一聲汽笛重新開動了,呂紅有些后悔,自己為什么不能也揮揮手,僅僅是,揮揮手而已。
看著遠去的人,那些你一生都不會再見到的人,他們毫無意義地在你的生命中停留了幾分鐘的那些好人,呂紅想到自己無怨無悔地做了七年第三者,她都快被自己感動了。她不知道這七年發生了什么。直到忽然有一天,這種離開就發生了。七年,她的生活就像坐在一個隨時要坍塌下去的沙丘上。她只是在等著什么時候會坍塌下去。
還有一半的行程,還可以睡上很久,這樣的旅程總是如此,你隨時可以睡上一覺,甚至不知道什么時候醒過來了,然后再睡過去。呂紅知道,很多人就是喜歡在這樣行駛的列車上昏昏欲睡,甚至睡在發動機上也并不影響,這樣前進的火車,讓人覺得存在一個目的地。
鵝蛋臉一直沒有睡,起身去車廂連接處抽煙,忽然問呂紅,要一起嗎?
呂紅本來要說,對皮膚不好,可是想了一下,為什么要在一個皮膚不好的人面前說皮膚不好,于是她必須抽一根。呂紅說要先去下衛生間,等出來的時候,兩個人就在車廂連接處抽起了煙,她們關上了玻璃門,這樣車廂里面的人才不會一直說冷,說個沒完沒了……透過玻璃門,呂紅看見瘦女人正在吃方便面,呂紅想,先不要進去了。胖女人什么也沒有再做。就是像一個胖女人應該有的那樣姿勢,坐在車廂里,她們的老公在旁邊,大概是坐了太久的緣故,都閉上了眼睛。遠遠看上去,家庭就應該這樣。
呂紅和鵝蛋臉沒有說話,鵝蛋臉于是又抽了一根,她們看著窗外沿著鐵路延伸出去的皚皚白雪。呂紅抽得很慢,她想這樣可能會對皮膚好一點。其實她根本不在乎皮膚,她只是想抽得慢一點。她把手機落在了座位上,于是問鵝蛋臉,幾點了?
鵝蛋臉沒有看手機,說,還早。
呂紅不知道還早是什么意思,這里到處都是白色,太陽都是亂的,如果現在有一個人告訴她,這里的天空沒有太陽,她都相信。
鵝蛋臉穿了一件大衣,大衣敞開,里面是一件T恤,T恤上面的英文字母寫著:獨角獸是真的。
樹枝上新的雪和舊的雪混在一起。
這真不錯。呂紅沖鵝蛋臉說。也許說這些僅僅是感謝她給了自己一根煙。
反正我們死了,這些地方還是這樣兒。鵝蛋臉說。
那還想怎么樣……呂紅想,于是她說,是啊。但是又覺得說這些太喪。
鵝蛋臉又說,死在這里也不錯。
呂紅呵呵笑了一下,她覺得這種想法太平庸了,死的想法已經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了。有時候想到死,呂紅覺得很自卑,于是又呵呵笑了一小會兒,呂紅不知道怎么面對這種問題,除非她死過一次,但是一個死過的人不用再次面對這種問題。這是一個悖論。
煙快被抽到了手指,呂紅忽然笑起來……她覺得自己好渺小,整個列車都好渺小,在這樣的天地之間,已經快五十歲的杜楊竟然還發了那樣的四個字,還關心她,或者想被她關心一下,因為渺小,這樣的關心,看上去十分詭異。還有鵝蛋臉和那兩對夫妻、導游啊,所有人,一起構成了渺小這個現實。
一陣顛簸之后,呂紅朝著鵝蛋臉點了個頭,拉開玻璃門,回到了座位上。
方便面的味道沖過來,她又煩躁了,呂紅有時候會想,為什么總是忽然變得煩躁?也許,是多年不如意的生活導致的。她內心覺得不值。但是這種不值,她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尤其沒有對杜楊說過,如果她那樣說,那這種不值,就真的成立了。她只是默默吞下這種想法,也許早就變成了肚子上的一塊肥肉。她打開手機,依然沒有信號。所有的事情都很明確:她根本不需要一個嘲笑別人的機會,對她來講,連愛都沒有了,就沒有恨了,只是一些碎片,證明和你在一起的人,那些時間,那些地點,真的存在過,中性的碎片。只具有一些物理性質……
看著近處,但其實是很遠處,北美第一高峰上升起來的光亮,呂紅忽然覺得鵝蛋臉說的是對的:死在這里也不錯。這是一座很遼闊的山,山的頂上有一條明亮的光帶,就像一排大鉆石在燃燒。有一個瞬間,她覺得雪就這么融化了,沖自己流過來。
就在這個時候,她看見前面的瘦女人站了起來,做了幾個伸展的動作,很突然。頭發像一把短毛刷子,很短很短,年輕的時候搞不好喜歡搖滾樂,呂紅不知道為什么會得出這些概念化的結論。但是她很快想到,過不了幾年,瘦女人的皮膚就會像風干的果脯,無論她的男人是不是愛她,都會無法面對那些風干的果脯。而胖女人,脖子上堆積的贅肉在她的衣領里,看上去就像一條肉色的圍脖。同樣過不了幾年,無論她的男人是不是愛她,一定也會無法面對這條肉色的圍脖。但是他們依然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呂紅閉上眼睛,她覺得很羨慕。她寧愿變成果脯或者圍脖,得到這樣的幸福。她并不想變成鵝蛋臉,雖然她誰都不了解。他們僅僅是幾十年人生中,十個小時的同路人。所以,她根本不用給杜楊回那些愚蠢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就像這兩對夫妻一樣,一起生活下去,才需要理由,而分開,不需要理由,僅僅需要一點點決心。
鵝蛋臉也進來了。
呂紅想,是不是應該問那樣的問題:你為什么也在這里?畢竟,她們一起抽過了煙。
她還沒有問,是鵝蛋臉開始自己說起來,呂紅沒有太聽懂,大概意思是:因為鵝蛋臉的護照丟了,他們所在的 F市沒有中國使領館,她可以去到最近的S市,但是去S市要坐飛機,坐飛機就需要護照。或者鵝蛋臉可以坐火車,但是火車要經過相鄰的C國,也需要護照。于是鵝蛋臉需要有人從中國飛到S市,否則她無法離開F市。于是她就一遍一遍在火車上等待有人從S市給她快遞新的護照,所以這列小火車,她并非第一次坐,也不會最后一次坐。
呂紅不知道她為什么和自己說這個,這聽上去太倒霉了。她真應該死在這里,丟了護照,簡直是天意,再說,死在這里也不錯。
說了這些之后,鵝蛋臉又不說話了,她也許就是想告訴呂紅這樣一個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也許從她一上車就想告訴什么人,也許她會告訴所有人,畢竟這不是一個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情,簡直稱得上是一個炫耀的事情。她表現得很沉默,只是等待一個爆發機會。讓一切看上去那么自然地就發生了。呂紅想到這些,也就覺得沒有安慰的必要了。可惜她想,鵝蛋臉說錯了對象,如果她對那兩個女人說該有多好,那一定會有一番熱烈的討論。就在這個時候,杜楊的短信又過來了,還是一樣的四個字:“我離婚了。”呂紅看了半天,她想到一個情況——杜楊真的老了。
就像老人一樣,擔心發不出去,或者自己為什么沒有回復,于是又發了一遍。又或者,也許杜楊只是告訴自己這樣一個事實,并且告訴了自己兩遍。甚至連道理都不需要證明。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需要被證明的道理。
呂紅一點兒都不想問下去,杜楊已經離婚了,可是他現在離婚還有什么意義?對他有意義,呂紅想,對自己來講,一點兒意義都沒有。可她還要什么意義呢,但既然連意義都不需要,為什么不能出于禮貌,僅僅是出于禮貌,給他回一句,隨便回一句?
可是,看著窗外,她連隨便都想不出來,于是她把手機關掉,這四個字,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想到七年前。
七年前,兩個人在中國科技館的球幕電影里看過北極光,寒冷的空中,無緣無故燃燒起來的一些綠色的火,呂紅驚呆了。對她來說,或者對他們兩個人來說,北極太遠了,這太神奇了。
也許中國的北方就有?她問杜楊。
誰愿意去北方看呢?杜楊這么說的時候,正在十二月里用鋁勺挖一個西瓜吃。
你不覺得涼嗎?呂紅覺得他這樣說只是不想陪自己去。
杜楊挖了一勺西瓜給她。西瓜很甜。可是鋁勺碰到牙齒的時候,太涼了。
接下來,他們便開始做愛,不知道為什么,也不知道在什么樣的時間和地點,每一件事情都會指向一個結果:他們做愛。
在那七年中,呂紅提出過三次,是不是兩個人可以生活在一起。第一次是在他們最開始的一年,也許是在兩個人吃西瓜或者看球幕電影的時候,因為提得這么隨意,以至于杜楊什么也不回答的時候,也沒有留給呂紅太多的尷尬。杜楊說,他的婚姻走到了頂點,除非還有一個孩子能夠挽救,于是上天就真的在第二年,給了他們一個孩子,呂紅停掉避孕藥,也想給他生一個孩子的時候,杜楊說,現在不是時候。杜楊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很確定,現在不是時候。所以呂紅第三次說出一模一樣的要求時,因為已經是一個三十歲的女人了,她在乎的東西越來越少,包括被拒絕,所以連自取其辱都算不上,她想,反正也是隨便說說,反正,杜楊,也是隨便聽聽……
三十四歲,呂紅變成了一個人,雖然在別人看來,她一直是一個人,至于忠誠,當然談不上,在這七年中,她隨時準備好了離開杜楊,就像一根接力棒一樣,有人可以把她從一段殘破的關系中完整地帶走,可是沒有那么傻的人,所有人都能看出,呂紅才是殘破本身。直到忽然有那么一天,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她想,算了吧,杜楊到最后都不明白,她說的“算了吧”是指什么,什么算了?算了什么?呂紅想,他應該懂吧,杜楊還是說不懂。呂紅想,也許只是裝不懂。可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人,裝不懂?一下子呂紅又覺得,這個世界都不好玩兒了。
沒有人要求他們必須在一起,更沒有一部法律安排他們必須在一起,所以他們不在一起,就成了比在一起更合理的一件事。大概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七年之癢”,但是很快,這種念頭就被另外一個念頭取代了:七年?加一起才一年呵。于是,她連痛苦都沒有資格。呂紅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么自己會忽然做出這樣的決定,也許那一天,她的頭頂出現了北極光。這是不是就是導游說的“幸運哦”,她甚至也想從自己的那張嘴里模仿出那樣的臺灣腔調“幸——運——哦——”。說到哦的時候,嘴真的成了一個O形,她打開手機的拍照功能,就像一個鏡子的功能,看了看這個呆頭呆腦的O形。她開始懷疑,杜楊是不是真的愛過自己。
誰會愛這樣的O型呢?如果不愛,那七年的時間對人生只是一瞬間。
呂紅對著手機捋了捋自己的頭發,有些時候,她覺得自己長得很普通,甚至算不上好看,可也有一些時候,她覺得自己算得上好看。那些算得上好看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和杜楊在一起的時間,就是一出悲劇,因為不好看的人連演的悲劇都不好看,所以那些不好看的時刻,呂紅僅僅是想到——他搞了七年的婚外戀,自己做了七年的第三者,他們,還想要什么下場?現在能各走各的路,就是最好的下場。甚至都不能用下場兩個字,應該是一個happy ending。
于是,她打算真的去一次北極,就算是慶祝這個happy ending。只是,這要花不少錢,但是想到是一生一次的事情,她決定把手里的錢好好攢攢。隨著杜楊一起換掉的還有做了七年的工作,想要賺更多錢,在她看來很簡單,只要把工作目標定位為想要賺更多錢就好了。
但這些都過去了。
四
幾個小時之后,火車到站了,大家被導游小姐安排到了客房里,做短暫的休息,然后等待夜里的極光。
客房里很冷,盡管配上了電熱毯還是很冷,很干燥。沾滿油污的電視機里只有一個當地頻道,還有一個國家臺,但是沒人看得清是什么,只有一些時隱時現的雪花。呂紅的習慣是總要撥一下電視,她受不了那樣的安靜。電視旁邊有一個咖啡壺,看上去從來沒有人用過。房間四周的鑲板都變形了,有的擠下去有的擠上來,仔細看,有些像和杜楊當時約會的地方,可是沒有人覺得這會是問題,只有現在,呂紅一個人仔細觀察這些鑲板,好想給它們碼整齊啊。床單畫著一些當地的動物,呂紅覺得臟極了,床單如果不是白色都會讓她覺得臟極了。她從書包里拿出一根煙,她才想起來自己帶了一整條煙,如果抽不完,她愿意留給鵝蛋臉。
冷得受不了,呂紅打算去浴缸泡一個熱水澡,整整一天,她都快凍僵了。打開浴室的門,聞起來,像藏著一堆臟衣服,呂紅四周看了看,好像在確定真的可以找出一堆臟衣服一樣。她想打開浴室的窗戶散味道,可,一股寒冷逼進來,外面的光亮就像隔著幕布的大探照燈,每一塊的顏色都不一樣。是拼接起來的吧。呂紅想。在這外面,就是一個冰凍星球,她很快就把窗戶關上了。浴缸旁邊擺著一個風干的南瓜,浴缸就像一個等待裝滿水的長方形棺材。
南瓜真是一個神來之筆啊,呂紅想著,于是脫掉衣服,一邊躺在里面一邊放水,太冷了,她把自己的身體折疊起來。墻壁很薄,隔壁客房的聲音都可以聽見。大概是胖女人和瘦女人的聲音。胖女人的聲音更大一些。但是聽不清在說什么。她還隱約聽見鵝蛋臉在和一個人說護照的事情,呂紅覺得很好笑,她不知道鵝蛋臉在對誰說,搞不好是自言自語吧。她把耳朵貼在墻壁上,確定真的是在說護照的事情。她又想到她的衣服上寫著:獨角獸是真的。
就這樣,她泡在溫暖的洗澡水中,一些重的東西升起來,一些輕的東西沉下去。她覺得舒服極了。她又打開手機看了看,沒有任何新的短信,但是她的失望已經不強烈了。也許是因為暖和起來的緣故。在黑暗的浴室中,她驚奇地發現,手機四周的亮光竟然有些像電視上的極光,于是,拿著手機,呂紅多看了一會兒,因為她甚至都不想洗過熱水澡之后再跑到外面去看,對她來講,此行的目的已經很模糊了。于是她關掉手機,浴室重新變成了漆黑的一片,仔細聽,還是有隔壁的聲音。不知道為什么,她總是覺得鵝蛋臉編了一個故事,但是,不應該拆穿她。而胖女人和瘦女人,僅僅是旅行中兩塊不同比例的背景而已。伴隨她一路的,只有那四個字,她想,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于是,呂紅閉上了眼睛,她覺得自己很快又可以睡著了,這一天,什么也沒做,但是太累了。她不確定是不是真的睡著了,也許是夢中,也許不是,她想起一件事:在自己和杜楊分手前的不久,也泡在同樣溫暖的洗澡水中,也是在這樣一個鑲板隨時會掉下來的普通客房里。當時她說,杜楊,不要老泡熱水澡啊,會陽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