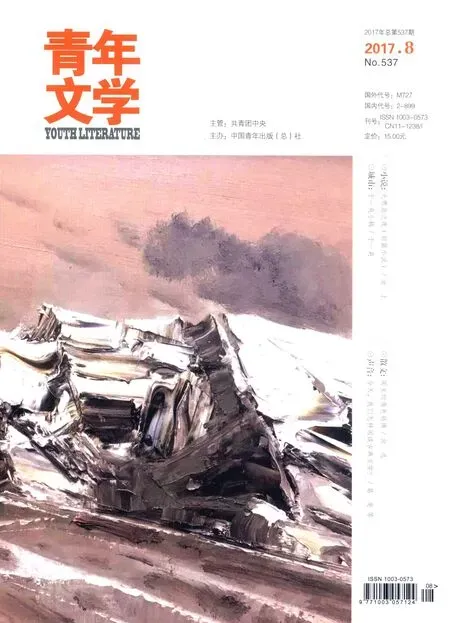于無聲處聽一爽
——于一爽城市小說印象
⊙ 文 / 趙 依
于無聲處聽一爽——于一爽城市小說印象
⊙ 文 / 趙 依
趙 依:一九八九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文學碩士,現為魯迅文學院教研部教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從事中國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已在《南方文壇》《當代文壇》《小說評論》《名作欣賞》等核心報刊上發表論文近二十萬字。另有譯稿在《現代哲學》《美德與權利——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學與人權》等書刊上發表收錄。
于一爽的這兩篇城市小說并未聚焦典型的城市意象,無論是“寒冷地帶”還是“西出陽關”,在地理坐標上首先都遠離了城市及其中生活的百態,可誰說遠離城市不是城市生活的宏大主題之一呢?
大概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心中都多少向往遠方的緣故,近幾年開始流行起一種名為“性冷淡”的風格,在時尚領域,從口紅粉底到手袋成衣,無一例外趨向于某種中性的、沒有態度的,而在事實上“我”值極高的設計。于一爽的小說就有這股子勁兒。這里的“性”,不單單是《開往寒冷地帶》里呂紅對杜楊說“陽痿”的及物,也不僅僅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里“我”與楊元虛實關系的指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切都還在“性”的層面發生,只有“性”本身超越了“性”。所以具體到這兩篇小說的呂紅和“我”也都一樣,她們不針鋒相對什么,卻也絕不聽之任之,小說如果有朝一日幻化成人,那么“他”或“她”一定很高冷,精神狀態有那么一點萎靡不振、無欲無求,這種無欲無求也一定是來自于其內部人物身上發生的“不可求”和“求之不得”,因為不可能被滿足,干脆性冷淡到一了百了,有點悲觀。誰都知道,總會有那么些場合和人、事,讓少許的樂觀都成為一種徹頭徹尾的不自量力,城市就是這些場合和人、事的集合。
更何況,于一爽這兩篇小說的主人公,一個是沒能上位的小三,一個是多年深扎的隱三,本來已經被道德綁架了,哪里還有力氣再在這壓抑的生活中去認真追求什么。讀者也只能感覺肺里進了一口煙,先是堵得慌也嗆得很,吐出來倒也能于此一爽,慢慢抽離……我并不知道于一爽為什么會選擇寫這樣兩個女人,或許她們是一種新的可憐又可惡的“多余人”,或許她們也有原型,過得可能還行或者也不太好,或許是突然想談談城市里頻發的社會道德倫理問題,不管怎樣,關注時代和現實是好小說產生的必要條件。
于一爽的小說似乎并不刻意設置某種結構,以至于以前初讀她的作品,總覺得小說感不強,差點意思。后來讀于一爽讀得多了倒覺得,這種“差點意思”正是她真正的意思:小說泥沙俱下式的娓娓道來,作為一種無法現身的結構,與冷淡、無所謂的內容風格共同承載著于一爽的小說主旨,對現實做冷處理,是對現實最頑強的抗爭——你無法收買一個無所企圖的人。
毫無疑問,于一爽一直站在個體的本位,確立她的人格獨立性與審美主體性。她與現實血肉相連,卻不在合唱中強求一律,她不被束縛,卻又溫和克制。尤其讓人欣喜的是,于一爽開始結合所處時代的精神情態,重新建立小說與文學傳統的對話關系。“西出陽關無故人”,寫天涯此時、生離死別。“興、觀、群、怨”,“詩以言志”,浩浩湯湯幾千年的詩歌傳統,于一爽借用詩中典故坐實“我”與楊元的告別。在小說的后半段,“我”讓司機掉轉車頭去了陽關,這個舉動讓楊元的死顯得開闊而不悲痛,小說里寫“我想到那首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想——你們都翻譯錯了,因為正確的意思是,去死吧”,斗轉星移,世事變幻,人無非一死,于一爽小說里所做的聯結,使王維的元姓友人和楊元成了平行世界里的“參”與“商”(怪不得小說人物取名楊“元”),楊元的死在歷史感的籠罩下平添壯美,更不必說多出來的那幾分恰到好處的詩意。文學不失去傳統與歷史,才不喪失未來的可能。好的小說家應當具備一種追溯和叩問傳統的能力,而只有歷史感才能讓一位負責任的寫作者建立起時空的序列,并以此準確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進而在綿延的文學史中尋求自我的定位。
正如文章最開始對城市文學主題的探討,伴隨豐富的物質條件和生活經驗,受新的文學觀、美學范式影響,城市文學逐漸顯現并贏得矚目,它不僅是關于城市的,也是無關于城市的,它甚至就像于一爽的這兩篇小說一樣涉及城市即可,觸及城市生活的本身似乎不是必須。或許是城市的怪象太過蕪雜,它也樂于接受文學語言的遮蔽,并在種種遮蔽中獲得主觀上更為深刻的顯現,但也正因為城市文學的這種不定性,它在類型、題材和主題等方面才更能提供發揮的空間。只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寫作者大多也會遭遇迷失,希望他們可以借由傳統與歷史在未來減少遺憾、贏得時間。還有一句既俗又雅、跟城市與城市文學貼切的話: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