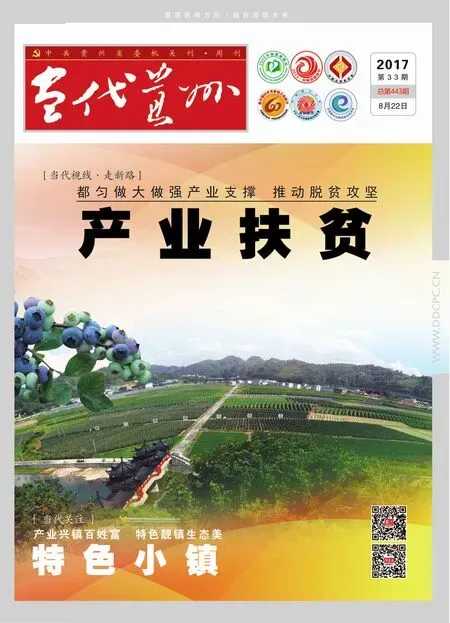亞圣孟軻(三)
亞圣孟軻(三)

王蒙
著名作家。歷任北京市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十三屆中央委員。
孟子認為,人應該努力提升自己的修養與境界,級別待遇則是順便的事,不能反過來靠級別樹威信、靠級別顯品德與才能。
孟子是言必稱堯舜——仁政,孔子是夢欲見周公——重建郁郁乎文哉的禮樂之邦。這與其說是復古,不如說是懷念中華文明的奠基——啟蒙階段,恰如一個人在躁動焦慮哭哭鬧鬧的青年時期回憶自己單純快樂的童年。草創階段,百廢待興、百事最美、人情天理、中規中矩、新鮮活潑,正是堯舜文王時期的特殊魅力。然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文明使生活規范,規范漸漸引起逆反,英雄(梟雄)不畏也不全信規范,他們懂得了使規范為己所用。
美好的語言與意向溫暖人心,時間長了,美言變成套話空話,好心變成作秀,禮儀變成虛與委蛇,仁義道德變成幌子。一種文明、一種體制、一個朝代,在它的初始化階段大多是生氣勃勃、引人入勝、萬民歡呼的。而過了一個時期,各種僵化、老化、空化、異化、腐敗與病毒入侵的現象漸漸滋生,甚至成為痼疾。于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孔孟竭力要求回到唐堯時代,而莊子干脆要求回到更古老的前神農時代,老子的希望則是人人回到嬰兒時期。
這里的復古懷舊是現象,批評現實、要求調整變化、因應挑戰、恢復活力、重新從零開始做起才是實質。
這樣,孔子認為自己是西周文脈的最后唯一代表,孟子則深深意識到他是孔子后的文化、政治、救世、天命的擔當人。
孟子鼓勵自己與自己的門徒,還有自己一類的、大體上是以自己為帶頭人的社會精英群。
這樣的精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是一般人。
這樣的精英,“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后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藐視權貴,牛氣自身。
孟子還發明了天爵、人爵之說,用今天的話說,一個人本身的精神境界與能力是“天”給你的級別,晉升什么職銜,則是由人事部門定的級別。人應該努力去修養自己的境界能力,級別待遇則是順便的事。這話對于今天的中國,太合適也太必須了。
他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認識與擔當,毫不含糊。他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皆備于我”,與其說是主觀唯心,不如說是對于天人合一的信仰,善德即是人性,人性即是天性,人心即是天心,人道即是天道,只要不受后天的異化與“非人”“非仁”的惡劣影響,推己及人,推己及物,推己及天下,其樂莫大,求仁莫近。一個仁一個樂,便是天道,便是人性的根本。
這樣的精英不是白吃飯的,而是起著大作用的。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這樣的精英要求尊重禮遇,高看自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要樂而忘勢,“樂”是滿足與自信,“勢”是權貴乃至君王。孟子的理論給力,但中國的后世,精英們的處境與自我感覺是每況愈下。
尤其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此言,帶幾分狠勁!
精英們做了君王的臣子,仍然要求雙向的尊重與忠誠,而不是單方面己方的“罪該萬死”與君王方的“口含天憲”。孟子甚至提出來,“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他認為,貴族精英圈子可以因君王的過失而更換之,搞得“王勃然變乎色”。
(責任編輯 /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