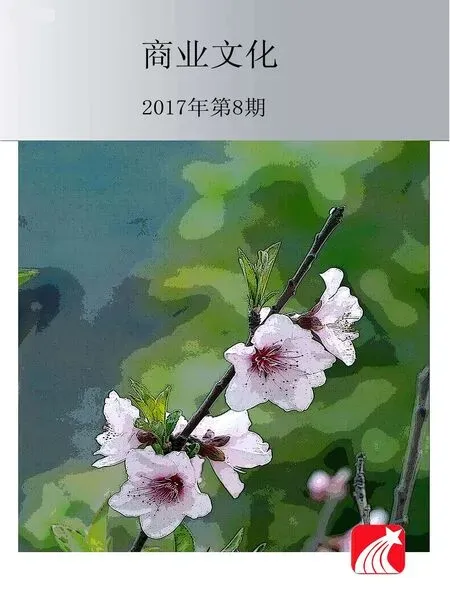形式獨特 格調高古
呂永生
書法之藝事,“觀其變,可以知世之文質,觀其跡,可以見君子小人,則藝而進于道矣。”此語表明了中國書法的不斷演變,氣象萬千,可以窺見先民對宇宙萬物的觀念,可以體味陰陽剛柔、相克相生的古老哲學思想,也可領略華夏大地的文明現象與書法創作主體的胸懷大志。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當代書法藝術隨之蓬勃輝煌,人才輩出。尤其京城書家群墨守成規,成績斐然,其中京城優秀書法家吳明禮先生可以說是當代中青年書家中最富有強烈創新意識的先驅者。吳先生在遵循藝術發展自律性的基礎上進行革新,達到了繼承與革新的辯證統一,正如李可染先生所說:“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
吳明禮先生75年出生于才子圣地江蘇徐州,曾就讀于解放軍第二炮兵指揮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首屆中國中青年優秀書法家研究生班。吳先生的兄長在當地就是名副其實、足有成就的書法家,使之自幼受家庭墨香的熏陶而與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并且具有天才般的藝術表現才能,多年的軍營生活,能將軍人勇士般的日常隊形訓練技能與筆歌墨舞相結合,造就了吳先生對書法藝術的理解與思想別具一格,頗有與眾不同的創新意識,尤其對秦漢文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與高度,其深邃的思想與平日的艱苦實踐決定了他的創作方向,趨向于古隸的演繹。
觀摹吳先生近幾年在全國大型的書展中頻頻入展與獲獎的作品,隸書的藝術形象尚帶有篆書的意味,但橫向氣勢已無明顯的波挑,然而已無篆書圓潤纖麗的形態。其線條粗壯樸實而厚重,筆畫縱橫有度,沉凝遒勁。用墨濃淡枯潤過渡自然,幾十年的辛勤耕耘與持之以恒的臨摹取法,無意識中已形成筆勢徐遲沉穩而骨力洞達,再摻以行草流暢的筆意,其作品更顯飄逸灑脫,自然奔放,在平正中見崎嶇,于奇險中又復歸平正。造型獨特,亦有弛張,形體抑揚,往往采取夸張與變形的浪漫主義手段,大開大合,收放自如,金石味與篆籀氣撲面而來。章法別具匠心,有行無列,貌似亂石鋪街,實則富有形行而上的經營位置能力,令人煥然一新,賞心悅目。總而觀之,從筆法到字法,從章法到用墨技巧,予以觀賞者播種了形式獨特與格調高古的精神食糧。
一幅完整的作品形式是由內在的結構和外部的藝術語言等兩種形式因素構成。而且內外兩種形式因素常常緊密相關,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從結構來看,由于吳先生對文字內部結構的演變有著深刻的理解。筆畫與筆畫之間,字與字之間以及行列之間的特殊組合,經過吳先生內部精神與主觀意識的消解,能夠激起審美者的特殊興趣與審美情感,達到了感性與理性、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據筆者了解,吳先生天然與功夫俱佳,對夸張與變形的造型能力有一定的把握,并迎合了取舍、虛實、主次、疏密、掩映、斜正、開合、呼應等經營位置的藝術原理,使其筆法、字法、章法等所構成的藝術形象既新穎又古雅,既自然又活潑。獨具性靈,格外至致,令人意趣盎然,美不勝收。尤其在空間的處理方面,打破了篆書的均衡與對稱,刪繁就簡,省去了隸書橫畫波磔的一般特征,保持了秦漢隸變時期的原始質樸之姿,蘊含著神秘怪誕的藝術思想,按照藝術真、善、美的發展規律,其字顯得空靈而妙趣橫生。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虛實實,神采奕奕,無畫處皆成妙境。從藝術語言來探析,吳先生經過無數次的艱苦實踐與大膽嘗試,對筆墨技巧以及物質材料、線性線質等的運用有獨到的見解與駕馭能力,并充分運用唐以前絞轉與平動的微妙表現方法,逆入平出,見筆見墨,造就了線條厚重而凝煉,古樸而富有音樂般的節奏與旋律。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再融以潤澀相兼、濃淡相宜的用墨技巧,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傳達了神奇變幻的藝術內容,具有準確、生動、鮮明、豐富、新穎等高質量高水平的藝術語言特點,在繼承傳統藝術語言的基礎上,富有強烈的革新精神,并隱含著無窮變化的表現能力。
無論內部結構還是外部的藝術語言,吳先生始終將情感與思想交織在一起,達到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有機統一,令人癡迷,也令人震撼,再加上對藝術語言的靈活運用,還原了書法的本源,主張復古主義。因此,經過吳先生意象物化的精品力作顯得格調高雅,古色古香,意蘊不溢于表象,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意與境合,思與境偕,融儒、釋、道于一爐。
高格調的書法作品往往能表現出吳先生的美學品格與思想情操,尤能表現出吳先生的獨立人格和對書法藝術繼承與創新的嚴肅認真的態度。觀其作品無不體現吳先生有著深厚的傳統功底,并能恰如其分地運用秦篆、漢隸、簡帛書的筆法特點,來表達相應的思想感情,遵循道法自然的藝術思想,既不裝腔作勢,也無嬌揉造作,道與藝合,無意于法,無意于佳。俯而察之,似乎脫胎于《祀三公山碑》與帛書、篆隸相間,有的字并不像隸書那樣放縱而橫向逸出,意在筆先而加以約束,取篆書大雅的縱勢,但各字又隨形而書,長短肥瘦各有態,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其姿態豐富,委婉而華美,含而不露,典雅靜穆,舒暢流麗,筆勢時兒曲伸,時而起伏,如虎步龍行。再細細品味,其作品又吸收了《石門頌》的藝術精髓,古拙自然,循石而行,以毫端做逆鋒狀,含蓄蘊藉,中間運筆遒緩,肅穆敦厚,動靜結合,奇趣逸宕。而且,還有《張遷碑》的雄厚古茂,運筆樸拙,略含生澀的特點,也融入了《西狹頌》那端莊方正,雄渾跌宕的氣勢,骨力內含,短促中見開張,開張外見神韻。
綜上可見,吳先生平時的臨帖日課就取法乎上,游離于漢碑各經典之作,拆骨還父,拆肉還母。以漢隸為標榜,另辟蹊徑,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隸書風格,象外之旨,書外求書,境外求境,一貫追求英國克萊夫·貝爾“有意味的形式”的藝術理念。吳先生將精神退回到自身,直接表現出主體精神的內在內容,展示內心的意象思維,表現自我,抒發情感,獲得了浪漫型藝術精神美與古典型藝術靜穆和悅的理想美相結合,在理性的肩膀上感性馳騁,似乎已真正吻合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核心思想——藝術美是“理性的感性顯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