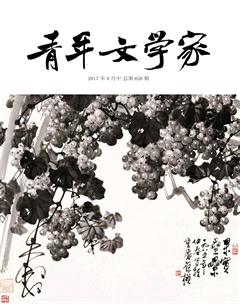丘為與盛唐山水田園詩派
冉婷
摘 要:丘為和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王維以及祖詠交往深厚,彼此間常有詩歌的唱和。其山水田園詩在立意、風格以及技法上均與盛唐山水田園詩的典型特征相近,因此可以說丘為屬于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中的一員,而且其山水田園詩具有“清幽”、“和平淡蕩”的詩境。
關鍵詞:丘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6-0-03
丘為是盛唐時代的詩人,因其存世的詩歌數量少,生平資料殘缺不全且多零星散見而不被人熟知。也因此,學界對丘為的關注歷來較少,有的也只是零星提及或對其某一首詩進行分析。那么,在此種現狀下是否可以將丘為劃入山水田園詩派呢?雖然葛曉音在《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中說:“與王孟詩派風格近似的作家還有綦毋潛、丘為、薛據等。因存詩數量少,一向不受重視,其實也可劃入王孟詩派。”[1]由韋鳳娟等人編著的《新編中國文學史》也說到:“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著名詩人,還有常建……此外,還有丘為、盧象、王縉等人。”[2]然而,還有一些涉及到山水田園詩派的研究著作和論文卻絲毫沒有提到丘為。因此,為了證明是否可以將丘為劃入盛唐山水田園詩派,本文擬從兩大方面入手:一為考察丘為與這一詩派詩人的關系是否密切,二為通過其具體的詩歌文本來確定其立意、風格和技法是否與這一詩派的典型特征相符。
一、丘為的生平與交友
關于丘為生平的傳記,《新唐書·藝文志四》載:“《丘為集》卷亡。蘇州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余,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為異,唯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為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3]此外,還有《唐才子傳》、《唐詩匯評》、《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唐詩大辭典》( 修訂本)中對其有類似的相關記載。由此我們可知:丘為,生卒年不詳,嘉興人,剛開始累舉不第,后歸山讀書數年,于公元743年進士及第,累官太子右庶子,以左散騎常侍致仕。為人謙恭有禮,以孝敬繼母聞名,卒年96。初有《丘為集》行世,后亡佚。
關于丘為的交友,《唐才子傳校箋》中寫到:“王維甚稱許之,常與唱和。”[4]《唐詩匯評》寫到:“為詩長于五言,與王維、劉長卿友善唱和。”[5]由此可知,他與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王維以及詩人劉長卿交好。此外,與王維的交往也可由以下這幾首詩為證,如丘為的《湖中寄王侍御》,其中“每有南浦信,仍期后月游” 這兩句直接抒發作者每次收到對方的信后便渴望與友人的再次重逢之情,而通讀整首詩,更能明顯地感受到二人間的深厚交往所言非虛。此外還如《留別王維》:
歸鞍白云外,繚繞出前山。
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閑。
親勞簪組送,欲趁鶯花還。
一步一回首,遲遲向近關。
雖然這首詩有學者認為是王維寫給丘為的《留別丘為》,但不管怎樣,從詩句本身入手,我們可以感知二人間的交往及深厚情誼。首聯點明送行的地點及環境,頷聯寫出自身近日的心情,頸聯用“簪組”表明對方身份為自己送行,并和對方約定春天再回來,而尾聯“一步一回首,遲遲向近關”的描寫,動作畫面感極強,我們仿佛親眼看到了一幅難舍難分的友人分別圖,畫面中詩人每走一步便回頭望望為自己送行的友人,腳步似有千斤重,“遲遲”既表明詩人動作緩慢,久久不能前行,又點明詩人此時內心對即將與自己分離的友人的深深不舍之情。
另外,王維也為丘為寫過一些送別的詩以表達二者之間真摯的友誼,例如《送丘為落第歸江東》、《送丘為往唐州》等。以第一首為例,這首詩作于開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此時王維正在京城做官,整首詩既有對丘為落第的惋惜和同情之情,又有自己雖在朝為官卻無力幫助丘為的愧疚之情。除此外,他們二人還和皇甫冉一起共同創作了詩歌《左掖梨花》等。當然,丘為還與山水田園詩派中的詩人祖詠有所往來,例如他曾為丘為的落第表示過不平,《送丘為下第》這首詩便是明證。
在這些詩篇中,我們能夠看到詩人善于抓住闊大空間中的山水意象,并在這些山水之中表達對友人的依依不舍或者思念之情。而從他與王維的交往唱和之中,我們或許也能推斷二者之間會有詩歌的交流,從而使得其詩歌風格向山水田園詩派更靠近一步。
丘為除了與山水田園詩派中的這些人有所往來唱和外,還和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中的大多詩人一樣與禪僧以及隱士等有所往來,并將其體驗融于山水田園詩的創作之中。例如《辛四臥病舟中群公招登慈和寺》、《尋西山隱者不遇》、《尋廬山崔征君》、《題農父廬舍》、《泛若耶溪》等。
那么,據以上推斷,我們可以說其詩風與山水田園派風格相似,但是否便可以將他歸為山水田園詩派中的一員呢?因此,我們需要繼續從其詩歌的立意、風格與技法等方面來考察其是否與山水田園詩派相一致。
二、丘為的山水田園詩
“盛唐山水田園詩派”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內涵,它是一種“非自覺型的文學流派”。[6]即這一詩派中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從題材的選擇到審美趣味、藝術風格和表現技法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其具體體現為:詩人在繼承和發揚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的詩歌創作傳統上,大多以五言的體式去描繪山水田園的自然美,從而表現出閑情逸致和超塵出世的思想情緒,風格清幽恬淡。那么,丘為的山水田園詩是否具有這些典型特征呢?
首先,從詩歌體式看,《全唐詩》中共存丘為的詩13首,另外《全唐詩外編》補詩5首。這些詩中屬于五言詩的有13首,且18首詩中除《渡漢江》疑為戴叔倫的《江行》,《留別王維》疑為王維的《留別丘為》和《省試夏日可畏》疑為張籍作這三首外,剩下可嚴格算山水田園詩的有《尋西山隱者不遇》、《題農父廬舍》、《泛若耶溪》等8首。其他的如《湖中寄王侍御》、《送閻校書之越》、《左掖梨花》、《竹下殘雪》等詩也兼具山水田園詩的風格。由此可知,在丘為僅存的這些詩中,以山水田園詩為主。endprint
其次,從詩歌的立意看,丘為詩中也有表現隱逸高趣、體現佛禪之理的詩。盛唐的隱逸之風盛行,無論是哪種類型的“隱士”總免不了與山水田園結下緣分,因此王、孟詩派的詩中常見的類型之一便是表現隱逸高趣的詩。在這類詩里詩人們在大自然的澄懷靜照中頓悟佛禪之理,但又并不把它們直接寫入詩歌,而是將象外之旨和意外之趣蘊含在簡約的意象描繪之中,從而創作出與山水審美體驗相結合的山水田園詩。如《尋西山隱者不遇》(一作《山行尋隱者不遇》):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關無僮仆,窺室唯案幾。
若非巾柴車,應是釣秋水。差池不相見,黽勉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窗里。及茲契幽絕,自足蕩心耳。
雖無賓主意,頗得清凈理。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如題,詩人是專程到山中去尋訪隱者的,卻不遇,按常理本是令人掃興的,但見到清凈的居處環境以及猜想主人的去向后卻產生了興趣,有感而發,從而寫了這首詩。或許這就是葛曉音所說的:“盛唐山水詩皆由直尋興會而得。”詩句開門見山,直寫隱者的棲身之所,據所在“絕頂”,距離山下三十里,點明所處之高,而“直上”二字寫出了山勢的陡峭高峻,這兩句似敘事,實際暗示出了隱者的避世心態,以及尋訪者不憚艱辛的誠意。接下兩句和題目照應寫“不遇”,并環顧主人所居環境的清靜。緊接著展開聯想:隱者不在居處,可能是駕著柴車出游或者臨淵垂釣去了,這猜想既符合隱者閑適雅趣的生活情況,又體現了作者的情趣。本來鋪敘隱者的日常生活和潔靜幽雅的居處,在山水田園詩里是常見的內容,但這里不正面描寫,而是從懸想落筆,體現了作者詩句描寫的靈活有致。“差池不相見,黽勉空仰止”這兩句雖體現了作者對隱者的仰慕之情以及因錯過機會不能和隱者相見的遺憾之情,但詩寫至此卻宕開了去并不對這種失望之情加以延伸。如果說前八句表達了詩的第一層意思——尋隱者不遇,那么接下來八句則體現了作者于不遇中有得的體悟:在山間清新幽絕的景色中,尋得幽情雅趣并體會到佛禪的“清凈”之理。前兩句從視覺和聽覺兩方面寫景,為抒情作鋪墊,接下來四句為全詩的主旨所在,寫作者因山間景色由先前的失望變得滿足,由敬仰隱者變為自己領略到隱者的情趣和生活。最后兩句作為全詩的總結,“下山”與首句“直上”二字呼應,“何必待之子”與詩題“不遇”相應,同時化用王子猷雪夜訪戴,至門興盡而返的典故,從而抒發了自己曠達的胸懷。因此,這首詩與其說是訪隱者,不如說是尋幽趣;與其說是寫隱者,不如說是詩人的自謂。總之,詩人另辟蹊徑,從“不遇”著筆,變掃興為有興,從中既尋得幽雅之趣又悟出了佛禪的清凈之理,較之“遇”的泛泛而談似乎更新鮮別致,耐人尋味,由此體現了其構思的新穎以及意趣的風雅。
最后,從詩歌的風格和技法看,丘為的詩中不僅只體現了陶詩中的精神旨趣,還能在繼承吳越山水詩清新詩風的基礎上,通過白描、煉字以及從日常生活中選取獨特角度的構思等技法,將田園隱逸和山水風光結合起來,形成一番別有風味的詩歌。具體來說,即在丘為的田園詩中,他用近似口語話的詩句,白描的藝術手法,為我們展現出了一幅平靜樸素的田園圖景。如《題農父廬舍》:
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
湖上春已早,田家日不閑。
溝塍流水處,耒耜平蕪間。
薄暮飯牛罷,歸來還閉關。
該詩雖題為《題農父廬舍》,但其實并不是表現農舍,而是向我們展現了一幅湖上早春,農家忙于挖溝耕作的生活圖景。在丘為的這首詩之前,田園詩里并沒有出現過湖邊田家的生活,這算得上丘為的首創。從詩句本身入手,首聯平易質樸,似口頭語般向我們描繪出了一幅在不知不覺間便被悄然而至的春風將漫山遍野染得春意盎然的美景圖,雖看似平易,實則飽含巧思,尤其是“綠”字,看似漫不經心隨手拈來,實則體現了作者的煉字功夫,創意頗奇。晚明鐘惺、譚元春在其合編的《唐詩歸》中評這句詩:“不說出草樹甚有味。此‘綠字虛用有情。”[7]清人張文蓀在《唐賢清雅集》中也評價其“妙不費力,是煉神法”。[8]接下來四句用白描的手法寫了農家春忙的景象,表面上雖沒寫人,但實際上正是寫人,這正如陶詩中人與景混成一片,景色既由人的活動見出,又能引起詩人觀賞自然的手法一般。最后兩句表現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圖景,也隱約體現了作者向往與世無爭的、寧靜閑適的生活心態。從整首詩來看,詩人是以一個旁觀者的欣賞態度來贊美農家生活的,因而我們可說這首詩和大多數王、孟詩派中詩人的田園詩一樣,因時代的變化,詩里少有陶詩中那種窮幽人玄的哲理思辨,只是較多的從意象上接受了陶淵明所提供的一種現成的田園模式,通過創造類似的隱居環境來表現與陶淵明類似的心境。
另外,丘為還和王、孟詩派中的很多詩人一樣,受吳越山水詩的影響很深,在詩歌創作時遵循吳越山水詩從舊識中見新情的創作路數:以吳越山水為題材,從平時日常生活所見中取景,詩歌語言口語話同時和聲律相結合,具有明白易懂、淺近流暢的特點,詩風清幽平淡,正如明末唐汝詢 《唐詩解》評丘為詩:“丘為,蘇人,未免染吳音,然亦清情不凡。”[9]如頗具一番風味的《泛若耶溪》:
結廬若耶里,左右若耶水。無日不釣魚,有時向城市。
溪中水流急,渡口水流寬。每得樵風便,往來殊不難。
一川草長綠,四時那得辨。短褐衣妻兒,馀糧及雞犬。
日暮鳥雀稀,稚子呼牛歸。住處無鄰里,柴門獨掩扉。
若耶溪是越中的名勝,歷來為人們寫詩稱贊,但大多數人在此泛舟時只注意到了此地的山水之美,而丘為在此卻和王績、孟浩然等人一樣,使山水、田園兩大題材的表現和意趣融為一體。詩中具體表現為,詩人通過選取獨特的角度,將若耶溪中川草常綠的優美自然環境和陶詩中的田園風味結合起來,向我們展現了一幅近水田家的生活圖景:隱者在若耶山里構筑了房舍,若耶溪從房屋兩邊流過,房舍周邊川草四季常綠,隱者平日釣魚、砍柴,穿著粗布短衣的妻子、孩子相陪,用多余的糧食喂雞犬,日暮時鳥雀歸林,稚子呼牛歸家。整首詩的描寫正如《唐詩歸》所評“說來只是清幽,全不蕭條”、“說得逶迤而不閑散”[10],別具一番風味。endprint
總之,丘為的詩從整體上看,正如葛曉音所說:“從內容到風格都較為接近孟浩然,而又有自己獨特的角度。構思新穎,卻因皆來自生活而不傷于工巧,所以亦頗清新可誦。”[11]而其詩境又有清幽、和平淡蕩的特征,即他在詩里無論是表達對理想的追求、生活不平的抱怨,還是對優美自然風光的描寫、樸素田園生活的展現,都表現得較為平和,既沒有激烈的躁動也沒有深沉的悲哀。這也可以從清人賀裳《載酒園詩話》中“讀丘為、祖詠詩,如坐春風中,令人心曠神怡。其人與摩詰友,詩亦相近,且終卷和平淡蕩,無叫號梟噭之音。唐詩人唯應幾近百歲,其詩固亦不干天和也。”[12]得到一定的印證。
綜上所述,丘為與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中的王維交往深厚,并和這一詩派中大多數的詩人們一樣常與禪僧以及隱者往來;其山水田園詩從其立意、風格和技法上來說也具有五言的體式、隱逸的思想、清凈的佛禪之理、白描的藝術手法、淺近流暢的詩歌語言、清幽平淡的詩風等盛唐山水田園詩具有的典型特征。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將丘為歸入盛唐山水田園詩派。
注釋:
[1]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274.
[2]韋鳳娟、陶文鵬、石昌渝. 新編中國文學史(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81-283.
[3](北宋)宋祁,歐陽修撰.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1605.
[4]傅璇琮. 唐才子傳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5:73.
[5]陳伯海.唐詩匯評(增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55.
[6]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2.
[7](明)鐘惺,譚元春.唐詩歸[M].續修四庫全書本.(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8](清)張文蓀.唐賢清雅集[M].清乾隆三十年抄本.
[9](明)唐汝詢.唐詩解[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
[10](明)鐘惺,譚元春.唐詩歸[M].續修四庫全書本.(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11]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276.
[12](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卷二)[M].
參考文獻:
[1](清)彭定求等編纂.全唐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王重民等.全唐詩外編[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
[3]丁成泉.中國山水田園詩集成[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聞銳.構思新穎 獨辟蹊徑——讀丘為《尋西山隱者不遇》[J].課外語文(初中),2008(3).
[5]張彥.劉昚虛與盛唐山水田園詩派[J].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