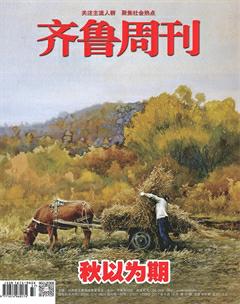蟋蟀:秋之意象
“蟋蟀獨知秋令早,芭蕉正得雨聲多 ”蟋蟀聲聲漫吟輕唱中,涼風四起。
在山東,寧陽和寧津是蟋蟀的主要產地。2010年,寧津被選為中華蟋蟀第一縣;《斗蟋隨筆》:自光緒21年至1940年,全國蟋蟀悍將26個,山東占17個,其中寧陽就有9 個。今年秋季,寧陽和寧津都傳來了數萬元一只的天價蟋蟀的新聞,蟋蟀火爆再次上演。白峰是玩蟋大家,他對蟋蟀的文化理解,獨到而有深意。
蟋蟀在先民的視野中,是作為“物候”而凸顯的。年復一年,蟋蟀逢秋而鳴,不差毫厘,所謂“鳴不失時,信也”。民諺中有“促織鳴,懶婦驚”的說法,說的是雖然天氣似乎依然很熱,但是蟋蟀鳴叫了,表明秋天已經來臨,再不抓緊紡織,一家人就要挨凍,因為冷空氣已經在路上了,再有個把月,天地肅殺,露化為霜,草木凋零,冬天就要來了。
南北朝時的崔豹,曾經著《古今注》,言及蟋蟀,還專門提及濟南人稱為“懶婦”,其實取的就是這個意思。
《詩經》中有兩篇提及蟋蟀,一是《邠風·七月》,一是《唐風·蟋蟀》,這是古文獻中有關蟋蟀的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蟋蟀的關注卻遠遠早于此,在倉頡造字的夏商時代,字以象形為要,皆出自人們對萬事萬物的理解。初創時期,文字并不統一,文字的統一還要有待千年之后秦始皇的霸業,甲骨文中“秋”字的寫法不止一種,其中一種活脫脫就是一只蟋蟀。應當說,遠古先民很早就把“蟋蟀”和“秋之物候”聯系在了一起,設定為秋天的象征,這是早期農耕生活的記憶和遺留,口傳心授,代代相傳。
在我們后來見到的“秋”字的各種寫法中,以“火”“禾”的組合居多,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的結果。在稍早的籀文中,“秋”字與“龜”有關,現代的書法中有時還會保留這個寫法:“龝”。這時候的文字已然由初創期的象形文字轉化為文化理解的“形聲字”,“龜”這個字,當時應當就是發“秋”的音。
但“龜”這個字并不僅僅表音,也表意,在上古文化中,先民對世間萬事萬物以“五行”分類,動物分類亦如是,分為毛蟲、翼蟲、鱗蟲、裸蟲、介蟲,對應木、火、水、土、金,《尚書》中說,“毛蟲三百六十,以麒麟為長;翼蟲三百六十,以鳳為長;鱗蟲三百六十,以龍為長;裸蟲三百六十,以人為長;介蟲三百六十,以龜為長”,所謂介蟲,就是甲殼類的動物,蟋蟀即屬介蟲,可以看出這時候的文字已是著眼于文化的理解了。
秋于五行中屬金,其色白,其音商,方位西。
以介蟲為秋字的字符組合,顯然包含著物候的意義。
而“火”“禾”組合的“秋”字,今日最為常見,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的結果,但為什么要用“火”來表達秋天呢?秋天的五行不是屬于“金”嗎?有些研究者認為這和占卜有關,古人將龜板放在火上灼燒,依據其所列紋路而得卦象,這個說法也有一定依據,甲骨文中有一種寫法,就在禾木旁,然后是在蟋蟀形下加“火”字。有放火燒荒的意思在,直到今天有些地區仍有秋收后放火燒荒的習慣,一方面是對秸稈的處理,使其成為來年的肥料,再則也有殺死昆蟲類蟲害的作用。至于說與“占卜”有關,既然象形的蟋蟀已然演化成“龜”,火燒龜板也似乎說得過去,但是占卜卻并非秋天的特指,似當另有來源。
事實上,火禾“秋”這個字來源亦當很早,當出自先民早期的天文觀測和歷法,據李學勤先生的考辨,上古時期曾有過“火歷”,是以“大火星”出現在天際為標志而酌定四季。從上古的文字遺留中,可以看出古時曾有一個時期,以秋為一年之始,就是所謂“火歷”。對天象的這類觀察,在后世文化中,仍有痕跡,比如《詩經》有句:“七月流火、八月授衣”,意思不是說七月份熱,而是說大火星西行,天氣將寒之意。再一個月要加衣服了。
我們在蟋蟀和“秋”這些聯系中,可以看到的是中國文字多重的文化來源,有物候的,有文化的,有天象的,映射出我們先民在認識自然之路上所做出的不懈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文化成果。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輪轉,川流不息。秋天是收獲的季節,一年的勞作都要在這里結果了,人們要儲存下一年的食物,度過寒冷的冬天,迎接新的一次輪回,生命由此而延續,生活由此而展開。沒有比秋天更讓人振奮和期盼的了。可以想見,先民們聽著蟋蟀的鳴唱,夜里睡的有多踏實,心中充滿溫情。慶典安排于此,當得、當得。
秋天也是肅殺的節氣,天地肅殺這個意象以霜降最為典型,一大早推門出來,望遠一看,屋瓦、樹木,處處皆白,秋之色定為白,這大約也是一個因素。古時人犯判了斬監侯,在監牢里押著,侯什么呢,侯的就是秋天這個節氣,所以執行是在秋天,而且要推出西門外斬首;在軍中則要推出西轅門執行。取的都是秋天肅殺這個意象。春天里不能殺嗎?能殺也不殺,以免傷了天地生發之氣。
天一降霜就到了秋之正氣了,經了霜,滿樹的葉子齊齊的黃萎,不出幾日就陸續掉光了。此時,惟楓葉、柿子,霜重色愈濃,點染荒郊野嶺,煞是好看。這時候已是蟋蟀最后的鳴唱了,回味著一生的征戰和奮斗,帶著無盡的眷戀,入土歸元。
都市里的人懷戀蟋蟀,說穿了是對大自然的一份鄉愁,是對先祖來路的一份不自覺的眷戀。蟋蟀這個小生靈遍布世界各地,但唯有在中國,它的鳴唱穿越數千年,從《詩經》到唐詩宋詞、明清小說,不絕于縷。可以說只有在中國,蟋蟀才是文化視野中的一員。斗蟋蟀也才成為中華獨有的民俗活動和人文景觀。
在當代優質蟋蟀的主產地中,山東南有寧陽,北有寧津,每年秋季的蟋蟀是農民重要的經濟收入,全國各地市的蟋蟀愛好者也如約而至,共同構成當地這一年中最重大的一次盛典和狂歡。
可是蟋蟀卻越來越少了,現代耕作技術已經使得人們不再有食物匱乏之虞,人們也很少再像古代先民那樣在意和關心蟋蟀這個小小的生靈了,蟋蟀兀自在田間地頭、房前屋后孤獨地叫著,呼喚著它的佳偶。可是我們注意過沒有,蟋蟀已經遠比我們少年時稀疏了。城市里不用說了,鋼筋水泥的建筑不再給蟋蟀筑巢的可能,硬化路面也不再讓蟋蟀來去自由;就是在鄉間,農藥化肥的普遍使用,也使得蟋蟀的鳴聲愈漸稀少,可以說,蟋蟀在當代更能體現一個區域的環境指標,已然成為了環境安全的晴雨表。
你能想象一個沒有鳥啼的春天,和一個寂然無聲、沒有蟲鳴的秋天嗎?
(白峰,著名蟋蟀研究專家,著有《中華蛩家斗蟋精要》《蟋蟀古譜評注》《解讀蟋蟀》《斗蟋小史》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