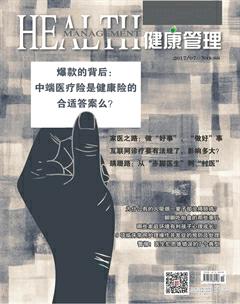蹣跚路:從“赤腳醫生”到“村醫”
【編者按】
小編前段時間因某個小毛病需要去醫院,然而又連續找不到空閑時間,一天晚上小編母親便感嘆道:能怎么辦呢!現在沒有赤腳醫生了呀。
赤腳醫生在小編小時候還是個常見的詞,有什么小毛小病,頭疼腦熱,赤腳醫生過來打了一針開點藥片,幾天就好了。后來赤腳醫生進化成了村醫,但村醫的存在感就再也沒有赤腳醫生這么高過,大家對于看病的印象,漸漸固定在了掛號、看醫生、刷醫保這一套程序上。赤腳醫生的隨傳隨到隨手一針,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醫改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曾有朋友留言:我從小時候跟我媽去醫院上班就聽說了醫改,而如今我已經是主治了。很多醫生朋友都有這個感覺,醫改這個詞,貫穿了整個職業生涯啊?改了很久的樣子?
是的,沒錯。
1985年被稱作中國的醫改元年,通常討論醫改就是從這一年開始的。
然而,“什么是醫改”這個問題的答案,卻是藏在元年之前,那么,1985年之前中國的醫療是怎樣一種形態呢?
我們的目光回到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志指示: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自從有了這個指示,衛生部開始從城市的衛生系統抽調人力,組成衛生服務隊,下到農村去提供醫療服務。
但是,這樣依然解決不了醫療服務匱乏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衛生事業人力不足。事實上,當時和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衛生資源無法滿足全國人民的衛生需求。好在,當時的一項措施有效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培養“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的誕生
話說,當開始有了“赤腳醫生”這個定義以后,許多醫療隊在當地找到一些素質較高、有一定文化基礎的青年農民,并且對他們進行了短期的培訓,這就是最早的赤腳醫生。
用現在的眼光,這些赤腳醫生根本算不得醫生,甚至連專科的醫學生水準都不如,只是一批受過短期訓練的農民。
但是,在當時,這些人負責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農村基層醫療保障,并且取得了很顯著的改善。
正如 1965 年《中央轉批衛生部黨委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所指出的:
“大力為農村培養醫藥衛生人員。爭取在五到十年內,為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培養質量較好的,不脫產的衛生人員。”
一邊拿著“赤腳醫生手冊”,一邊扛著鋤頭,這就是赤腳醫生最真實的寫照。
赤腳醫生的興起
從 1966 年開始,全國范圍內大量的赤腳醫生被培訓出來。到了1980年的時候,全國有赤腳醫生的生產大隊有 65 萬多個,占全國生產大隊總數的 93.7%。根據這個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赤腳醫生的普及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我們如何看待“赤腳醫生”制度的存在呢?
單純從專業技術角度看,赤腳醫生當然存在缺陷。當時推行的所謂“三土四自”意思是:土醫、土藥、土辦法,自種、自采、自制、自用。
赤腳醫生普遍使用了中草藥和針灸這類診療技術,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醫療服務當然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但是,在當時卻是解決問題的不二選擇,因為這樣極大的降低了醫療成本。
同時,赤腳醫生的收入也是符合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的,那么這些赤腳醫生的收入從哪里來呢?請注意剛才提到的1965年的那份文件,其中“不脫產”三個字就是答案。
赤腳醫生并沒有受過系統的醫學訓練,嚴格意義上說并不是醫生,他們同樣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靠掙工分過日子。事實上醫療活動只是赤腳醫生的副業,而這個副業也是靠工分來體現價值的。
正是因為這種形式,赤腳醫生和農民既是鄉里鄉親、大部分沾親帶故,又都是生產隊的勞動者,同時還是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者。可以說是休戚與共,所以赤腳醫生的巨大優勢就是“養得起、留得住、用得動”。
在當時經濟基礎上,這樣一種模式運轉良好。談起現在的醫療,我們會時常見到這樣一句話:中國有世界罕見的大規模跨地區就醫現象。事實上,患者的高流動是造成醫療花費大幅提高的極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在赤腳醫生時代,這個問題并沒有出現,至于其原因,身為醫務人員的你通過上面的討論,肯定想得比本文作者清楚,在此就不做過多討論。
赤腳醫生所提供的低水平、廣覆蓋的醫療服務,真正體現了中國特色,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正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指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赤腳醫生制度之所以得以良好的運行,正是因為它和當時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相協調,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體系良好解決方案。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個體系的崩潰呢?
赤腳醫生制度的崩潰
是否還記得 1978 年,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的 18 位農民簽下了那份著名的保證書。從此“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登上了歷史舞臺,1980 年小平同志肯定了小崗村的做法,此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斷得到鞏固和推廣。
1983 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產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農村改革無疑是件好事,但是,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醫療體系沒跟上節奏。赤腳醫生沒有了工分也就沒了動力,這個曾經運轉良好的體系,日薄西山了。1985 年,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這一制度成為了歷史。這一年也正是“醫改元年”。
通過以上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醫療體系的是否運轉良好,要看它是否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制度相符合。
而自 1985 年來,計劃經濟已經轉型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而這期間所進行的一切嘗試,都是在構建能夠與之相符的醫療體系。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能看清如今所進行的醫改要做的事情。歷史不能給我們每一個問題的答案,但是能夠幫助我們看清所處的時代。endprint
鄉村醫生:改良版未進化
我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后,“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觀念就已深入人心。近四十年來,盡管偶因國際、國內之不利因素的影響在個別年份或者短期內出現疲軟或者增速放緩之態,但總體平穩發展之勢卻從未改變。
在國家和地方合力且側重發展經濟的同時,農村居民之生活水平得到了質的提高,交通狀況(如交通工具、路況等)更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于是他們不再滿足于溫飽等最低層次的需求,轉而愈發關注自身之健康問題。隨著科技、媒體之迅猛發展及廣泛應用,人們獲取(健康)知識的速度常常令人驚詫,獲取知識的手段亦更加多元與豐富,尤其是進入高等教育成為大眾化的21世紀之后,率先在城市進行的患者權利運動也隨之侵襲了原本鄉土氣息濃厚的鄉村,國民之法律意識普遍得到提升。
“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這曾是對赤腳醫生的執業歌頌與品德寫照。1965年,國家開啟了培養第一批赤腳醫生的大幕,二十年后(即1985年)易名為“鄉村醫生”。至此,“赤腳醫生”這一名稱肩負昔日輝煌,正式步入中國農村醫療衛生之史冊。
與赤腳醫生相比,盡管鄉村醫生難現昔日“赤腳醫生”時期之數量鼎盛,但醫療技能與就醫環境得到實質上的提高與改善,卻亦是不爭之事實。然而,與同期農村居民釋放出的醫療衛生需求相比,仍可謂“小巫見大巫”,實難契合自洽。
對于鄉村醫生而言,其醫療知識和技能除了培養環節中的修習可得之外,同等甚至更為重要的則是畢業后的在職培訓,因為它可以精準把握農村居民之具體訴求。客觀而公允地說,國家、地方衛生行政部門以及鄉鎮衛生院等單位整體上還是比較重視鄉村醫生的培訓工作,至于存在的問題,有些可以歸咎,有些則已超出其能力范圍,完全屬于法律與政策上之缺陷所致。
當前,我國鄉村醫生培訓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需要上下聯動,群策群力。
培訓對象和培訓師資的規定不完善
國家在一般培訓方面(即針對所有鄉村醫生)還差強人意,但在擇優培訓方面則明顯不足,未來應當結合進行。培訓師資的遴選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并未普遍建立細致及可操作性的規則,未來應當按照《全國鄉村醫生教育規劃(2011—2020年)》的規定進一步細化,寧缺毋濫。在制度建設上,可以考慮通過設立“專家庫”的方式進行,全面聽取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及時更新一部分授課專家以保證培訓效果。
培訓方式和內容存在一定的欠缺
在很多地區,對于中醫藥、基本藥物、信息化技能方面的培訓嚴重不足,但在一些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項目的技能上,卻存在著低水平重復的現象。未來應當圍繞“鄉村醫生向執業助理醫師轉化”之國家目標,參照有關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大綱設置培訓內容,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幫助其達到崗位要求。遠程視頻播放雖然時新,但交互性嚴重不足,社會實效也就一般,未來應適當增加一些面授和實踐課程。
培訓的頻次和時限參差不齊
我國于2003年頒布的《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曾經明文規定,每位鄉村醫生每兩年至少接受一次培訓。然而時隔十年之后,國家衛生計生委等五部門于2013年10月18日頒布的《全國鄉村醫生教育規劃(2011-2020年)》、2014年6月3日頒布的《村衛生室管理辦法(試行)》均作出了與之不同的規定,即要求鄉村醫生每年至少接受兩次培訓,且累計時間不少于兩周。于是,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就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盡管在法理上行政法規的法律效力高于部門規章,但就實際應用觀之,新頒布的部門規章卻是占據了上風,多少有些“雖下猶上”之蘊味。因此,建議將《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中鄉村醫生的培訓頻次修改為“每年至少接受兩次”。在鄉村醫生的累計時限上,應當按照《村衛生室管理辦法(試行)》、《全國鄉村醫生教育規劃(2011—2020年)》對鄉村醫生的最低培訓時限作統一規定,即每年累計培訓時間不少于兩周。但對于具體何時進行,則可以由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按照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設定,并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備案,以便后者通過常規檢查、隨機抽查等方式加強監管。
培訓地點少有規定且考核制度不完善
國家對鄉村醫生培訓的地點缺乏原則性或統一性規定,考慮到鄉村醫生出行的距離、時間等因素,一般應當限定在鄉鎮衛生院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行。在例外的情況下,可以經有關部門審批而選擇在其他地點進行。在農村這一熟人社會中,其特殊的血緣、親緣以及地緣優勢容易致使有關部門在鄉村醫生培訓考核的環節上出現一些問題,這主要表現為考核過程偏重形式化以及考核尚未普遍實現獎優罰劣的功用等。考核制度的不完善,影響到鄉村醫生對待培訓的態度,必然不利于其綜合能力的提升。未來可考慮引進第三方考核、考核結果與績效補助掛鉤等機制,切實做好這項工作。
培訓經費和培訓補助尚未妥善解決
對于組織培訓的單位而言,如果培訓經費不足或者不能及時到位,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培訓工作的開展。盡管國家以及一些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對此均有規定,但由于衛生行政部門需要列項申報由財政部門審批,在當前教育、衛生、能源、農林、金融、環境等領域需要綜合平衡的時候,用于鄉村醫生培訓的財政經費有可能面臨著不足的問題。但我們更應看到,當前還存在相當一部分省份對鄉村醫生的補助數額較低,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對鄉村醫生的培訓沒有任何補助或者補助微薄,鄉村醫生參加培訓的積極性定會受到很大挫傷,農村居民也就不可能就近享受優質醫療衛生服務,從而陷入“惡性循環”的境地。因此,在發展理念上需要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以多種方式支持、參與鄉村醫生培訓工作,在常規機制上,對政府及其主管部門按規劃組織的鄉村醫生在崗培訓,所需資金由同級財政預算安排,不得向鄉村醫生收取費用。在培訓補助上,應當考慮(尤其是邊遠或者貧困地區的)鄉村醫生合理的伙食、交通、誤工等費用,并且列入財政,申請專項經費予以保障。
村醫: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