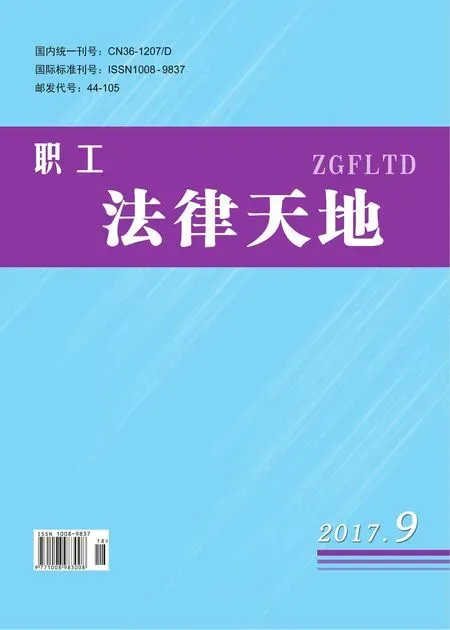淺析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制度
弓家衛
(252000 山東萬航律師事務所律師 山東 聊城)
淺析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制度
弓家衛
(252000 山東萬航律師事務所律師 山東 聊城)
證明是民事訴訟的核心,而舉證責任分配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雖然,我國新出臺的民事訴訟司法解釋中,對舉證責任分配作出了具體規定,但理論界對法律規定的理解仍然存在誤區,理論上對舉證責任分配規定的原則有: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法官自由裁量原則、免證原則等。理論和實踐中對這些原則的理解和適用存在一定誤區,實踐中法律對一些特別糾紛又作出相應的特別規定,導致實踐中經常對一些舉證責任概念的混淆,對舉證責任倒置適用對象的理解錯誤。所以,應當明確一些特有名詞的概念、舉證責任倒置的范圍,整體把握舉證責任分配。進一步規范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中的自由裁量權,明確裁量范圍及裁量規則,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實現訴訟中的真正公平。
一、舉證責任的概念
舉證責任也稱證明責任,是指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窮盡所有調查證據方法后仍然無法確信案件主要事實,在真偽不明的情況下確定由哪一方承擔敗訴后果的制度。舉證責任在民事訴訟中一般有兩種含義即主觀舉證責任與客觀舉證責任。主觀舉證責任是指一方主體對相關事實負有舉證的義務,主觀舉證責任后果一般有兩個:一是法院有權行使釋明權要求提出主張的當事人提供證據,另一個則是,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不能提供證據時直接讓其承擔敗訴的結果,無需審查另一方提供的證據;客觀舉證責任是指真偽不明時由那方承擔不利結果,其實質是法律適用的問題。
二、舉證責任的性質
1.權利說
這種學說認為舉證責任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依據訴權原理當事人有權要求法院通過審判來給予當事人司法救濟,實現其民事權益。所以舉證程序與訴訟程序相伴隨,當事人只有在訴訟過程中積極舉證,證明其主張的真實性,才能維護其合法的實體權利。隨著我國學術界的研究及實務中的驗證,逐漸認識到“權利說”的弊端。首先,權利是與義務相對應的,有權利就應有與之相對應的義務,但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并沒有與其權利相對應的義務;其次,如果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無法提供與其訴求相應的證據將承擔敗訴的結果,與權利的屬性相悖。
2.義務說
《民事訴訟法》第64條中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有些學者認為該條肯定了義務說,即將舉證責任稱為責任,也就是說舉證責任是一種義務,當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真實目的就得履行自己的訴訟義務,不能履行證明責任就得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但是該種觀點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果將舉證責任定義為一種義務的話,當事人不能履行該義務時就應當受到懲罰,但法律并未規定該方面的制裁措施,再就是不履行證明責任并不會給他人造成損失,與法律義務的屬性不符。
3.負擔說
負擔說以主觀證明責任為中心,當事人通過努力舉證盡量避免客觀證明責任這種不利裁判后果的出現,強調提供證據的重要性。負擔說的根據是:訴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案件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而法院此時不能以事實不清拒絕裁判,只能假定該事實存在或不存在做出裁判,將證明責任作為一種敗訴的風險。當舉證不能時法律規定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負有敗訴的風險,這樣更有利于促進當事人舉證,提高訴訟效率。
三、有關舉證責任分配的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1991)中規定:“當事人有責任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提供證據”。也就是理論上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2)第2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提出的訴訟請求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不能證明時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將承當不利后果。”在“誰主張,誰舉證”的前提下更加強調了在不能證明時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承擔敗訴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訂)中對舉證責任做出原則性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15)對當事人舉證、證據調查、舉證時限、質證等作出了具體規定。盡管,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對舉證責任分配作出原則性規定,《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對其作出了具體規定,但是舉證責任分配中的諸多問題仍然沒有縷清,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舉證責任分配不明確、邏輯自相矛盾的現象,以至于司法實踐中法官在有些時候分配證明責任時依據自己的主觀印象或者是考慮真正的公平。
四、幾種特殊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分配
1.醫療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規定:“由醫療機構證明在醫療事故中醫院不存在過錯、損害結果與醫療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醫療事故侵權中,患者應當證明與醫院存在醫療合同及在醫療過程中受到的損害,醫院應當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立法者考慮到醫療訴訟中患者處于弱勢地位,醫療事故中存在許多專業知識,相對于患者來說醫院證明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更容易。而且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醫院的注意義務,減少醫療事故的發生。但是醫院無法控制醫療事故發生,因為其中存在很多不確定性,醫療事故與環境污染不同,可以通過引進設備等手段避免損害結果的發生,這樣舉證責任倒置就會在避免環境污染訴訟產生中發揮很強的作用,從而避免環境污染的發生,醫療事故中則不會起到這樣的效果。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加之法官自由心證的傾斜,完全可以保護患者的利益。反之,則會嚴重損害醫院方面的利益,無法實現最終的公平。
2.公益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分配
相對于傳統的“誰主張,誰舉證”證明原則,公益訴訟中證明責任分配需要綜合考量多種因素。首先,考慮公平因素,對舉證責任公平的追求恰恰是對“特權”的削弱,制約現實中的不公平以期達到實質的公平,在傳統的民事訴訟中原告對其提出的主張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對其抗辯負有舉證責任,但是在公益訴訟中雙方當事人的能力不會因為公益訴訟的介入而直接轉變,不得不承認公益訴訟中原告方處于弱勢地位,如果公益訴訟中原告因為此種弱勢地位被拖累,就會影響案件真正的公平;其次,考慮便利因素,公益訴訟中原告一般處于弱勢一方,關鍵證據常常掌握在被告手中,只有通過對證明責任的分配才能最近距離獲取被告手中的關鍵證據,提高民事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也更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后,對公益訴訟蓋然性的傾向估計,雖然在訴訟之前法官不能對案件作出具體的裁判,但是法官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基本情況和社會環境對案件作出傾向性判斷,然后對當事人具體舉證責任的分配作出初步判斷,有利于實現案件真正的公平,維護當事人的根本利益。
3.虛擬網絡財產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
由于虛擬網絡在我國迅速發展和崛起,我國法律并未對虛擬網絡財產中的證明責任分配作出具體的規定,只是在相關法條中作出籠統的規定,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證明責任分配不統一。在法律對網絡虛擬財產未作出列舉規定的前提下,有些法官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認為原告應該對虛擬財產遭受損害是由被告過錯所造成的承擔舉證責任,從司法實踐中來看,這種做法雖然在少數情況下可以保證原告的利益,不用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原告處于劣勢地位,無法對損害結果是由被告過錯所造成提供充分證明,因而承擔敗訴的結果;有些法院的法官則根據公平原則,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在虛擬網絡財產訴訟中,考慮到此類案件的特殊性,結合具體案情及雙方舉證能力,法官根據公平原則在窮盡一切手段后仍然無法查清事實時,行使自由裁量權,在網絡虛擬財產糾紛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以期保護當事人的根本利益。司法實踐中,一些案件法官雖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運營商、開發商仍然處于強勢地位,仍無法實現真正的公平。
五、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在法律規定中通常由一方當事人舉證的部分,在法律規定下無需由其舉證,而是由另一方承擔舉證責任的一種責任分配制度,應該注意的是舉證責任倒置是要件事實的敗訴風險而非主觀意義上提供證據的責任。我國法律對舉證責任的倒置進行了列舉性的規定。在環境污染訴訟中被告需要對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建筑物及其上面的懸掛物、擱置物發生倒塌、脫落造成他人損害時,由所有人及管理人對其沒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在動物致人損害的案件中飼養人或實際管理人要對受害人存在具體過錯提供證據加以證明,避免自己承擔不利后果;因產品質量造成他人損害時,產品生產者對自己免責負有舉證責任;在共同危險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訴訟中,實施危險行為的人需要對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雖然,司法解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了列舉性的規定,但是此種手段無法窮盡所有特殊例子,而且對一些舉證責任倒置中具體是那方面進行倒置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只是進行了籠統規定,導致在適用時存在諸多問題,需要法官裁量的部分較多,實踐中同案不同判,損害當事人的根本利益。
六、舉證責任分配中的司法裁量
舉證責任在民事訴訟中居于核心地位,而舉證責任分配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雖然法律已經規定了客觀的分配責任,但訴訟過程中具體情形千變萬化,嚴格按照事先規定的舉證責任分配風險,有時會帶來過于機械適用的副作用,可能會導致裁判結果無法實現真正的公平。所以舉證責任分配中的司法裁量是不可或缺的。舉證責任的司法裁量權一般是指審理結束后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法律法規未對舉證責任進行分配,法官可以根據公平正義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經驗法則以及當事人的舉證能力等因素對當事人雙方的證明責任進行分配的權利。這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并不是隨意的,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首先,法律未對真偽不明時法律后果的承擔做出具體規定,法律做出具體規定時必須適用法律規定;其次,雙方當事人未對真偽不明時法律后果的承擔做出具體約定,有約定時應該從約定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最后,在沒有法律規定又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按照法律分類要件說又會違反司法公正,不能實行真正的公平時,法官才能行使舉證責任分配裁量權。
七、完善我國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的法律建議
雖然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以及后來出臺的訴訟法司法解釋都對證明責任分配做出了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證明責任的具體應用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具體適用也不統一。因為法律規定中存在諸多空白點,實踐中遇到一些具體問題無法適用,需要法官根據公平原則進行自由裁量。例如,司法實踐中進行司法鑒定到底應該由誰提出,誰應該承擔不進行鑒定所帶來的不利后果,這些都是沒有定論的,由法官來自由裁量。通過對實踐中實務的總結及與一些基層法官的探討,他們在司法鑒定中舉證責任的分配也沒有固定標準,而是根據具體案情需要及實踐中公平的考慮分配司法鑒定中的證明責任。所以,應當進一步完善我國舉證責任分配制度。首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舉證責任作出更加細致準確的法律規定,減少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的自由裁量范圍,規范實踐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其次,應當確保當事人自行取證的權利,擴大律師取證的范圍,將原有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才能調取證據的權利下放給律師,既能減少事實無法查清情況的出現,又能提高整個訴訟過程的效率,在證明責任分配之前解決該問題。也許在發生證明責任分配之前解決問題是更好的解決方式,既能節省成本又能避免復雜舉證責任分配,更好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也能維護真正的公平。
八、結語
雖然我國法律中對證明責任的分配既有原則性的規定也有列舉式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往往是憑借自由心正對證明責任的分配進行自由裁量,根據證明責任中的公平理念對其進行分配,而且實踐中法官對“誰主張,誰舉證”的理解和適用標準也不同,這正好證明了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在構建中。無論是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中,各個法學領域就像一個個待建的“大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