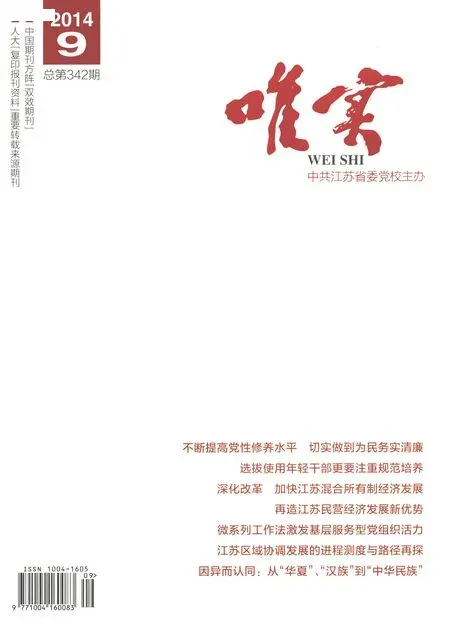“蘇作”中的工匠精神
余大慶
蘇州一直以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歷史悠久而聞名。蘇州的輝煌離不開眾多巧奪天工的工匠們。他們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精湛的技藝、敬業的精神,將心血和智慧投入所從事的行業中,打造了“蘇作”品牌,創造了人間“天堂”。今天,工業4.0又重新展現了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的前景,為了在更高層次上回歸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們應該重視挖掘傳統“蘇作”這一文化富礦。
一、現代工匠精神是傳統工匠文化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
傳統社會生產(手藝)的特點是:個性化、精致性、慢工細活。而現代社會生產(機器)則是標準件、模式化、批量高效的大規模生產。匠人變成工人,丟失的不僅是匠心。傳統手藝人對自己的產品負責,從頭到尾產品制造的每一道工序都出自己手,看著原料慢慢成形,最后變成產品,感覺就像上帝創造世界一樣。工匠創造了產品,有一種造物主那樣的創造欣喜和成就感。相對而言,機器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被分割在某一道工序之中,猶如機器上的零部件,只在特定流程起作用,而不能對整個產品負責。尤有甚者,資方為了節省勞動成本,把機器生產的效益推到極致,還發明了“泰羅制”,工人只能以最節省時間的機械動作勞動,這種勞動沒有絲毫樂趣,遑論在工作中追求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所以像傳統工匠那樣一生專注地做一件事,精益求精,為手藝而自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事物發展總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歷史發展規律,呼喚工匠精神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細究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發展,“泰羅制”一類異化勞動是第一、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即工業1.0和工業2.0時代的事情。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把人訓練成機器”。但是工業革命并非只是那一兩次,現代社會幾百年的發展,迄今已經發生四次工業革命,尤其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工業1.0是機械制造時代,工業2.0是電氣化與自動化時代,工業3.0是電子信息化時代,“工業4.0”則描繪了一個通過人、設備與產品的實時聯通與有效溝通,構建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新的生產方式宣告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有人稱之為“后現代”。
區別于近現代機器大工業標準件批量制造,后現代理論家布西亞指出了當下社會個性化、精致化消費需求引領的生產趨勢,也是一種高附加值的新生產。這時提出工匠精神,不僅僅把工作當作賺錢養家糊口的工具,而是樹立起對職業敬畏、對工作執著、對產品負責的態度,極度注重細節,不斷追求完美和極致,給客戶無可挑剔的體驗。將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個環節,做出打動人心的一流產品。所以李克強總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二、歷史蘇州是各行各業手藝人創造的人間天堂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還排在杭州前面,不為美景,而因多財。若論自然風景,蘇州沒有杭州那樣的湖山勝景(蘇州真山真水都在城外遠郊)。而且偌大中國,山水之勝豈獨蘇杭?風景再美,也當不得飯吃。所以人們贊譽蘇州,都稱道其市井繁華。曹雪芹《紅樓夢》開篇就說姑蘇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而李斗《揚州畫舫錄·城北錄》也引有劉大觀語:“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說明三個名城中,蘇州是以經濟繁盛領先的。當然,這并不是否定蘇州的“城里半園亭”。以蘇州領銜的整個太湖地區也因“蘇湖熟,天下足”為人向往。
但是,蘇州并非從來就是人間天堂。江南地區曾經是經濟文化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西漢時期,江南農業還停留于粗耕階段,生產手段相對比較落后,雖然礦產、林產資源豐饒,然而尚有待開發。“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漢書·地理志下》)。“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史記·貨殖列傳》)。當時江南地區“火耕水耨”,也就是燒去雜草,灌水種稻的簡單耕作方式。江南地域遼闊,人煙稀少,稻米和魚是主要食物,人們還可以從山澤中采集植物果實和貝類為食,放火燒荒,耕種水田,不需要商人販賣貨物,沒有非常富裕的人。
與此相對,開發最早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則是我國古代的政治和經濟重心,也是中原逐鹿的場所。一旦發生大規模戰亂,由于南方地區較之容納量有限的北部邊疆在自然和社會條件方面更為優越,避難人群往往將江南各地作為首選目標。這類以逃避戰亂為目的的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以兩晉之際永嘉之亂后的人口南遷、唐代安史之亂后的人口南遷和兩宋之際靖康之亂后的人口南遷最為典型,史稱“衣冠南渡”。
早在兩漢之際,中原兵爭激烈,據說流民數量之多,甚至可能達到原有戶口數不能存留百分之一的程度。人口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避亂江南”。東漢時期,連年水旱災異,導致流民移徙,其中也往往有渡江而南者。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使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升,有了大量的糧食作物和農業生產技術、工具和勞動力,還有了南方的紡織業、瓷器。
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逐漸開發,為我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奠定了基礎。“江南之為國盛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沈約《宋書·孔季恭等傳論》)唐朝中后期,我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地區農業發展逐漸超過北方。南宋時南移完成,標志為“蘇湖熟,天下足”,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南方特別是東南地區。蘇杭正是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獲得了“人間天堂”的聲譽。中唐時期南方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史稱“天下大計,仰于東南”,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愈加明顯。隨著東南地區的發展,蘇州的地位開始凸顯。白居易《詠懷》開篇第一句就是:“蘇杭自昔稱名郡。”兩宋時期南方的糧食產量、農業技術、手工業技術與規模、商業貿易、城鎮數量都超過了北方,江浙一帶已經成為全國糧倉地帶和最大的紡織中心和商業中心,同時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進程也終于完成。詩人范成大在《吳郡志》中寫道:“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后杭……”接著,他又援引白居易詩句進行論證,指出,“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可見,人間天堂是手藝人造就的。在傳統農業社會,不僅手工業靠手藝,農活也是一門手藝活而不再是火耕水耨的原始生產。endprint
來自封建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黃河流域,擁有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豐富的勞動經驗的北方移民,給江南帶來先進手藝,帶來繁華,甚至把原本斷發文身的吳人、輕死易發的吳文化,改造成為郁郁乎文哉的才子之鄉、溫柔婉約的江南文化。比如江南水鄉常見的農業灌溉工具方板枱式鏈泵翻水車(及其制作工藝)就是來源于河洛。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認為王充《論衡·率性》所載“洛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就是這種翻水車。而范曄《后漢書》卷78《宦者·張讓傳》中說水車是東漢末年畢嵐發明的。不管這些技術在兩漢出現的具體時間早晚,發明人是誰,江南蘇杭的開發得益于中原,經過江南各行各業手藝人傳承改進的種種工藝技術,乃為不爭的事實。傳統手藝促進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造就人間天堂。明清時期,蘇州的工藝技術達到鼎盛,創造財富無數。不僅曹雪芹夸它“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連皇帝修的頤和園里都建有一條“蘇州街”,以慰藉帝王對蘇州繁華生活的向往之情。
三、明清蘇州的生活樣式與手工制造業
在我國明清時代,蘇州成為當時全國時尚的風向標,出現“蘇意”一詞。明代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小序》亦言:“當世言蘇人,則薄之至用相排調,一切輕薄浮靡之習,咸笑指為‘蘇意,就是‘做人透骨時樣。不僅如此,在當時,一切稀奇鮮見的事物,也徑稱為‘蘇意。吳從先《小窗自紀》說,‘焚香煮茗,從來清課,至于今訛曰蘇意。天下無不焚之煮之,獨以意歸蘇,以蘇非著意于此,則以此寫意耳。”萬歷《建昌府志》稱:“邇來一二少年,浮慕三乏吳之風,侈談江左,則高冠博袖,號曰蘇意。”這些記述都充分說明蘇州先民富于文化創意的精神特質。
這種創意造就了流行全國的“蘇樣”或“蘇式”——就是蘇州人生活中累積的一種文化樣本,即蘇州人的生活態度、審美取向以及因此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等。“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其實,明人在當時就已經為“蘇式”的這種含義作了詮釋。如前述《小窗自紀》所言,同為焚香、煮茗,一般人只會注重實用價值,而蘇州人卻把它上升為一種意境,體味的是其中的美學價值。
而“蘇式”這種時尚化的特點,同樣存在于當時人們對器物的認識上。舉凡蘇州人所尚之物,即為流行。《廣志繹》中還說:“姑蘇人聰慧好古,善于仿古法造器,家具亦是如此。又如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尚古樸不尚雕鏤,即物有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海內僻遠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為盛。”這種質地好,但古樸不尚雕飾的“蘇式”家具,被公認為“雅”的代表。擁有這樣的“雅”物,成為文人士大夫們附庸風雅,彰顯身份的重要手段。謝肇淛言:“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為之,此為進御言耳。文房中既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而制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為柄,圓玉為紐,置幾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制瓦瓶,一時傳尚,價遂涌貴,吾亦不知其解也。”鄒樞貫在記述自己與金陵名妓卞賽之交往時寫道:“常以金陵十竹齋小花箋、閶門白面圓簿畫蘭,邀余題詩,余信筆題就,頗愜其意。每以十竹齋珠砂印色及水沉香等贈余。”在記錄與沙女交往時又說:“常以閶門云母箋截斗方吟小令,作蠅頭楷贈余索和,余取宣德紙以碎珠研粉砑石賦詩一半兒十首答之,喜甚。”著名文人袁宏道為此還專寫《時尚》一篇,介紹了蘇州一帶的著名工匠,以及他們所制作的器物如何風行全國的過程。
“蘇式”之所以能成為時尚和潮流的代名詞,這里面有著復雜的原因。“吳中素號繁華……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饈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產益多。至于人才輩出,尤為冠絕。”明人王鑄《寓圃雜記》這段記載點出了蘇州時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為天下所宗的最重要因素:一為“物產益多”,二為“人心益巧”。張瀚《松窗夢語》說:“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重吳器而吳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終日雕鏤,器不盈握而歲月積勞,取利倍蓰;工于織者,終歲纂組,華不盈寸,而錙銖之縑,勝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織也。”工藝美術較高的商業價值,進一步刺激了它的生產與進步,加強了蘇州引領海內風習的優勢地位。
形而上的蘇州創意(蘇意),轉而化作形而下的工藝、器物(蘇式),同時成為流行寰中,四方追慕模仿的生活時尚、文化樣板(蘇樣)。早在“日風”、“韓流”造就哈日族、哈韓族粉絲之前六七百年,蘇州就已經以自己強勢經濟+強勢文化的優勢地位在東亞文明圈獨占鰲頭。蘇州私家園林對日本枯山水庭院風格的形成,桃花塢年畫對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藝術的流行等等,均發揮了巨大作用。今天被視為日本民族服飾的“和服”,其實就是“吳服”的日本版。
四、“蘇作”與蘇州工匠文化
北宋時,朝廷開始在蘇州設立造作局。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有“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的名句。明清時期蘇州獨占鰲頭,經濟富庶,人文薈萃,已經成為全國區域經濟與文化中心。蘇州地區繁盛的藝術創作和工藝品制作,舉凡園林、繪畫、絲織、刺繡、玉雕、漆器、家具、文房雅玩、竹木牙角雕刻,甚至連書畫作偽的“蘇州片”,都代表了當時全國的最高水準,并被贊譽為“蘇州工”。清浙江巡撫納蘭常安在其所著《受宜堂宦游筆記》中說:“蘇州專諸巷,琢玉、雕金、鏤木、刻竹、髹漆、裝潢、針繡,咸類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顯微鏡燭之,方施刀錯。其曰水盤者,以沙水滌濾,泯其痕跡。凡金銀、琉璃,綺、銘、繡之屬,無不極其精巧。概之曰蘇作。”于是誕生了中國傳統制造業的一個專有名詞:蘇作,既是其書面字義蘇州制作的直接表達,也承載著極其精致、引領風騷的文化意涵。
本來傳統社會“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工分途,輕視工匠“賤業”。但蘇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卻是手工勞動中加入了文人的匠心,不知不覺提前嘗試了我們今天知識分子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社會理想。這也毫不奇怪,生產原來就是為了滿足消費需求。面對附庸風雅的富豪權貴和追逐時尚的社會人群,為了制造適銷對路的產品,手工工匠必須借力于文人雅士的蘇州創意,蘇意讓文化人與工匠走到一起,形成“蘇作”。比如蘇作家具和其他風格家具最明顯的區別在于用料、結構和造型。蘇作家具的造型是很有靈氣的,因為這些家具基本是文人在指導,就跟蘇州的園林一樣。據說蘇州有些私家園林就是唐伯虎、文徵明這些文人參與設計的。由于文人大多擅長山水,注重景致,因此在設計園林的時候強調移步異景,有一種明顯的畫意在其中。蘇州的家具也是如此,文人有自己的審美觀,家具做出來好不好看很重要,如果成品家具無法滿足他們的審美要求就會重新制作,這種追求完美,刻意制作的家具就可列入蘇作家具精品。當時進貢給天子的蘇作家具,重視家具結構,雕飾較少,有明顯的江南靈秀風格。endprint
家具之外,其他蘇作產品也是一樣。蘇州玉雕的風格以小巧、精致、細膩為主,在題材選取上深受蘇州深厚的歷史文化影響,這也成為蘇州玉雕區別于其他地區玉雕的主要標志。歷史上蘇州玉雕行業能工巧匠輩出,明代陸子岡就是玉雕大師中的巔峰人物,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在玉器上留下自己名字的琢玉人。據《蘇州府志》載:“陸子岡,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發。”陸子岡不僅技藝高深,且能書善畫,所有雕刻,從設計、繪畫、題款均出自自己之手。中國古代工匠藝人向來不為世人所重,稱其為“雕蟲小技”,而陸子岡以一介手藝人,在琢玉業超凡入圣,被士大夫所推崇敬重。陸子岡是中國玉雕史上唯一一位堅持留名于玉雕作品上的藝術家,也是第一位要求社會承認其藝術價值的藝術家。晚明作家張岱,對陸子岡推崇備至,在《陶庵夢憶》中,將陸子岡治玉與鮑天成治犀并列,稱為“吳中絕技”,“上下百年,保無敵手”,詡為“蓋技也而進乎道矣”。
近世蘇州更出現學者傳統與工匠傳統走向結合,傳統工匠升級轉型的現象。一批文化匠師同時具備學者與工匠兩種素質,“習藝求名,志在不朽”是其人生追求。明末蘇州人孫云球身處世亂、家道中落,于是放棄舉業,改習匠作,有了許多制造發明以及一部著作《鏡史》。另一位造鏡名匠薄玨,通過自學及刻苦鉆研掌握了豐富的人文、自然科學知識,創制望遠鏡,成為當時民間有名的制造匠師和工業科學家,著有《格物論》百卷。計成以造園這個一技之長在江南交游文人士大夫,著有作為文化匠師的經典之作《園冶》。及至晚清、民國,原本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蘇繡大師沈壽,也繼承了蘇州文士與工匠結合的傳統,對一生刺繡技術進行理論總結,口述了一部《雪宧繡譜》。香山幫后期重鎮姚承祖教授撰著《營造法原》并作為蘇州工業專科學校的講義。這一新傳統其實是歷史的發展揚棄了傳統社會的職業偏見,回到了文化發展與工匠精神成長相輔相成的歷史正軌,正如儒家經典《大學》中所言:“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這一句將“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儒家立身行道、修身養性的不朽追求完美地結合了起來。
蘇作不僅是蘇州一市的文化財富,也是簡稱“蘇”的整個江蘇省的精神遺產。眾多巧奪天工的工匠們,用精湛的技藝、敬業的精神、畢生的心血、別致的匠心,創造了蘇作驕人的業績。我們今天緬懷先輩賢達們的光輝業績,體悟其敬業樂業勤業精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并大力弘揚,可為創造現代新“蘇作”,把產品做精、技術做深、利潤做厚提供精神助力。
(作者系中共蘇州市委黨校教授)
責任編輯: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