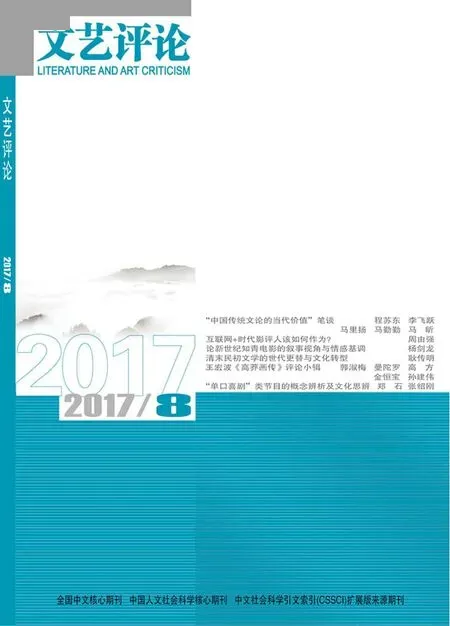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上官體”生成原因探析
○李 巍
“上官體”生成原因探析
○李 巍
“上官體”是唐代第一個以個人命名的風格稱號。上官儀在貞觀時期就已嶄露頭角,“綺錯婉媚”之風已基本形成,為何“上官體”在高宗朝才風靡一時,且對龍朔詩壇的進程及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因此研究“上官體”的生成原因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地位之貴顯是“上官體”形成的外因
上官儀在貞觀初年及第,開始入朝為官,但是一直官位平平。《舊唐書·上官儀傳》云:“貞觀初,楊仁恭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常預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1]
貞觀朝上官儀的官職并未有大的提升,由從六品下之弘文館直學士升為從六品上之秘書郎,后轉官起居郎也只是從六品上,升遷調動不大。弘文館學士深受禮待,“給以五品珍膳”[2],太宗還經常讓上官儀“視草”,甚至“依靠他潤飾自己粗糙的詩稿”[3],作為皇帝身邊的貼身文人,可謂十分榮耀,但由于官低位卑,“顯而未貴”,并無實權。
按照聞一多先生的說法,上官儀生于608年,[4]貞觀元年(627年)20歲,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已42歲,人生的黃金期都在貞觀時期度過,其詩才已經展露頭角,且現存詩作中作于貞觀時期的詩作占了很大的比例,“綺錯婉媚”之詩風基本形成。他雖然也很見重于太宗,但并未引起一場詩風新變,并未產生很大的影響,“上官體”的形成及在詩壇上產生影響是在高宗朝他的地位顯貴之后。關于此事文獻多有記載:
《舊唐書·上官儀傳》載:“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5]
《新唐書·上官儀傳》亦載:“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6]
《唐詩紀事》卷六亦云:“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人效之,曰‘上官體’。”[7]
由以上文獻記載可知,“上官體”之形成是在他“貴顯”之后,也即在龍朔至麟德元年(661年—664年)之時或之后。為何上官儀在高宗時地位陡然“貴顯”,2013年8月至9月,上官昭容墓志的出土為我們揭開了這個謎團。《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簡稱《墓志》)詳細記載了上官儀所歷官階的基本情況:“皇朝晉府參軍、東閣祭酒、弘文館學士、給事中、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贈中書令、秦州都督、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三千戶。”[8]除了“晉府參軍、東閣祭酒”外兩《唐書》本傳都有記載。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上官儀與高宗李治之間有著特殊的關系。高宗即位前被封為晉王,而上官儀曾擔任過“晉府參軍”,也就是說上官儀在太宗朝太子之爭中屬于李治一黨(按:太宗朝太子之爭主要有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和晉王李治),李治即位之后重用、擢拔上官儀是理所當然之事。
正由于唐高宗即位后上官儀地位之“貴顯”,人們紛紛效仿其體,方被稱為“上官體”。在他沒顯貴之前,雖然“綺錯婉媚”風格基本形成,只不過人們沒有或者很少仿效而已,可見,上官儀之“貴顯”是其詩體形成的外因。
二、“上之所好”是“上官體”形成的動因
高宗即位后仍然繼續沿襲太宗朝制定的各項政策,加之貞觀舊臣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等共同輔政,國家出現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局面,史稱“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9]。更為重要的是平定高麗,大破西突厥,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國家版圖為唐代最大。為了彰顯自己的文治武功,高宗攜武后同赴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祭天勒碑而還。
高宗在永徽年間有“貞觀遺風”,由于貞觀熏舊遺老的存在,他的政績顯得相對暗淡,隨著他們的離去,偶然因素繼承皇位的李治迫切需要文人對其治績進行謳歌頌揚,以彰顯其功績,進而向世人證明自己皇位的合理性。永徽六年高宗不顧大臣反對而極力廢王立武的事件,就是以此彰顯自己至高無上權威的體現。另外,從永徽六年之后一系列的樂舞制定中也可看出高宗的喜頌好諛心理。
《舊唐書·音樂志一》載:“顯慶元年正月,改《破陣樂舞》為《神功破陣樂》。”[10]
同卷又載:“(顯慶)六年三月,上欲伐遼,于屯營教舞,召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圉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阇、上官儀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11]
《破陣樂》前加“神功”二字,名異實同,以彰顯自己掃除寰宇、一定天下的卓越功勛。《一戎大定樂》又名《大定樂》,取名大定,象征著平定高麗后天下也會隨之大定。此樂是由太宗時期的《破陣樂》踵事增華而成,人數由太宗時期的120人增至140人,陣勢更加雄壯,聲勢更加浩大,顯而易見,高宗整改陣容是炫耀自己的赫赫聲威,彰顯自己的功德。
“永徽之治”使高宗產生喜頌好諛心理。正所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喜好是文學風尚的方向標,直接促成文學風氣的演變。因此上官儀探索詩藝、提高詩技有了動力,文人們學習與提高詩技也有了途徑與方法,以至一時間追攀摹仿,形成一種精研的風氣,一種創作的高峰。
三、類書之編纂是“上官體”形成的契機
“上官體”之形成與當時的文化建設事業相關。史載:“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12]這部書凡3年方修成,“(龍朔)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弘遣司玄太常伯竇德玄,進所撰《瑤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詔藏書府”[13]。
《瓊山玉彩》選擇的標準是采摘“古今文集”中的“英詞麗句”,編纂的體例是“以類相從”,纂集的目的不外乎創作時便于查找,以提高詩藝水平。除了《瓊山玉彩》外,上官儀還參與過《芳林要覽》等大型類書的編纂活動,涵詠其間,精研不輟,一定收獲頗多。上官儀在參撰的《芳林要覽》序中云:
且文之為體也,必當詞與質相經,文與聲相會。詞義不暢,則情旨不宣;文理不清,則聲節不亮。詩人因聲以緝韻,沿旨以制詞,理亂之所由,風雅之攸在。固不可以孤音絕唱,寫流遁于胸懷;棄徵捐商,混妍蚩于耳目。[14]
《芳鄰要覽序》中明確了上官儀的纂集標準,也是他倡導的作詩標準即要注重聲律,靠聲律來使詩作音韻協調。參與修撰的學士們在編纂期間和閑暇之余向上官儀請教作詩的技巧方法,上官儀一方面為學士們請教的促使,一方面也是長期編纂類書有所領悟,加之自己創作經驗,總結出一整套的作詩技巧和方法,在長期的互動交流中,上官儀的詩學理論逐漸被學士們所接受并運用到實際創作之中,“上官體”逐漸形成并產生很大的影響。
深受上官儀影響的一批人,或者說追捧上官儀的一批人,如元萬頃、郭正一等,他們近體詩律化程度很高,這一方面可以看出上官體的詩歌理論的可操作性及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上官儀詩歌理論與創作脫節的原因是由于詩歌多創作于貞觀時期,而偶對的總結是在高宗朝編輯大型類書的過程中在已有創作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以往的佳言名句提煉升華而成的。其詩作的律化程度沒有后學詩人高是可以理解或者說是正常的。
四、偶對之總結是“上官體”形成的關鍵
除了上述客觀原因外,“上官體”形成更重要的原因是上官儀總結了一整套簡明扼要、行之有效的作詩方法,使后學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較短的時間內可使詩藝有較大的提升。上官儀的詩學著作早已散佚,《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載有上官儀《筆花九梁》二卷,日本小西甚一認為此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所錄之《筆札華梁》二卷,且古字“花”與“華”同字,“九”與“扎”乃書寫訛誤,二書應為同一本書。王夢鷗先生在其《初唐詩學著述考》中也認為偽題魏文帝《詩格》,實即《筆札華梁》之刪節本。[15]王利器先生和盧盛江先生在整理《文鏡秘府論》中也認為《筆札華梁》是上官儀所著,此從其說。
雖然《筆札華梁》已經失傳,但其相關理論散見于《文鏡秘府論》所引各書中。上官儀的詩學理論表現在聲病理論上提出“八病”之說,表達詩歌情感意緒的“八階”“六志”之說,更重要的是提出對偶理論的“六對”“八對”之說。前兩者學人論述較為詳備,此就對偶理論展開論說。
南齊周颙發明了“四聲”,沈約等人據此提出講求四聲、避免八病、強調聲律的詩韻要求,以“竟陵八友”為代表的作家創作了大量“永明體”詩歌。他們的詩歌理論主要側重于韻律。齊梁之際,劉勰的《文心雕龍·麗辭》從對偶方面探索詩藝:“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16]不但總結出“言對”“事對”“反對”“正對”四種方式和其中的難易優劣,且強調“自然成對”。上官儀在前人的基礎上,對詩歌的屬對理論進行了拓展和延伸,提出“六對”“八對”之說。《詩人玉屑》卷七《屬對》引《詩苑類格》云: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是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17]
“六對”是從最基本的字詞之間的對偶來闡釋對屬理論,是初學者入學之門徑。前兩對“正名對”“同類對”是從詞義角度進行例說:“正名對”是指類似于“天地日月”之類的專有名詞,側重于單詞之對;“同類對”即同一屬類事物之對,較“正名對”多了修飾成分,因此由單字對擴而為詞對,且“花”“草”和“葉”“芽”又兩兩相對。中間三對主要從語音的角度例說:“連珠對”從字音的角度兩字相同連綿成對,“雙聲對”“疊韻對”分別從雙聲和疊韻的角度連詞成對。
最后“雙擬對”的例句“春樹秋池”,模棱兩可,似乎不知所云。《文鏡秘府論》有詩證為我們作了注解:“春樹春花,秋池秋日;琴命清琴,酒追佳酒;思君念君,千處萬處。”[18]可見“雙擬對”是一句之中同一個字間隔出現,八對中也有“雙擬對”,其例句云“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很顯然是一句之中隔字相對。“雙擬對”是從側重結構的角度闡釋為對的方式。
“八對”是將“六對”中的基本字詞對法運用到句聯之中,對“六對”理論進行演繹和延伸,有所提高和深化。“的名對”和“異類對”是從詞義的角度進行闡釋。“的名對”例句“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送”“迎”和“去”“來”都是反對,且是動作方向對,“酒”與“琴”是寬泛的同類對,“東南”與“西北”是方位名詞兩兩相對,是正名對。“的名對”是將“六對”中的“正名對”和“同類對”進行簡單的應用,是作詩最簡單的構句之法。“異類對”則在此基礎上有所變化和延伸。例句“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風”與“蟲”是不同屬性事物的名詞對,“織”與“穿”是不同的動作對,“池間”與“草上”是不同位置的方位名詞對,“樹”與“文”更是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之名詞對,上下句中都屬于不同類屬的詞義對,構成兩聯的異類特點,造成迥異之感。“雙聲對”和“疊韻對”是從語音的角度構句,與“六對”分類一致,但是內涵有所差別,“六對”是一句之對,此是一聯之對,也即將雙聲、疊韻在具體的詩句中進行運用。“連綿對”和“雙擬對”是從結構的角度構句,但有所差別,前兩對也可以說是反復對,一聯之中某個字反復出現,只不過出現的位置不同而已。“連綿對”是同一個詞連續出現,而“雙擬對”是同一個詞間隔出現。“回文對”和“隔句對”雖然也是從結構的角度構句,但是突破了兩句之間同位相對的簡單模式,上升到句式的變化,是從結構角度對句的變式,但又不是簡單的結構變化,還考慮到句間語義之銜接,意脈之相承,情感之升華,特別是“隔句對”的示例可謂是一首完整的五言絕句,不但有相同“復”字的隔句相對,還有“夜夜”“朝朝”不同聯綿詞的隔句相對。在意脈上一脈相承,將相思相盼相顧之情刻畫得淋漓盡致,也稱得上閨怨詩的上乘之作。
“六對”“八對”由詞到句,由聯到篇,由淺入深,是一個簡單易行的作詩范式,不但對初學者來說是入門之法,對于有一定基礎的人來說也是提高詩藝行之有效的法則。
另外,這“六對”“八對”并不是只考慮到語音、語義、結構等方面詞句的對應,而且在音律上也很講究,每種例對都力求做到平仄相應。“六對”中“花草葉芽”是平仄仄平;“蕭蕭赫赫”是平平仄仄;“黃槐綠柳”是平平仄仄;“彷徨放曠”是平平仄仄;唯獨“春樹秋池”是平仄平平,平仄不是特別嚴格,但是第二個字和第四個字做到了平仄相對。
“八對”中“的名對”是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除第三個字外嚴格相對;“異類對”是平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除一二字外嚴格對仗;“回文對”是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除第三字之外嚴格對仗;“隔句對”是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上官儀總結的聲律規律成為作詩者遵守的規范,為近體詩的定型鋪平了道路。
“六對”“八對”不但總結如何煉詞成句,而且在調聲上也講求平仄相應、清濁相對、緩急相異,使一句一聯至四句乃至全篇詞義相對、韻律和諧。上官儀總結的作詩范式簡要但不簡省,簡易但不簡略,簡便但不簡約,“六對”“八對”對屬范式的理論和范式的提出,對初學者來說不但直接而且有效,如登云之梯,不但平緩而且入云,成為作詩之不二法門,對推廣、普及、提高近體詩有很大裨益。
要之,與高宗的特殊關系使上官儀官位日顯,為“上官體”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條件;高宗武后的喜尚頌美心理,使上官體研究詩藝有了動力;《瑤山玉彩》等大型類書的編纂為上官儀精研詩藝提供了契機;上官儀“綺錯婉媚”詩風創作實踐和一整套作詩的理論和技巧的總結是“上官體”形成的關鍵。龍朔文士為了能使自己詩藝大增,勢必對上官儀的詩歌及其理論心琢手摹,希冀早日“成才”,加之上官儀的理論和技巧簡單易行,這些文人更是將之奉為圭臬,對其人大加尊奉,對其詩作奉為“標桿”,他的詩歌理論成為作詩之不二法門,廣為普及流傳。因此“上官體”風靡一時,他們學詩之目的并非修身養性,更非個人單純的愛好,而是為了巴結逢迎,為了討好獻媚,為了最終身顯位高,為了在政治的舞臺上有其光彩耀眼的時刻。
(作者單位:哈爾濱商業大學)
[1][5][10][11][12]劉昫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43頁,第2743頁,第1046頁,第1047頁,第2828-2829頁。
[2]吳兢編著《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頁。
[3][美]斯蒂芬·歐文著《初唐詩》[M],賈晉華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頁。
[4]聞一多《唐詩大系》[A],《聞一多全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
[6]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035頁。
[7]計有功撰《唐詩紀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73頁。
[8]李明、耿志剛《〈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箋釋》[J],《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
[9]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070-6071頁。
[13]王溥撰《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版,第657頁。
[14][18][日]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 1582 頁,第707頁。
[15]王夢鷗《有關唐代新體詩成立的兩本殘書》[A],《古典文學新探》[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43-244頁。
[16]劉勰著《文心雕龍注釋》[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頁。
[17]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M],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29頁。
黑龍江省哲學社會青年項目“中國唐前天人思維敘事模式研究”(編號:16ZWC02),哈爾濱商業大學青年創新人才支持項目(編號:2016QN01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