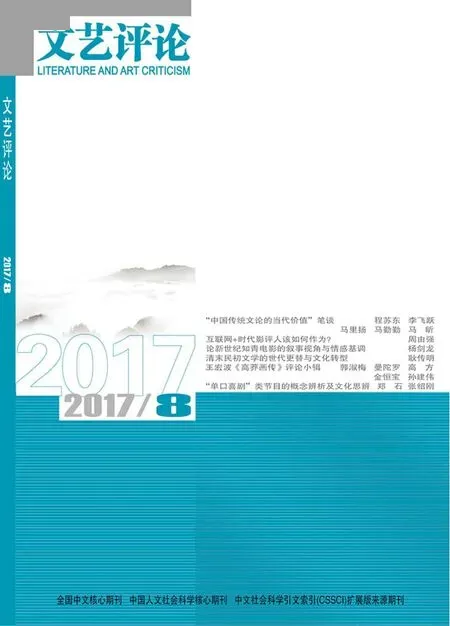大眾文化視野中的網絡文學IP
○周子鈺
大眾文化視野中的網絡文學IP
○周子鈺
近一兩年來,IP漸漸成為一種文化現象。IP,簡單說就是既能轉換為其他藝術形式又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品,比如飽受熱議的電視劇《歡樂頌》,就是由本身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同名網絡文學作品改編而成。但是,IP的概念又不僅限于此。常見的IP多是源自于網絡文學,比如《步步驚心》《鬼吹燈》《花千骨》《瑯琊榜》等等,它們都以網絡文學為藍本轉化為影視、游戲等,網絡文學成為IP的原產地,另外,中國的網絡文學IP目前的培育機智尚未成熟,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以網絡文學IP作為研究對象,探討網絡文學IP產生的原因、存在的問題和影響,希望可以對網絡文學IP重新認識。
一、什么是IP
提到IP,很多人都會不自覺地想到互聯網中的IP地址。可如今的IP,完全是一個新的含義。IP是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簡稱,直譯為知識產權。在中國大眾文化語境下,IP的含義更為豐富。騰訊副總裁程武于2011年提出“泛娛樂”這個詞,而“泛娛樂”的核心是IP運營,就是利用IP的轉化帶動游戲、動漫、文學、影視產業的發展。他認為:“IP實質就是經過市場驗證的用戶的情感承載,或者是說在創意產業里面,經過市場驗證的用戶需求。”[1]也就是說原生IP經過市場驗證后,以用戶的情感為轉化機制和消費對象,更容易得到用戶的認可。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認為IP與互聯網環境密切相關:“IP說是知識產權,其實也跟我們IP地址的那個IP有一定的關聯性。我們可以理解成具有互聯網IP價值的知識產權IP。這是雙IP的含義,它是互聯網因素創造的。”[2]IP的確和互聯網有關系,但是IP不一定都來源于互聯網,比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兒》大電影都是來自于同名綜藝節目IP而不是互聯網。IP的影響力和價值是靠用戶創造出來的。“‘用戶’成為了產業鏈條中大家最容易共識和判斷的價值硬通貨。”[3]他把IP看作一個承載著用戶群的通用貨幣,是和外界資本進行交易、投資和開發的標準和載體。用戶群越大,IP越有價值。
結合以上分析,IP可以理解為改編,但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改編。不同于原有的著作權、版權之意,IP由個人的私有權變成了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相互轉換的公有權,逐漸成為了一種文化概念。有人認為對于IP的定義可有可無,因為IP只是一場商業資本下的炒作。不可忽視的是,由一個IP的運作所產生的影響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文化的生產領域,還影響到文化的傳播和消費領域,IP的轉換與我們息息相關。而弄清楚IP的含義和特征更利于我們研究網絡文學IP,因此對于IP的定義顯得尤為必要。
我們可以認為,IP以商業為目的,以擴大傳播為手段。IP可以來自于音樂、電影、文學等多種藝術形式,但是它應該是有版權的原創作品,而且能夠再生產轉化為電影、電視劇、圖書出版、話劇、網游等不同媒介形式。IP轉化的條件是作品是通俗的、有影響力的,且有大量受眾基礎(或一定粉絲群體)而又能夠引起人們的廣泛參與和情感投入。IP轉化的核心是用戶:用戶群是IP的市場價值,用戶的情感共鳴是IP的情感價值。商業價值和情感訴求是IP的價值訴求。IP以通俗化的內容為主,具有濃厚的商業氣息,是大眾文化市場化、商業化下的產物,跨媒介的多元化生產又使它有產業化的特征。
二、網絡文學為什么成為IP
大多數IP來自于網絡文學。從電影《失戀33天》到《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何以笙簫默》《左耳》《匆匆那年》《盜墓筆記》,再到電視劇《甄嬛傳》《瑯琊榜》《花千骨》《歡樂頌》等,它們都是網絡文學IP轉化的成果。
(一)網絡文學的可轉化性
一般認為,中國的網絡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勢頭強勁,不僅僅停留在文學層面上,還輻射了政治、經濟、媒介傳播和文化,成為了一項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寫作運動。網絡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由抒發個人情感到有目的地為了賺錢寫作再到現在的IP式全媒體開發寫作,商業性越來越強。之所以網絡文學能成為IP,離不開網絡文學自身的特征。
從網絡文學的內容來看,網絡文學具有很強的通俗性和娛樂性,適應當下社會人們壓力大于放松、娛樂的需求,是人們逃避現實、尋求蘊藉的一種方式。網絡文學作品以直白的語言、通俗易懂的內容和具有吸引力的情節構筑成的“民間田地”,能夠契合當下大眾的心理需求和審美需求。網絡寫作約束較少,作者可以自由抒發自己的情感,通過自由想象來創造文學,像《花千骨》《鬼吹燈》《盜墓筆記》等奇幻通俗、架空歷史的網絡文學正體現了作者天馬行空、淋漓盡致的想象力。還有一些貼上青春、愛情、校園、職場等標簽的現實題材作品,如《致青春》《歡樂頌》等等,這些作品反映當下社會現實生活,注重表達個體細微的感受,折射出當下社會人們的心理狀態,以“一種平常生活中小喜小憂世界的展開,小感傷和小感慨的生活情感與小成功和小收獲的世俗利益之間的矛盾”[4],引起閱讀群體的共鳴。
從網絡文學的創作看,網絡文學具有商業性和互動性色彩。首先,當下網絡文學大部分采取收費閱讀的營銷模式,這使得作者除了抒發自我的真實情感外,也為了某種商業目的功利性寫作,只有符合讀者口味的作品才能吸引讀者,得到讀者的付費和點擊。其次,不同于個體化、封閉化的傳統寫作,網絡文學是一個群體性的、開放式的創作過程。一部網絡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會和讀者進行互動,作者邊寫邊發表,讀者則守在屏幕的另一端等待更新,并將自己的想法直接、及時地反饋給作者,作者會關注并根據讀者的意見來完成后面的創作。讀者可以通過打賞、催更、訂閱等方式和作者進行良性互動,使得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這種連載的方式,需要讀者和作者長時間共同將注意力傾注在作品上,讀者在閱讀和等待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投入自我的情感,一部作品因承載了讀者的感情而逐漸形成了忠誠度極高的用戶群體。網絡文學的這種以“讀者為中心”的模式一方面充分體現了大眾的審美趣味,更容易得到大眾情感的共鳴;另一方面也在收費閱讀的過程中刺激了粉絲群體的消費,成為一種當代文化消費形態。
網絡文學還體現了大眾性。在移動互聯網的環境下,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網民整合碎片時間通過移動設備進行閱讀。網絡文學內容的通俗化和閱讀方式的便捷,使得網絡文學有大規模的粉絲和讀者,這些讀者主要是“80后”“90”后的青年群體,他們被稱為“網一代”——伴隨互聯網成長的一代人。不同于上一代人在紙質圖書的陪伴下成長,他們在網絡的伴隨中成長。“隨著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和90后一代崛起,粉絲效應和娛樂功能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日益加深,網絡文學逐漸成為中國大眾文化的策源地。”[5]這些年輕群體數量巨大,是網絡文學的主要消費群體。而網絡文學既可以供人們娛樂消遣,又提供了一種日常化的感性愉悅,使大眾獲得情感上的滿足,這些特點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大眾進行閱讀和消費。網絡文學是典型的大眾文化產品。
通過以上對網絡文學特征的探討,發現網絡文學是一個市場化下極好的投資對象:通俗性的文本易于其他形式的轉換,商業化的特征能夠獲取利益,大眾化的特征可以覆蓋多數消費群體。從網絡文學的轉換性來看:首先,網絡文學和其他像話劇、動漫、影視等藝術形式都是大眾文化的產物,有內容的相似性和受眾的共通性:在內容上都要求情節性和新奇性,在受眾上以年輕人為主要群體,它們之間不是完全孤立的,有轉換的可能。其次,網絡文學能夠以豐富的故事資源彌補其他媒介形式的不足,類型的多樣覆蓋了大眾的各類選擇,迎合了市場的消費需求。此外,某一類型的網絡文學會吸引對這一類型感興趣的相對固定的粉絲群體,例如《致青春》和《匆匆那年》。這些都是其他藝術形式所不具備的。種種原因,決定了網絡文學能夠成為可以轉化的IP。
(二)IP商業投資與運營的需要
網絡文學IP的投資能夠實現投資風險最小化、政治風險最小化、經濟利益最大化。網絡文學是一個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對象,適宜改編成IP。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跨界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進行投資。影視、動漫等都是高風險、大投資的行業,而這些資本的掌握者多數并不一定諳熟這些行業的運行規律。對于投資者來說,原創劇本是充滿風險的,網絡文學可以幫助他們走捷徑,因為有影響力的網絡文學是有大量閱讀群體的,是經過網民和市場檢驗過的,粉絲量、訂閱量和點擊數是他們投資參照的標準。而且“網絡文學作為一種大眾通俗文學的意識形態保守性質——通俗文學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是撫慰人心的,是最安分守己的,它的任何突破冒犯都必須在一個安全值范圍內,超過這個安全值,就會讓同樣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可能大流行。這個安全值就是‘主流價值觀’。可以說,正是通俗文學相對于精英文學的‘保守性’,先天保證了它在政治上的安全性”[6]。網絡文學的政治風險最小化,投資風險最小化,投資者何樂而不為呢?
IP的運營使大眾成為了被利用與被滿足的對象。對大眾來說,網絡文學IP能夠生產出不同類型的產品,滿足大眾不同的需求,帶來不同的審美體驗。特別是對于沒進入網絡文學場的大眾,他們對走紅的網絡文學充滿期待,在文化速食的環境下,選擇較火的網絡文學改編作品使得自己不會落后于流行文化,網絡文學IP不僅正適合大眾的審美趣味,還能夠降低他們的選擇成本。在當下這個圖像化的時代,影視、動漫等訴諸視覺的快感式審美方式比起網絡文學的文字呈現更容易被他們接受,多種媒介的運營使大眾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一種形式。但IP強烈的商業性決定了它的生產和運營絕對不僅僅是滿足大眾的需求,而是以取悅大眾的方式從大眾中獲益。網絡文學由單一的在線閱讀付費到現在多種媒介的強勢參與,表面上看,跨媒介運營能夠讓受眾的選擇更加多元化,但實質上多種媒介共同運營的背后是利用大眾的消費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在文化的意義上真正實現媒介融合靠的不是技術,也不是資本,而是使用媒介的人。”[7]目前我國的消費呈現出低齡化的趨勢,年輕群體一直生活在消費文化環境中,他們也有能力消費。他們樂于接受IP,接受不同形式的文化產品。當然,他們中有一部分是忠實粉絲群體。約翰·費斯克認為“對大眾文化迷來說,社會效忠從屬關系和文化趣味之間的關聯是主動的和明顯的,他們的辨識行為所遵從的是社會相關性,而非審美特質的標準”[8]。這些忠誠度極高的粉絲在IP的運作中成為了多種媒介的多重消費對象。IP成為了商業利益和多種媒介的合謀。此外,在IP的開發中,依賴于原生IP的成功以及多種媒介形式的宣傳和開發,逐漸將網絡文學由某一群體的追捧擴大到整個大眾,比如《花千骨》最初的網絡文學小說只在網絡上被讀者接受,后來改編成電視劇,受眾群體更大。多種媒介的炮轟以“增加用戶粘性,創造‘強關系’,架構生態鏈”[9]的形式,使不少圍觀群體逐漸變成用戶,再變成能夠消費的粉絲。而這正是商業資本所看重的,越多的人為一個IP消費,它的商業利益才會越大。
三、網絡文學IP存在的問題以及影響
當下我國網絡文學IP的培育機制不太成熟,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網絡文學IP的轉化是有條件的。作品不僅要有影響力,更為關鍵的是這個網絡文學作品是否適宜成為IP。隨著IP熱潮的來臨,一些現象級IP、超級IP的出現,使得整個市場極為浮躁,越來越多的資本盲目地購買IP,哪個網絡文學作品點擊率高、哪個排名靠前就投資哪個,投資者過于注重建立在作品瀏覽量之上的人氣、影響力,純粹是為了打造IP而打造,不看作品的內容囤積了大量IP。但是點擊率高不代表就是好的原生IP,只看數據不看內容會導致投資者對文本的判斷不準確。IP的適不適合還要來自于文本,要看這個作品的故事性。文本中很多好的東西可能不適合轉化或經過轉化被丟掉了:《花千骨》在敘事上不如《鬼吹燈》,但是《花千骨》卻比《鬼吹燈》更適合轉化,也轉化得更為成功。目前市場上買網絡文學版權的有很多,但真正做出來的其實并不多;買回的一些IP是無法用或勉強用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其次,網絡文學的文本還要能夠轉化成其他藝術形式。這既需要制作團隊的能力水平,還需要不同藝術形式的創作隊伍之間的磨合,如果缺少對話和交流,則不利于有效轉化。當下的不少情況是網絡文學的原著作者處于弱勢地位,賣出版權后作品的話語權在制作公司,原著作者毫無話語權。而制作公司也多是憑以往的經驗完成作品,缺少像英國、美國將暢銷書改編為影視時那樣對劇本和創作進行嚴密的分析:比如什么時間設置第一個高潮,人物應該怎么轉化等。此外,IP的轉化,也應結合不同媒介自身的特點進行再創造,而不應該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式的復制。
再次,市場上本來能夠適合轉化成的網絡文學IP本就不多,目前已經購買和轉化完成的網絡文學多是前幾年的作品。網絡文學IP需求量大,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好的作品都被簽訂了,市場上出現了網絡文學優質IP的荒漠化和斷裂現象。投資公司等不及,網絡寫手只好在商業利益驅動下不停地寫,導致網絡文學質量的下降。
四、結語
網絡文學IP的發展給網絡文學帶來新的發展方向。只有網絡文學作品適合轉化,有用戶的情感價值和一定的受眾基礎才能成為IP;只有既保留了原生作品原汁原味,又能對觀眾產生較大影響,如《瑯琊榜》《花千骨》《歡樂頌》等,才能說是轉化成功的IP;只有被有效轉化的IP,才能獲取利益最大化。因此,網絡IP要能出精品,才能獲得利潤。網絡文學這棵小樹在近二十年的成長過程中還沒有長成參天大樹,需要呵護,網絡文學IP不能因為商業利益過度地破壞和開發網絡文學。網絡IP要有效轉化成適宜大眾欣賞、滿足大眾需要的作品,才能讓IP更好地成長。對于其他藝術形式來說,不能僅僅從網絡文學汲取營養,而應該大膽創新、支持原創,這樣才能在新的互聯網背景下提升競爭力,只有各種藝術形式良性互動,才能推動文化產業大繁榮。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藝學教研室)
[1]程武、李清《IP熱潮的背后與泛娛樂思維下的未來電影》[J],《當代電影》,2015年第 9期,第 18頁。
[2][3]尹鴻、王旭東、陳洪偉、馮斯亮《IP轉換興起的原因、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J],《當代電影》,2015年第9期,第24頁,第24頁。
[4]張頤武《網絡文學與影視——一個新的文化構成》[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第6頁。
[5]梁曉飛《網絡文學漸成中國大眾文化策源地》[OB/OL],新華網 http://www.s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5-01/03/c_1113855413.htm.
[6][7]邵燕君《“媒介融合”時代的“孵化器”——多重博弈下中國網絡文學的新位置和新使命》[J],《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6期,第190頁,第185頁。
[8][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73頁-174頁。
[9]曾祥敏、倪樂融《承上啟下氤氳突破——2015年國產電視劇熱點述評》[J],《當代電視》,2016年第1期,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