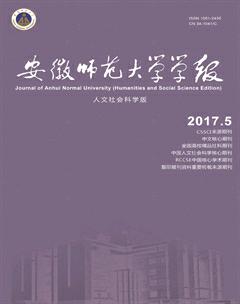清代徽州文會運作及其科舉功能
張小坡
摘 要:清代徽州文會是專為讀書人而設的文人組織,數量眾多。就其類型而言,以血緣性的宗族文會為主體,地緣性的社區文會、合都文會也為數可觀。清代徽州文會的資產主要分為田和錢兩種形態,其來源有集資入股、樂輸捐助及付喜慶銀等其他出銀形式。為保證會產增殖,文會購置并出租田地屋店,還以“打會”形式將銀錢借給會員收取利息。圍繞會產的管理與使用,文會制定了嚴格的措施并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調整。清代徽州文會的功能集中在科舉方面,日常活動以會課為主,訓練士人參加科舉考試的技巧,幫助他們熟悉科舉考試的環節。文會資產則主要用來獎助科考,為士人提供盤費。文會的正常運轉有力地推動了清代徽州科舉的興盛。
中圖分類號:K24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2435(2017)05054308
關鍵詞:徽州;文會;科舉;宗族
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 the Huizhou literary society was a literary organization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numerous. As far as its type was concerned, it would b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among whom the kinship clan would be the main body, and the geographical Community Culture Association would be the sam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ssets of the Huizhou Cultural Association we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types:farmland and money. The sources of the assets were as follows:raising funds to buy shares, making donations and paying for celebrations. In order to appreciate its assets, the Huizhou literary society purchased and rented out housing and land, as well as lent the money to members and get interests in the form of "play". Around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the assets, the Huizhou literary society developed strict measures and constant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The functions of the Huizhou literary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hich started daily activities in class, trained scholar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kills, helped them be familiar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asset was mainly used to provide grants for their expeditions.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Huizhou literary society strongly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H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文會在明清徽州各地廣泛存在,如黟縣鄉村“多有斯文之會,但不盡黨庠之人”[1]卷3,27。文會一般擁有固定的場所,與宗祠、社屋、水口共同構成徽州鄉村社會的文化景觀,所謂“鄉有祠,有社,有文會,有水口”是也。①
文會具備明清徽州會社運作的一般特點,其“置會有地,進會有禮,立會有條,司會有人,交會有際” [2]考卷5,93。不但類型多樣、功能多重,并且發展成為官方系統之外的一種鄉村社會組織。
學術界已對明清徽州文會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討。主要成果有:葛慶華《徽州文會初探》,《江淮論壇》1997年第4期;施興和、李琳琦《明清徽州的書屋、文會及其教育功能》,《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年第4期;史五一、杜敏《徽州文會個案研究——以民〈呈坎潈川文會簿〉為中心》,《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等。
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以《張氏文昌會根源》《萃英社文會條目》《鼎元文會同志錄》等徽州文書為主,輔之以地方志、族譜等資料,探討清代徽州文會的實際運作過程,考察文會為提高士人的科考中舉比率而采取的諸種措施。
一、明清徽州文會的發展概況
中國文人自古講究同類相求,“夫會文于友,求同也。同類相求,同明相照,同業相勵,同美相成,胥會焉是賴”[3]卷11,682。元泰定年間,歙縣沙溪儒士凌慶四在村南的八畝坵創辦北園文會,與槐塘唐仲實、雙橋鄭玉兩位先生時相往還,講論闡明程朱之學。[4]卷1,611這是目前所見徽州文會最早的文字記錄。明代中期,徽州文會有了較大發展,如歙縣,“士則郡城有斗山會,自郡而西巖鎮有南山會,其余巨族間亦有之……大都進德修業,由來尚矣,迄今百十余年。人文郁起,為海內之望,郁郁乎盛哉” [2]考卷5,93-94!在科舉功名的召喚下,徽州文人結合起來,揣摩時文,研究八股,如汪道昆的兩位胞弟為了提高科舉制義,聯合七君子結成同盟,創建豐干社,“諸君子孳孳本業,徒以其余力稱詩” [5] 卷72,1481。明末徽州文會盛況空前,“當時承東林、復社之流,意凡有井水處,皆有文社矣”[6]卷6,183。明末文人社團門戶森嚴,互相傾軋,引起清初文人的強烈不滿,清政府也認為“士習不端,結社訂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為可惡,著嚴行禁止”《清實錄·世祖實錄》卷132,順治十七年正月,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16頁。。 嚴厲打擊士大夫的結社活動。清代的文人結社不但褪去了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且類型也縮減很多,只有應付科舉考試的文會保持著長盛不衰的勢頭。endprint
清代徽州文會一部分是從明代延續而來,如歙縣潈川文會系呈坎前羅21世祖羅瓊宗于嘉靖年間創辦,其子侄輩相繼入會,“三閱寒暑,十余人者悉升于郡邑學,乃景弦遂領賓薦,諸士益奮勵,若聞野、若靜泉相繼登第取青紫,迨今升太學者若干人,充弟子員者若干人”民國《歙縣呈坎潈川文會簿》,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資料室復印件。 。明清鼎革后,羅氏族人不斷修訂章程,使得該文會一直持續到民國。相當一部分文會是入清之后才開始出現的,如濟陽江氏文會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創辦,“文會之設,所以崇獎冠裳,合一姓之俊髦而澤以詩書者也”。江氏宗族此前在宗祠東側設立禮生會屋,以備作文會,因該屋已由租賃者裝修,即由60位文會會員湊銀22兩交與租房者,令其搬出,文會將房屋上下四面進行整修,又在旁邊修建小閣,內奉文昌帝,每年仲春月初三進行祭祀,并立章程以垂永久。乾隆《重修新安東關濟陽江氏宗譜》卷14《事宜·濟陽江氏文會記》,乾隆五十四年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又如歙縣飛霞文會館在城南七里,為張氏厚塢、七里、鮑家莊三個宗支所建,在張氏宗祠之側。[6]卷27,956
清代徽州文會主要分為血緣性文會和地緣性文會。血緣性文會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面向族內子弟而創建的宗族文會,這是徽州文會最基本的形態,數量也最多。如婺源縣龍灣詹氏毓英文會、桃溪潘氏起元文會,黟縣南屏葉氏文會、范氏雉山文會,休寧縣率東程氏率溪書院文會、古林黃氏培元文會,績溪縣荊州胡氏梯云文會、梁安高氏學愚文會,祁門縣善和程氏文昌會,歙縣江村江氏聚星文社、大阜潘氏阜山文會等。
徽州地緣性文會又可細分為社區文會、合都文會兩類。社區文會是指聯合數姓或特定村落設立的文會。如黟縣萃英文社由靄門、集益兩文會合并而成,嘉慶年間,靄門12姓捐資置田,在龍家磨設靄門文會。光緒元年(1875),黟縣城外的15姓捐資設立集益文會,擬待文會款產充足再建家塾,以課子弟。地方士紳葉曉春、吳德瀚等人認為靄門、集益兩文會同處一鄉,便集合27姓,共同決定將靄門文會的屋宇田地、各種器用和集益文會的捐款合并為一,組建成一個新文會“萃英文社”,并訂立議約條規保證文會正常運作。[1]卷14,417績溪縣和尚塢四姓文會是由余、許、方、汪四姓創建的。和尚塢原有古剎,四姓負責安燈,寺內塑文昌帝君像,每年四月初八日聚集士子祭祀文昌帝君。禮畢,飲胙、插花傳唱以為令。置有文會田產,取租息作為生童膏火、燈油、會課、花紅、獎賞。咸同兵燹后,古剎傾頹,無僧人住持,文會田產散失無以稽考。光緒《績溪縣南關許余氏惇敘堂宗譜》卷10《雜說·和尚塢四姓文會》,光緒十五年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飛布山坐落在歙縣縣城東北,素產煤,山石亦可煅燒成石灰,“奸民虎踞以為利藪,日剝月削,陷若井坑”,埋葬在山中的數萬座墳冢受到極大影響,引起當地民眾的強烈不安。為切實保護山脈,有人提議在飛布山后幽靜空曠之處建立文會館,選八鄉俊彥之士肄業其中,并置田作為會課膏火,春秋佳日,鄉里賢人先達群集于此,“評其文藝之工拙,為之督課而講學焉”,此舉被視為既能培養人才,又能保護山脈的一舉兩得之良法,瑞金文會很快便設立起來。[3]卷11,682
合都文會是以一都為范圍設置的文會。都圖里甲是明清縣級政區的基本組成部分,所轄范圍相對固定。與宗族文會相比,徽州合都文會的數量較少,黟縣知縣李登龍在為聚奎文會所作的序文中提及,“黟邑各都之設有文會,一以敦氣誼,一以廣觀摩,誠美舉也。” [7]卷15,511聚奎文會為五都文會,五都在黟縣之南,“周環約二十里許”。祁門二十二都鼎元文會為合都文會的典型。道光二十年(1820),祁門新任縣令方殿謨為振興科考,令全縣520甲以5年為期,每甲必須推出1人參加童子試。辟處祁門之西的二十二都“地周二十余里”,轄有16個自然性村落,居民共有八姓,因都內山多田少,地瘠民貧,習舉子業者甚少,于是經官府示諭,紳耆主導,鼎元文會得以創設,文會公所立于新安洲上,都內各村捐輸田產百余畝,文會資產初具規模。道光《鼎元文會同志錄·鼎元文會記》,道光二十八年刻本,道光二十八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清代徽州文會活動的場所被稱為文會所或文會館,設于宗祠或建于書院,或附于文昌閣,有的亦為獨立建筑,坐落在村中水口或風景秀麗處,其建筑規制一般為亭、臺、樓、閣,與周圍景致相得益彰,形成村落文化景觀。黟縣碧山汪氏文會初興時,在宗祠開展活動,該祠面對巽靄峰,右為石盂山,左為章水,地勢較低。汪氏宗族認為宗祠的坐落有礙風水,會文于宗祠也多有不便之處,便合族捐資3千金,于章水西岸建造一座塔,名為云門書屋,登塔而望,村居鱗比,煙火相次。[8]卷15,509歙縣雄村竹山書院筑有文社,臺榭幽窈,花木靚秀,“繚以短垣,面新安江,峰壑如屏,帆纜上下,擅勝在遠,山澤之姿,可以坐嘯。”景色十分優美。[6]卷10,339婺源縣明經胡氏在村內水口筑造文昌閣,為文會活動之所,時人曾撰文描述文昌閣周圍的景致:“水口兩山對峙,澗水環匝,村境經其下。由前山麓筑堤數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以去堤起處,出入孔道兩旁為石板,橋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墻垣四周,方廣二丈。亭上有閣,高倍之,鐵馬鉆錚,圍山碧綠,榜其楣曰‘文昌閣,村之人蓋歲以祀文昌帝君云。”道光《仁里明經胡氏支譜》卷首《文昌閣記》,道光四年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
二、清代徽州文會的資產及其管理
文會作為一種文人組織,每年都要舉行會課、祭祀活動,或者撥付經費資助士人參加科舉考試,這就需要文會擁有一定規模的資產。與徽州其他會社組織相似,文會的資產結構分為田和錢兩種形態,其來源則有集資入股、樂輸捐助及付喜慶銀等其他出銀形式。為保證會產增殖,文會多措齊舉,購置并出租田地屋店以收取租息,還以“打會”形式將銀錢借給會員收取利息。圍繞會產的管理與使用,文會采取了嚴格的措施并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調整,保證了會產規模日益擴大,從而維持文會正常運作。
(一)會產來源endprint
文會設立之初,籌措經費的辦法主要分為勸捐和集資兩種。捐輸是指以個人或群體的名義向文會自愿捐贈資金、田地或其他資產。績溪城西周氏“我族之有文會,我高祖士暹公暨二十三公捐貲置產而起也”光緒《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20《文會》,光緒三十一年刊本,安徽省圖書館藏。。歙縣濟陽江氏宗族興辦文會時,族人江志學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捐元絲銀九五平100兩,買上路店屋1間,每年租錢6000文,龍舌頭店屋1間,每年租錢4000文。租錢由文會司事收取,每年二月初三備辦祭儀,祭祀文帝,頒發祭胙。乾隆《重修新安東關濟陽江氏宗譜》卷14《事宜·文會胙產》。祁門鼎元文會強調自愿捐產,平等入會的原則,提出都內各村只有捐輸田產者才有資格入會,明確規定:“文會為培養本都人材而設,八姓捐租之家日后不得將原輸之租借稱與都外之宗族,相共希圖入會。”道光《鼎元文會同志錄·公議規則》。同時要求,已經在文會課簿上登記捐輸者,聽其酌量加輸。如果各村有富裕之家屢經勸諭而不肯捐輸,日后要每人捐良田5畝以上才可以加入。《鼎元文會同志錄》收錄了78份捐產入會的輸契,所捐產業均為田產,共1054秤3斤11兩,捐輸的宗族主要有洪氏、王氏、陳氏等8家,其中王氏和洪氏二姓捐輸的最多,王氏捐出561秤4斤1兩,洪氏捐出207秤2斤。鼎元文會為表示獎勵,規定凡捐輸之家,不論所捐多寡,均可登錄會簿,并獲領會簿1冊。
部分文會采用集資入股的辦法籌措經費。會眾參股入會,視各會情況交納銀錢或以田地、會租等形式入股。雍正二年(1724),祁門縣二十一都磻溪陳際交、陳懷等人因族內子弟赴縣應歲試無一人獲售,決定建立文會,每月做課,培養讀書生童。在陳際交的倡導下,共有12人加入文會,每人出餅銀21錢,資金交齊后,采用徽州錢會的運營方式,編派首人2人管值一年,輪派生放,周年加3分利息。編派首人的原則為第七會搭一會,第八會搭二會,第九會搭三會,第十會搭四會,第十一會搭五會,末會搭六會。值年首人領到會銀后放典生息,于次年五月十六將本利布心餅銀一并交付下首首人,不得違期,如違期一日,每兩罰銀一鑄。[9]462徽州張氏文昌會在會規中明確了會資需每股出租谷1秤,由值年首人收取用于祭祀,租谷按時價折銀后亦由值年首人收貯,除去祭祀開支,剩余銀兩存典生息。同時規定日后如有人退股,只準退還其起初入股的租谷5秤,并不得再入會分胙。《張氏文昌會根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婺源鳳山查氏正誼文會經歷了由出資入股改作勸捐集資的過程。文會創始之初,每人每年出錢200文入會生殖,以3年為1周期,編鬮推定值年總理5人,領錢收租,辦理會事。會錢按每年2分生息增殖,次年正月初七在孝義祠公同算賬,交付下首,不得過期,亦不許押包轉領。光緒二年(1876),正誼文會的集資方式發生變動,入股改作勸捐,起因在于文會開辦之初,采取入股的辦法能有效集資,但時間長久,文會若再局限于入股參會的會友之間,就勢必產生門戶之見,其他人很難再加入進來,文會也就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因而需要破除股數之名,只要自愿捐輸皆可入會,以擴大會員范圍,做到“前人集而成之,后人合而守之”。正誼文會向村內已取得功名且入會之人勸捐,希望有余資生殖以期補助。經過勸捐,文會共收到:“一、原始五十九戶捐,皮租、骨租一百二十三秤二十一斤。一、丙子二月本族紳衿共捐本洋三百九十元整。一、丁丑至辛卯十五年內共收各友入會折席洋二百三十二元整。”
光緒《婺源查氏族譜》卷尾之九《序·正誼文會序·捐數附述》,光緒十八年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
文會集資的第二種形式是入會出銀或考取功名者向文會繳納回報錢。入會出銀一部分是在入會之時交納,如績溪城西周氏文會制定了入會出銀三則:“有余者,出銀三兩,兩次二兩,又次一兩,違者不許入會。”光緒《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20《文會》。入會出銀的另一種形式是會友遇到過壽、婚娶、生子、入學等喜慶之事,文會支錢慶賀,主事之家要復禮以示回報。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率溪書院文會的收支為例,可見復禮錢在文會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該年文會共收入銀212192兩,其中收湘芷付出本利銀107855兩、云源付出本利銀464兩、叔倫付出本利銀35667兩,三項共計189922兩, 其余的2227兩皆為會員復禮銀收入。而當年文會共支錢銀3035兩,其中賀會友入監、娶媳、旬禮等項支出123兩。《率溪書院文會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會員考取功名后向文會繳納一定數額的回報錢亦是徽州文會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績溪梁安高氏制定了文會捐例:“一、生員補廩捐銀二兩。一、出五貢者捐銀四兩。一、中式舉人捐銀二十四兩。一、中式進士捐銀四十八兩。”光緒《績溪梁安高氏宗譜》卷11《文會》,光緒三年刊本,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資料室復印件。徽州張氏文昌會的喜銀條款比較詳細:“一、議入泮者出喜銀三錢。一、議補廩者出喜銀二錢,歲科考一等五名前者出喜銀一錢。一、議鄉試中式者出喜銀三兩,會試中式者加倍。一、議出仕者出俸金三兩。”并規定每年二月十五上下首交賬日,喜銀交付首人入匣存貯生息,以應付會友支用及赴考盤費。《張氏文昌會根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表1即以康熙雍正年間張氏文昌會的收支賬目為例,對徽州文會的資產規模進行簡單說明。
我們結合上表所示和其他徽州文會收入可以看出,張氏文昌會的資產規模較弱,每年結余資金有限,甚至還出現入不敷出的狀況。該會每年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上年結余資金、會眾交納的舉辦祭祀的谷價折銀、喜慶銀以及從文會借款到期付還的本利,而主要支出項目為首人備辦祭祀文昌帝君各類物件及演八仙慶壽戲劇的費用。
(二)會產管理
會產是文會存在的經濟基礎,會產管理是否得法,直接關系到文會的興衰存廢,所謂“第所會,銀既有其本,而生息貴得其人,輪管須得其法”[10]宋元明編.卷8, 228。文會大都設有會首,定有會規,置有會簿。
文會正常運作的基本前提是制定規條。時人認為:“會文之規,必不可廢。會文之規不廢,則正道昌明,人文鼎盛,斯不蹈領餅散胙之陋習,此會規之貴籌劃于始基也。”光緒《婺源查氏族譜》卷尾之九《序·正誼文會序》。各地文會的規約對會首的推舉及其職責,會員的權利及其義務,會產的管理和經營以及會務活動等方面皆有嚴格的規定,并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修改。婺源縣鳳山查氏正誼文會起初制定的規約共有九條,其后裁并為六條,規約未盡完善之處,則由后人“隨時斟酌而損益之”。光緒二年(1876),文會司事主持制定了文會新章九則,在第一條就提出“因舊章以慎終始也”,意即不能完全廢除舊章,應尊重舊約的合理之處。光緒《婺源查氏族譜》卷尾之九《序·正誼文會序》。endprint
文會的管理者一般稱為司事、司年、司會等,具體負責會產的租佃收息、錢財生放、錢糧繳納、備辦祭儀、頒胙散福等日常事務。因“會內司事之人,公事之興廢系焉,興莫興于司事之經理初心,廢則廢于司事之據為世業,故司事之人責承最重”道光《鼎元文會同志錄·公議規則》。。清代徽州文會高度重視司事人選的任用,并嚴格約束司事的職權,獎懲有度,賞罰分明。歙縣呈坎潈川文會對管會人員的資格做出限定,年過六十及仕宦游學無子弟在家者不在管會之列。民國《歙縣呈坎潈川文會簿》。歙縣雄村竹山書院文會設司賬綜理出入,“舉殷實至誠者任之,毋推諉規避”,每年設司年2人,“以齒為序,輪次而下,慎勿憚勞”《文會條約》,該碑刻現鑲于歙縣雄村竹山書院內,由歙縣黨史地志辦主任邵寶振制成碑拓并承蒙惠賜,謹致謝忱。。績溪城西周氏文會要求每年舉司值4人收租存貯公所,辦祭輸糧,公同支用,事竣算帳,如有私自支用,公同議罰,入眾公用。會內存貯銀兩如借出生息增殖,必須4人同見,不得私自專行,更不得侵漁吞噬。如違,革出會外,永不許入,同時追討侵吞之數。光緒《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20《文會》。
祁門鼎元文會立會局從事日常管理工作。會局設司事4名,定期推舉產生,“必公舉讀書老成者任之”,但司事有任期限制,不得“長管不辭”,應于遞年糶谷算賬后自行卸任,公舉他人接管,以免局外人士議論,如確系辦事深得人心,可公同再舉薦擔任司事。如司事推托,即公舉他人為接管之人,并務必同上班司事查明其經手出入的賬目,將契匣、簿書、銀錢字據等檢點交接清楚,免生事端。司事的主要職責是負責秋收租谷,總理并監管秋收倉谷的數目封鎖蓋印,次年照時價出糶,由經手之人收貯銀錢,不得私自使用。每年秋收,從各村選出生童擔任司年,若家中無生童或無暇理事,應由本家紳士與董事之人承值。秋收時,從4名司事中推舉1人專門在局照應,支給食用谷2石,辛力谷2石,其辛力谷由司事攤分各村輪管。另舉2人監督收租,將租谷晾曬干凈收入倉內,每人給食用谷1石,辛力谷1石。再給谷12石請人收曬、搬拕、幫貼、炊煮。鼎元文會的錢糧分寄在3約,立鼎元文會的總戶名,每年上限以四月初十為限,下限以十月初十為限,會內司事務要如限經手解納錢糧,倘若超過期限,致使官差追催,其費用由經手者自行支付。各戶因私事照糧派費者,會內不得幫貼。3約有應辦官事及合邑公事,當在各約之會與各村祀會開銷,不得牽涉鼎元文會。道光《鼎元文會同志錄·公議規則》。
可以看出,司事在管理支配會產的同時,也要負責文會資產的保值增值。除了制度的約束外,司事個人的操守及鄉村社會輿論也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歙縣巖鎮南山文會,每年以5人司其事,會內如有余資則5人分領,至次年三月初十即將其資交出,不征利亦不得短缺。康熙年間,司事汪嘉襲循例分領五金,交與其子經商,囑咐次年三月初十之前要將本錢寄歸回里。不料遲至三月初九,信件仍未送達。汪嘉襲躊躇四顧,不知如何應對,為免受他人誚嚷,最后投澄潭而死,但次日一早,信件就送到了,令人扼腕嘆息。[11]貞集,藝文下,255
三、徽州文會的科舉功能
徽州科舉人才的興盛,與該地區重教興文的傳統、多層完善的教育體系以及徽商雄厚的經濟支持密不可分,而徽州文會所發揮的作用也同樣不容忽視。作為文人的團體組織,清代徽州文會的功能集中在科舉方面,其日常活動以會課為主,旨在訓練讀書士子參加科舉考試的技巧,幫助他們熟悉科舉考試的環節,以提高應試能力。為激發士子的應試熱情,減輕貧困儒生赴考的經濟壓力,徽州文會的會產支出主要用來獎助科考,提供盤費。清代徽州文會體現出“考課有法,膏火有資,獎勵有制”道光《鼎元文會同志錄·鼎元文會記》。的運行邏輯。
雍正八年(1730),婺源雙杉王氏文會制定了詳細的會課條例。王氏文會每年舉行4次會課,以四季為期,分別為正月初八、五月初七、八月十七、十二月十七。會課事務由文生辦理,照科分輪值。四季會卷,掌院向祠首領價,預為做定。臨近會期,輪值者向掌院領用,剩余會卷仍交給掌院。會課前數日,輪值者在文昌院的院墻上張貼通知,另具貼敦請名儒出試題并密封起來。會課日的黎明時分,舉監、貢監、生監和生童整理好衣冠,自帶筆、硯、紙、墨、油燭到文昌院赴試。人到齊后,封鎖院門,當眾拆開試題,生監以上編號坐中堂,童生編號坐東西兩廊。試卷的卷尾字號事先編定,領卷時填寫本人名字于浮票之上,交卷時各人揭去浮票,與所發試卷進行比對,依次書于簿冊,以防頂替作弊。參加會課的文生照題分做二藝,當天完卷。其后要求,凡一書、一經、一詩有不完成者即不給燈油。會課飯食照清明墓祭席案,依名分給定,不設酒,每人計錢3分。會課次日進行閱卷,分出等第以示勸懲,有以名次在后冒犯閱卷者,日后不許入會。對于命題、閱卷,每五卷給筆資一錢,照數遞加。輪值文生不參加該季會課,但仍給燈油。輪值者負責準備會課當日的飯食及器物等,要求在未封院門前備辦齊集,封門后不得擅自出入,違者罰輪值者本季燈油。所需費用由輪值者向祠首領取,支用賬目逐項登記在冊,賬冊當即交給掌院以便核對。輪值者還要在會課期間巡查考生有無插卷、夾帶、代作等作弊行為,一經發現,罰作弊者本季燈油。如果考生拒絕接受檢查,但其后被查出作弊,即當場鳴眾,罰本年燈油。輪值者如失察,罰本季燈油,故意失察,則罰本年燈油。左右同坐者知情不舉同罰。燈油折成錢發給各生,每年給文舉人16兩,文生8錢,武生6錢,文童4錢,武童3錢,分在四次會課日發給,文武兼考者給文不給武。此外,凡赴院會課者無論文武生童,另給飯食銀16錢。光緒《婺源雙杉王氏族譜》卷17《文會總覽》,光緒十九年木活字本,張海瀛、武新立、林萬清主編:《中華族譜集成》(王氏譜卷)第18冊,巴蜀書社1995年版。
時人曾對清代徽州文會提出批評,認為里中文會大多有文會之名,而無文會之實,主要因為部分文會僅是賽神、演戲、分餅胙、張筵席,而于文章一事無聞焉。光緒《婺源查氏族譜》卷尾之九《序·正誼文會序》。婺源查氏正誼文會要求“定會期以會斯文”,遵照舊規,每年正月初六會春課,八月十六會秋課。由司年提前3天出帖通知,屆期會內備辦茶點,齊集孝義祠,按名給卷,自辰時至酉時,一文一詩,不挾帶不給燭。文成篇詩滿韻,交卷時給丁餅一對。有文無詩,有詩無文,半篇中股或詞賦詩歌,皆可與會,但僅留茶點,而不給餅。光緒《婺源查氏族譜》卷尾之九《序·正誼文會序》。績溪梁安高氏學愚文會規定:“一、孤子讀書已作文者每年貼筆墨錢一兩;一、文會每年會課或由本族前輩出題閱卷或請他姓飽學,由首事預備師生茶飯酒席,取超等者給膏火錢八百文,特等六百文,一等四百文。”光緒《績溪梁安高氏宗譜》卷11《文會》。黟縣萃英文社要求“延師主講為爾士觀摩”,聘請品學名儒為師,不拘科甲,每年束修節敬因時酌定,分三節敬送。生童課期為每年十課,每月初五發卷,初十繳卷,二月初四至文社蓋戳,憑單領卷。童生應過縣試,監生應過鄉試,皆給單應課,其他人等不準應課。生監卷每4人取1名,第一名獎銀5錢,第二名獎銀3錢,其余獎銀2錢。童生卷也是每4人取1名,第一名獎銀3錢,其余獎銀2錢。《萃英社文會條目·學校規條》。該份文書承蒙業師王振忠教授惠賜,謹致謝忱。endprint
從徽州文會的規條可以看出,文會會產支出以資助科考為主。績溪城西周氏文會規定,每年從會內公舉誠實廉能之人收貯租息,除辦祭輸糧、頒胙散福外,剩余錢數存貯公匣,以備鄉會試盤費之用,不得侵蝕挪借。另外將3年所余錢數存貯生息作為會試盤費,照入闈者多寡分送。中舉者每人送銀8兩,中進士及鼎甲、翰林、拔貢、上京朝考者,俱照中舉例分送。每逢恩科,若公匣無存銀,動支3年所余,按兩科分給。赴闈盤費臨期贈送,不許預支,不赴闈者不給。倘已領盤費卻借故不去應試者,將盤費追回,并罰在祖宗神像前跪香一炷。光緒《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20《文會》。績溪梁安高氏學愚文會制定了文會貼例,文童應縣試貼錢400文,覆試一場貼錢200文。應府試貼錢600文,覆試一場貼錢200文。應院試貼錢600文。生員應考優拔貢貼銀4兩。生員下科貼銀4兩。舉人應會試貼銀10兩。進士應殿試貼銀10兩。光緒《績溪梁安高氏宗譜》卷11《文會》。黟縣萃英文社規定,生童觀風,每人給盤費錢240文,文童應院試者每人給程儀錢1000文,文生歲試每人給程儀1000文,文生科試與貢監錄科者每人給程儀錢1400文,生童院試考中者每人給費用錢600文,以上生童程儀要到府城發放,經手發程儀者議貼錢500文,作為換錢搬錢的資用。參加鄉試者每人給程儀錢2000文,會試與朝考者每人給程儀錢10千文。童生應縣試,各族長在考前3日自查應試人數,到值年處報名領票轉交生童,并投禮房辦卷,憑票算與卷資,不得混雜,如有混雜,查出議罰。各姓經手府試盤費者每人發洋6角,院試同縣案首正榜獎英洋1元,府試同入舉賀英洋2元。士子赴鄉試、會試盤費,鄉試每人發英洋3元,會試每人發英洋15元,科試每人發英洋1元,歲試不發。對考中功名的賀儀,鄉試一名賀英洋30元,副榜10元,舉人加倍。會試一名賀英洋40元,進士賀洋30元,殿試一甲一名賀英洋100元,獲選內用者賀英洋50元,外用者賀英羊30元,歲科試一等獎洋角補增賀英洋1元,補廩賀英洋3元,歲貢同恩拔、優貢各賀英洋10元。《萃英社文會條目·學校規條》。
四、結語
徽州文會在明、清兩代呈現了不同的發展特征。明朝中后期,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有所松動,社會風氣發生變化,徽州文會的發展呈現多元特色,除了以應付科考為主要活動內容的科舉類文會,屬于文人結社性質的詩社、文社數量更為龐大,分布也更為廣泛,文人在風景幽盛處詩酒唱和,切磋技藝,體現了這一群體空靈飄逸,較為自由的生存境況。清朝統治者加強了對知識分子的控制,文人自由活動的空間日漸逼仄,徽州文會的“文”學色彩大為削減,詩社、文社退出歷史舞臺,科舉類文會成為主體。清代徽州文會以血緣性的宗族文會為主體,是宗族重視文教,培養族內人才,提升家族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舉措。而超越血緣關系的地緣性社區文會、合都文會雖然數量不多,但更多地折射出徽州地域社會的統合結構,多個家族聯合舉辦文會,每年定期進行祭神、會課、宴飲等活動,不但加強了士子彼此的交流,幫助他們提高科舉應試能力,同時也密切了家族間的關系,對維持村落社會秩序的穩定大有裨益。清代徽州文會都擁有一定規模的資產,其來源多途,捐田置地、集資入股、入會出銀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徽州文會為了維持正常運作,設專人或固定機構管理會產,制定章程規范會產支出。徽州文會在經費籌措、資產管理、運營等方面與祝圣會、關帝會、清明會、觀音會、錢會等其他類型會社的運行邏輯具有很強的相似性,考察徽州文會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徽州會社的認識。需要指出的是,能夠體現徽州文會主要特征之處在其功能方面,“文會乃斯文之藪,凡有功名者皆得與焉”光緒《婺源查氏族譜》卷尾之九《序·正誼文會序》。。參加者的身份具有了天然的門檻,從而使文會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可視為讀書人的共同體。正因為普通民眾對讀書識字的敬畏感,文會成員多被視為明理之人,具有某種權威,他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宗族事務管理和地方社會事務處理,徽州文會頻頻從事宗祠修造、族譜編纂、族產管理等活動。徽州宗族與文會交相嵌入,互相奧援。文會與宗族有機整合,在徽州地方社會結構的序列中居于重要位置,彰顯了徽州基層社會中民間組織的多元統合性質。
參考文獻:
[1] 吳克俊,程壽保,等.民國黟縣四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2] 謝陛.萬歷歙志[M].張艷紅,王經一,點校.合肥:黃山書社,2014.
[3] 江登云,江紹濂.乾隆橙陽散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4] 凌應秋.乾隆沙溪集略[M]∥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1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5] 汪道昆.太函集[M].胡益民,余國慶,點校.合肥:黃山書社,2004.
[6] 許承堯.歙事閑譚[M].李明回,等點校.合肥:黃山書社,2001.
[7] 謝永泰,程鴻詔.同治黟縣三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8] 吳甸華,程汝翼,俞正燮.嘉慶黟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9] 祁門二十一都二圖磻溪陳氏文書[M]∥劉伯山.徽州文書:第5輯 第1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10] 王欣鈺,周紹泉.徽州千年契約文書[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
[11] 佘華瑞.雍正巖鎮志草[M]∥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責任編輯:汪效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