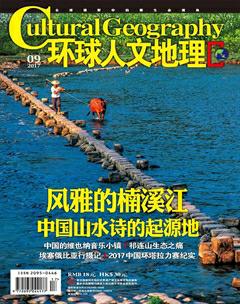祁連山生態(tài)之痛 半個世紀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治理戰(zhàn)
歐維
祁連山是河西走廊的“生命線”,其生態(tài)破壞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在近幾十年中又遭遇了森林采伐、探礦采礦、水電開發(fā)、旅游設(shè)施建設(shè)等多輪大規(guī)模破壞,除此之外,據(jù)中央督察組的督察,甘肅省多個部門不僅不作為,甚至為違法、違規(guī)行為開起了“綠燈”……2017年7月,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發(fā)出問責通報后,甘肅省打響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生態(tài)治理戰(zhàn)”,但是,光靠治理能解決問題嗎?
4分46秒!2017年7月20日,《新聞聯(lián)播》用大約1/6的時間,播報了一則題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就甘肅省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發(fā)出通報》的新聞。
事實上,近幾年來,關(guān)于祁連山生態(tài)問題的報道不絕如縷,但“兩辦”同時發(fā)出通報、《新聞聯(lián)播》長時間曝光,力度之大十分罕見。
祁連山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的交匯地帶,由于具有重要的水源涵養(yǎng)作用,祁連山被譽為河西走廊的“生命線”和“母親山”。然而,由于人們長期的過度開發(fā)和破壞,這座“母親山”早已千瘡百孔。盡管此前,中央曾多次要求甘肅省進行整改,但情況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
河西走廊上的高山水塔“生命線”將變“死亡線”?
從陜西西安出發(fā),沿著絲綢之路一路西行,在茫茫的沙漠中,一片綠洲赫然出現(xiàn)——這就是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勢平坦,土質(zhì)肥沃,灌溉農(nóng)業(yè)發(fā)達,是西北地區(qū)最主要的商品糧食基地和經(jīng)濟作物集中產(chǎn)地,而這里之所以如此富饒,就是因為祁連山。
祁連山位于河西走廊南側(cè),由多條西北—東南走向的平行山脈組成,綿延近千公里,山脈海拔大多在3500米以上,主峰素珠連峰高達5564米,山脈頂部終年積雪,發(fā)育了3066條冰川,此外,祁連山區(qū)年均降水量達300~700毫米,被人們譽為天然的“高山水塔”,這些雨雪、冰川融匯而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內(nèi)陸河水系,用源源不斷的水源孕育了河西走廊,并養(yǎng)育了河西地區(qū)及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地區(qū)的400多萬人民。古往今來,無數(shù)詩句描繪過當?shù)氐氖⒕埃骸叭跛髁鹘訚h邊,綠楊蔭里系漁船。”“稻花風(fēng)里稻花香,妾去采花郎插秧。”“不望祁連山頂雪,錯把甘州當江南。”因此,人們甚至宣稱:沒有祁連山,就不會有河西走廊,更不會有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絲綢之路。
考慮到祁連山不可替代的生態(tài)地位,1988年,甘肅省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正式成立,保護區(qū)位于甘肅省境內(nèi)的祁連山北坡中、東段,地跨武威、金昌、張掖3市的涼州、天祝藏族自治縣、古浪、永昌、甘州、山丹、民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8縣(區(qū)),總面積198.72萬公頃,略大于北京市的面積。然而,隨著全球變暖、人類活動的不斷加劇,這道西北地區(qū)最重要的生態(tài)屏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
據(jù)中科院、甘肅省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管理局、甘肅省氣象局等多部門的監(jiān)測,祁連山的最低雪線正在逐年升高,局部地區(qū)的雪線以年均2~6.5米的速度上升,個別地區(qū)的雪線年均上升甚至高達12.5~22.5米。專家預(yù)測,面積約2平方公里的小冰川將在 2050 年前基本消亡,而較大的冰川也只有部分可以勉強支持到本世紀 50 年代以后。冰川的消失,必然會導(dǎo)致河流來水量的減少,甚至出現(xiàn)斷流的情況。據(jù)調(diào)查,黑河祁連山北出水口的流量,近20年來大幅度減少;石羊河的中下游流域已經(jīng)出現(xiàn)水荒……
此外,祁連山的草原也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祁連山草原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清代地理名著《秦邊紀略》形容道:“其草之茂為塞外絕無,內(nèi)地僅有。”然而,據(jù)統(tǒng)計,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祁連山區(qū)甘肅境內(nèi)的天然草地面積為7305萬畝,但目前退化的草地面積已達5621萬畝,占草地總面積的77%。一位從小在祁連山區(qū)長大的老牧民無奈地說:“十幾年前,我?guī)еQ蛟诓菰铣圆荩F(xiàn)在,牛羊就只能在草原上啃草了。”
祁連山的生態(tài)狀況令人擔憂,中科院專家警告說:如果人為活動的影響再得不到徹底的禁絕,退化的速度還會加快,到那時,祁連山就不再是人們所說的“河西的生命線、幸福線”,而是“河西的死亡線”了,“西北的綠色走廊”可能最終不復(fù)存在,而且祁連山一帶的大氣候環(huán)境也將發(fā)生不堪設(shè)想的變化。
破壞開始于2000多年前祁連山為何遍體鱗傷?
祁連山的生態(tài)破壞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據(jù)《河西志》記載:2000多年前,祁連山擁有約9000萬畝天然森林,樹木茂密,濃蔭蔽日。到西漢時期,漢武帝開始在河西走廊設(shè)郡,并實行大規(guī)模的“移民實邊”,人們開始在祁連山一帶屯墾開發(fā),祁連山的天然植被開始遭到破壞。到了清雍正年間,年羹堯西征平定叛亂,為了清剿隱藏在祁連山密林中的叛賊,年羹堯下令放火燒山,這使得祁連山出現(xiàn)了毀林歷史上最慘痛的一幕:幾萬畝森林毀于一旦,周邊的草場也出現(xiàn)了擴展性退化和萎縮。19世紀30年代末,國民黨駐甘青部隊,對祁連山進行了剃頭式的大規(guī)模砍伐,在他們的影響下,祁連山周圍的百姓也開始亂砍、濫伐,到解放初期,祁連山幸存下來的天然森林已不足200萬畝。而在20世紀50年代末,全國為大煉鋼鐵,掀起了砍樹熱潮,祁連山的森林資源再次遭到嚴重破壞。直到1980年,甘肅省委、省政府決定全面禁伐森林,祁連山地區(qū)的森林亂砍、濫伐才基本停止。
不過,森林采伐只是祁連山生態(tài)破壞的開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祁連山陸續(xù)遭受了礦山探采、水電開發(fā)等幾輪大規(guī)模破壞。endprint
祁連山素有“萬寶山”之稱,境內(nèi)礦產(chǎn)資源豐富,蘊藏了黃鐵、鉻鐵、銅、鉛、鋅等多種礦產(chǎn)。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小煤礦為主的礦山開采在祁連山地區(qū)迅速發(fā)展,并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高峰,據(jù)統(tǒng)計,在當時,僅張掖市就有800多家礦山企業(yè),而其中700多家竟然都在保護區(qū)內(nèi)。
在張掖市肅南縣祁豐鄉(xiāng)觀山村,有一條寬闊的公路直通甘肅省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的深處,這條公路由當?shù)氐牡V業(yè)公司修建,沿著公路來到礦井,殘留的活動板房、礦石棄渣、塌陷的地表讓人觸目驚心。然而,開礦的破壞不僅影響到礦井周邊,蘭州大學(xué)資源環(huán)境學(xué)院院長張廷軍對媒體表示:開礦將會影響地下凍土,引發(fā)地質(zhì)災(zāi)害,使得地表大面積干旱化,而開礦產(chǎn)生的灰塵還會降低雪和冰的反射率,加速冰雪消融,而這些都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傷害。據(jù)中央督察組的督察,截至2017年4月,在保護區(qū)內(nèi),還設(shè)置有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多達 144 宗,對當?shù)厣鷳B(tài)的破壞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祁連山一帶又興起了小水電站建設(shè),據(jù)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wù)院辦公廳發(fā)出的通報,當?shù)卦谄钸B山區(qū)域的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共建有水電站 150 余座,42 座位于保護區(qū)內(nèi),其中,黑河流域小水電站的密度更是令人咋舌。
2015年8月,中國河流生態(tài)聯(lián)盟發(fā)起人邵文杰到達張掖后,第一時間趕往當?shù)氐暮诤印.斔竭_黑河邊上時,被眼前的景象震驚得目瞪口呆:在寬約幾百米的河床上,竟然一滴水都沒有。究其原因,當?shù)厝烁嬖V邵文杰:“水都在山里(水電站)攔著,只有水電站放水,河道中才有水,這河大半年都是干的。”
黑河全長800多公里,年均徑流量約16億立方米,其流量僅相當于中國南方的一條小河,但在這條河的上游卻分布著8座水電站。按照《自然保護區(qū)條例》和《環(huán)評法》的要求,為了對下游河流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進行補償,水電站需下泄符合規(guī)定的生態(tài)用水。但是,為了盡可能多地發(fā)電,多座水電站選擇了象征性放水,甚至根本不下泄生態(tài)用水,這就使得黑河下游徑流減少,甚至出現(xiàn)了斷流的現(xiàn)象。中國河流生態(tài)保護聯(lián)盟的相關(guān)人士說:“黑河是祁連山發(fā)育的最大的內(nèi)陸河,但它一年中很長時間都是斷流的,其他河流可想而知。沒有水,(河西走廊的)綠洲生態(tài)系統(tǒng)如何維系?”
除此之外,旅游業(yè)的興起、旅游項目未批先建,掠奪式的放牧等行為不斷加重祁連山的生態(tài)問題。一位長期研究祁連山生態(tài)的環(huán)保專家說:“祁連山已經(jīng)遍體鱗傷,兩辦同時發(fā)出通報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掀起問責風(fēng)暴治理真能解決問題?
事實上,對于祁連山的通報并不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第一次同時就環(huán)境生態(tài)問題發(fā)出通報。2014年,“兩辦”就已經(jīng)同時就“騰格里沙漠污染問題的處理情況”發(fā)出過通報,不過,與2014年的通報不同,這次對祁連山的通報,是首次對相關(guān)責任人進行問責:甘肅3位省級干部被點名批評,8名負有主要領(lǐng)導(dǎo)責任的責任人被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嚴肅問責,其中4名受到撤職處分,其他7名相關(guān)部門的負責人被甘肅省委和省政府依紀依規(guī)進行問責。這也就意味著,促使兩辦發(fā)出通報的原因,除了嚴峻的生態(tài)問題,還有相關(guān)部門的整改不力。
早在2015年3月,環(huán)保部就通過遙感衛(wèi)星對祁連山進行檢查,發(fā)現(xiàn)了頻繁的違法、違規(guī)開發(fā)礦產(chǎn)資源的活動。在當年的9月,環(huán)保部會同國家林業(yè)局就保護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對甘肅省林業(yè)廳、張掖市政府進行公開約談,這次約談是環(huán)保部針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的首次公開約談。約談后,甘肅省著手進行整改,但情況并沒有明顯改善。2016 年5月,甘肅省組織對祁連山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整治情況開展督察,但形成督察報告后就不了了之,并未查處典型違法、違規(guī)項目。在2016年年底,中央第七環(huán)境保護督察組對甘肅省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督察,發(fā)現(xiàn)舊的問題沒有整改好,新的問題又出現(xiàn)了。2017年2月12 日至3月3日,由黨中央、國務(wù)院有關(guān)部門組成中央督察組,再次進入祁連山,開展專項督察,仍然發(fā)現(xiàn)許多問題。最終,兩辦在2017年7月正式發(fā)出通報,在“通報”中措辭十分嚴厲,直指相關(guān)部門“不作為、不擔當、不碰硬、亂作為、監(jiān)管層層失守”。
為何整改會如此困難?專家認為,其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原因——保護區(qū)范圍曾多次調(diào)整。雖然在1988年,甘肅省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就已經(jīng)成立,但直到2014年10月,才明確劃分了保護區(qū)的范圍和功能區(qū),并實地立標,而在此期間,保護區(qū)的范圍經(jīng)歷了多次調(diào)整。一位保護站的護林員說:“有些礦山探采、水電開發(fā)項目在幾十年前就獲批建設(shè)了,忽然就被劃入了保護區(qū),企業(yè)已經(jīng)投入上億的資金,怎么可能說撤走就撤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劃定保護區(qū)之后,當?shù)厝匀淮嬖谶`法、違規(guī)審批項目的行為。據(jù)中央督察組的督察,在保護區(qū)設(shè)置的144宗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中,有14宗都是在2014年后審批的。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王向晨說:“甘肅是一個欠發(fā)達的省份,經(jīng)濟增長對礦產(chǎn)、水電等資源的開發(fā)依賴程度比較高,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有向經(jīng)濟發(fā)展讓步的傾向。”以張掖市肅南縣為例,肅南縣環(huán)境保護和林業(yè)局副局長彭吉廷在接受《西部商報》采訪時說,肅南縣礦產(chǎn)資源開發(fā)收入,一度達到全縣財政收入的80%以上。由于環(huán)保壓力,肅南縣的一些礦山企業(yè)逐漸停產(chǎn)、關(guān)閉,2015年,肅南縣財政收入倒退到了5年前,2016年的增幅不足1%。“之所以現(xiàn)在一些地方出現(xiàn)不作為的問題,既有長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一些地方還保持著過去(片面追求GDP)的慣性思維。”中國人民大學(xué)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發(fā)展學(xué)院副院長鄭風(fēng)田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覺得有一句話特別好,再三強調(diào),不如一次問責。”
事實正如鄭風(fēng)田所說,在“兩辦”發(fā)出問責通報后,甘肅省明確表示:2017年,全面停止祁連山保護區(qū)核心區(qū)、緩沖區(qū)內(nèi)所有探采礦、水電建設(shè)、旅游資源開發(fā)等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活動;2018年底前,所有探采礦活動全面清理退出;2020年前,全面消除自然保護區(qū)內(nèi)礦山地質(zhì)環(huán)境問題。這些舉措被稱為“半個世紀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生態(tài)治理”。不過,治理就可以解決問題嗎?一位經(jīng)濟學(xué)專家解釋說:“為了GDP,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是不正確的,但是,對于一個欠發(fā)達的地方來說,究竟要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既保護青山綠水,同時又能夠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但是很顯然,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ndprint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