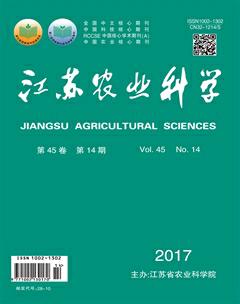基于糧食發展指數的我國糧食生產發展變化和區域差異分析
摘要:在分析近9年我國糧食生產變化態勢基礎上,構建糧食發展指數模型,計算我國省級單位的糧食發展指數,比較不同省級單位在糧食發展方面的區域差異,并針對不同變化原因提出建議與對策。結果表明:(1)自2003年以來,我國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整體呈增長態勢,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00 kg的營養安全要求,糧食供需處于低水平的緊平衡狀態下;(2)糧食發展水平最高的4個省級單位,區域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人均糧食產量均提高較快,2011年人均糧食產量為營養安全標準的2.26倍,為國家糧食生產和提供余糧作出重大貢獻;(3)糧食發展水平居中的10個省級單位,在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人均糧食產量等方面的增長速度均處于中等水平,人均糧食產量略有盈余。此區今后在播種面積提高方面潛力有限,增產方面須要加大經濟和科技投入,在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上實現突破,才有望在今后的糧食生產中提高本區的地位和作用;(4)糧食發展水平最低的17個省級單位,糧食播種面積總體呈減少趨勢,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速度較低,人均糧食產量增長總體較低,其中較多單位人均糧食產量呈減少態勢。這17個省級單位2011年人均糧食僅為251 kg,遠遠低于營養安全要求,須大量由外區調入糧食。此區人口稠密,今后在播種面積提高方面潛力有限,增產方面由于基數較低,加大經濟和科技投入,大力提高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是提高糧食自給程度,承擔國家糧食安全責任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糧食發展指數;區域差異;糧食生產規模;糧食生產效率;糧食輸出貢獻
中圖分類號: F326.11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4-0257-05
2008年暴發的糧食危機使糧食安全再次成為全球最為關注的問題[1-3]。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歷來備受學界和政府的關注[4-6]。我國的糧食供求目前狀態是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7],但伴隨著人口增長,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我國糧食消費呈剛性增長,水土資源、氣候等制約因素使糧食持續增產的難度加大[8],就不同農業分區、省、市(縣)尺度的糧食生產狀況開展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國糧食生產供給增長前景不容樂觀[9-12];區域格局變動方面的研究表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糧食生產布局呈現糧食產能向主產區和糧食大縣集中趨勢[13-16]。目前我國的糧食生產發展總量和區域研究大多著眼于生產總量、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或人均糧食產量等單個因素進行分析,著眼于綜合指標構建基礎上的量化分析較為少見。
糧食生產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密切結合的物質生產過程,資源稟賦、投入、技術手段、政策、市場等因素均影響糧食生產行為,在區域上表現為特定區域的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隨時間的延長產生變化,最終影響糧食產量和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考慮區域人口分布的差異,區域糧食發展研究不但要分析糧食產量,還要體現出具體區域在國家糧食安全中提供余糧的地位和作用。綜上所述,本研究考慮糧食生產和人口因素,以近年來糧食產量最低的2003年作為基期,2011年作為末期,綜合考慮資源、效率和輸出等方面,構建糧食發展指數,對我國糧食發展的區域差異進行量化分析,為國家制定科學合理的糧食生產戰略、統籌區域資源、共同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1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為在宏觀上把握我國糧食生產和發展的總體情況和區域差異,本研究在分析我國糧食變化總體情況的基礎上,構建糧食發展指數(grai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GDI)對我國31個省級單位的糧食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借鑒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數構建方法,選取糧食生產規模變化、糧食生產效率變化、糧食輸出貢獻變化3個維度構建糧食發展指數,考慮指標的代表性和數據獲取的可能性,其中規模變化維度采用糧食播種面積變化量作為指標,效率變化維度采用單位面積糧食產量變化量作為指標,糧食輸出貢獻變化維度采用人均糧食變化量作為指標,綜合以上3個指標的幾何平均數來計算糧食發展指數,以評價省級單位的糧食發展能力強弱。
由于各個指標的量綱不同,采用極值法對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式中:Bi表示糧食播種面積變化量標準化值;Di表示單位面積糧食產量變化量標準化值;Ri表示人均糧食變化量標準化值;GDI表示糧食發展指數,數值越大,表明其發展優勢越強。
2我國糧食發展變化及區域差異
2.1整體變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的糧食產量呈現臺階式上升特征,跨越2.0億、2.5億、3.0億、3.5億、4.0億、4.5億t等6個臺階,現進入5億t新臺階,但在整體增長的大趨勢下糧食產量存在起伏。由圖1可知,自1990年以來,我國糧食總產量變化趨勢基本和人均糧食變化趨勢相同,90年代初期(1990—1995年)產量徘徊在4.5億t左右,人均糧食在 380 kg 左右;1996—1999年糧食產量在5億t左右,人均糧食保持在400 kg以上,達到盧良恕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人均營養熱值標準并結合我國國情計算并提出的人均糧食消費400 kg的營養安全要求[17];自2000年糧食產量開始迅速下降,2003年到達20多年的最低點,糧食產量僅為4.3億t,人均糧食降至333 kg;2004年開始逐年增長,2011年人均糧食再次達到408 kg。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糧食供需處于低水平的緊平衡狀態下,糧食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不斷起伏變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必須要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2.2區域差異
在近9年糧食產量連續增產下,我國人均糧食剛剛達到400 kg的營養安全要求,為明確我國省級單位近年來在糧食安全中的作用與地位,計算2003—2011年省級單位的人均糧食產量及其變化。由圖2可知,近年來我國在省級層面上人均糧食產量總體呈增長趨勢,但省級單位之間差異懸殊,增長最快的是黑龍江省,人均糧食增長量為794 kg;減少最快的是廣東省,人均糧食降低50 kg;2011年人均糧食最高的黑龍江省為1 463 kg,人均糧食最低的上海僅為52 kg;2011年人均糧食高于400 kg的省級單位僅占15個,這說明我國有一半以上的省級單位要依靠調入糧食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糧食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說明區域在國家糧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量化區域為國家糧食安全所作貢獻須要綜合考慮資源稟賦、生產效率、輸出供給能力。根據糧食發展指數模型構建方法,計算全國31個省級單位2003—2011年間的糧食發展指數,對我國31個省級單位的糧食發展狀況進行量化評價。由表1可知,我國13個糧食主產區中有12個單位位居前13名,僅四川省位次稍后,位居第19名。可見,近9年來我國糧食主產區充分發揮資源優勢,不斷提高糧食播種的規模和效率,糧食輸出貢獻較大,為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省級單元層面上,我國31個省級單位在近年來的糧食安全地位和貢獻方面差異懸殊。黑龍江省的糧食發展指數最高,近9年來黑龍江省在糧食生產播種面積擴大、單位播種面積糧食產量提高、人均糧食產量增加方面均位居全國第一。在播種面積變化方面,黑龍江省與減少最多的廣西省之間播種面積變化差異高達378.542萬hm2;單位播種面積產量變化方面,黑龍江省與減少最多的貴州省之間的差異高達 2 531.98 kg/hm2;在人均糧食產量變化方面,黑龍江省與減少最多的廣東省之間差異高達844.69 kg。空間上,近年來在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人均糧食產量減少最多的3個省級單位均位于我國熱量條件較高的南方地區,而此三方面增長最高的黑龍江則位于我國緯度最高的北方。糧食發展指數位于全國第二的內蒙古自治區位于大陸腹地,氣候干旱,年降水相對變率大,水資源較為貧乏,生態環境脆弱,但近9年來,內蒙古自治區的糧食生產播種面積擴大量位居全國第二、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位居全國第八、人均糧食增加量位居全國第二。在國家層面上,這種自然資源與糧食生產之間的錯位現象須要進一步深入分析其原因和機制。
本研究根據糧食發展指數將我國31個省級單位劃分為高[CM(25]、中、低3個組(表2),分別統計各組的耕地面積、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人均糧食產量、余糧量,分析其在國家糧食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表2可知,在2003—2011這9年期間,我國糧食發展指數最高的省級單位有4個,分別是黑龍江省、內蒙古自治區、河南省、吉林省,糧食發展指數在0.45~1.00之間,這4個地區單位耕地面積為3 243.8萬hm2,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26.65%;2011年4個省級單位人口共18 45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3.70%;農業生產資源較為豐富,人均耕地面積為 0.18 hm2、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0.18 hm2;糧食播種面積為 3 147.0萬hm2,占全國總量的28.46%;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5 298 kg/hm2,高于全國5 166 kg/hm2的平均水平;人均糧食產量為904 kg,遠遠高于全國424 kg的平均水平。以人均400 kg作為消費標準的話,高出消費標準2.26倍。這4個省區在滿足自身人口需求的基礎上,可以為國家提供余糧 9 292萬t。
我國糧食發展水平居中的省級單位總計有10個,糧食發展指數在0.25~0.44之間,這一組總耕地面積為 4 847.5萬hm2,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39.82%;2011年人口為56 74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2.10%;糧食播種面積為 4 607.6萬hm2,占全國總量的41.67%;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 5 578 kg/hm2,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 166 kg/hm2);人均糧食為453 kg,雖然這10個單位中有8個屬糧食主產區,但不論是從全國平均水平(424 kg)還是以人均400 kg作為消費標準計算,此組均僅為略有盈余。
我國糧食發展水平最低的省級單位總計有17個,糧食發展指數在0~0.24之間,17個單位中僅四川省為糧食主產區省份。這一組總耕地面積為4 083.4萬hm2,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33.55%;2011年人口為58 84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3.68%;糧食播種面積為3 302.8萬hm2,占全國總量的2985%;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4 467 kg/hm2,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 166 kg/hm2),人均糧食為251 kg,不論是從全國平均水平(424 kg)還是以人均400 kg作為消費標準計算,此組均大量虧缺。
3對策與措施
為進一步分析我國糧食生產的區域差異及其原因,基于各地的資源稟賦和環境條件進一步提高各區域的糧食生產能力,合理進行空間格局優化,本研究對劃分出的高、中、低3個組進行進一步細化分析,并分別提出糧食發展建議與對策。
我國糧食發展指數最高的省級單位共包括黑龍江、內蒙古、河南、吉林4個省。總體而言,此區域播種面積平均增加159.2萬hm2,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平均增加1 412 kg/hm2,人均糧食平均增加431 kg,在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提高均較快,為國家糧食生產、提供余糧等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此組內部存在較大差異。以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例,近9年來黑龍江在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方面增產量為全國第一,但2011年黑龍江省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 4 843 kg/hm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河南省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增加量位居全國第三,2011年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 5 622 kg/hm2,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吉林省的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增加量位居第四,2011年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 6 977 kg/hm2,已經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內蒙古自治區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增加量位居全國第八,2011年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為4 293 kg/hm2,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此組中黑龍江省、內蒙古自治區2個單位雖然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增加較快,但起點較低,現產量仍低于平均水平,考慮到黑龍江省地處高緯度地帶、無霜期短、經營粗放、農田基礎設施薄弱,內蒙古自治區水資源短缺,現有耕地中主要為旱耕地,質量較差的中低產田面積占70%以上,耕地自然質量等別、利用等別、經濟等別均處于全國等別系列中的中下等,這2個省今后糧食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空間較大,但自然限制因素的突破須要加大農業投入,改善農業條件。河南、吉林2省現有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已經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河南省現有耕地中高產田面積為274.16萬hm2,僅占34.53%;中低產田面積518.37萬hm2,占65.47%,在提高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方面還有空間。吉林省地處亞洲黑土帶,土地肥沃,是國家糧食主產區和最大的玉米產區,全省優質耕地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區,但中部地區城鎮密集,是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心,提高單位播種面積產量與發展經濟相比較而言比較效益低,糧食生產面臨生產要素流失問題。
比較近9年來的播種面積變化可知,黑龍江省、內蒙古自治區、河南省分別位居全國第一、第二、第三,吉林省播種面積積增長較慢,位居第八。這主要是因為黑龍江省、內蒙古自治區等地的土地資源豐富。通過查閱各省土地利用規劃可知,4個省中除河南省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后備資源不足,其他3個省均具有較大發展空間,但也面臨不同的限制因素。2006—2020年黑龍江省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數據顯示,黑龍江省雖然后備資源整體較大,集中連片的耕地后備資源約為 27.38萬hm2,但多為禁止開發的沼澤地、灘涂,開發利用難度大;2006—2020年內蒙古自治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顯示,未利用地資源可利用類高達235.16萬hm2,主要類型為荒草地、鹽堿地、沙地等,但由于地處歐亞大陸架腹地,氣候干旱、風力強勁,是我國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補充耕地數量的同時,須要提高質量,解決土地沙漠化、荒漠化、土壤鹽漬化、草場退化、水土流失等土地退化問題。2006—2020年河南省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顯示,河南省耕地后備資源不足,開發利用制約因素較多,宜耕后備土地資源主要分布在黃河沿岸(灘涂)和豫西、豫南、豫北等低山丘陵區,對其開發既有來自生態保護等政策方面的制約,又有地形坡度大、水資源缺乏等自身條件的限制,開發難度較大。吉林省整體上后備土地資源豐富,未利用地集中在“三化”問題嚴重,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西部,經濟發展中心與黑土帶在中部地區重疊,糧食播種面積擴大壓力較大。
我國糧食發展水平居中的省級單位總計有10個。比較近9年的播種面積變化和單位播種面積產量變化可知,此區域播種面積增加平均值為51.4萬hm2,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增加值平均為755 kg/hm2,人均糧食增加值平均為108 kg,考慮到此區域人口稠密(人均耕地面積為0.09 hm2、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0.08 hm2),今后在糧食播種面積提高方面潛力有限,增產方面須要加大經濟和科技投入,在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上實現突破,才有望在今后的糧食生產中提高本區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糧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級單位總計有17個,就省級單位而言,此組中除寧夏自治區、四川省按人均400 kg消費標準計算有余糧之外,其他15個省級單位均須從外區調入糧食來滿足基本需求。其中缺糧最多的是廣東省,缺糧高達 2 841萬t,其次為浙江省,缺1 403萬t糧,上海、福建省缺糧也達800多萬t。比較近9年的播種面積變化和單位播種面積產量變化可知,此區域播種面積平均減少2.0萬hm2,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平均增加437 kg/hm2,人均糧食平均增加8 kg,其中較多的單位人均糧食呈減少態勢。就糧食播種面積而言,此組有7個單元的糧食播種面積減少,其中廣西壯族自治區糧食播種面積減少最多,近9年來減少了近40萬hm2,其次減少較多的省份為廣東、福建、重慶。除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耕地減少、近年連續自然災害的影響等原因外,我國南方稻作區光照、熱量條件具備的地方,在種植雙季稻、三季稻的生長時間長,氣候條件不確定帶來的風險系數大,水的需求量高,水利設施不足等限制因素下,“雙季稻”“三季稻”改“單季稻”現象也是導致糧食播種面積明顯減少的重要原因。在現有自然條件下,這些地區須要改革糧食補貼制度,改善農田水利設施,提高農業科技應用水平來減緩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現象。比較這組2011年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可知,17個省級單位中高于全國平均值的有7個,其中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最高的前3位依次為上海市、浙江省、北京市,但這3個省級單位的糧食播種面積在全國的比重很低,分別為0.17%、1.13%、0.19%。總體而言,這組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平均為 4 467 kg/hm2,遠低于全國平均值 5 166 kg/hm2。增產方面由于基數較低、加大經濟和科技投入、大力提高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是提高糧食自給程度、承擔國家糧食安全責任的重要途徑。
4結論與討論
自2003年以來,糧食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整體成增長態勢,人均糧食產量達到人均糧食消費400 kg的營養安全要求,糧食供需處于低水平的緊平衡狀態下;糧食發展水平最高的4個省級單位,在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人均糧食方面均提高較快,2011年人均糧食產量為營養安全標準的2倍多,為國家糧食生產和提供余糧作出了重大貢獻;糧食發展水平居中的10個省級單位,在糧食播種面積、單位播種面積產量、人均糧食產量方面增長速度均處于中等水平,人均糧食產量略有盈余。此區域今后在播種面積提高方面潛力有限,增產方面須要加大經濟和科技投入,在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上實現突破,才有望在今后的糧食生產中提高本區的地位和作用;糧食發展水平最低的17個省級單位糧食播種面積總體呈減少趨勢,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速度較低,人均糧食增長總體較低,其中較多單位人均糧食呈減少態勢。2011年人均糧食僅為251 kg,遠遠低于營養安全要求,須大量由外區調入糧食。此區域在糧食生產方面人口資源矛盾突出,今后在播種面積提高方面潛力有限,增產方面由于基數較低、加大經濟和科技投入、大力提高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是提高糧食自給程度、承擔國家糧食安全責任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Chatterjee N,Fernandes G,Hernandez M. Food insecurity in urban poor households in Mumbai,India[J]. Food Security,2012,4(4):619-632.
[2]Bogale A. Vulnerability of smallholder rural households to food insecurity in Eastern Ethiopia[J]. Food Security,2012,4(4):581-591.
[3]Munns R. Editorial:food security,climate change and biofuels: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is now in the spotlight[J]. Functional Plant Biology,2008,35(8):iii.
[4]Funk C C,Brown M E. Declining global per capit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arming oceans threaten food security[J]. Food Security,2009,1(3):271-289.
[5]殷培紅,方修琦. 中國糧食安全脆弱區的識別及空間分異特征[J]. 地理學報,2008,63(10):1064-1072.
[6]鄭振源. 中國土地的人口承載潛力研究[J]. 中國土地科學,1996,10(4):33-38.
[7]Zhang J. The grain-popula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effect of main food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10(4):64-68.
[8]徐志宇,宋振偉,鄧艾興,等. 近30年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的驅動因素及空間格局變化研究[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3,36(1):79-86.
[9]陳百明. 中國農業資源綜合生產能力與人口承載能力[M]. 北京:氣象出版社,2001.
[10]陳百明. 未來中國的農業資源綜合生產能力與食物保障[J]. 地理研究,2002,21(3):294-303.
[11]張晶. 基于SSM的山東省糧食生產變化研究[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3,34(4):11-21.
[12]陳印軍,易小燕,方琳娜,等. 中國耕地資源及其糧食生產能力分析[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2,33(6):4-10.
[13]張晶,楊艷昭,王景平. 中國糧食生產變化類型研究[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07,28(3):11-16.
[14]封志明,楊艷昭,張晶. 中國基于人糧關系的土地資源承載力研究:從分縣到全國[J]. 自然資源學報,2008,23(5):865-875.
[15]劉彥隨,翟榮新. 中國糧食生產時空格局動態及其優化策略探析[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09,28(1):1-5.
[16]龐英,段耀. 黃河流域糧食主產區耕地利用集約度及政策指向——基于23個縣1422個農戶成本數據的分析[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2,26(4):5-10.
[17]盧良恕. 立足于食物安全的大局著眼于生產能力的提高確保我國新時期的糧食安全[J]. 中國食物與營養,200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