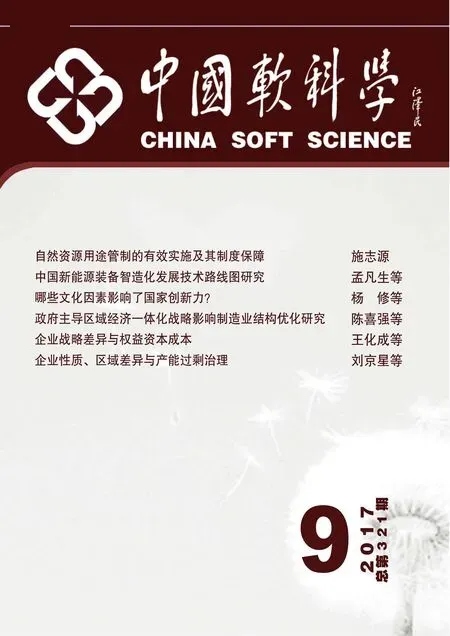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研究
——以泛珠三角區域為例的考察
陳喜強,傅元海,羅 云
(1.廣州大學 經濟與統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2.韶關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研究
——以泛珠三角區域為例的考察
陳喜強1,傅元海1,羅 云2
(1.廣州大學 經濟與統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2.韶關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隨著國家層面區域規劃綱要的密集出臺及實施,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但現有研究在影響機制和政策主張等方面仍然存在截然不同的對立觀點,這引發了對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復雜性的重新思考。我們利用1996-2012年泛珠三角地區9省區制造業的面板數據,運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實證檢驗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影響的差異性。結果表明: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條件下,政府干預和區域一體化對制造業的區域分工、結構升級和結構合理化均沒有顯著影響,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條件下,二者的交互作用即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促進了區域內制造業產業分工,提高了制造業合理化水平,但降低了制造業高級化水平。
政府干預;區域經濟一體化;身份治理;制造業結構優化
Abstract:As the regional planning frequentl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o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used by the government has brought the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opposing views in the past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the policy proposals, lea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orient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By us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anel data of 9 provinces in the pan-river delta region from 1996 to 2012 and utilizing the dynamic panel GMM estimation method, we examine the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orient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on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without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dentity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have no prominent impact o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upgrade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regional manufacturing. Whereas,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dentit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rategy, a promotion of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the regional manufacture industry is presented, with an increasing rationalization level but a decreasing upgrading leve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dentity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一、引言
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是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國構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從“十一五”至今,我國出臺國家層面的區域規劃綱要和相關政策文件超過了70個,數量之多、密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經過多年來的實踐,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發展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盡管我國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是不爭的事實,但理論界對政府推動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作用的認識有著截然不同的對立觀點。那么,在我國實踐十多年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對區域制造業協調發展的影響如何?是否促進了區域制造業結構的優化?本文擬從制造業*制造業作為產業結構的核心部分,是拉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主導部門,制造業結構優化能夠反映出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趨勢,代表了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基本方向。協調發展的視角出發,通過探索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影響,試圖對上述問題作出解答。制造業結構的優化包含了制造業產業分工差異化、合理化和結構高度化三個層面。本文擬以泛珠三角地區作為考察對象,探索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綜合效應*盡管我國有許多成功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案例,但由于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已經具有十多年的發展歷史,合作成效顯著。十多年來,泛珠三角區域的GDP由4.9萬億元激增到18.6萬億元,十年增加3.8倍。2016年3月1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優化區域發展格局、共同培育先進產業集群、引導產業有序轉移三大區域發展目標。因此,本文選擇泛珠三角地區作為考察對象具有典型意義。。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文獻很少,但研究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及協調發展的成果很多。有學者認為,行政層級架構是中國特有的治理方式,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具有凸顯的身份治理屬性,通過行政層級的差異化形成不同的資源配置權力,影響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Henderson et al., 2009[1];Henderson et al.,2011[2];陳喜強,2011[3]),但其對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方向不盡相同。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信息約束和風險規避導致地方政府采取模仿經濟發展戰略上的方式最大化自身利益,從而形成產業同構化而影響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劉瑞明,2007[4]);另一種觀點認為,在晉升激勵假設下確實存在上述這樣的結果,但放松假設后,地方政府的行為將出現分化,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制度創新可以促進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地方政府追求財政收益控制權的行為,有利于地區產業結構的差異化,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王燕武、王俊海,2009[5];溫鐵軍等,2016[6])。對于政府干預的手段,有研究文獻從制度調整和政策調整著手,從打破地區分割的歧視性政策出發,探討區域內部結構轉型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及其協調發展機制(McCann et al., 2011[7];Barca et al.,2012[8];皮建才,2011[9])。在實證分析方面,有學者從不同技術進步路徑對中國制造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響機理進行了研究(傅元海、葉祥松、王展祥,2014[10])。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地區專業化將促進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結構高級化,抑制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結構升級,制造業結構合理化則更多依賴于地方產業的多元化協調發展(孫寧華、韓逸平,2016[11])。有研究認為我國目前是在借助于推動產業高效集聚過程中解決區域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區域產業轉移對我國工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和不確定性(趙祥,2010[12];朱希偉、陶永亮,2011[13];張延愛,2011[14];葉琪,2014[15]);有學者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為例研究其內部產業同構化的必然性,認為需要關注由產業同構化背后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不完善對產業結構優化產生的影響(陳建軍,2004[16];蔣伏心、蘇文錦,2012[17])。針對泛珠三角區域,一些學者通過對泛珠三角地區產業集聚與轉移的實證研究發現,泛珠三角地區產業發展較為散亂、沒有形成分工有序的產業鏈(張秀萍、余樹華,2005[18]),制造業結構優化效果不夠明顯;另一些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則發現,在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中,制造業專業化優勢具有層次性,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制造業已經進入到集聚與擴散并存的新階段(黃新飛、鄭華懋,2010[19];周詩、胡曉鵬,2013[20]),制造業結構優化效果明顯。
關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影響區域產業結構的研究文獻不多,多數文獻是從市場一體化角度來討論的。對于市場一體化是否促進了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方面,總體來看,有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在區域市場一體化過程中,發達地區相較于落后地區擁有區位優勢和技術優勢,制造業不易向周邊轉移,會影響制造業的合理分工和合理化發展,影響制造業結構的優化,最終影響經濟增長(銀溫泉、才婉茹,2001[21];陸銘、陳釗,2009[22])。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區域市場一體化過程中,由于去除了貿易壁壘后,區域間的商品、要素和技術能夠自由流動,能夠產生經濟上的規模效應,從而能夠在正面上影響制造業的分工和合理發展,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影響區域經濟的增長(徐現祥、李郇、王美今,2007[23];卜茂亮,高彥彥、張三峰,2010[24];盛斌、毛其淋,2011[25])。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對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討論有著截然相反的觀點。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復雜性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絕大多數研究文獻選擇從全國的層面來研究制造業結構的優化,其好處在于對總體情況能夠加以把握,但卻忽略了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內部優化機制復雜性的認識。因此,本文將基于制造業結構優化的3個維度(產業分工、合理化和高度化),運用動態面板廣義矩(GMM)估計方法實證檢驗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影響。
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運用身份治理理論揭示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三個層面結構優化作用的不確定性;利用1996~2012年泛珠三角地區9省區制造業的面板數據,運用GMM估計方法實證檢驗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全面影響,通過構造產業分工指數連乘式,實證考察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三個層面結構優化的差異性,判斷促進區域制造業分工和協調發展的路徑。
二、身份治理、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與制造業結構變遷
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區域資源的流動從而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具體到制造業的結構變遷和協調發展問題,政府主導也就是政府通過身份治理,借助于政策工具去影響區域制造業分工協作,促進區域制造業合理化發展和結構升級。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具有凸顯的身份治理效應,也就是說,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意味著政府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行政推動作用,它不僅是一個經濟資源整合的過程,而且是一個身份重新界定的過程。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過程中,中央政府通過對特定區域進行身份定位來重置地方政府的身份定位,這將使地方政府獲得新的權力和資源,從而推動區域內各地方政府根據自身的身份定位去發展經濟,其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我們所說的身份治理效應。下面,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討論。
1.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能夠帶來身份治理的正效應
首先,上級政府通過發布規劃綱要的方式賦予特定區域新的身份,從而完成對特定區域實施身份治理。這種身份治理能夠對區域地方政府形成約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利于消除負外部效應。也就是說,通過一體化的協調機構和協調協議的約束,使得區域內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行為有了一定的約束,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共同目標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區域內各地方政府根據自身的資源條件來選擇有利于本地區發展的制造業,從而推動區域制造業向差異化方向發展,有利于促進制造業結構合理化發展。其次,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目標之一是逐步消除區域內部的隔閡,促進市場一體化發展。在市場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各種生產要素能夠低成本跨地區流動,使得地區制造業的地理空間集中和擴散更為容易,為地區制造業產業轉移和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發展契機。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區域內各市場主體會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投資方向,從而形成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差異。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影響逐步脫離地區行政壟斷而開始獨立發揮作用(于良春、付強,2008[26]),從而促進制造業的地區差異化發展,這有利于制造業結構合理化。再次,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消除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因而具有明顯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效應。也就是說,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區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會逐步趨于縮小,在相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各地區容易發展同層次技術水平的制造業,表面上看,同層次技術水平的制造業往往被認為是同構化的體現,但實際上,發展同層次技術水平的制造業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的同構化,尤其是在政府主導下,由于有了身份治理的約束,在一個全局發展觀的指導下,各地區更容易達成差異化發展。這種身份治理的協調效應能夠從正面影響制造業的分工和合理發展,也能夠從正面上影響制造業的結構升級。
2.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可能帶來身份治理的負外部性
其一,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其外部性表現形式往往就是地方政府憑借行政權力對市場配置資源進行干預或者替代,盡管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是多元化的,但追求地方財政收入最大化仍然是各地方政府的最主要目標之一。在此目標函數驅動下,地方政府更熱衷于向上級部門爭政策、爭優惠、上項目等方式來推動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其最終結果可能導致區域產業的同構化發展,從而影響制造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其二,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并沒有完全消除地方政府的競爭。這是因為,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宗旨是協調地方經濟發展,經濟目標導向的干預顯然容易引發地方政府的經濟競爭,雖然一體化發展可以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但政府并沒有足夠的能力完全消除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性所導致的區域經濟發展競爭性依然存在。這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地區競爭的發展模式極大地調動了各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通過改善各地投資環境來推動地區制造業發展。在制造業轉移的過程中如果能夠得到合理補償,后行動的地方政府愿意退出所在產業,從而會逐步消除制造業轉移趨同現象;另一方面,若沒有得到合理補償,承接制造業轉移時存在政府間的競爭,制造業轉移趨同現象就無法在短期內消除。實際上,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其經濟政績,不僅不會急于把有利于本地區的制造業轉移出去,相反會創造條件吸引其他地區有利的制造業轉移進來,地方政府這樣的短期行為會延緩制造業轉移和升級的速度。可以說,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競爭性不僅導致了制造業同構化而影響制造業結構合理化發展,而且阻礙了制造業結構升級,影響其高度化發展。其三,盡管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目標之一是逐步消除市場壁壘,促進市場一體化發展。但政府主導并沒有能夠消除市場機制對制造業結構優化帶來的雙重性影響。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市場經濟追逐利潤的特性會引發區域內各省區投資的趨同性,出現投資行為以及制造業發展的“羊群效應”,對某些行業尤其是盈利效果比較理想的制造業項目競相追逐投資而形成重復建設,此外,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驅動也將進一步加速制造業的同構化發展。其結果不僅制約了制造業結構的合理化,而且制約了制造業結構的升級,阻礙制造業結構高度化發展。
綜上所述,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目標是旨在推動經濟活動高效集聚的過程中解決我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問題。但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經濟合作區內,由于政府主導帶來的身份治理效應具有雙重性,導致了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具有不確定性,其最終走向取決于區域的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博弈結果。向心力主要來自于區域的外部性,這個外部性可以理解為各地方政府干預的結果;離心力主要來源于制造業的市場化發展機制。由于兩種作用力的方向不同,導致一體化區域內部制造業發展過程會出現不確定性,可能有利于促進制造業結構優化,也可能制約制造業結構優化。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選取泛珠三角地區作為研究對象來實證檢驗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制造業三個層面結構優化影響的實際效果。
三、計量模型與研究方法
(一)模型設計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因素很多,政府通過身份治理推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制造業結構優化具有重要影響,制造業的結構變遷和空間擴散與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劉傳江、呂力,2005[27]),市場化程度會影響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速度,一國的開放模式和開放程度也會對產業結構產生重要影響(陳翔飛、居勵、林善波,2011[28])。因此,本文將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和市場化作為控制變量。由于產業結構特征具有連續性(于澤、徐沛東,2014[29]),意味著計量模型被解釋變量可能存在自回歸,被解釋變量是內生變量,為解決內生性問題,初步構建動態面板如下:
ISit=α1ISit-1+α2GIit+α3RI+α4EDit+α5ODit+α6NSit+α0+νit
(1)
Hit=β1Hit-1+β2GIit+β3RI+β4EDit+β5ODit+β6NSit+β0+μit
(2)
Git=δ1Git-1+δ2GIit+δ3RI+δ4EDit+δ5ODit+δ6NSit+δ0+εit
(3)
基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本文利用泛珠三角地區9省區共計17年制造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本文數據未包含香港和澳門。。產業結構的優化包含區域內產業分工、合理化和結構升級三個層面,IS、H和G分別表示制造業產業分工、制造業合理化和制造業高度化。i表示第i(i=1,…,9)個地區;t表示第t(t=1996,…,2012)年;α1至α6、β1至β6、δ1至δ6為待估參數,α0、β0、δ0為截距,v、μ、ε為隨機誤差項。GI表示政府干預,RI表示區域經濟一體化,ED代表經濟發展水平,OD代表對外開放,NS代表市場化。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政府干預對制造業結構優化的作用可能需要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才能發揮,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分工協作具有重要影響;同樣,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的作用要通過政府的政策發布、投資、產業政策等政府干預手段來實現。因此,政府干預和經濟一體化通過相互作用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產生重要影響。為了檢驗政府干預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交互作用對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本文引進兩者的連乘項GI·RI對模型(1)至模型(3)進行改造,得到模型(4)至模型(6)如下:
ISit=φ1ISit-1+φ2GIit·RI+φ3EDit+φ4ODit+φ5NSit+φ0+τit
(4)
Hit=λ1Hit-1+λ2GIit·RI+λ3EDit+λ4ODit+λ5NSit+λ0+ηit
(5)
Git=θ1Git-1+θ2GIit·RI+θ3EDit+θ4ODit+θ5NSit+θ0+υit
(6)
模型(4)至模型(6)中φ1至φ5、λ1至λ5、θ1至θ5為待估參數,α0、β0、δ0為截距,v、μ、ε為隨機誤差項,構造連乘項的目的是比較兩組模型中GI、RI和GI·RI的估計系數在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上面的差異,以檢驗政府干預與經濟一體化戰略的交互作用分別對制造業差異化分工、制造業結構合理化和制造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進而考察政府干預與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
(二)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
傳統的產業結構分析指標大多是從三次產業的角度來分析,但就中國經濟發展現狀而言,針對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變遷研究更具意義。制造業結構分工協作采用28個制造行業測度,因為行業分類越細致,制造業分工協作測度越準確;制造業合理化和高級化的測度借鑒傅元海等的處理方法,按技術含量將制造業劃分為低端技術制造業、中端技術制造業和高端技術制造業*為了分析方便,本文采取OECD的分類方法,把我國制造業重新分類:高端技術產業(第三類)包括通用設備、專用設備、交通運輸、電氣機械及器材、通信電子、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化工醫藥等行業;中端技術產業(第二類)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橡膠、塑料、非金屬礦物、黑色金屬冶煉、有色金屬冶煉和金屬制品等行業;低端技術產業(第三類)包括食品加工制造、飲料、煙草、紡織、服裝、皮革、木材、家具、造紙、印刷和文體用品及其他制造業(參見傅元海、葉祥松、王展祥. 制造業結構優化的技術進步路徑選擇——基于動態面板的經驗分析[J]. 中國工業經濟,2014(9): 79-80.)。此外,本文將橡膠制品業和塑料制品業統一合并為橡膠與塑料制品業,2003年以后的工藝品、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等則并于其他制造業,刪除了武器制造業和2011年之后才出現的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維修業,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以便進一步測度制造業結構高級化及合理化。
(1)制造業分工指數
“產業分工指數”又稱為產業同構系數,是由Krugman于1991年提出,用于考察區域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和專業化水平。本文在Krugman的公式基礎上利用28個制造行業數據進行計算,來衡量泛珠三角地區各省區與九省區制造業整體水平之間的差異,調整后的產業分工指數計算公式為:
(7)
其中i表示第i(i=1,…,28)類制造業,j為第j(j=1,…,9)個地區,Qij表示j地區的第i類制造業的總產值,Qj表示j地區制造業的總產值,Qi為泛珠三角九省的第i類制造業的總產值,Q為九省的制造業總產值。IS為0時表示各省的制造業結構完全相同,值越大則表明該省與泛珠三角地區平均制造業結構的差異性越大。同時,本文利用制造業的總產值、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分別計算制造業分工系數,以檢驗模型的穩健性,這樣模型(1)和模型(4)就細化為模型(1a)、模型(1b)、模型(1c)和模型(4a)、模型(4b)、模型(4c)。
(2)制造業合理化
產業結構合理化基于要素配置效率假設:在要素充分流動下,各部門的邊際產出、勞動生產率或人均資本相同。該指標主要反映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程度和聚合質量,一般采用結構偏離度和泰爾指數來度量(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2011[30];傅元海、葉祥松、王展祥,2014[10])。泰爾指數考慮了不同類型產業的相對權重,較結構偏離度更優,因此本文采用泰爾指數(H)來測度制造業合理化,同樣從制造業的總產值、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三個指標來計算,模型(2)和模型(5)就細化為模型(2a)、模型(2b)、模型(2c)和模型(5a)、模型(5b)、模型(5c)。
(3)制造業高級化
產業結構高級化一般用來衡量產業結構的演變,制造業結構的高級化則是表現為低技術水平產業向高技術水平產業的演進。參照傳統分析,采用高端技術制造業產值占制造業總產值比重(G1)來反映制造業高級化,但是這一方法并不能準確反映中端技術制造業變動對制造業高級化的影響:即便低端技術產業比例下降,中高端技術產業的比例卻可以同時上升,而高端技術產業比例上升幅度可能小于中端技術產業。因此本文采用高端技術制造業和中端技術制造業之比(G2)進一步測度制造業高級化的變動。兩種方法測算制造業高級化也分別采用制造業的總產值、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計算,這樣模型(3)可細分為6個模型:模型(3a)至模型(3f);模型(6)也細分為6個模型:模型(6a)至模型(6f)。
2.解釋變量
借鑒已有研究如羅長遠(2007[31])、韓劍和鄭秋玲(2014[32])、趙勇和魏后凱(2015[33])的處理方法,核心解釋變量政府干預度(GI)采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或財政支出占GDP比重來表示,但是財政收入是制造業結構變遷的結果,而財政支出具有更強的政策導向,因此選擇用財政支出與GDP之比來表示政府干預*關于政府干預的測度指標,國內不少權威期刊也是采取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測度,即使有些變化,也是在此基礎上延伸出來的。為了考察研究結果的穩定性,我們在穩定性檢驗中增加運用泛珠三角地區9省區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進行測度政府干預,因為國有企業是中國政府進行干預的重要載體,實證結果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研究結論一致。。從理論上看,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制造業結構的影響始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正式實施之時,因此可以采用虛擬變量考察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泛珠三角經濟一體化戰略實施于2004年,考慮到其影響的滯后性,2004年及以前RI值為0,2004年以后對應RI值為1。
控制變量如經濟發展水平(ED)用人均GDP測度;對外開放度(OD)用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測度,即進出口總額/GDP;市場化過程在我國可以理解和表現為經濟成分的變動,故本文用非國有企業銷售額占全部銷售額比例來測度市場化程度(NS)。
(三)數據說明
本文選擇了1996~2012年泛珠三角9個省區制造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對于被解釋變量,各省區的制造業產值、固定資產凈值和就業人數來自于國研網和各省統計年鑒;各省區的財政支出、各省區的GDP值、各省區的年末人口、各省區的進出口總額、各省區的非國有企業銷售額和全部銷售額數據主要來源于中經網,部分數據來源于對應年份的各省區統計年鑒*四川省制造業工業增加值數據為1996~2007年,貴州省制造業固定資產凈值數據為1996~2007年,廣西省缺少2012年制造業工業增加值數據,云南省制造業固定資產凈值缺少2008~2011年數據。個別缺失數據用插值法補齊。。
四、檢驗結果
對上述模型進行系統GMM估計,并利用Collapse選項控制工具變量過多造成自由度損失而導致的偏誤。具體來看,模型(1)至模型(2)的估計結果列入表1,模型(3)的估計結果列入表2,模型(4)至模型(5)的估計結果列入表3,模型(6)的估計結果列入表4。從結果來看,二階自相關檢驗和Hansen檢驗對應的p值均顯著大于0.1,這說明接受模型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和過度識別正確的原假設,即模型的設定以及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理的。
1. 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檢驗結果
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只考慮政府干預GI或者經濟一體化戰略RI所帶來的影響效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模型(1)至模型(2)的GMM估計
注:表中*、**、***、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顯著,括號里面為t統計值;一階自相關、二階自相關和Hansen檢驗數值為伴隨概率P, C表示各公示中對應的常數項C1和C1。下表均相同。
從表1可以看出模型(1a)、模型(1b)和模型(1c)的估計結果。結果表明,GI的估計系數均為正,RI的符號不一致,但均不顯著;這說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干預和經濟一體化對泛珠三角區域制造業分工沒有顯著影響。模型(2)的估計結果顯示,在模型(2a)和模型(2c)中GI的估計系數為為正,在模型(2b)中GI的估計系數為負,在3種情況下RI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但是GI、RI均不顯著。因此,假若其他因素不變,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或者經濟一體化對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合理化水平沒有顯著影響。
從表2可知,GI的估計系數在模型(3a)、模型(3c)和模型(3e)中為負值,在其他3種情況下則為正值,但GI的系數在6種情況下均不顯著。RI的估計系數在六個子模型中均為負且都不顯著。這就說明,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或者經濟一體化對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高度化也沒有顯著影響。
2.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檢驗結果
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考慮政府干預GI和經濟一體化戰略RI所帶來的綜合影響效果,如表3和表4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政府干預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連乘項(GI·RI)的估計系數在模型(4a)中為0.206,顯著水平為1%;模型(4b)中GI·RI的系數為1.15,顯著水平達到1%;模型(4c)的GI·RI系數為0.511,顯著水平達到5%。也就是說,其他條件不變,連乘項每變動0.1,制造業分工指數同向變動0.02~0.12。結合模型(1)和模型(4)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或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內制造業分工沒有顯著影響,而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作用則顯著促進了區域內制造業分工。

表2 模型(3)的GMM估計

表3 模型(4)至模型(5)的GMM估計
模型(5a)和模型(5b)中GI·RI的系數分別為-0.054和-0.073,顯著性水平均為10%,模型(5c)中的GI·RI系數為-0.045,顯著性水平達到5%,這也意味著政府干預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作用顯著提高了制造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具體來說,GI·RI增加0.1,泰爾指數會下降0.005~0.007,即制造業結構合理化水平上升0.005~0.007。因此,比較模型(2)和模型(5)估計結果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或區域經濟一體化沒有顯著影響區域制造業結構的合理化;而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借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手段,或者說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借助于政府干預手段,顯著提升了區域內制造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
從表4可知,在模型(6a)、模型(6b)和模型(6c)中GI·RI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55、-0.146和-0.465,且均在5%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GI·RI增加0.1,泛珠三角地區高端技術產業的比例降低0.006~0.047。在模型(6d)、模型(6e)和模型(6f)中GI·RI估計系數分別為-1.210、-0.736和-0.811,顯著水平均為1%、10%和5%,意味著GI·RI增加0.1,高端技術產業與中端技術產業之比下降0.074~0.121。比較模型(3)和模型(6)的結果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沒有顯著影響制造業的高級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基本沒有影響制造業的高級化;但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借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手段,或者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借助于政府干預手段,顯著阻礙了制造業結構升級。
3.穩健性討論
為了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對于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分別利用不同指標來檢測。第一,被解釋變量方面:用來反映制造業結構優化的三個被解釋變量(產業分工、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使用了制造業的總產值、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三種維度計算,其中制造業高度化進一步利用高端技術制造業產值比重和高中端技術制造業產值之比兩個指標來衡量。從我們關注的變量的計算結果來看,各個模型以及對應子模型的結果是高度一致的:從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來看,GI和RI在各個子模型中的系數都不顯著;從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來看,GI·RI在各個子模型中的系數符號都一致且均為顯著。第二,對于核心解釋變量政府干預程度,在使用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比重來分析,兩種測度指標檢驗結果高度一致*由于論文篇幅的限制,論文只提供了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的政府干預的計算結果,省略了國有工業總產值占比表示的政府干預的詳細計算過程和結果。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在沒有考慮交互項的時候,也就是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均沒有顯著影響制造業的產業結構趨同、合理化和高度化;當引入了交互項之后,也就是在考慮身份治理情況下,政府干預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互作用,降低了制造業產業同構化,提高了合理化但不利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提升。實證結果非常穩健。

表4 模型(6)的GMM估計
五、研究結論及啟示
1.研究結論
前文的理論分析表明,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過程中,由于政府主導帶來的身份治理效應具有雙重性,導致了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具有不確定性。利用1996~2012年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面板數據,運用GMM估計法檢驗發現: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或者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均不顯著,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政府干預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連乘式即政府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影響非常顯著。具體來說,政府干預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連乘項對3個維度測度的制造業分工均有正向作用,對3個維度測度制造業結構的合理化均具有正向作用,對6種方法測度的制造業結構高度化具有負向作用。也就是說,政府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借助于身份治理和市場機制的相互作用促進了區域內制造業分工發展、提高了制造業合理化水平,但降低了制造業高級化水平。
2.對研究結論的解釋
在不考慮身份治理影響情況下,為什么政府干預、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3個維度測度的結構優化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也就是說,政府主導往往會形成行政壟斷,行政壟斷對制造業結構優化產生重要影響。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其根本的表現形式是地方政府憑借行政權力對市場配置資源進行干預甚至替代,這一因素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是政府干預形成行政壟斷,由此形成了產業政策扭曲、地方保護、市場分割等資源配置歪曲行為,抵消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正面作用,制約了區域制造業的差異化發展。二是在沒有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之前,由于缺乏共同目標的約束,區域內部各政府之間各自為政,為了追求各自財政收入,各地政府采取相應優惠政策等手段和措施,吸引甚至爭奪利益比較高的制造業,重復投資的結果導致制造業同構化,偏離了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所要求的分工協調發展目標。在我國目前的行政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經濟發展目標無形中加強了地區行政壟斷的力量,這一作用力能夠改變其他因素比如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合理化的形成,也制約了制造業向高度化發展。
在考慮身份治理影響的條件下,為什么政府干預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泛珠三角地區制造業3個維度測度的結構優化影響顯著?這是因為,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政府干預與經濟一體化發展機制交互作用,對地區制造業結構優化形成了一種綜合影響力。
第一,如前所述,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身份重新界定的過程。上級政府通過對區域身份的重新定位,將使區域組織獲得資源配置的新權力,從而推動區域內部各省區選擇與自身身份定位相適應的制造業發展模式,這會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區域制造業的差異化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盡管各省區行政壟斷因素依然存在,但由于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是一個較為深入合作的經濟體,十多年來合作的發展造就了區域合作強有力的合作機制。比如,形成了以各省區行政首長為主要成員的協調委員會,成立了常設工作機構——協調委員會秘書處,并形成了以各省區政府各部門為運作機構成員的運作機制。這種機制強有力的保證了區域整體目標的推行,在運作的過程中,盡管不可避免會有些省份偏離總目標,但制度的約束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這種偏離的程度,從而保證區域內部制造業結構向差異化和合理化方向發展。
第二,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泛珠三角地區9省包含了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地帶的省區,區域內9個省區在其所處的區位中具有多重身份特征,區位的差異帶來區域內各省區追求制造業發展路徑的不一致。比如廣西、江西、湖南、福建、四川,除同屬于泛珠三角經濟區之外,廣西同時又處于西部大開發區和處于環北部灣發展區;江西、湖南同時處于中部開發區;福建同時處于西岸開發區;四川同時處于成渝經濟合作區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試驗區,等等。這些不同的身份特征形成了綜合的身份治理效應,進一步強化了各省區制造業向分工差異化發展和合理化發展。
第三,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通過身份治理不僅能夠減少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還可以內化區域之間的交易成本,克服區域之間的負外部性,尤其是可以阻止負外部性以乘數效應進行擴散(劉普、李雪松,2009[34])。具體到區域制造業轉移問題上,一方面是受到成本制約以及利益關系制約而導致制造業轉移困難,尤其是高附加值制造業的轉移更為困難,使得各省區的制造業發展在原有路徑依賴的約束下出現差異化,客觀上促進了區域制造業結構向合理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產業升級可以看成是企業以及產業整體在價值鏈或者價值鏈間的攀越過程,制造業高級化的過程就是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的產業與高附加值的環節升級的過程(Gerrifi,1999[35];馬珩,2012[36])。但政府主導所推動的產業擴散過程加劇了區域產業結構的沖突,主要體現為由于區域內部各省區經濟利益的競爭導致制造業轉移中高附加值產業轉移不易,因此,各省區的產業轉移往往以低附加值產業外推的方式來轉移,形成了相對多地區從事低端制造業的格局,使得制造業結構高度化受到影響。
3.幾點啟示
基于前面實證的結果,考慮到我國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是不爭的事實,本文在結合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和《中國制造業2025年規劃》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精神的基礎上,得到了對區域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幾點有益啟示:(1)運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來推進區域制造業的協調發展和合理化發展。在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過程中,借助于身份治理,可以通過系列不同層次的協調機構和協調協議等方式,構建區域共同目標約束機制。在共同目標約束下,借助于身份治理手段及相應政策工具去推動區域制造業的分工合作和合理化布局,推進區域制造業的差異化和合理化發展。(2)利用區域內部多層次身份治理的機制來調整和優化區域制造業結構。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過程中,同一區域的地方政府往往處于不同的身份治理結構中,從而形成了影響制造業轉移和制造業結構優化的復雜機制,我們要充分挖掘、發揮這種身份治理影響制造業結構優化的正面功能,引導制造業在區域內部及區域之間的有序轉移,在推進制造業空間合理布局的基礎上,推進制造業結構的高級化。(3)借助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市場一體化機制來推進和優化區域制造業結構。政府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能夠逐步消除區域內部的隔閡,促進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在一個特定的政府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區內,要注意通過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水平來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通過完善市場化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促進產品與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在推動經濟活動高效集聚的過程中去實現區域制造業的分工差異化和合理化發展,引導區域制造業結構向高度化發展。
[1] Henderson J V,Quigley J,Lim E. Urbanization in China: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Z].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rown University, 2009.
[2] Henderson J V, Shalizi Z,Venables A.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phy, 2011,1(1): 81-105.
[3]陳喜強. 中國城市基層社區組織身份治理模式研究[M]. 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1.
[4]劉瑞明. 晉升激勵、產業同構與地方保護:基于政治控制權收益的解釋[J]. 南方經濟,2007(6): 61-72.
[5]王燕武,王俊海. 地方政府行為與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的理論及實證分析[J]. 南開經濟研究, 2009(4): 33-48.
[6]溫鐵軍,謝 欣,高 俊,董筱丹. 地方政府制度創新與產業轉型升級——蘇州工業園區結構升級案例研究[J]. 學術研究,2016(2): 82-89.
[7] McCann P,Acs Z J. Globalization:countries,cities and multinationals [J]. Regional Studies,2011, 45(1): 17-32.
[8] Barca F, McCann P,Rodriguez-Pose A. The cas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place-based versus placeeutral approaches[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2, 52(1): 134-152.
[9]皮建才. 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機制研究[J]. 經濟學家,2011(12): 15-22.
[10]傅元海,葉祥松,王展祥. 制造業結構優化的技術進步路徑選擇——基于動態面板的經驗分析[J]. 中國工業經濟,2014(9): 78-90.
[11]孫寧華,韓逸平. 地區專業化與制造業結構優化——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J].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1): 34-44.
[12]趙 祥. 集聚還是分散——兼論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策略[J]. 產業經濟評論,2010(3): 87-108.
[13]朱希偉,陶永亮. 經濟集聚與區域協調[J]. 世界經濟文匯,2011(3): 1-25.
[14]張延愛. 中國工業經濟區域協調發展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 企業經濟,2011(9): 86-89.
[15]葉 琪. 我國區域產業轉移的協調效應及發展趨勢[J]. 當代經濟管理,2014(1): 66-71.
[16]陳建軍. 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同構及其產業定位[J]. 中國工業經濟,2004(2): 19-26.
[17]蔣伏心,蘇文錦. 長三角高新技術產業同構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基于空間計量經濟的實證分析[J]. 江蘇社會科學,2012(3): 77-82.
[18]張秀萍,余樹華. 泛珠三角產業集群與區域競爭力問題探析[J]. 南方經濟,2005(12): 98-100.
[19]黃新飛,鄭華懋. 區域一體化、地區專業化與趨同分析[J]. 統計研究,2010(1): 90-96.
[20]周 詩,胡曉鵬. 泛珠三角區域制造業集聚與轉移:2003-2010年[J]. 社會科學家,2013(4): 62-64,68.
[21]銀溫泉,才婉茹. 我國地方市場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 經濟研究, 2001(6):3-12.
[22]陸 銘,陳 釗. 分割市場的經濟增長——為什么經濟開放可能加劇地方保護[J]. 經濟研究,2009(3):42-52.
[23]徐現祥,李 郇,王美今. 區域分割、經濟增長與政治晉升[J]. 經濟學季刊[J]. 2007(4):1075-1095.
[24]卜茂亮,高彥彥,張三峰. 市場一體化與經濟增長:基于長三角的經驗研究[J]. 浙江社會科學,2010(6):11-17.
[25]盛 斌,毛其淋. 貿易開放、國內市場一體化與中國省際經濟增長:1985~2008年[J]. 世界經濟,2011(11):44-66.
[26]于良春,付強. 地區行政壟斷與區域產業同構互動關系分析[J]. 中國工業經濟,2008(6): 56-66.
[27]劉傳江,呂力.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制造業空間擴散與區域經濟發展[J].管理世界,2005(4): 35-39.
[28]陳飛翔,居 勵,林善波.開放模式轉型與產業結構升級[J].經濟學家,2011(4): 47-52.
[29]于 澤,徐沛東. 資本深化與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基于中國1987~2009年29省數據的研究[J].經濟學家,2014(3): 37-45.
[30]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 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11(5): 4-16.
[31]羅長遠. FDI與國內資本:擠出還是擠入[J]. 經濟學(季刊), 2007(2):381-400.
[32]韓 劍,鄭秋玲. 政府干預如何導致地區資源錯配——基于行業內和行業間錯配的分解[J]. 中國工業經濟, 2014(11): 69-81.
[33]趙 勇、魏后凱. 政府干預、城市群空間功能分工與地區差距——兼論中國區域政策的有效性[J].管理世界,2015(8):14-29.
[34] 劉普,李雪松. 外部性、區域關聯效應與區域協調機制[J]. 經濟學動態,2009(3): 68-71.
[35]Gerefft,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1(48):37-70.
[36]馬 珩. 制造業高級化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及其實證研究[J]. 南京社會科學,2012(9): 30-32.
(本文責編:王延芳)
ResearchontheImpactsoftheGovernment-led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StrategyonStructualOptim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ACaseStudyofthePan-PearlRiverDeltaRegion
CHEN Xi-qiang1, FU Yuan-hai1, LUO Yun2
(1.SchoolofEconomicsandStatistics,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oguanUniversity,Shaoguan512005,China)
F120.4
A
1002-9753(2017)09-0069-13
2017-03-11
2017-08-3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一般項目(7147305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4YJAZH007)。
陳喜強(1964-),男,廣西靈山人,廣州大學經濟與統計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及管理、產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