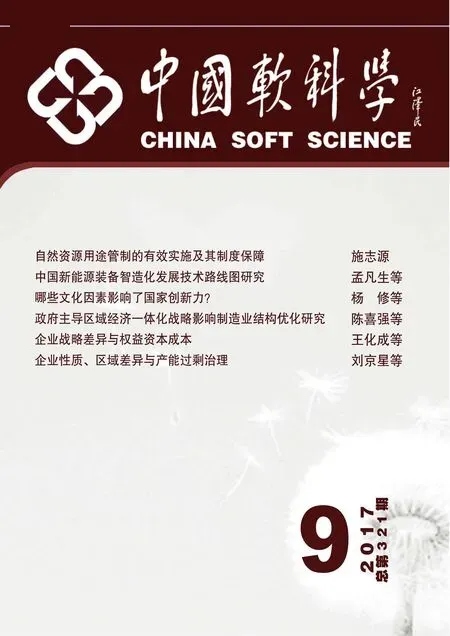財稅政策對中國綠色發展的影響研究
——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檢驗
王全良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河南 鄭州 450046)
財稅政策對中國綠色發展的影響研究
——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檢驗
王全良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河南 鄭州 450046)
文章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測算了2000——2014年中國30個省份的生態效率,將生態效率衡量區域綠色發展水平,運用空間杜賓模型檢驗財稅政策對中國綠色發展的影響。研究表明,資本投入效應顯著為正且具有積極的空間溢出效應,公共服務效應和綠色財政效應的作用很不顯著,社會監督效應并未提升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對此,本文提出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對要素資源配置優化作用,加強公共服務的財政支持力度,強化財稅政策的社會監督功能,扎實推進環保投入和落后產能調整的財政支持,優化區域綠色發展的財稅制度設計,實現地區經濟與環境保護的共贏式發展。
財稅政策;綠色發展;生態效率;空間溢出效應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method to measure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measur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by us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use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test the effects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on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capital investment is positive and has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the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effect and green fiscal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social supervision effect has not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to optimize the rol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public services, strengthen the social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y adjustment, and optimize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design, to achieve win-wi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Keywords: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fficienc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環境污染作為代價的。當前,我國環境污染嚴重,霧霾天氣呈現頻發性、全國性態勢,且短期難以消除;地下水超采嚴重,飲用水安全堪憂;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生態系統退化,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37%,沙化土地占國土總面積的18%,這些現象凸顯我國走綠色發展之路的艱巨性。我國區域綠色發展的本質是通過減少對資源過度消耗,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追求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研究發現,單純就綠色發展的效率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如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北京等地綠色發展水平整體顯著高于全國其他地區。究其原因,當地政府有力的財政稅收政策支持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當前,財稅政策支持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提升區域發展“綠色度”已上升為國家“十三五”時期的重要戰略,如何合理而充分地發揮財稅政策對區域綠色發展的支撐作用,對未來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財稅政策對中國地區環境影響的研究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財政政策對區域環境的影響。多數學者關注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對區域環境質量的影響。如,閆文娟[1]對1999-2008年30個省區的研究發現,財政分權通過刺激地區政府競爭降低了當地環境質量;而吳俊培等[2]基于2003-2012年中國省區層面的研究發現,財政分權降低環境質量作用的發揮會受到當地收入水平的顯著影響;王敏和胡漢寧[3]從“縱向財政競爭”和“橫向財政競爭”兩個層面,探討了當前財政分權對地區環境質量的主要影響機制。此外,財政支出對地區環境的影響也是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方面。如,王藝明等[4]利用省區數據研究發現,生產性財政支出顯著增加了地區碳排放,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對地區排放則有顯著抑制作用;馮海波和方元子[5]利用城市層面數據研究發現,財政支出對地區環境質量的影響可以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的直接效應、刺激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兩個渠道產生,財政支出整體降低了地區環境質量;顧程亮等[6]對省區層面的研究發現,財政節能環保支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受到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地區發展水平越高,環保財政支出的積極效果越顯著。第二,稅收政策對區域環境的影響。眾多學者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模擬分析環境稅對地區環境的影響。如,童錦治和沈奕星[7]的研究發現,環境稅減免對地區環境質量造成了長期負面影響;梁偉等[8]的研究發現,科學合理的環境稅可以有效地實現地區二氧化碳減排和就業增加“雙重紅利”的實現;梁偉等[9]的研究發現,對于地區節能減排來說,消費型環境稅比生產型環境稅的效果要更加顯著。一些學者借助經濟理論模型探討環境稅對區域環境污染的影響。如,馬草原和周亞雄[10]基于污染外部性新經濟地理模型框架對環境稅影響的研究發現,差異化稅率的環境稅征收有利于地區環境質量改善;范慶泉等[11]利用包含動態環境稅、污染累積的宏觀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發現,動態環境稅政策更有利于地區節能減排和經濟增長目標協同發展。稅收政策對中國環境污染影響的實證研究則相對少見。李建軍和劉元生[12]利用2001-2013年省區數據,實證考察了企業所得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等不同稅種對區域環境質量的影響。第三,財稅政策對環境的影響方面。多數學者側重于探討促進環境質量改善的財稅政策改革思路。如,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13]圍繞節能減排、清潔能源發展和低碳城市建設等問題,探討了財稅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何利輝[14]從財政資金投資方向、財稅結構調整等方面探討了促進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改革思路;楊志安和王金翎[15]則集中探討了財稅政策在支持環保產業發展、改善地區環境質量方面的改革方向和著力點。財稅政策地區環境效應的實證研究則極為少見,只有王振宇等[16]利用生態足跡法對遼寧省財稅政策的環保效應進行了簡要探討。
整體來看,財稅政策對地區環境的影響方面,國內學者已經做出了較多探索。國外學者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不同環境稅制的政策比較、利用CGE模型對環保財稅政策效果的模擬、環境稅收對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分析等幾個方面[11]。但是,財稅政策對中國綠色發展的影響機制,現有文獻尚無系統的梳理和總結;財稅政策整體對地區綠色發展的研究仍以改革思路的探討為主,缺乏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而且,財稅政策作為區域競爭的重要手段,不僅影響本地經濟增長,還影響周邊區域的經濟增長,即會產生空間溢出效應[17],但基于空間溢出效應考察財稅政策對地區綠色發展的研究更加少見。因此,在系統梳理財稅政策影響地區綠色發展機制基礎之上,文章利用中國30個省區的2000—2014年的面板數據,將空間相關性納入財稅政策與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效應當中,試圖厘清財稅政策影響中國綠色發展的作用機理,為提出財稅政策在中國綠色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提供決策依據。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理論分析
中國綠色發展要求以更少的資源投入實現更高的經濟產出和減少環境污染,從而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財稅政策影響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作用包括資本投入效應、公共服務效應、社會監督效應和綠色財政效應。資本投入效應就是通過稅收收入擴大資本投入規模,使得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創新而獲得經濟產出;公共服務效應就是通過民生投入到資源利用效率高的地區,從而提升地區綠色發展和經濟產出水平;社會監督效應就是通過監督社會腐敗而提高地區資源利用效率,可以降低綠色發展中的環境污染等壞產出的數量;綠色財政效應就是通過對地區綠色和環保產業等提供資金和稅收優惠,對環境污染較大的產業征收環境稅,進而有效降低環境污染等壞產出。綜上所述,財稅政策對區域綠色發展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為了檢驗區域間的擴散或者回流效應,下文將通過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考察。
(二)模型設定
地方政府間的財稅政策與環境保護的互動通常具有空間外溢效應。文章將以財稅政策影響綠色發展的資本投入效應、公共服務效應、社會監督效應和綠色財政效應的指標作為主要變量,通過建立空間面板回歸模型實證考察財稅政策對環境保護的空間溢出效應。空間面板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度量鄰近地區生態效率誤差引起的溢出效應對本地區生態效率的影響[18]。其模型表達式如下:

(1)
空間面板滯后模型(SLM,Spatial Lag Model)研究的是相鄰地方政府生態效率間的直接攀比影響,實證檢驗的是鄰近地區的生態效率對本地區生態效率的影響,
yit=ρWyit+βXit+μi+νt+εit
(2)
空間杜賓模型(SDM,Spatial Dubin Model)綜合考慮SEM模型和SLM模型構建同時包含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滯后項的計量模型[19],以此捕捉不同來源所產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應[20],其模型表達式如下:
yit=ρWyit+βXit+θWXit+μi+νt+εit
(3)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表示地區性,νt表示時間性擾動項,εit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擾動項。ρ為空間滯后系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β反映的是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影響變量Xit包括財稅政策變量和其他控制變量。其中,控制變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科技進步水平和人口密度。文章選擇混合權重矩陣進行空間計量權重設定,具體形式為Wm=Wd·We,其中Wd為地理權重矩陣,We為經濟權重矩陣。
(三)測算方法與數據來源
被解釋變量為中國區域綠色發展,本文用區域生態效率表示當地綠色發展水平。區域生態效率,是指在某個經濟區域內“以較少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生產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人類需要和改善生活”,其核心是少投入、少排放、多產出,是在不對生態環境構成威脅的前提下努力發展區域經濟,因而符合可持續發展有關經濟、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核心理念,成為測度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概念和工具[21]。文章以測度的生態效率(eco-eff)作為代理變量[21-22],目前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測度生態效率,以期達到以較少的資源投入實現較高的經濟產出和綠色發展[23],文章將借助Tone[24]把非期望產出引入到非徑向和非角度的方向性距離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 model,SBM)來測度生態效率。楊斌[25]、成金華等[26]用固定資本存量、就業人數、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用水總量、能源消費總量等作為投入變量反映資源約束,以GDP代表好產出,用環境污染物排放量代表壞產出來反映環境約束。為充分考慮各種環境污染物構成的綜合環境污染程度,參考黃建歡和呂海龍等[27]的做法并根據數據可得性,考慮的污染物包括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水中污染物化學需氧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六種。
財稅政策影響綠色發展的資本投入效應、公共服務效應、社會監督效應和綠色財政效應的指標選取如下:資本投入效應以人均地方政府收入(fiscal-re)表示,公共服務效應以政府人均民生支出(liveli)表示,社會監督效應用財政違規資金(illegal)表示,綠色財政效應以環境規制(reg)表示[28],我國目前沒有開征環境稅,文章選用環境類稅收占第二產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29]。控制變量方面:①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各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衡量[30]。②技術進步水平(techno)采用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項專利的年授權數來衡量區域的技術水平。③人口密度(popden)用人口密度用各地區總人口除以行政區面積表示。相應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檢察年鑒》、《中國法律年鑒》以及各省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
三、計量結果與分析
(一)區域生態效率的時空變遷
文章選取除港澳臺地區和西藏外的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00—2014年的數據作為樣本,分析我國區域生態效率的時空變遷。文章根據分布動態非參數估計方法,采用Kernel核密度函數分析方法考察中國區域生態效率時空分布的動態演變模式。
圖1是運用核密度分析中國生態效率變化,分別選擇2000年、2007年和2014年的核密度水平,從時間跨度分析中國區域生態效率的變化情況。由核密度曲線的可知,中國省域生態效率水平空間分布演進受到自身地理相鄰省域生態效率高低的影響。相鄰省域生態效率趨向一體化方向發展,區域間生態效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近鄰效應解釋。中國生態效率的分布呈現多峰,分布密集區處于1.0左右,說明中國絕大多數省域生態效率在全國平均水平之間;此外,“次峰”說明中國生態效率演進存在俱樂部收斂趨勢。2000-2014年的生態效率主峰值不斷減小,波峰變得平緩,這表明中國省域生態效率低水平的集中程度在下降,“高生態效率俱樂部”與“低生態效率俱樂部”之間的差距在減小,組成空間上鄰近的“俱樂部趨同”,導致區域間生態效率產生明顯的非均衡發展狀態。

圖1 中國生態效率的Kernel密度估計圖
圖2顯示了2007年、2014年中國生態效率的區域分布。通過兩年區域生態效率的比較,本文從空間維度分析了中國生態效率的變化情況。由圖2可知,通過探索性空間相性檢驗研究發現,中國區域生態效率呈現出“東高西低,逐漸擴散”的非均衡性發展狀態。以東部地區“高高集聚”的核心區域,以中部地區“高低集聚”、“低高集聚”,以西部地區“低低集聚”的外圍區域分布特征。具體而言,東南部沿海地區和京津地區保持較高生態效率狀態,中西部地區的區域生態效率在逐步下降,與東部地區的差距逐漸擴大。生態效率較高的區域往往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而生態效率相對較低的中西部省份往往也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這初步說明兩者具有較高程度的空間相關關系。

圖2 2007年、2014年中國生態效率地區分布圖
(二)空間溢出效應的檢驗
為了避免空間面板模型計量的偽回歸問題,采用同質性LLC檢驗和異質性Fisher-PP檢驗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所有回歸變量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進而可以運用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進行面板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可以進一步做空間計量檢驗。選擇混合權重矩陣進行空間計量權重設定,即考慮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的交互影響對我國區域環境污染治理的影響,具體形式為Wm=Wd·We,其中Wd為地理權重矩陣;We為經濟權重矩陣。為了確保空間權重矩陣每行元素之和等于1,對構造的空間權重矩陣進行標準化(row-normalization)處理(見表1)。
空間面板誤差模型(SEM)和空間面板滯后模型(SLM)參數估計結果表明,空間面板估計模型中Hausman檢驗的P值小于0.1,因此文章選擇空間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實證分析。文章中LMlag檢驗的統計量比LMerror檢驗的統計量大,而且SLM模型的調整R-squared和對數似然值相對于SEM模型的整體數值較大且擬合效果更好。因此,選擇SLM模型分析財稅政策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效應更為合適。空間自回歸系數(ρ)為正,說明鄰區綠色發展對本地區綠色發展的具有一定影響,區域間綠色發展存在空間競爭。因此,文章接著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分析包含外部性和溢出效應的影響作用,SDM模型的擬合程度在0.729-0.818之間,證明中國財稅政策促進區域綠色發展在地區分布確實存在空間自相關性。本文的實證結果的解釋以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果為基準,以更加客觀全面地考察財稅政策對本地綠色發展的影響和其他區域綠色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見表2)。

表1 財稅政策影響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的空間面板模型估計結果
注:*、**、***分別代表在10%、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變量圓括號內的數值是回歸系數統計量的穩健標準誤,Hausman、LMerror和LMlag檢驗方括號內的數值是P值。模型I、V采用的是鄰接權重矩陣;模型II、VI采用的是地理權重矩陣;模型III、VII采用的是經濟權重矩陣;模型IV、VIII采用的是混合權重矩陣。下同。
人均地方政府收入(fiscal-re)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且估計系數為正。近年來,隨著國家日益重視環境保護,以綠色發展為考核指標的體制性因素,能夠提供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有效推動地區綠色發展[1]。W×fiscal-re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鄰地區人均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將能夠提高當地綠色發展,即區域間貿易保護主義工具的綠色貿易壁壘,促進了區域間綠色發展競爭[2]。政府人均民生支出(liveli)和W×liveli對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可能是,地方政府對民生支出的力度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對環境保護的公共財政支出力度仍需有效增加導致的[5]。財政違規資金(illegal)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且估計系數為負。這說明,政府通過提高環境治理技術研發投入資金,監督治理力度不夠,沒能有效提高環境污染治理水平[31]。W×illegal的系數顯著為負,即相鄰地區財政違規資金越高會惡化本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環境規制(reg)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隨著我國地方政府提高環了境污染治理投資在政府環境中的比重,然而對企業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政策激勵作用相對不足,導致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效果不理想[9]。W×reg的系數顯著為負,即相鄰地區環境規制將會抑制當地綠色發展。地方政府間在綠色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利益博弈,不利于實現經濟、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1]。在其它控制變量中,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估計系數為負。國外資金涌入是的產業結構鏈的“切片”,導致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產業通過外包形式轉移到我國,從而加劇本地區環境污染[31]。W×fdi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科技進步水平(techno)和W×techno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人口密度(popden)和W×popden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系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國家環境保護政策主要是針對生產者進行環境保護的引導工作,而缺乏對消費者行為的約束,導致我國民眾對于環保的參與度較低、環保意識不夠[16]。

表2 財稅政策影響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的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基于2000-2014年中國30個省區的數據,在對財稅政策影響地區綠色發展的主要機制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采用面板空間計量方法,將空間相關性納入財稅政策與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效應當中,較為系統地考察了財稅政策對本地區綠色發展的影響和對其他區域綠色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發現,中國省區綠色發展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空間計量估計顯示,財稅政策的資本投入效應顯著促進了本地和鄰近區域的綠色發展水平,財稅政策的社會監督效應則降低了本地和鄰近區域的綠色發展水平;財稅政策的公共服務效應、綠色財政效應對本地以及鄰近區域綠色發展分別產生了負面、積極影響,但統計上都不顯著。因此,本文對“十三五”時期中國財稅政策調整、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制定,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加強財政資金對實體經濟發展的穩定支撐作用,發揮財稅政策優化要素資源配置和對技術創新的支撐作用,夯實地區綠色發展的經濟基礎。政府要適度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以彌補“減稅降費”帶來的減收下降,并對實體經濟產生支撐作用;適度擴大各級財政支出規模,全面盤活存量財政資金,確保財政支出強度不減且實際支出規模擴大,保證經濟在合理區間穩定增長。繼續“落實并完善營改增試點政策”,進一步清理規范基金和收費,加大取消、調整和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力度,擴大稅費減免對實體經濟的積極效應,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繼續加強對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自主創新示范區等“創新”驅動園區的稅收優惠政策,繼續保持對園區內部企業所得稅收的減免,減輕高新技術企業技術轉讓和與技術轉讓有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培訓的稅收負擔,加強對高新技術園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和生產性、經營性基本建設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為地區經濟發展轉型提供更多科技創新支撐,夯實地區綠色發展的經濟基礎。
第二,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對社會公共服務提升的支撐作用,全面改善優化地區綠色發展的社會環境。各級政府要加大對就業培訓、就業援助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繼續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財稅優惠,保障社會就業穩定,激發地區綠色發展的經濟活力;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和個人繳費標準、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財政補助標準,合理提高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落實和完善支持養老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提升地區綠色發展的社會保障;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兩免一補”政策,加強城鎮義務教育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的財政支持力度,為薄弱學校辦學條件改善提供充足資金支持,優化地區綠色發展的人力資本條件。
第三,積極強化財稅政策的社會監督功能,大力查處環保領域財政資金腐敗問題,為地區綠色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各級政府部門加強預算執行管理,在促進依法征管、應收盡收的同時,堅決防止和糾正收取“過頭稅”以及采取“空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的行為;硬化預算約束,嚴格控制預算調整事項,建立健全的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機制。同時,加強對環保領域資金的審查監督力度,確保污染治理資金專項專用;嚴厲打擊騙取、套取財政環保資金行為,堅決糾正制止擠占、挪用環保資金行為;科學評估環保項目投入產出效率,對造成環保資產嚴重閑置、損失浪費的責任單位進行嚴厲查處,嚴格保障地區綠色發展財政資金投入的實際效果。
第四,扎實推進環保落后產能調整的財政支持,加大環境治理資金投入、優化區域綠色發展的財稅制度設計,為地區綠色發展提供良好的財政資金支持。地方政府要更加嚴格地執行環保、能耗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繼續發揮財政資金對落后產能調整中的支持作用,堅決淘汰環保不達標的落后產能,為地區產業綠色發展騰出有效空間;繼續加大財政對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財政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點工程項目,全面推進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修復工程,進一步落實新一輪草原生態保護財政補助獎勵政策,為地區綠色發展提供良好的生態基礎;加大節能環保產業的財政資金支持,促進地區綠色產業持續健康發展,著力推進礦產資源權益金制度改革、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的優化設計,加快推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范圍擴大,使環境改善與經濟發展實現雙贏。
[1]閆文娟.財政分權、政府競爭與環境治理投資[J].財貿研究,2012(5): 91-97.
[2]吳俊培,丁瑋蓉,龔旻.財政分權對中國環境質量影響的實證分析[J].財政研究,2015(11): 56-63.
[3]王 敏,胡漢寧.財政競爭對中國環境質量的影響機理及對策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5(10):164-169.
[4]王藝明,張 佩,鄧可斌.財政支出結構與環境污染:碳排放的視角[J].財政研究,2014(9):27-30.
[5]馮海波,方元子.地方財政支出的環境效應分析: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考察[J].財貿經濟, 2014(2):30-43.
[6]顧程亮,李宗堯,成祥東.財政節能環保投入對區域生態效率影響的實證檢驗[J].統計與決策, 2016,(19):109-113.
[7]童錦治,沈奕星.基于CGE模型的環境稅優惠政策的環保效應分析[J].當代財經,2011(5): 33-40.
[8]梁 偉,張慧穎,姜 巍.環境稅“雙重紅利”假說的再檢驗:基于地方稅視角的分析[J].財貿研究, 2013(4):110-117.
[9]梁 偉,朱孔來,姜 巍.環境稅的區域節能減排效果及經濟影響分析[J].財經研究,2014(1): 40-49.
[10]馬草原,周亞雄.配套型環境稅、技術進步與污染治理: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5(2):118-135.
[11]范慶泉,周縣華,張同斌.動態環境稅外部性、污染累積路徑與長期經濟增長:兼論環境稅的開征時點選擇問題[J].經濟研究,2016(8):116-128.
[12]李建軍,劉元生.中國有關環境稅費的污染減排效應實證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8):84-91.
[13]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中國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J].財貿經濟,2011(10):11-16.
[14]何利輝.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的財稅政策探討[J].財政科學,2016(7):118-125.
[15]楊志安,王金翎.新常態下財稅政策支持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16(2): 71-79.
[16]王振宇,連家明,郭艷嬌.生態文明、經濟增長及其財稅政策取向:基于過寧生態足跡的樣本分析[J].財貿經濟,2014(10):32-40.
[17]管彥慶,劉京煥,王寶順.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政策空間依賴實證研究:基于政府效率的視角[J].當代財經,2014(3):38-47.
[18]LESAGE J P, PACE R K. Introduction tospatial econometrics [M]. Boca Raton,US: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19]ANSELIN L, REY S. Properties of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1, 23(2):112-131.
[20]ANSELIN L. 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88.
[21]李勝蘭,初善冰,申晨.地方政府競爭、環境規制與區域生態效率[J].世界經濟,2014(4): 88-110.
[22]張雪梅.西部地區生態效率測度及動態分析:基于2000-2010年省際數據[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2):78-85.
[23]王 兵,吳延瑞,顏鵬飛.中國區域環境效率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010(5): 95-109.
[24]TONE K. A slack-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 143 (1): 32-41.
[25]楊 斌.2000-2006年中國區域生態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實證分析[J].經濟地理,2009(7):1197-1202.
[26]成金華,孫 瓊,郭明晶,徐文赟.中國生態效率的區域差異及動態演化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1):47-54.
[27]黃建歡,呂海龍,王良健.金融發展影響區域綠色發展的機理:基于生態效率和空間計量的研究[J].地理研究,2014,33(3):532-545.
[28]AFONSO A, FURCERI D. Government size,composition,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26(4):517-532.
[29]劉潔,李文.中國環境污染與地方政府稅收競爭[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4):81-88.
[30]MIELNIK O, GOLDEMBERG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coupling between energy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Energy Policy, 2002, 30(1):87-89.
[31]李子豪.地區差異、外資來源與FDI環境規制效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6(8):89-101.
(本文責編:辛城)
TheImpactofFiscalandTaxPoliciesonChina’sRegionalGreenDevelopment:EmpiricalTestBasedonSpatialEconometricModel
WANG Quan-liang
(He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Zhengzhou450046,China)
F812.0
A
1002-9753(2017)09-0082-09
2016-10-20
2017-06-11
河南省優勢特色學科建設項目。
王全良(1970-),男,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臨空經濟、環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