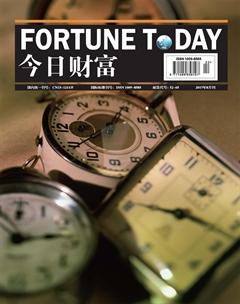中國《詩經》與日本《萬葉集》的比較研究之一
曲迪
中國跟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友國,兩國在文化融合過程中,產生著不可思議的共鳴;有時也因為各自的民族背景差異,分道揚鑣的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萬葉集》與《詩經》作為兩國各自詩歌文學發展的源頭,對于各自的文化領域來說處于同樣重要的文學地位。本文主要通過分析《萬葉集》與《詩經》的異同來比較中日文學。
一、中國《詩經》與日本《萬葉集》的產生
(一)《詩經》的產生及淵源
《詩經》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大瑰寶,在文學史上占有啟蒙性地位。它是中國古代詩歌的起源,共分為《風》、《雅》、《頌》三集,它們分別有不同的來源。其中,《風》藏詩160余篇,主要起源于十五“國”,涉及面積幾乎遍及全國,創作者既有貴族階級,也有農民階級,是對春秋時期社會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的全方位體現。它不僅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荒淫無度、驕奢淫逸,也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疾苦,他們在貴族的剝削下從事繁苦的勞役,過著地位低下沒有尊嚴的生活。同時,《風》也頌揚了勞動人民的勤勞勇敢和樸實心靈,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雅》藏詩105卷,分為《大雅》和《小雅》,前者大部分是用于朝賀的獻詩和政治諷諫詩,多半由統治階級所作。而《小雅》多半由下層階級所作,表示對統治者昏庸無能的憎恨,揭露黑暗的現實,也流露出反壓迫、反侵略之情,只有少部分的詩歌反映的是普通群眾的生活。《頌》總共包含詩歌40首,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其中《周頌》數量最多,講述的是商祖先對于民族發展的貢獻和豐功偉績,他們不僅是華夏民族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是保家衛國、馳騁沙場的民族英雄。
(二)《萬葉集》的產生及淵源
在中國古典詩歌源源不斷地涌入日本的大文學背景下,日本想要發展本民族文學時碰到的首要問題就是,日本還沒有屬于本國的獨立文字,所以《萬葉集》整部歌集都借用漢字記錄而成,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萬葉假名的廣泛使用。萬葉假名的創造,本身是基于大量記錄和歌的需求而實現的,在它產生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相輔相成的促進了和歌的發展。日本文學由口頭發展為書面,漢字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不僅起到了純粹的記載作用,而且進一步在文字的基礎上進行了詩歌的二次創作。
因此《萬葉集》在漢詩的影響下,宮廷編撰的宮人為了追求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韻律,進行了對和歌以短歌為基礎,長歌為主體的一再改造,其中短歌在形成之初的詩型的基本節律是“五七、五七七”,這種節律經過文人的提煉,進一步發展為“五七、五七”的雙重連綴的形式。這種韻律的和歌,經過歌伎編曲者的進一步進化,最后以更口語化的形式流傳于民間。
二、中國《詩經》與日本《萬葉集》的相似性
由于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廣泛傳播以及當時日本上層社會對中國的漢字和漢學的尊崇和推廣,中國的漢字和漢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已經深入日本的各個文化階層。漢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深入影響也集中體現在了《詩經》和《萬葉集》的諸多共同點之上。
首先,它們都具有豐富性和廣泛性。兩部詩集都是對當時不同階級現實生活狀態的真實反映,作者出身也各有不同。《詩經》中的作者既有王公貴族描繪了祖先的豐功偉績,也有貧民百姓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壓迫。描繪的內容既包括戰爭的疾苦,也有甜美的愛情,都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反映。《萬葉集》的作者上至天皇,下至黎民、軍人和流浪漢,內容上同樣包羅萬象,我們既能讀到“班田制”下勞動者饑寒交迫的悲慘生活,也能讀到遠征的軍人對于戀人的深深思念,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縮影。
其次,二者都反映了現實批判主義精神。《詩經》中“風雅之興,志思蓄憤,以諷其上,皆為情而造也。”其中的詩篇雖然現在看起來略有夸張,但并不是文人墨客的無病呻吟,而是作者針砭時弊,對社會真實生活的批判之作。同時,真實性和批判性也是《萬葉集》的顯著特點,作者不加粉飾的揭露統治階級的扭捏作態和昏庸無能,其表現手法多以直白的平鋪直敘為主,以“寫實”手法抒發情感,帶有濃濃的現實主義氣息。
三、中國 《詩經》與日本《萬葉集》的差異性
第一、從“詠貧”出發看政治性的不同。首先我們來看《萬葉集》中反映百姓窮苦生活的憶良的代表之作:《貧窮問答歌》:“值此寒氣來,只有麻衣披,所有布肩衣,盡著身上矣。較我更窮人,寒夜如何濟?父母饑且寒,妻子求且泣。試問當此時,如何度斯世?”這段為問歌部分的一段,說的是冬天的寒冷已經到來,身上粗布麻衣,連棉被都是破的,房屋缺磚少瓦,父母妻兒的啼哭聲在耳邊環繞,漫漫長夜不知如何躲過,此詩反映了當時百姓生活的窘迫,描寫了農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倍受折磨的生活,感嘆著對生活的無望,此作之所以成為稀有作品,是因為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下,天皇處于絕對統治地位、天皇權利屬于上升趨勢,當時的人們一般是把天皇作為現世真神來謳歌頌揚,鮮有不滿的詞句。
中國自東漢時期以來,“詠貧”詩作便成為詩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詩經·大雅·生民之什》中的一篇代表作《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句詩句的大概意思為:人民勞苦卻不得休息,如果王能愛民,真為百姓著想則不至于此,而后的字里行間透漏著對政治的不滿,對王的諫言與規勸,希望不得小人蠱惑與詭騙。
同樣是“訴苦的”的詩篇,《詩經》有著較多的反應現實社會政治特質,有著怒而不言的道德批判傾向,有著鮮明的刺世的現實主義精神,對政治的忿恨不平,詩人懷著無人是伯樂卻又想試圖以詩干政的道德批判的意圖寫作詩篇,這樣對比之下便能看出其代表政治性的不同。《萬葉集》無論在詞語的尖銳強度上,還是政治的批判角度上看,都不可與《詩經》相提并論。
第二、從“詠花”出發對比中日文學。在日本家喻戶曉的《萬葉集》中,吟詠花草樹木的詩歌大約占了《萬葉集》總歌數的三分之一。其中《梅花歌并序》序云:“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佩后之香”“于是蓋天坐地,促膝飛觴。忘言一室之里,開衿煙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攄情?詩紀落梅之篇,古今夫何異矣!宜賦園梅,聊成短詠”,這句段序詞除了描寫景色的美麗,讓詩人沉醉于自然之中,也表達了想遠離世俗的政治心愿。
但是《詩經》中提及“梅”的詩句更多是借花喻人,以花喻情,《召南·摽有梅》中有詞: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此詩為大膽的求愛詩篇,直指以為姑娘看見梅花落地,感嘆時光流失,青春不再,望能早日嫁得如意郎君的心愿。陸游的辭《卜算子·詠梅》更是寫出了梅花可貴的精神:“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梅最早見于《詩經》,歷代文人雅士把梅作為一種精神象征,寄托著文人雅士的高尚品性。
由此可見,同樣是歌頌花卉,日本詩人多半是感嘆其美麗,純潔,少有借題發揮的詩句。而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只描寫景色的卻極為罕見,我國詩人在提及梅的過程中,多是把梅花當作是鄉情、友誼的象征,借梅喻人,睹物思情,或者表達詩人壯志難酬的情懷,甚者以詠梅花的冰情雪質,比喻自己潔身自持的人格。
四、結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深受中國文化典籍和歷代詩歌詩詞影響的《萬葉集》在經過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之后,才具有了求同存異,富含自己民族特色的和歌文化,其表現出來的不朽的生命力,達到了“和魂漢才”的境界。《萬葉集》和歌在整體構思和語句的表達上從漢詩文中獲得了靈感和啟迪。但由于中日兩國傳統審美情趣的不同,漢詩賦與和歌的根本差異便凸顯出來。由于各國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政治體制的差異,即使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有著明顯彼此交融的痕跡,卻也在高度的融合之后產生了各自的特色。(作者單位為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