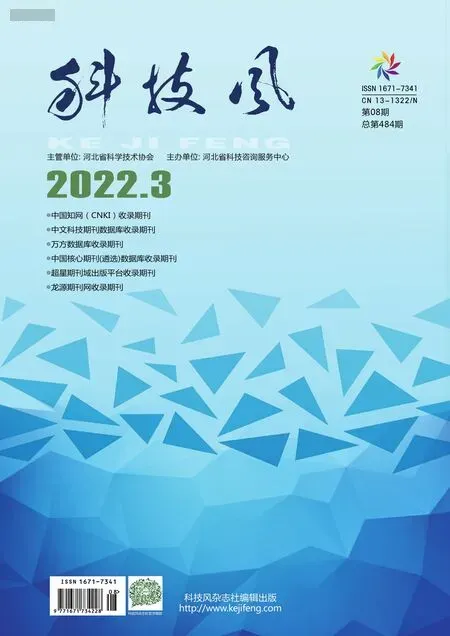淺析儒學思想與中國古代技術的關系
王燁
摘 要:盡管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的中國古代社會曾經有過諸多輝煌的技術成就,但是當今世人對于“儒學”和“技術”的關系仍存在誤解。本文首先陳述了社會上對于二者關系誤解的具體體現,進而從三方面對這些誤解給予駁斥,最后在更深層次上,論述了筆者對于二者關系問題的思考。
關鍵詞:儒學;技術;科學;關系
對于“儒學”和“技術”的研究屬于“技術與社會”的范疇當中,技術與文化的相互關系的一個方面。技術的發展是現代化進步的標志,而儒學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在2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史中綻放出了璀璨的光輝。在當今的社會中,對于儒學與技術關系的誤解仍然是較為嚴重。在此,筆者認為對于二者關系問題的探討,是不容忽視的,并且是具有廣闊前景的。
提到“儒學”和“技術”這兩個詞匯,大家并不會感到陌生。儒學指的由春秋時期孔子在總結、概括了夏、商、周三代尊親文化傳統之上而形成的思想體系,后經過漢代董仲舒的改造,形成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局面,儒學自此之后便成為了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影響深遠。技術通俗的解釋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遵循自然規律,在長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知識、經驗、技巧和手段,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總和。東北大學陳凡給技術下的定義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勞動過程中所掌握的各種活動方式的總和。”[ 1 ]
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在技術的發展方面,為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古代技術發明至今仍使國人引以為傲。而儒學作為中國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對國人的思想觀念、行為規范頗有影響。然而,時至今日,國人對于儒學與技術的關系還是存在頗多誤解,并不能承認二者存在一種良性的關系,反而認為儒學對于技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阻礙作用。
一、誤解的具體表現
(一)儒學輕視技術的發展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儒家學說將其重點放在了倫理綱常上。特別是對于“禮”的重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提到儒學,大多數人的反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樣子,作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作父親要像父親的樣子,作兒子要像兒子的樣子。再比如封建社會當中的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還有一些人認為儒家的思想重視個人的修養,偏重于修養身性,講求以自身的修行來體認天理,進而達到圣賢的大道。比如錢穆先生認為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者重視“‘格、致、誠、正私人修養上。”
這種觀點在某些方面對于儒學的理解是正確的,儒學的學術理論當中,確實是有一些封建倫理色彩,但我們不能以偏概全,我們今天對于儒學與技術關系的思考就是為了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中,同樣有一些對于技術重視的成分,比如耳熟能詳的《周禮·地官》當中的“六藝”、“六德”、“六行”之學,其中“禮、樂、射、御、書、數”,作為六種具體的知識和技能,這些知識和技能君子是必須要予以學習的,只有掌握了這些“六藝”,才能做到“學而利用”,人們想要學習知識,必須首先要以“六藝”為本,精通六藝,用到人倫社會便是“六行”,用到自身便是“六德”。
(二)儒學對技術的發展起阻礙作用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儒學的存在,阻礙了技術的發展。比如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就明確表示“儒家反對對技術作科學的解釋和推廣。”特別是隨著近代中國五四運動的開展,“打到孔家店”的口號激起了一批仁人志士對于儒學的批判,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以及之后爆發的文革運動,對于儒學一直持有否定和批判的作用,使得傳統儒學在改革開放之前,在大陸的學術環境中無法獲得應有的地位。
儒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就已經占據了學術界的主流思想,被歷朝歷代都奉為正統思想。中國古代的技術成就也是不容人們所忽視的,那么,如果說儒學的存在阻礙了技術的發展,是否就等同于占據主流地位的社會思想阻礙了技術的發展,并且還創造出了諸多令今人仍引以為傲的成就?這在邏輯上無法解釋的通。
二、對誤解的駁斥
對于人們對儒學和技術的關系所存在的誤解,如果不進行根除,儒學的復興便無從談起,儒學與技術的有效結合也是無稽之談。本部分從三個部分對于上述誤解給予駁斥,并力求展示出儒學與技術的一種良性關系。
(一)儒學以寬容的態度對待技術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思想,次之則為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確實是排斥技術的,比如道家學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則純白不備。”有了機械,就會產生技巧之事;有了技巧之事,就會產生技巧之心,而人如果有了技巧知心,內心就會不純潔了。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所主張的是“一個不用利器、不乘舟車、不用文字的‘小國寡民的社會。”如果說道家對于技術持排斥思想,還情有可原,但絕不能說儒家思想對技術持否定排斥的態度。相反,儒家思想對于技術的態度,還應當算是比較寬容的。
古代的諸多技術是依附于儒家思想的,也就是說儒家思想是給予了技術存在的空間的。例如上文所列舉了《周禮》當中“六藝”的例子,這六種具體的知識和技能在先秦時期曾是訓練官宦子弟的基本內容之一。如果儒學沒有一種對技術寬容的態度,又何必去學習它呢?《皇帝內經》當中的核心理論——陰陽五行學說,正是源于《尚書》和《周易》等儒家經典著作的。[ 2 ]如果儒學沒有一種對技術寬容的態度,為什么自家的理論要讓論述醫學技術的書籍來用?《四庫全書》所制定的科學分類中,將天算農醫諸科歸為“子部”。如果儒學沒有一種核心的態度,為什么要將技術收錄于四部之中?
(二)中國古代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成就
在中國古代技術發展的歷程上,曾出現過不少杰出的人物,出現了不少輝煌的成就。正是因為這些人物和成就能夠使我們自豪的翻閱關于中國古代技術史方面的相關記載,也正是因為這些人物和成就能夠使我們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巔,同樣也正是這些人物和成就推進了世界文明的進程。
據《世界自然科學大事件年表記載》:“16世紀以前,影響人類生活的重大科技發明約有300項,其中175項是中國人發明的。”中國古代的四大方面對于世界的意義自然不必多說。《考工記》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記述官營手工業各工種規范和制造工藝的文獻,據《考工記》稱,當時“‘國有六職——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和婦功,表明手工業者在社會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3 ]《考工記》當中有對車輛制造、弓箭的制作、鼓、鐘、磬的制造以及練絲、染色和皮革加工技術方面的介紹,真可謂是手工業技術規范的總匯。而《考工記》的出處正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周禮》。明代宋應星搜集、整理、編纂的《天工開物》,是世界第一部有關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百科全書,這部書也被稱為“儒家留給世界的科技著作”。
(三)儒家學者以技術知識來闡述理論思想
《春秋·谷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在這句話中,“工”指的就是中國古代工匠,工匠是一種心靈手巧,有某種手藝專長,并能夠制成某些器物的人。工匠在古代中國社會是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工匠在古代社會基本可以說就是手工業從業者,而“傳統手工業是古代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4 ],所以工匠是與古代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所緊密相連的。
我們可以在諸多儒家經典著作中發現,儒家代表人物也是深受技藝的影響,并且以具體的技藝來闡述自己的學術理論,使得自己的學術理論更為有說服力。
例如,大家最為熟悉的一句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句話出自于《論語·衛靈公》,是孔子的弟子自貢問孔子怎樣修養仁德,而孔子給出的答案是:工匠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需要將自己的工具磨鋒利,住在一個國家,要侍奉大夫中的賢人,與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工匠從事技藝的勞作與個人修養仁德看似是完全不相關的,然而孔子的這句話卻一語中的,說明了二者所表達的道理是相同的。工匠在做工之前要打磨好自己的工具,進行品德上的修養也要先去與品德高尚的人交朋友。
再比如,荀子在論述民心是作戰取勝的關鍵時曾說:“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用兵作戰的根本在于民心的統一。如果弓和箭不能相統一,那么即便是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標;駕車的時候,六匹馬不能相統一,那么即便是造父也不能駕車行駛很遠的距離,如果統治者不能使士兵和百姓統一,那么即便是商湯和周武王也不會取得勝利。“射”和“御”是“六藝”中六種技能,荀子在此是在運用這兩種具體的技能來闡述自己的軍事思想。
三、對于二者關系問題的思考
本文第一部分,筆者從兩個方面論述了人們對于技術和儒學關系的誤解。然而究其更深層次的原因,筆者認為應當歸結為社會上對于“科學”和“技術”概念的混淆,山東大學陳炎教授在《清華大學學報》上的文章《儒家與道家對中國古代科學的制約——兼答“李約瑟難題”》中指出,李約瑟也沒有在理論上將“科學”和“技術”的概念加以嚴格區分。
我們經常會把科學和技術統稱為“科技”,然而二者本身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并且現如今對于“儒學”和“科學”相容性的討論還在進行。在我國學術界對于“儒學”和“科學”相容性的討論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科玄論戰”,新中國成立后世人對于科學和儒學的關系也未給予正確的認識,而儒學又經常作為傳統封建文化的代表,被世人所批判,再加上科學和技術的混淆,這就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人們也沒有正確認識儒學與技術的關系。
四、結語
就上文所述,儒學與技術關系誤解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可以分為四方面內容即世人對“科學”和“技術”概念的誤解、“科學”和“儒學”是否具有相容性、大陸語境對儒學長期持有批判態度、“科學”和“技術”的關系問題討論。
首先,對于“科學”和“技術”的區分,相關文章已經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筆者在此不必贅述。
其次,而對于“科學”和“儒學”的相容性的討論,令筆者感到欣慰的是現如今人們已經逐漸在以一種客觀的態度看待“儒學”,例如,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所馬來平教授及其博士生們曾多次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等刊物上發表關于“儒學”和“科學”相融的文章,并且有一定的影響。筆者認為,馬來平教授的所選取的視角是正確的,“科學”和“儒學”必然有一定的相容性,而這種相容性的存在對于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再次,筆者認為不管是學術界還是社會,我們都應該對于儒學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我們不能只看到儒學思想中為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理論,也應該看到儒學作為中華民族2000多年的正統思想,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我們要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我們不僅要“取”,更需要“揚”。
最后,如果對于上述三個方面我們都能做到的話,那么“儒學”與“技術”的關系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參考文獻:
[1] 陳凡,程海東.“技術認識”解析.技術哲學,2011年第4期.
[2] 馬來平.科技儒學之我見.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年第6期.
[3] 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4] 張迪.中國的工匠精神及其歷史演變.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5] 陳紅兵,陳昌曙.關于“技術是什么”的對話.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年第4期.
[6] 陳炎.儒家與道家對中國古代科學的制約——兼答“李約瑟難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