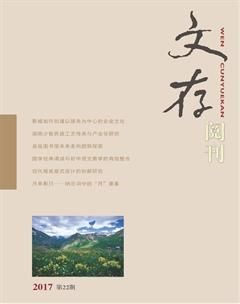從大眾文化的視角談設(shè)計(jì)的社會(huì)學(xué)特征
一、大眾文化的界線
隨著科技的發(fā)展,社會(huì)的進(jìn)步,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變。古典文化幾乎走入了“偃旗息鼓”境地,而另一種文化必然影響更大,這就是大眾文化。理論界對(duì)大眾文化一般的定義認(rèn)為,大眾文化是以工業(yè)方式生產(chǎn)、消費(fèi)的文化商品。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shuō),大眾文化在中國(guó)產(chǎn)生應(yīng)該在80年代初,改革開(kāi)放以后。隨著新興工業(yè)在中國(guó)蓬勃的發(fā)展,它同時(shí)也給人們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和視角沖擊,如影視、勁歌等等。大眾文化越來(lái)越豐富了人們對(duì)生活存在方式的需要,成為了市民在機(jī)器宣泄后,尋求心理平穩(wěn)的一種普遍動(dòng)力。大眾文化有著不同與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的特點(diǎn)及功能。
大眾文化首先要與作為傳統(tǒng)的精英文化的純藝術(shù)相區(qū)分。一個(gè)最明顯的特點(diǎn)就是大眾文化具有普遍性,它消除了文化的階級(jí)性。不論你是那個(gè)階級(jí)、種族、年齡、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城鄉(xiāng)的差別,你都可以擁有它、享受它。費(fèi)西克說(shuō):“大眾文化是一個(gè)斗爭(zhēng)的場(chǎng)所,日漸成為對(duì)支配文化的一種抵制力量。表現(xiàn)在生活中是沒(méi)有權(quán)的階級(jí)對(duì)有權(quán)階級(jí)的抵制。”[1]費(fèi)西克舉了美國(guó)青年傳牛仔褲的例子,牛仔服舒適耐磨,不需要經(jīng)常熨燙,可以為社會(huì)中任何一個(gè)階層接受,上至總統(tǒng),下至貧民,男女皆可,老少咸宜。穿牛仔服由是成為一個(gè)自由符號(hào),既可讓人自由地展現(xiàn)自身,也可以讓人自由地隱藏自身。所以牛仔服是美國(guó)大眾文化的符號(hào)。大眾文化一開(kāi)始就作為精英文化的對(duì)立面存在。精英文化是少數(shù)人的精神活動(dòng),非工業(yè)的,對(duì)大眾是一個(gè)給予、帶領(lǐng)和引導(dǎo)的單向關(guān)系。如果說(shuō)純藝術(shù)能夠形成對(duì)當(dāng)代社會(huì)的批判性反思的宏大敘事,那么與之相對(duì)的設(shè)計(jì)藝術(shù)則更可能從其它方面切入當(dāng)代社會(huì),例如大眾文化的視角。如果說(shuō)先鋒派藝術(shù)家和詩(shī)人完全從大眾中退離出來(lái),通過(guò)把藝術(shù)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現(xiàn)絕對(duì)來(lái)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藝術(shù)的話,那么設(shè)計(jì)師則義無(wú)反顧最大限度地融入社會(huì),將市場(chǎng)作為一個(gè)基本的前提。先鋒派藝術(shù)在專業(yè)上的專門化、精英化和對(duì)題材、內(nèi)容的冷漠,疏遠(yuǎn)了許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們技藝奧秘的人,大眾對(duì)精英文化的漠不關(guān)心使先鋒派在當(dāng)代文化的發(fā)展中由于缺乏群眾和市場(chǎng)基礎(chǔ)而受到生存的威脅,與之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則是設(shè)計(jì)藝術(shù)的出發(fā)點(diǎn)在于大眾文化的市場(chǎng)根基。某種程度上,設(shè)計(jì)藝術(shù)更能代表具有后現(xiàn)代主義特征的流行文化的特征。設(shè)計(jì)藝術(shù)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的視覺(jué)關(guān)聯(lián)較之前者更直接、更充分、更形象,它是生活著的藝術(shù),而非傳統(tǒng)意義上放在展覽館中的藝術(shù)。由于大眾文化的介入,設(shè)計(jì)藝術(shù)真正成為“藝術(shù)生活化、生活藝術(shù)化”這一美學(xué)宗旨的體現(xiàn),它與“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和“純?cè)姟痹趯?duì)大眾文化的態(tài)度問(wèn)題上徹底劃清了界線。大眾文化是在精英文化衰落的前提下發(fā)展起來(lái)的,在中國(guó)自然也不例外。但我們也要看到目前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趨勢(shì)即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合流、相互滲透、融合的趨勢(shì)。而且這種發(fā)展隨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及文化自身的發(fā)展,有加快的勢(shì)頭。精英文化是歷史的、經(jīng)典的、高學(xué)術(shù)質(zhì)量的文化結(jié)晶,而大眾文化是通俗的、即時(shí)的、輕松的文化,兩者的結(jié)合更有利于滿足社會(huì)的各層次的需求。如大眾文化在滿足即時(shí)的趣味之時(shí),也研究社會(huì)重大的問(wèn)題,而精英文化的經(jīng)典著作,也利用高速發(fā)展的信息技術(shù),通過(guò)縮寫(xiě)本、袖珍本、錄音、復(fù)制等方法迅速大眾化。
我們還應(yīng)該區(qū)分設(shè)計(jì)藝術(shù)與庸俗藝術(shù)的界線。1939年,格林伯格在他最重要的現(xiàn)代主義理論名篇《先鋒派與庸俗藝術(shù)》中提到在同一社會(huì)可以并存著看起來(lái)似乎并無(wú)關(guān)系的不同事物,例如愛(ài)略特的詩(shī)與《星期六晚郵報(bào)》的版面,也就是所謂的“精英藝術(shù)”與“通俗藝術(shù)”的差異和并存。設(shè)計(jì)藝術(shù)和后者更為接近,但通俗藝術(shù)在工業(yè)化的催生過(guò)程中有更多的可能流于庸俗。根據(jù)伯林格的歸納,它包括流行的商業(yè)性的藝術(shù)和帶有彩色照片的文學(xué)、雜志封面、插圖、廣告、通俗黃色小說(shuō)、戲劇、流行音樂(lè)、踢踏舞、好萊塢電影等(在今天,我們還應(yīng)該加上電視娛樂(lè)節(jié)目、數(shù)碼影像、動(dòng)漫、電腦游戲等),實(shí)際上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熟悉的流行藝術(shù)與大眾文化,是一種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鄉(xiāng)下人所需要的消費(fèi)文化,這些市民與民工對(duì)傳統(tǒng)的文化價(jià)值無(wú)動(dòng)于衷而又渴望某種文化娛樂(lè),借以打發(fā)無(wú)聊與派遣城市生活的壓力。
今天,大眾文化己成洶涌潮流,設(shè)計(jì)藝術(shù)與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日益緊密,本雅明所預(yù)見(jiàn)的復(fù)制性藝術(shù)對(duì)傳統(tǒng)的手工技藝的經(jīng)典藝術(shù)造成極大沖擊。我們對(duì)待大眾文化已不能再持一種簡(jiǎn)單的批判與聲討,而應(yīng)該更深入地研究當(dāng)代設(shè)計(jì)藝術(shù)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復(fù)雜的美學(xué)關(guān)系。
二、大眾文化的層次和特性
從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和庸俗文化的區(qū)分來(lái)看,大眾文化可以有以下幾個(gè)層次:第一層次是屬于高品位的。在這一層次上,文化制作者本身有較高的藝術(shù)造詣渾厚的藝術(shù)底蘊(yùn),他們展示給大眾的作品大部分是通俗易懂而又意趣頗高,無(wú)論從作品的內(nèi)容或作品本身的表現(xiàn)手法都屬較高層次。這促使人們?cè)诮邮艽蟊娢幕倪^(guò)程中,追求的不僅僅是感官的刺激和輕松的時(shí)刻,在娛樂(lè)和消遣的同時(shí)也在思考人生、社會(huì)和自己的責(zé)任。另一方面,過(guò)去只有少數(shù)人士才接觸到的高雅文化,現(xiàn)在在大眾傳媒中廣泛流傳,人們已經(jīng)有機(jī)會(huì)接觸它,并且這些高雅文化本身也在自我改善和更新的發(fā)展。這同時(shí)也說(shuō)明,大眾文化本身也在攝取著一切文化之中的精華。第二層次屬于中等品位的。這一層次的文化主要以純娛樂(lè)和休閑為目的。緊張工作后,盡情的享受是一種現(xiàn)代化生活方式的準(zhǔn)則。工業(yè)社會(huì)使人們經(jīng)常處在一種高節(jié)奏而忙碌的生活狀況中,人們?cè)诠ぷ髦鄬で缶褪且环N輕松愉快的文化享受。大眾文化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充當(dāng)一種潤(rùn)滑劑,其作品涉及嚴(yán)肅的主題、娛樂(lè)、漫畫(huà)、輕喜劇等都是與之相應(yīng)的大眾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第三層次是屬于低品位的。大眾文化在這個(gè)層次上藝術(shù)性極低,甚至無(wú)藝術(shù)性可言,粗制濫造之后被貼上大眾文化的標(biāo)簽。在這些作品中,人欲橫流、道德淪喪、色情暴力、神秘、恐怖充斥其中,消磨人的意志,腐蝕人的心靈,用“文化垃圾”來(lái)形容最恰當(dāng)不過(guò)。這種低劣品由于滿足某種欲望而被大量制造,泛濫成災(zāi),影響極壞,大眾文化所遭到的攻擊和指責(zé)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
大眾文化是由商業(yè)性的文化工業(yè)機(jī)構(gòu)利用高科技媒介技術(shù)批量生產(chǎn)的,明顯受到港臺(tái)地區(qū)和西方國(guó)家大眾文化(用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話說(shuō)是“文化工業(yè)”)的影響。陶東風(fēng)發(fā)表于1993年的文章《欲望與沉淪一大眾文化批判》中,對(duì)于“大眾文化”進(jìn)行了這樣的界定:大眾文化是“商業(yè)化的、批量生產(chǎn)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電子傳播媒介傳播的、娛樂(lè)性消費(fèi)文化”。[2]
由上我們可以得出“大眾文化”的特點(diǎn)是:第一、它并不是在任何社會(huì)歷史階段和社會(huì)形態(tài)都可能出現(xiàn)的通俗文化類型,而是專指工業(yè)化社會(huì)才出現(xiàn)的商業(yè)文化形態(tài),可以說(shuō)大眾文化的基本含義是消費(fèi)和娛樂(lè),通俗性;其次,它以大眾傳播媒介(機(jī)械媒介和電子媒介)為傳播手段,因而其傳播的范圍是任何前工業(yè)化時(shí)期的民間文化或通俗文化不能比擬的;第三、它具有突出的感性愉悅性,它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目的在于滿足現(xiàn)代大眾的休閑娛樂(lè)需要。第四,大眾文化的運(yùn)作模式是形成規(guī)模,創(chuàng)造效益,依靠工業(yè)化的組織和生產(chǎn),“引導(dǎo)消費(fèi)”“制造需要”。
以上對(duì)大眾文化的層次和特點(diǎn)的分析,可以得出下文我們對(duì)“設(shè)計(jì)為大眾服務(wù)”這一理念的五個(gè)層次的涵義。
三、設(shè)計(jì)為大眾服務(wù)
著名設(shè)計(jì)公司 Smart Design的設(shè)計(jì)總裁戴文·斯特威爾說(shuō)過(guò)“通常設(shè)計(jì)師太在乎產(chǎn)品本身,把它看作是一種藝術(shù)品而忽視了人的使用。我們告訴設(shè)計(jì)師不要考慮他們?cè)O(shè)計(jì)的產(chǎn)品,而應(yīng)該多想想產(chǎn)品能夠干什么,怎樣讓人盡可能用著舒適。這樣,設(shè)計(jì)帥才能真正從使用者的需要出發(fā)學(xué)會(huì)關(guān)注功能,關(guān)注人們使用甚至擁有產(chǎn)品時(shí)的愉悅心情。我們開(kāi)始問(wèn)自己在為誰(shuí)做設(shè)計(jì)?答案很顯然,是為大眾做設(shè)計(jì)。”[3]這段話和設(shè)計(jì)的價(jià)值取向問(wèn)題密切相關(guān),簡(jiǎn)明地說(shuō)“設(shè)計(jì)為大眾服務(wù)”的內(nèi)涵包括了設(shè)計(jì)自身與大眾文化的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聯(lián)。
設(shè)計(jì)和大眾文化之間的交叉和整合,構(gòu)成了當(dāng)代文化發(fā)展的新景觀—設(shè)計(jì)文化的蓬勃發(fā)展。在當(dāng)代信息社會(huì)中,我們對(duì)設(shè)計(jì)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在物質(zhì)的、技術(shù)的、理性的層面上,還應(yīng)該在精神、情感、心理層面上,進(jìn)一步灌注“以人為本”的設(shè)計(jì)思想,以現(xiàn)代人所生活和包圍的文化為基礎(chǔ),真正使設(shè)計(jì)藝術(shù)成為“文化的肌膚”。
第一,設(shè)計(jì)對(duì)大眾文化可以產(chǎn)生在倫理道德觀念方面的正確、恰當(dāng)?shù)囊龑?dǎo),如“適度消費(fèi)”、“適當(dāng)設(shè)計(jì)”、“綠色設(shè)計(jì)”、“可持續(xù)發(fā)展”等設(shè)計(jì)理念,最終形成一種積極的設(shè)計(jì)文化。當(dāng)今,技術(shù)如同脫韁之馬拉動(dòng)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車輪,使商業(yè)競(jìng)爭(zhēng)愈演愈烈,被競(jìng)爭(zhēng)魔力所驅(qū)使的設(shè)計(jì)活動(dòng)把不斷刺激消費(fèi)者的欲望作為核心任務(wù),以至日益喪失了對(duì)方向的把握和思想的獨(dú)立,偏離了對(duì)人類生活的本質(zhì)要求。所以,從根本上設(shè)計(jì)應(yīng)該切實(shí)關(guān)懷大眾生活質(zhì)量的提高,應(yīng)該以高質(zhì)量的產(chǎn)品設(shè)計(jì)體現(xiàn)對(duì)人的本質(zhì)關(guān)懷,設(shè)計(jì)人員的人文情懷或人文精神在這方面得到具體的體現(xiàn)。大眾是一個(gè)社會(huì)整體,不是某一個(gè)具體客戶的私欲,因此,設(shè)計(jì)師不能放棄建立在整體社會(huì)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價(jià)值觀,從而放棄設(shè)計(jì)的理想和品格。設(shè)計(jì)從根本上是審美性與功能性完美統(tǒng)一的實(shí)用藝術(shù)。
第二,設(shè)計(jì)師的設(shè)計(jì)活動(dòng)沒(méi)有藝術(shù)家或匠人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那樣自由隨意,而 是與生產(chǎn)、營(yíng)銷、消費(fèi)相協(xié)調(diào),因此大眾文化視野下的現(xiàn)代設(shè)計(jì)必定呈現(xiàn)出社會(huì)化和集團(tuán)化的特征。與個(gè)體設(shè)計(jì)對(duì)應(yīng)的是設(shè)計(jì)管理,設(shè)計(jì)本質(zhì)所決定的系統(tǒng)性。綜合性的效應(yīng)在設(shè)計(jì)管理中得到最大的發(fā)揮。設(shè)計(jì)管理成功的基礎(chǔ)是設(shè)計(jì)組織按
照一定的宗旨來(lái)制定自己的設(shè)計(jì)策略、并且能夠有效實(shí)施自己的設(shè)計(jì)計(jì)劃。這個(gè)過(guò)程與工業(yè)化社會(huì)大眾文化的傳播具有相似的結(jié)構(gòu),可以說(shuō)是一種“異質(zhì)同構(gòu)”。
第三,設(shè)計(jì)日漸成為浸潤(rùn)到日常生活方式中的不可剝離的一部分,成為“生活藝術(shù)化、藝術(shù)生活化”的最精彩的注腳。設(shè)計(jì)就是生活,它與我們每個(gè)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溶化在生活中的側(cè)重目的、實(shí)際功能、生產(chǎn)成本的平民化設(shè)計(jì)必將代替追求風(fēng)格、表現(xiàn)形式、藝術(shù)效果的所謂的“藝術(shù)化”設(shè)計(jì)。
第四,設(shè)計(jì)與大眾通過(guò)“理解”構(gòu)成一種共益體,使得一種嶄新的健康的設(shè)計(jì)文化成為可能。大眾文化的濫觴已成為一個(gè)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設(shè)計(jì)只有與之構(gòu)成互動(dòng),而非簡(jiǎn)單的附庸,方能成就新的更有意義和內(nèi)涵的設(shè)計(jì)。設(shè)計(jì)通過(guò)“理解”原則去找尋人類行為背后的意義、情感、價(jià)值與象征系統(tǒng)。設(shè)計(jì)師要做的就是理解一個(gè)更大范圍內(nèi)的普遍性的用戶,理解一個(gè)特定人群在不同時(shí)間環(huán)境下不同的行為與意義系統(tǒng),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才會(huì)有更好的創(chuàng)造。同理,我們對(duì)設(shè)計(jì)的評(píng)價(jià)也據(jù)于此。
第五,當(dāng)代藝術(shù)設(shè)計(jì)越來(lái)越依賴外部信息的攫取與篩選,設(shè)計(jì)活動(dòng)強(qiáng)調(diào)配套操作,大眾媒介、時(shí)尚流行與市場(chǎng)日益成為具有評(píng)論價(jià)值的重要因素而發(fā)揮著影響力。當(dāng)代設(shè)計(jì)師已經(jīng)意識(shí)到通過(guò)商業(yè)廣告與大眾媒介建立自己的符號(hào)系統(tǒng)即商品品牌識(shí)別系統(tǒng),從而增加設(shè)計(jì)神話的附加值的重要性。因此,選擇社會(huì)熟悉的大眾文化符號(hào)成為設(shè)計(jì)與大眾和傳媒建立緊密的消費(fèi)關(guān)系的重要公關(guān)策略。
總的來(lái)說(shuō),浸潤(rùn)于大眾文化中的設(shè)計(jì)者應(yīng)保持一分理性和清醒,在紛雜的文化氛圍中保持自己獨(dú)立的文化人格,去挖掘、弘揚(yáng)、創(chuàng)造那利于提高大眾修養(yǎng)的文化產(chǎn)品。
注釋:
[l]陸毅、王毅:《大眾文化與傳媒》, 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年10月版,第50頁(yè)。
[2]陶東風(fēng):《欲望與沉淪一大眾文化批判》《文藝爭(zhēng)鳴》1993年第6期,這個(gè)定義后來(lái)被批評(píng)界廣泛接受。
[3]美國(guó)《商業(yè)周刊》中文版 2003年第8期
作者簡(jiǎn)介:
邵翼?yè)P(yáng),女,漢族,單位:鄭州市京廣實(shí)驗(yàn)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