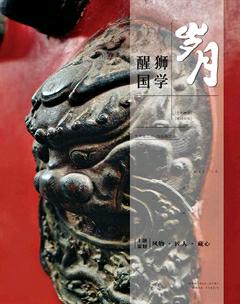權力的游戲
張康
中華文明的源頭,常常是以人類歷史的童年形象被認知和接受的。我們把熱烈的、野蠻的、直切的中華民族祖先的脾氣,統(tǒng)統(tǒng)灌注進對人類稚氣未脫的物質、精神文明生產的考察和闡釋中,從遠祖留下的只言片語和殘垣斷壁中,對自身遙遠的歷史展開逆向回憶。一切文明的進化都離不開對本族歷史的總結和反思,而這種逆向回憶正是反思的第一步。
在以孔子為歷史節(jié)點的早期理性倫理時代到來之前,華夏文明的自發(fā)力量所形成的社會秩序,經歷了許多重大變遷,即由原始氏族社會中的無差別的公約式的部落規(guī)范,到周代帝王政治雛形的確立。在這些變遷中,華夏文明的性格也隨之幾經變化,在這個復雜、充滿血腥氣息的歷史過程中,正是青銅器文明在歷史舞臺中最活躍的時期。
我們所熟知的“楚王問鼎”的故事,正是青銅器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鼎——的著名歷史事件。作為諸侯一員的楚莊王,似無意而有意地以九鼎之事問起王孫滿的時候,正是青銅文化所折射的先秦華夏文明最活躍的一段,而此時,也正是先秦諸家巨型貴族之間權力的游戲之高潮。
我們不妨回到這個游戲的準備期來考察一番。
夏禹初定天下,威望與權力集乎一身,原始氏族公約的平衡瞬間變得脆弱而頃刻瓦解,于是“公天下”之易姓,成為這場曠日持久的權力的游戲之第一步。夏王朝傾諸侯之力所集中起來的銅,成為游戲開始的最響亮禮炮。一聲震天巨響之后,這些銅化為巨大無匹的九鼎,鼎上鑄有九州山川文物,成為穩(wěn)固而義正言辭的權力象征。
權力的集中過程,是現代文明心知肚明而又避而不談的話題之一。這一過程與當今我們所自覺尊奉的一切價值觀念背道而馳,成為今天人類文明碩果累累的局面之背后的永恒瘡疤。夏王朝之所以能集中天下為數本不多的銅,并非一時之功。在夏禹登上歷史舞臺之前,甚至更久遠的以前,人類社會早已開始了權力集中的過程。
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而不勝必至于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于造五兵。……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zhàn)?大昊之難,七十戰(zhàn)而后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zhàn)而后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zhàn)而后濟;昆吾之難,五十戰(zhàn)而后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zhàn),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zhàn)益以多。
——【宋】羅泌《路史》卷五
毫無疑問,這些戰(zhàn)爭數字并不是用論辯、奏樂的方式堆積起來的。這一過程的丑陋和殘酷,現代人在心安理得地享受文明紅利的時候,常常緘口不提。當然,歷史進步的成本總是難于避免。在權力的游戲中,每一個角色都面臨著許多難以啟齒和無可奈何,當然更多的是心驚膽戰(zhàn)。先民踏過無邊的尸首之后,權力的游戲達到了一個新的平衡期。過去的原始氏族公約已經悄然分崩離析,新的平衡帶來了新的公約,于是沾滿鮮血的青銅九鼎化為冰冷威嚴的權力游戲的公告——舊的游戲從此停止,新的游戲已經開始。
青銅九鼎的落成,給過去的流血漂櫓和哀鴻遍野賦予了一副嚴肅而崇高的表情,也成為對過去一系列屠殺、劫掠、奴役和壓迫的總結和集中展示,是游戲勝利方發(fā)出的炫耀和警告。于是后來殷周一系列青銅器的誕生都成為九鼎權力象征的一個縮影,成為后代祭拜先祖之功和祈求保佑的禮器。這個“禮”和孔子的 “禮”是不同的,前者充滿野蠻者的暴力,后者充滿理性者的自覺。于是,殷周以來的青銅器造型充滿著怪異和恐怖,其上所紋飾的也多是以饕餮為首的兇狠之獸,因為這些紋飾之發(fā)端,正是權力爭奪游戲中流出的兇戾、狠辣所集中而成的震懾力。正如李澤厚所說:
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護的神祇。對異氏族、部落是恐怖、威嚇和符號;對本氏族、部落又具有保護的神力。
——李澤厚《美的歷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權力的游戲中,所謂天子乃至諸侯王這些巨型貴族,雖然站在權力的高地之上,卻常常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得不將權力分出一部分,交于一些特殊人群之手。正是這些特殊人群幾乎確立了所有青銅器紋飾的造型規(guī)范。他們正是從事占卜之事的巫覡。正是他們用敏感的內心和超出當時人的想象力,將權力的游戲的核心精神符號化為青銅器造型和紋飾的制造規(guī)范。他們是在權力的游戲之特殊生態(tài)中,運用自身的特殊技藝,將難以捕捉而又約定俗成的虛無力量形式化、具象化,從而符號化,于是兇戾的饕餮、猙獰的面孔、怒睜的眼睛、突兀的牙齒等青銅器造型(或紋飾)成了他們一次又一次符號化的成品。
因為巫師們的“真實地想象”(李澤厚語)的能力,使得他們實際上搖身成為權力游戲的規(guī)則制定者和掌握者。從現代的眼光看,他們或許比身為王公貴族的統(tǒng)治者更加具備游戲色彩。然而,縱使權力的游戲充滿了原始的血腥味和野蠻色彩,它畢竟是祖先掙脫動物性、走向更高級文明的必經過程。青銅器的造型和紋飾中,殺戮的血氣和野蠻的戾氣在時間的淘洗中逐漸消散,而其中所保留的先民的幼稚而淳樸的想象力和對世界的單純認知方式,卻實實在在地折射出強烈的美感。這種美從先民神秘化的宗教意識、歷史意識中提煉而出,積淀著深沉的歷史力量。先民在野蠻而粗暴的現實生存中,用自己稚氣未脫的認知與自然、與歷史進行著笨拙而勇敢的對話,這些淳樸而天真的對話內容,正是青銅器在今天所展示出的巨大的崇高之美和歷史意識。
歷史不能重來,游戲難于復位,并不是一切野蠻和暴力都能帶來美感,絞刑架、閘刀、刑具的運用距離當今的文明并不遙遠,無論它們如何制作精巧、紋飾造型多么細膩生動,仍然會散發(fā)出逼人的冰冷與恐怖。青銅器時代所折射出的權力游戲,實際隨著孔子的禮教(與詩教、樂教是一體的)在士人乃至統(tǒng)治階級的文化心理中得以確立之時就已經宣告終結。是以戰(zhàn)國及其后的青銅器,亦即郭沫若所說的青銅器“新式期”的青銅器,原本猙獰抽象的紋飾(有時還有造型)逐漸趨于寫實,竟至于原本嚴肅的青銅器,逐漸從宗教、權力的象征意味中疏離,而成為實用型的器物或欣賞型的玩物了。于是那種猙獰的、冷酷的美,又變換成為另一種性格活潑的、基于模仿的藝術品之美。
在今天,人們從原始宗教的簡單認知中已然脫出許久,社會的情感方式也早已從暴力的強橫野蠻走向平等、憐憫,物質已然高度發(fā)達,原始的殘暴和我們之間有著不計其數的時間、歷史、理性組成的障壁,只有這時,遙遠記憶中的殺戮和震懾,才能和我們當前的理性認知站在平等的階梯之上相互對話。
青銅器的美,正是在這樣的對話之中得到確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