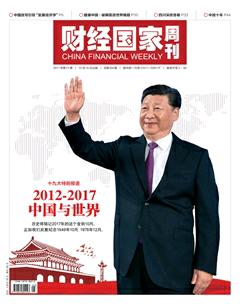“錢荒”催生的英格蘭銀行
李弘
英格蘭銀行成立是公眾與政府信用關系上的一大進步。
1688 年爆發的英法“九年戰爭”(1688-1697)打到1694 年, 國庫空虛的英國王室已處于彈盡糧絕的困境。為了和法國人打下去,威廉三世征足了稅,借爛了債,不得已頒發特許給英格蘭銀行,目的是解決它的戰爭“錢荒”。英國史學者認為,英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爭財政孕育了現代“金融革命”。
在英格蘭銀行成立之前,英國王室就想方設法向倫敦城里的富人和貴族封建主借錢。當時王家有金庫造幣局,富人會把金銀存在那里。王室的劣跡之一是曾拒絕兌付人們存在那里的金幣,其實就是挪用客戶存款。在英法“九年戰爭”中,國王的掌璽大臣印制了政府債券直接賣給商人們,承諾支付利息,并容許商人們以這樣的財政券用于繳稅。但這些借款的期限很短,在掌璽大臣幾次不履行利息支付承諾后,商人們再也不愿出錢購買財政券了。這樣,已失去自由加稅權力的國王山窮水盡。
倫敦城里的原始金融業務在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之后一直在緩慢發展,適應了貿易支付的需求。到了17世紀末,商人們在醞釀成立一家與荷蘭機構類似的銀行。政府的困境為他們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他們不愿意把錢分別借給王室,而是要把政府直接借貸的功能銀行化。
出面組織與政府談判的英格蘭銀行條款人是威廉·彼得森,一位蘇格蘭人。但真正的運作人是倫敦城中一位老到的商界大腕約翰·霍布倫爵士。英格蘭銀行的提案很快得到國會批準,國王授予了特許權, 允許這家銀行突破當時的法律規定,以不受限制的人數成立股份公司,建立一家資本雄厚的融資機構,前提是把錢長期借給政府。拿到特許權之后幾天,金融城中1208位股東只用了兩周時間就籌集到120萬英鎊。政府同意年息為8%,并支付銀行每年4000英鎊的管理費。只用了半年時間,這筆錢就被政府全部支取。描寫“九年戰爭”的學者們寫道,英國士兵在前線的裝備從此讓法國人羨慕不已。
從銀行業務的角度看,英格蘭銀行的成立算不上開天辟地。它所從事的借貸票據業務在荷蘭已有先例。據說1657年在瑞典成立的銀行開創了為王室融資服務的傳統,并且發行過金額確定統一的貨幣。在這些方面,英格蘭銀行是一個具有改造與綜合能力的杰出模仿者。它的模仿對象,主要是荷蘭1609年成立的股份制阿姆斯特丹銀行,來自荷蘭的新國王威廉三世對這一機制耳熟能詳。不過阿姆斯特丹銀行不是為王室亦非為戰爭成立,它的服務對象是新興的國際商貿,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后來也擴展至荷蘭聯合省的共和政府。它創造了存款賬戶、記賬貨幣、透支信用等金融工具。
盡管在機構設置與業務上是模仿,但英格蘭銀行超越了它的前輩,成為銀行史上的里程碑。這首先是由于它開發的是一個實力強大的新客戶——英國的王室加政府,它不會倒閉。“光榮革命”之后,英格蘭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實現了政治上的穩定,再沒有發生過內戰,告別了皇權及政權更替的動亂,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外部挑戰,爭奪世界霸權。做它的生意,是金融城雄厚的財力與雄心勃勃的權力的完美聯姻。其次,這個客戶的需求是欲罷不能,因為17 世紀后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與他國開戰。
除了“九年戰爭”——威廉三世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之間打,1756-1763年英國又和法國打了“七年戰爭”,奪取了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它與荷蘭打、西班牙打,在東方與印度莫臥爾王朝打,1775年和爭取獨立的美國人打,在18世紀末葉,又和法國的拿破侖打得不可開交。盡管戰爭為英國帶來貿易與殖民上的優勢,金錢滾滾流向英國,但政府越戰越要依靠金融城的財力支持,借款越滾越大。史學家們認為,從17-18世紀英國的人口與經濟實力來說,法國抵得過兩個英國。當時法國的人口近2000萬,是英國的三倍。為何英國最終戰勝法國,成就世界霸權,現代金融的支撐被視為重要基石之一。
英格蘭銀行成立是公眾與政府信用關系上的一大進步。以往的政府向私人部門舉債是單獨協議,政府有權違規,規則不透明。現在是政府與一個機構做生意,正式簽約,在商言商,相互制約。這家銀行必須是私人擁有的,才能作為與政府利益不同的一方,保證交易的公平性與安全性。英行的股東唯利是圖,但他們同時非常看重大英帝國在全球的崛起,看重以英國自由主義原則在全球推進貿易與殖民,這離不開國家與政府的力量。為了長遠更大的利益,商人們樂于與政府結盟。
英格蘭銀行當時并未想到控制國王和政府的永久債務,但后者在乞求前者解救燃眉之急。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條件,國王給了英格蘭銀行一個有時限的“特許經營權”:在11年(1706)之后,一旦政府還完初始貸款,經營權就會收回。這里要強調一句,此時的英格蘭銀行沒有穩定金融、貨幣、經濟、外貿的責任,這些概念當時完全不存在。英格蘭銀行后來發行的銀行券不過是替代了直接的財政債券,也不是國家貨幣。它成為所謂的“中央銀行”,還有漫長的一段歷史進程。
英格蘭銀行成立的故事及其留下的繪畫,使我們聯想起清圣祖康熙皇帝1690年開始的準噶爾征戰。這一仗一直打到1697年,康熙三次親自出征,時間正好與英法“九年戰爭”重合。乾隆皇帝曾說“兵不可一日不備”,他開疆擴土,東征西討,在18世紀幾乎和英國一樣,大小戰役,連綿不斷。那么,大清是如何解決戰爭財政問題的?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對比。史學家黃仁宇專門考證過明清的稅收與財政問題。據歷史學者梁柏力的綜合,清初戰事頻仍時期,除了稅收,朝廷還依靠捐納制度,即賣官鬻爵,鼓勵商人通過捐納取得功名。清政府和商人們有很多合作,如由“皇商”幫助運送戰爭物資,支持在準噶爾征戰的清兵。據信,到19世紀后半期,這些隱性的財政收入所占比例日增,通過捐納途徑當上地方官的人已占到官員的一半。晉封為“皇商”的“專賣”為皇家采辦貨物,將軍需物資送達戰事前線,不但獲得厚利,而且有了功名。這種戰爭財政的體制一直到同治朝還在實施,運作有效。只是到了“洋務運動”,清政府才認識到為強兵而購買洋人的槍炮,必須拿真金白銀,投資兵工廠要貨幣資本。
大清朝廷后期向外國銀行借了不少錢,這是后話。但直到倒臺,它也沒向國內市場借錢(只在1906年有一次失敗的嘗試),這未必不是中國近代金融沒有發達的原因之一。清末民初中國有一位改革家大聲疾呼政府應當大力發行內債而非僅靠外債(目的非為戰爭),并通過政府發債來發展現代銀行業與證券市場,他就是梁啟超。
1908年他說“東西各國,公債之用,真如布帛秫米”。而在中國,“除外債外,政府與國民,無一毫債權債務之關系”。仿英國200年前的做法,政府向國民舉債,在梁啟超眼中,“實我國人民目前相需最殷之問題也”。
(作者為財經作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