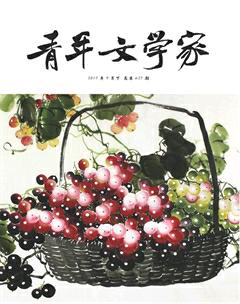《青銅葵花》
王啊滿++陶磊
摘 要:男孩青銅,女孩葵花,真摯淳樸的情感最終卻敵不過命運的殘酷。但苦難之下卻是一顆顆善良純凈的心靈,震撼人心的人間真情,最自然最純美的人性。
關鍵詞:童年;苦難;人性
作者簡介:王啊滿(1998-),女,漢,江蘇宿遷人,南京醫科大學本科在讀,主要研究方向:衛生事業管理;陶磊(1979-),通訊作者,男,博士,南京醫科大學講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7-0-01
一、《青銅葵花》的創作背景
曹文軒說:“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每一個時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絕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少年時,就有一種對痛苦的風度,長大時才可能是一個強者。”
曹文軒將苦難、大美、至愛這三個,抒寫了一個鄉村男孩青銅和城市女孩葵花的故事。在接受專訪時,曹文軒對他的新作頗為自得。他直言《青銅葵花》一樣張揚著天下人間的真善美主題。
作品中的人物活靈活現地展現在故事的畫面中,文字純凈唯美,敘事簡潔流暢,讓人沉浸在一種高雅深遠的意境當中,真摯的情感暖入每個人的內心。字里行間處處透露著純凈的人間真情,觸動心弦震撼人心。除此之外,人道主義的光輝也通過一字一句閃耀在每一個角落。在作品中,苦難達到了一種極致深刻的狀態,充滿生機與情義的大愛升華到了書的盡頭。無論是對苦難、真情,還是對美好人性的細致深刻的描寫和詠嘆,宛如一股源源不斷清澈的暖流,濕潤著每一個讀者的眼睛,洗滌著每個讀者的心靈,為我們在對追尋生命中永恒真善美的道路上指明了方向。
二、苦難下的童年與人性
古今中外,自從有歷史以來苦難的存在就伴隨著人類的發展,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會發現他的影子,甚至可以說,它隨時隨地的就圍繞在我們身邊。苦難是對人的靈魂的洗濯,經過洗濯之后的心靈會變得更加美好,更加充滿愛與美的圣潔光輝。苦難的存在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存在這個社會的價值和意義,領悟到人性的本質。
在《青銅葵花》中,哥哥青銅孝順懂事,乖巧聰明并且善良,是個啞巴,因為不能說話,沒人能夠理解他的內心和想法。但是他擁有很強的自尊心,有責任心會保護妹妹。妹妹葵花善良靈巧,樂于助人,七歲跟隨爸爸來到叫“大麥地”的村莊生活,被接到青銅一家與哥哥一起在這片蘆葦蕩中生活,與青銅一起同甘共苦。這些苦難本不該是他們這個年齡所承受的,在天災人禍的世界里,青銅一家從未絕望過,他們在苦難的長河中掙扎著、奮斗著,面對房屋倒塌、災年蝗蟲、水災、火災,他們都以從容的姿態迎接著,以處事不驚和樂觀的態度去克服。
風風雨雨中,青銅葵花彼此幫扶支持著,但是小孩子的童年總是籠罩在大人的話語權和權威之下。童年是質樸而又脆弱的,與大自然間親密無聲的交流,伙伴之間平等快樂的交流玩耍。爸爸的死使葵花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葵花和青銅成為了兄妹,青銅葵花一起生活,一起長大。但十二歲那年,女孩葵花被命運召回了她的城市,男孩青銅從此常常遙望著蘆蕩的盡頭,遙望著女孩葵花所在的地方……,失去妹妹的青銅心如刀絞,他望著蘆蕩的盡頭,居然開口說話,用平生最大的力氣,從心底高喊了一聲:“葵花!”喊聲震動了所有人的心靈。盡管青銅失敗了,但他對葵花的守候表明童年的話語權與地位以及自由一直都在被默默守護中,童年的夢想將不會消失,童年將一直會存在。
曹文軒借《青銅葵花》敘述了對“苦難”的看法,訴說了對孩子應如何看待“苦難”的美好希冀,“我們需要的是面對苦難時的那種處變不驚的優雅風度。”優雅風度是一種從容不迫的氣質,是在深刻認識“苦難”后,懷揣著對苦難、對生命的敬畏培養而來的,是身處困境時的永不言棄,是體驗痛苦時的堅定沉著,是面對苦難時的波瀾不驚,平靜淡然。弗蘭克爾在追逐生命的意義中多次指出:“如果人生有其意義,那么受苦也定有其意義……身臨逆境,我們承受苦難的態度,我們保持勇敢、尊嚴、無私無畏的姿態是真正的內心世界的升華。”
三、結語
《青銅葵花》將愛寫得充滿生機與情意。在絕望的苦難背后,是意志的頑強,人心的溫暖。前方的道路不可預知,險阻不可估量,這一道道看似不可突破的屏障,卻在純美的人性中漸漸融化,露出前方希望的曙光。人性中的真善美才是我們真正理應追尋與守護的。而與當今泛濫的享樂主義相比,這無疑是另一種聲音。它進行的是一種逆向的思考。它是對苦難與痛苦的確定,也是對苦難與痛苦的詮釋。凡是不能兼愛歡樂與痛苦的人,便是既不愛歡樂,亦不愛痛苦。凡能體味她們的,方懂得人生的價值和離開人生時的甜蜜。
參考文獻:
[1]鐘力.曹文軒《青銅葵花》中的苦難意識探析[M].云南:《新西部》,2017.
[2]袁曉松.曹文軒的苦難意識與弗蘭克爾意義心理學的雙重思考—評曹文軒的《青銅葵花》[M].內蒙古:《陰山學刊》,2011.
[3]橘麗.解析曹文軒《青銅葵花》對童年本質的思考[M].河南:《芒種論壇》,20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