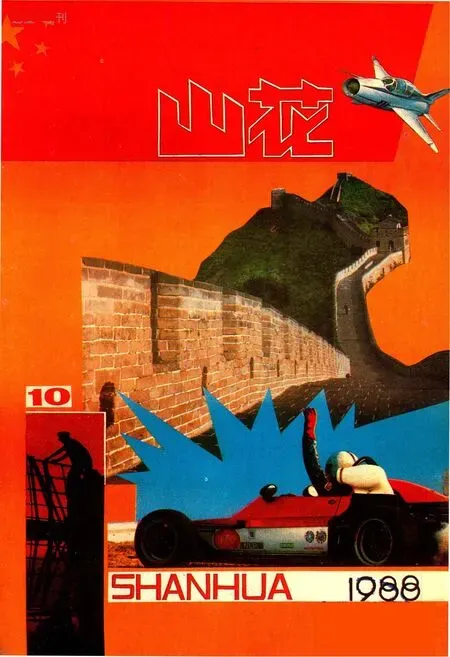我們的病生在了心里
科幻現實主義與虛幻的現實
郝景芳出生于1984年,大學與研究生階段均在清華大學攻讀物理學,后轉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現就職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從事宏觀經濟研究,2006年郝景芳進入清華大學天體物理中心攻讀研究生,同時也開始了科幻寫作,至今出版了長篇小《流浪蒼穹》(2016),中短篇科幻集《星旅人》(2011),《去遠方》(2016)和《孤獨深處》(2016)等。這些集子大都在她獲得雨果獎之后出版,長篇《流浪蒼穹》是之前兩部作品《流浪瑪厄斯》(2011)和《回到卡戎》(2012)的合集,《去遠方》是《星旅人》的調整版本,《孤獨深處》收錄了一些之前從未發表的故事,包括獲得雨果獎的《北京折疊》。《永生醫院》是她最近的有一篇力作,尚未收錄到任何作品集。
《永生醫院》繼承了郝景芳從《北京折疊》開始的科幻現實主義寫作,用近乎荒誕又極具幻想的描寫,描繪了一個與現實遙遠而又近在咫尺的空間。如果《北京折疊》預指這個城市病了,那么《永生醫院》應該可以說預指我們的心靈病了。主人公錢睿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將父母為自己的一切視為理所因得,也將自己對父母的一切視為理所應當,直到母親重病住進了醫院,才恍然大悟自己對母親的關愛是那么稀少而可伶,而自己之前的一切是那么的不應該。正所謂“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時候的錢睿恍然大悟,想要開始彌補自己之前犯下的錯誤。但事到臨頭依舊恨晚,母親住的醫院拒絕任何探視。這是人生最可悲也最可憐的遭遇,等到想要彌補親情時發現一切都晚了。于是可想而知,錢睿的心中該如何懊悔和糾結。但是幸運的是,中國人永遠是地球上最善于變通的種族,錢睿偷偷從醫院的后門溜進了病房,望著躺在病床上面色僵黃、一動不動的母親,他已經不知道該做什么。只能每晚偷偷溜進醫院,無望地看著母親一天天病情加重,一天天走向死亡。就在錢睿心如死灰時,他突然發現很久沒去的父親那里又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母親,只不過這個母親不再病入膏肓而是在一瞬間恢復了往日的生機。錢睿陷入了一個深深的謎團,為了弄清緣由,他想盡了辦法,但卻得不到父親的理解。而在最后,他發現了答案,他真正的母親確實已經去世,而父親那里生機勃勃的“母親”其實是永生醫院克隆出來的,完全是他母親的復制品,不僅復制出了身體還復制了記憶。他為此倍感痛恨,感覺是永生醫院欺騙了他,試圖去向社會揭露這個秘密。但面對真相,父親卻阻止他去揭露。他完全不能理解,直到永生醫院向他公布了真相,原來連他自己也是這個永生醫院的產品。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而曲折的故事,故事的最后來了個極地大反轉。除了克隆人,整部小說像極了現實主義作品,這就是現在流行的科幻現實主義。郝景芳的《北京折疊》就帶有鮮明的“科幻現實主義”風格,而她的《永生醫院》可以說也繼承了《北京折疊》的“科幻現實主義”。
科幻現實主義由青年科幻作家陳楸帆提出理念,由著名科幻作家韓松老師命名。陳楸帆在《對“科幻現實主義”的再思考》一文中對科幻現實主義進行了解釋,他稱更愿意將“科幻現實主義”理解為一種話語策略,面對現實,因為有太多禁忌問題,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在逃避,科幻文學反而可以關心現實 。在之后的闡述中,他將大部分“嚴肅”的科幻小說都歸為“科幻現實主義”的范疇,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風格,高于‘太空歌劇、‘賽博朋克、‘反烏托邦等亞文類之上,科幻現實主義可以作為一個定義加在任何一種亞文類的前面”。在小說中體現了某種邏輯自洽的“真實性”并由此必然跟現實產生聯系的科幻小說,都可以稱為“科幻現實主義”。在陳楸帆那里,是由于現實的某種限制和禁忌,讓科幻文學成為一個很好的表達現實的窗口;而對于郝景芳來說,“虛幻現實可以讓現實以更純凈的方式凸顯出來”,她采用科幻的形式,是為了更好地表達現實、關心現實。
《北京折疊》最令人震驚之處,在于第三空間的龐大人口徹底成為社會高速發展甚至正常運轉的一種贅疣,因此不得不以空間區隔的方式劃分時間,為他們的生存制造一種對社會發展而言完全沒有意義的時空。故事的新異之處不在于高速發展的技術,而在于技術發展之后的社會管理以及個體價值的實現,這是郝景芳執著求索的問題。
而在《永生醫院》一文中,郝景芳再次通過科幻凸顯現實問題。可以說無論在何等虛幻而遙遠的時空架構當中,她心心念念的其實仍是小說所被創作的當時以及人類在那樣一個時空中與現實的狀態。如小說所反映的現代社會親情的淡漠,主人公可以很久不回家一趟,偶爾回來一趟也被母親點破為“假意敷衍”。
他上樓的時候,擔心父母馬上要睡覺,又擔心母親苛責他聲色犬馬,于是惴惴不安起來,想了一大串說辭,進門看到母親臉色不好,就先聲奪人,母親還沒來得及說他,他就說了一番自己近來如何忙,工作有多么不順利,壓力多么大,要求家人不要阻礙他的前程。他說著就看到母親的臉越來越沉。他防御地抵抗想象中的苛責,卻沒想到正式這番虛偽的防御最讓母親傷心。母親沒說什么,只說以后如果忙,不來也沒關系,不用假意敷衍。
甚至在關心母親時都不知道父親在家里已經有了一個健康的“母親”在陪伴。
他見鬼了。他見到母親好端端地坐在沙發上吃晚飯。
這真是人世的悲涼,也是現實的寫照,在我們忙碌于工作和學習時,看似為了自己的遠大前程,卻忘記了家里真正需要關懷的親人,一句暖心的話,真正親情的交流,在看起來合情合理的理由面前消散得一干二凈。
還有小說中提到的醫患隔閡,醫院為了怕社會知道真相,設置了最嚴密的監控措施杜絕一切探視,而處于對醫院長期以來的不信任,錢睿絞盡了腦汁要尋求真相,甚至不惜通過黑客來幫忙。而在真相面前,他又變得不堪一擊。
當然,這篇小說還探討了克隆人是不是被人類社會所認可的嚴肅話題。這也是現實之中人類中心論最好的反映,或者可以說基于自身對他者的歧視。人類奴役屠殺動物,男性歧視女性,白人歧視有色人種,正常婚戀人群歧視LGBT,還有反向歧視。在這部小說中,克隆人也是一個不被認可的群體,即使他有正常人的記憶、思想和情感,但他仍然游離在法律以外的灰色地帶,不受法律保護,也不受整個社會的認可。即使你知道了真相也不敢把這樣的真相給揭露出來,因為最后數百萬克隆人的暴露會掀翻整個社會的倫理基礎。
《永生醫院》選取的這些話題直面我們的真實社會,讓我們無從逃避,而這也許就是科幻現實主義的魅力之所在,不在于炫耀多美多好的高科技,而是表達現實、關心現實,讓現實的丑陋暴露無疑,讓我們只能直接面對,正面解決。
隱喻中的科幻現實
郝景芳的科幻寫作呈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對個體困境的社會沉思,科幻于她而言是一種寫作的策略,將各種興趣和要素嚴絲合縫地編織在一起,最終引向的是作家自身的經驗、體悟和思考,形成了作家的個體特色。從中外科幻發展的角度看,郝景芳的科幻屬于一種典型的“軟科幻”,其中的科技內容僅在類比而非推測的層面展開,也可以說屬于一種暗喻或是隱喻。如何處理科學與技術的內容,是以之為敘事的整體邏輯和規約,還是僅僅把它們視為一種文學為數眾多可能因素或材料中的一種,這是“硬科幻”與“軟科幻”的區別,也許就是劉慈欣和郝景芳這兩位雨果獎獲獎者代表的不同書寫走向。
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曾說“科幻不是預測性,而是描述性的……一切虛構作品都是暗喻。科幻也是暗喻。它與更老的虛構作品之不同似乎在于對新暗喻的使用,源自我們當代生活的某種巨大的統治力量——科學,所有的科學以及技術,其中也有相對論和歷史觀念”。
語言學家斯托克維爾曾經將科幻構造替換現實的策略描述為“對隱喻的字面化”,因此從高速運動的時間機器上觀察天空,太陽真的變成了“一道火光,一抹燦爛的弧光”,在賽博朋克的宇宙中,情感真的能夠被機器調節控制。
著名科幻學者達科·蘇恩文為強調科幻文本中替換世界對現實的指涉性,重新闡釋了隱喻的概念。他將隱喻定義為“來自不同話語或語域系統的不可比擬的概念單位在語言層面上同時并存、相互聯系,由此產生一個整體性意義”。隱喻包含兩個層級,作為表述的喻體和作為被表述意義的喻旨。隱喻可以產生于句子層面或文本層面,科幻文本即為一種典型的隱喻文本,其中可能的世界或者是情節是喻體,而創造的新異則是喻旨,其他時空之中的關系,總是指涉著作家當下的人類關系。
在郝景芳的寫作中,如果說上述字面化隱喻僅僅是在概念層面的展開,那么《北京折疊》中的隱喻就帶上了“新異”的社會內涵,時空的區隔成了階級身份區隔的隱喻性展開。而就《永生醫院》而言,她的隱喻在于,我們對生命的渴望和生命短暫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或者也可以說我們對烏托邦的理想追求與惡托邦的現實之間的不可融合。人類自古就有對長生不老的渴望,而且很早就把這種渴望寫進了神話故事中。如《穆天子傳》所描述的周穆王去西天王母處求不死藥,秦始皇派徐福東渡蓬萊尋長生不老藥。乃至現代的科幻小說中依然有此描述,如美國科幻作家羅伯特·海因萊因的《時間足夠你愛》中用生命延長術讓人永生,中國臺灣科幻作家張系國的《超人列傳》把人的器官用人造器官替代來永生,而英國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則讓人變成了精神體存在于宇宙,不生不滅,永世長存。但對現實中的我們而言,永生真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即使醫學發達,我們的生命可以延續到百歲,但器官衰竭終會讓我們慢慢死亡。甚至現在西方經常宣傳的冷凍遺體等待復活的項目,也只是一個用于吸引投資的大IP而已,那些自愿冷凍的人們其實在冷凍之前都已經確認為生理死亡了。
雖說永生做不到,延長生命我們還是可以做到的。社會上永遠不缺可以讓你青春永駐的化妝品、可以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即使你得了不治之癥,最新的醫療技術依然可以讓你延長十年乃至數十年的生命。但這些難道真是我們所需要的嗎?就如《永生醫院》里所寫,我們是讓生命卑微地消失在病床上,還是克隆一個有著母親驅殼和記憶的克隆體。在大自然面前,我們是坦然接受生命的生老病死,還是冀圖人定勝天抵抗那些讓我們的生活質量下降的絕癥呢?有的人應該會選擇不惜一切辦法延長自己的生命,即使這種延長會降低我們的生活質量,會讓我們生不如死。而有的人應該會選擇坦然面對。我想這真的不是一種容易的選擇。
《永生醫院》的出現應該也是一種我們對未來美好的渴望,渴望我們的未來就是一個大的烏托邦,疾病不再是困惑,死亡也不再是問題。這種對烏托邦的渴望也是源自對古代先賢和宗教的演繹。孔子在《禮記》中曾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這是傳統儒家的大同社會。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則在世界末日的假想中設置了人類審判環節,通過審判去天堂,得到最后的救贖。佛教則指出生命會六道輪回,只有斷除欲念真正解脫才能擺脫輪回的困擾。托馬斯·莫爾則在《烏托邦》中塑造了一個財產共有、按需分配、婚姻自由、以人為本、和諧共處、宗教多元的理想社會。而在科幻小說中,我們經常所見是反烏托邦或者是惡托邦的描繪,像蘇聯作家扎米亞京的《我們》、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以及英國作家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都是這樣的典型之作。而郝景芳在《北京折疊》中創作的惡托邦,則是以渺小的個體無法抵抗整個社會來描繪未來的世界。就《永生醫院》而言,初看好像違背了科幻小說描繪反烏托邦小說的傳統,描繪了一個可以永生的“烏托邦”。但仔細想想,這其實也是一種惡托邦。雖然未來有了克隆技術帶來的永生,但這種永生被資本和權力所掌握,并不是普通人可以享有的,這其實也是種變相的隔離。有點像劉慈欣《贍養人類》,一個星球的資源99%被一個人所擁有,星球上的其他人只能分享剩余可憐的1%。
科幻小說的惡托邦對現實是有啟示的,因為他向我們展示了險惡的未來,在這一預示圖景下我們就可以避免走出這樣的道路。將時空旅行、外星人與基因改造等敘事手段能融入烏托邦的敘事中,再用科幻的隱喻來關心現實之中那一個個渺小的個體,讓我們的心靈不再生病。而這也就是郝景芳的寫作對于中國科幻的啟示意義。
作者簡介:
付昌義,南京工業大學副教授,科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