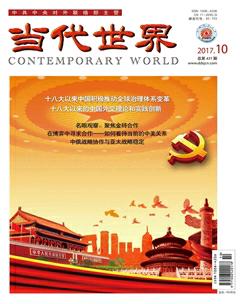在博弈中尋求合作
陶文釗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其個人多變的風格及在政策當中體現出來的不確定性給未來中美關系也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雖然如此,對于未來的中美關系,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當中還是有許多可供判斷的基本點。在看到美國視中國為今后數十年中對美國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戰者,要對中國進行牽制、平衡的同時,可以明確,中美兩國利益高度相關,不論政治還是經濟領域均深度依賴,未來的中美關系仍將是在博弈中尋求合作。
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勝選后,國內學界普遍認為這個結果給中美關系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本來,美國經過大選實行政權更替,在新政府執政的初期中美兩國有磨合期,也是正常的事情。但過去八個月中國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似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磨合期,因為當前美國政治就處在非理性時期,特朗普就是與眾不同的總統,中美關系有點不同尋常也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情。究竟如何看待當前的中美關系,它在最近的將來走向如何?筆者在這里談一點粗淺看法。
判斷中美關系的基本出發點
當前我們判斷中美關系有兩個基本出發點:一個是中美關系的基本狀況,兩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另一個是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看法,認為中國是在今后數十年中對美國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戰,因此要對中國進行牽制、平衡。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當政,這個基本的事實和基本的看法都是存在的。
第一,兩國利益的高度相關性。中美兩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不是一句宣傳,而是有實實在在的依據。最直觀、最說明問題的仍然是經濟利益。近39年來的實踐證明,盡管中美政治關系時有起伏,但雙邊的經貿關系卻持續穩定地發展,確實起到了中美關系“壓艙石”“減震器”的作用,而且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現在中美的雙邊貿易額超過了5000億美元,中美長期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投資截至2015年累計中國對美近500億美元,美國對華近800億美元。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美兩國在金融上的相互依賴更加突出。中國外匯儲備最多時近4萬億美元,至今仍有3萬多億美元,其中70%是美元。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券,這對美國金融穩定至關重要。美國擔心中國拋售,其政要一再希望中國繼續購買債券。截至2017年6月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票據和國庫券的總量達1.15萬億美元,仍然是美國最大的海外債主。中美兩國未來經濟的變化既會促進兩國的合作,也會導致兩國的競爭。但經貿關系作為兩國關系壓艙石的基本狀況沒有改變。中美兩國在政治、安全、環境等許多問題上的利益都密切相關。
第二,美國認定中國是對美國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戰者。大概2010年、2011年前后,美國戰略界(包括兩黨的戰略界人士)大致達成共識:現在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是對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主要挑戰者,是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前副國務卿斯坦博格(James Steinberg)及著名學者奧漢隆(Michael E. OHanlon)寫道:近來,由于中國經濟的引人注目的增長以及中國軍費和作戰能力的急劇提升,中國成了有關美國戰略主導地位辯論的焦點。美國政界領導人和學者認為,從蘇聯解體以來現在第一次有可能具體地來設想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挑戰。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主導地位以及美國的安全形成了直接的挑戰,因而美國必須牽制中國的能力。[1]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有復雜的背景,但一個重要目的是牽制中國。“再平衡”戰略的主要設計者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說:“美國歷史上保衛其利益的辦法,防止在亞洲出現一個霸權國家,仍然是美國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 [2]奧巴馬政府增兵亞太,強化在亞太的同盟體系,與發展中大國尤其是印度加強伙伴關系,重視亞太的多邊機制等等,做了很多布局。
奧巴馬政府卸任了,“再平衡”或“轉向”這樣的說法也終結了,但這絕不意味著特朗普政府不再把中國看作主要挑戰了。特朗普就任后,忙于國內事務,政府本身的許多重要崗位仍然空缺,還要削減國務院預算的30%,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還是個代理,因此還顧不上系統闡述其亞太政策,包括對華政策。
從以上兩國基本情況出發,似乎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一是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長周期已經過去了。這里所說的長周期是指布什政府時期。從2001年7月解決了“撞機”事件以后,到布什任期結束,有七年半的穩定,如果再加上2009年,那就是八年半的穩定發展。之所以有這樣的長周期,主要原因是中美都照顧了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中國在反恐、防擴散、應對金融危機方面支持、幫助美國,美國在“臺灣問題”、中國“入世”、北京2008年夏季奧運會問題上照顧了中國的關切。2010年起情況已經改變,現在更沒有這樣的條件。現在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沒有壓倒一切的關切,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引領、沖擊著兩國關系,使兩國關系呈現不斷起伏的狀況,這是中美關系的新常態,我們要習慣于這種狀態。
二是中美關系是一個大關系,是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大國關系體量大,抗拒風浪的能力也強。經過近40年的發展,中美關系是有韌性的。現在特朗普政府沒有對中國采取敵視態度,還是希望加強兩國之間的接觸和交流。最近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訪華,與中方簽署《美中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框架文件》、特朗普準備年內訪華都表明了這一點。有一些顛簸也不怕,這艘大船經受得住。以后我們要習慣于在博弈中尋求合作,在顛簸中推進兩國關系。
三是積極主動地塑造中美關系。中美兩國總的說來是彼強我弱。但在兩國關系中中國從來都不是被動的一方,而且隨著國力的增長,中國可以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越來越多,塑造中美關系的能力也越來越強。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來應對美方的“再平衡”戰略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雖然特朗普特立獨行,但在實踐中,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美國仍然離不開中國的合作。所以在兩國關系中我們仍然有運作、回旋的余地,仍然可以爭取主動。
需要高度關注的四個問題
在特朗普任內,以下四個領域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博弈可能主要在這幾個領域展開。
一是臺灣問題。臺灣問題長期以來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馬英九執政時期海峽兩岸關系實行了和平發展,美國的保守勢力對此十分不滿,總想著如何再把它逆轉過來。2016年大選中共和黨的競選綱領就是一個證據。這個綱領閉口不提“一個中國”政策,不提三個聯合公報,相反,不但講了《與臺灣關系法》,而且提到了里根政府1982年7月關于售臺武器對“臺灣”的“六項保證”。這在以前的共和黨競選綱領中是沒有過的。并稱臺灣問題必須以臺灣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解決,如果中國政府違反這一原則,美國就要去“保衛臺灣”。[3]綱領的說法可以看作是對海峽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一個反撲。
在美國政界和學界存在著相當大的親臺勢力。2009年11月和2011年1月兩個《中美聯合聲明》中都表示歡迎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引起保守勢力的強烈不滿。傳統基金會、2049項目、美國企業研究所等智庫的一些學者連篇累牘發表報告和文章,要求奧巴馬政府“將美臺關系解凍”,“滿足臺灣的自衛需求”,強烈要求向臺灣地區出售F-16C/D戰斗機,不一而足。[4]
國會中的保守勢力也在持續推動提升美臺關系。眾議院在2017年8月14日通過的《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包括了涉臺條款,“要求國防部長評估美臺軍艦相互停靠對方港口的可行性”,以及“將對臺軍售程序正常化”。8月23—25日,共和黨夏季會議又通過了“友臺決議案”,妄稱“《與臺灣關系法》和‘六項保證是美臺關系的基石”。顯然,共和黨是刻意要打臺灣牌了。如果總統是個明白人,政府工作有效,政府也是可以影響國會的。但特朗普似乎不是這樣的明白人。先頭他已經接過蔡英文的電話,雖然他后來做了關于一個中國的表態,但他對臺灣問題的敏感性是否已有充分認識仍然值得懷疑。在特朗普任內共和黨保守勢力可能進一步興風作浪,做出違反一個中國政策、大幅度提升美臺關系的事情來。
二是朝核問題。 特朗普當政以來,高調擯棄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實行“極限施壓”,試圖動員國際社會對朝鮮施加最大程度的壓力,迫使朝鮮放棄核計劃。美朝的口水戰不斷升級。朝鮮則不斷發射導彈,還威脅要對關島進行打擊。9月5日,又進行了第六次核試驗,而且據說是氫彈。聯合國安理會一再通過決議和主席聲明,對朝鮮的制裁越來越嚴厲,但實際效果仍然有限。特朗普政府想一股腦兒地把解決朝核問題的責任推給中國,多次發聲說,中國沒有在朝核問題上幫忙。
美國政界和智庫、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認為朝核是東亞地區最危險的問題,他們發了許多報告,但誰也提不出解決朝鮮問題的良方。特朗普政府在朝核問題上一直發出混亂的信息。特朗普自己朝令夕改,他的說法與國務卿蒂勒森、防長馬蒂斯的表態也不一樣。最有名的是8月8日他剛剛放出狠話,朝鮮“最好不要再威脅美國”,否則將會招致前所未有的“炮火與怒火”。第二天,蒂勒森就出來“滅火”,表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朝鮮半島核問題發生急劇變化,美國民眾可以放心睡覺。以致人們很難判斷,到底誰代表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是以往美國政府沒有發生過的。
對于中國來說,一個大的變化是,在當年主持六方會談時,中國與其他各方關系都不錯,只與日本關系差一點。因此中國可以在美朝之間勸和促談,中國的調停是雙方都接受的,因而是有成效的。現在情況變了,中國與朝、韓、日關系同時陷入困境,與美國又有深度的疑慮,還有薩德(THAAD)系統的部署在這里添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不應再以十年前的思維來考慮現在的朝核問題。[5]
現在阻止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韓國。因為如果爆發戰爭,首先遭殃的是韓國。韓國國內在別的問題上分歧很大,在這個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樸槿惠下野時,五位不同政黨的候選人一致反對美國對朝鮮發起先發制人打擊。現在文在寅也一再向韓國民眾保證,特朗普已經向他承諾,如果要對朝鮮進行軍事打擊,一定首先與韓國商量。
三是南海問題。特朗普上任以后,不再用“轉向”“再平衡”的說法,但這并不表明他的亞太安全政策與前任發生了重大變化,更不能指望特朗普政府會在南海放松對中國的壓力。特朗普要使美國再次強大,要把美國的艦艇從現有的270多艘增加到350艘,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中美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和適用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第一,軍艦在領海的“無害通過”權問題;第二,軍艦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活動權問題;第三,領海基線劃定問題;第四,軍事測量和海洋科學研究的界定問題。中國政府通過國內立法的形式,明確了自己的權利。美國則稱,海洋空間從法律上僅分為兩部分:國家水域(national water)和國際水域(international water),前者僅包括內水、領海、島嶼與群島水域,而后者則指領海之外的全部水域,包括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公海自由權利、軍事活動權利等均適用于國際水域。[6]中國一再要求“域外國家”不要做挑撥離間、制造緊張的事情,美國則宣稱,這里是公海,無所謂“域外國家”。
美國的“航行自由計劃”是卡特政府 1979年制定的一項行動計劃,旨在維護美國海洋自由原則,防止沿海國家的“過度海洋主張”對美國海洋大國地位的挑戰,保證美國軍事力量在全球的機動暢通。[7]自1992年起,美國就持續對中國的海洋主張進行挑戰,特別是2011年之后,美國針對中國所進行的“航行自由行動”挑戰內容顯著增加。在海上挑戰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海軍“航行自由行動”的主要任務之一。2016財年,美軍共對全球22個國家和地區行使了“航行自由權”。[8]奧巴馬政府時期,美軍方就多次派軍艦、軍機闖入我領海、領空。據美國媒體報道,每次行動軍方都要獲得白宮的批準。如軍方早想派“拉森”號來南海, 但2015年9月下旬習近平主席要對美進行國事訪問,白宮推遲了行動,招致軍方強烈不滿。
2017年,在特朗普當政的頭三個月,美國沒有在南海進行“航行自由行動”。 4月,防長馬蒂斯將一份年度計劃送交白宮,該計劃規劃了2017年全年美國派艦機在南海挑戰中國海洋權益主張的具體安排,已獲特朗普批準。此后,美軍已在南海地區開展了三次“航行自由”行動:5月24日美軍“杜威”號導彈驅逐艦闖入我南沙美濟礁12海里之內;7月2日美軍“斯坦塞姆”號導彈驅逐艦進入西沙中建島12海里范圍內;7月6日美軍兩架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在南海上空執行飛越自由行動。[9]
南海問題是兩國關系中的“慢性病”,它將在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美國要以此來顯示它的存在感,美方還表示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故不會影響未來的航行和飛躍;中方要維護自己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但雙方目標又都是有限的:闖入的美艦基本不進行軍事操作,[10]中方把你趕走了事,雙方都不想為此提升緊張態勢,更無意為此打仗。從這個意義上說,雙方的矛盾是可控的。在南海問題上還得繼續跟美國周旋下去。
四是經貿關系。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授權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對華發起“301”調查,主要涉及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商標、專利、商業機密等。這只靴子終于落下來了,兩國關系的氣氛也頓時緊張起來。特朗普這樣做有他自己的邏輯。首先,他在選舉中講得最多的是丟失就業崗位,矛頭又集中指向中國,他對中國發起調查,是對選民“還愿”;其次,他治國理政的宗旨就是“買美國貨,雇美國人”,而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占了美國全部逆差的一半以上,如果對中國不做點什么,他跟別的國家,那些貿易逆差只有幾百億美元的國家,如韓國、墨西哥、日本等也就更不好下手了。
現在是不是就開打貿易戰了呢?還沒有。美國現在是把大棒高高舉起,威脅打貿易戰。20世紀90年代,中美曾因知識產權問題發生三次激烈的糾紛,每次都到了貿易戰的邊緣。此次發起調查,特朗普的目的是以此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做出讓步。
特朗普的決定并非完全出乎中方意料。實際上中方一直希望與美國有話好好說,何必撕破臉,一旦雙方開打貿易戰,只能是兩敗俱傷。特朗普看重“結果導向”,海湖莊園會晤后,中美就發起了百日計劃,雙方經過30輪磋商,達成早期收獲10條共識,包括中方從美國進口牛肉、進口液化天然氣等。6月中旬,中方高端智庫赴艾奧華州和紐約,與美方進行對話,試圖推動兩國的經貿關系。7月19日,中美舉行了全面經濟對話。美方對此次對話抱著不切實際的期望,結果沒有達到目的。特朗普遂做出這個決定。后續發展值得關注。現在的情況與20世紀90年代又不同了。中美都是世貿組織成員,一旦美國出手,中國可以提交世貿組織仲裁。
2017年中美關系中還有別的大事,包括社會與人文對話、執法與網絡安全對話,以及特朗普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中美關系還在繼續發展,兩國的合作還在博弈中進行,中美關系還會在顛簸中前進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徐海娜)
[1] James Steinberg,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4, p.65.
[2] Kurt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and Boston: Twelve, 2016. pp. 121,145-146.
[3] The 2016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July18,2016,https://www.gop.com/the-2016-republican-party-platform/
[4] Deng Cheng, “ Meeting Taiwans Self –Defense Needs”,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February 26, 2010; Walter Lohman,“ Defros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eritage Foundation, WebMemo, March 1, 2011; Dan Blumenthal,“Rethinking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aiwan”, 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3/02/rethinking_us_foreign_policy_towards_taiwan;Rupert Hammond-Chambers, “Time to Straighten Out Americas Taiwan Policy”,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014240527487045044045761838310151722.html;Rupert Hammond-Chambers, “ Make Taiwan Part of the Pivo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9, 2012; Abraham Denmark and Tiffany Ma, “ Dont Abandon Taiwan for Better China Ties”, http://globalpublicsquare.blogs.cnn.com/2013/09/12/d0nt-abandon-taiwan-for-better-china-ties/, etc.
[5] 曉岸:《朝鮮半島局勢:特朗普的“炮火與怒火”》,載《世界知識》,2017年 第17期,第37-39頁。
[6] 參見曲升:《美國“航行自由計劃”初探》,載《美國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3頁。
[7] 參見曲升:《美國“航行自由計劃”初探》,載《美國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2頁。
[8] 連晨超:《特朗普還沒在南海挑戰中國?可能只是時間問題》,2017年4月26日,http://military.china.com/critical3/27/20170428/30470133_1.html.
[9] 《美媒稱特朗普已批準美軍2017年南海“航行自由”全年計劃》,2017年7月22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722/2207447.shtml.
[10] Michael OHanlon and James Steinberg, A Glass Half Full? Rebalance,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in the U.S.-China Strategic Relationship,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7, 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