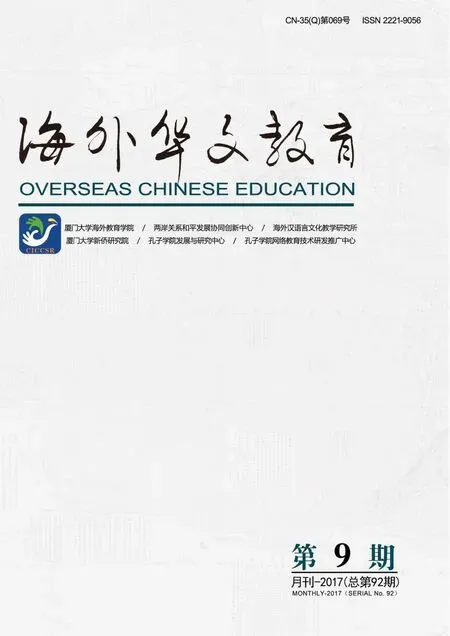派生詞的語素教學實驗研究
——以“VP者”為例
劉婭莉 王玉響
(四川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中國成都610068;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語言學系,美國加州95616)
派生詞的語素教學實驗研究
——以“VP者”為例
劉婭莉 王玉響
(四川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中國成都610068;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語言學系,美國加州95616)
語素和構詞法的教學對派生詞的習得十分重要,不同教學處理方式促進學習者不同的詞匯認知加工方式(聯結加工、激活加工和創造加工),進而影響習得效果。本文以派生詞“VP+者”為例進行教學實驗,發現:講解構詞規則或者讓學習者自己發現構詞規則能夠促進詞匯的深層加工,從而大大促進激活加工和創造加工,因而能夠抵抗記憶消退的影響,促進長時記憶,且規則介紹越清晰習得效果越佳;背誦法則主要促進聯結加工,雖能實現即時的教學效果,但無長期功效。在實驗的基礎上,本文指出派生詞教學的必要性并提出教學建議。
VP+者;對外漢語教學;聯結加工;激活加工;創造加工
一、研究背景
現行對外漢語語法教學中只有詞、詞組、句子三級語法單位,詞被認為是最低一級的語法單位。關于詞的教學只涉及詞類的劃分、詞在句中的語法功能等,構詞法是教學中的一個空白,然而語素和構詞法的教學對外國人學習漢語很有必要,可以大大提高學生學習詞匯、掌握詞匯、擴大詞匯以及正確運用詞匯的能力。(呂文華,2000)相對于英語等語言,漢語的構詞詞綴雖然不太豐富,但同樣具有較強的產詞能力,比如“者”和“家”。(陸志偉,1957;呂叔湘,1979;張斌,2002)此類派生詞具有一定的類推性,顯然沒有必要一個一個去教;如果教學處理得當,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Shqerra,2014)但教學中應該如何處理這類詞語呢?是向學生講解構詞規則,還是讓學生自己去發現規則?抑或是讓學生死記硬背或者不加任何干預,讓學生自然習得?不同的教學處理方法對派生詞的習得有什么影響?哪種教學方法對習得最有效?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有必要對教學方法——即如何教授派生詞,進行教學實驗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文通過教學實驗對比分析四種派生詞教學方法的習得效果及其成因,并分析不同實驗組在即時條件下的測試與延時條件下的測試呈現出的特征的異同及其成因。這四種教學方法分別是:講解規則法(教師呈現相關詞語和詞組并講解構詞法規則,學生只需接受教師的講解)、啟發規則法(教師呈現相關詞語和詞組,由學生自己發現規則)、死記硬背法(教師只呈現派生詞,讓學生記憶)、自然法(不對派生詞做任何教學處理)。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加精確,我們選取了二語者使用的高頻詞綴N——“者”(王茂春,2003;馮敏萱、楊翠蘭、陳小荷,2006);另外,鑒于“X者”的構詞規律比較復雜,我們只選取其中構詞規律相對清晰的“VP+者”進行構詞法教學實驗研究。
三、實驗方法
(一)被試
被試為48名中級水平的漢語學習者,來自日本、韓國、印尼、越南、俄羅斯、意大利、澳大利亞等13個國家,均為中山大學國際漢語學院留學生。
(二)實驗流程、材料與方法
我們參照張金橋(2008)、靳洪剛、章吟(2009)、洪煒(2011)等的實驗方法,將實驗分為4個階段,前后跨越4個月(見圖1)。

圖一 實驗階段
1.前測
在第1周進行。目的在于測量學習者對“VP+者”的掌握程度。使用紙筆測試,時間為5分鐘。讓學習者使用“X者”組詞,具體如下:
填空:使用“____者”組詞:
____者、__者、__者、__者、__者、__者、__者、__者
測試完成后,我們刪去非“VP+者”,包括:“形容詞+者”,如“智者”、“自信者”;“名詞+者”,如“理想主義者”;“數詞+者”,如“第三者”。
我們按照“VP+者”的正確構詞頻數,將被試分成四組,每組12人,組間差異不顯著F(3,47)=0.026,p=0.994(>0.05)。這保證了四組被試基本同質。
2.教學處理
在第2周進行。為了避免學習者猜測出實驗目的,“VP+者”的教學(部分參見王茂春,2003)與其它4個無關生詞的教學一起進行。在實驗前,教師明確告訴學生,實驗后將立刻對所學內容進行測試。
(1)“接受組”的教學處理
“接受組”重在向學生講解“VP+者”的構詞法規則,包括“者”是如何提取賓語的、“者”的音節組配規律。不僅展現正確的構詞形式,同時也強調錯誤的構詞形式。呈現部分,教師使用“×(錯)”、“(不常用)”、“(常用)”等增顯視覺的符號幫助學生理解和記憶構詞規律。該組的教學處理流程具體如下:
(PPT第1頁呈現,時間4分鐘)
他踢球 他唱歌 他獲獎 我殺人 我愛國 我捐款
×踢者 ×唱者 ×獲者 ×殺者 ×愛者 ×捐者
×他踢者 ×他唱者 ×他獲者 ×我殺者 ×我愛者 ×我捐者
踢球者 唱歌者 獲獎者 殺人者 愛國者 捐款者
構詞規則:
雙音節+者:踢球者、唱歌者
√ 謂+賓(V+O):踢球、唱歌;×主+謂(S+V):他踢、他唱
教師講解如下:
“者”常常與雙音節結構搭配,構成三音節詞。“者”也與個別單音節動詞搭配,但數量非常少。與“者”搭配的雙音節結構,常常是“謂+賓”,如“踢球”、“唱歌”、“獲獎”、“殺人”、“愛國”、“捐款”;不能是“主+謂”,如“他踢、他唱、他獲、我殺、我愛、我捐”。
(PPT第2頁呈現,時間4分鐘)
我研究歷史 我使用電腦 我表演節目
研究者 使用者 表演者
他挑戰極限 他翻譯文章 他經營公司
挑戰者 翻譯者 經營者
構詞規則:
雙音節動詞+者:研究者
教師講解如下:
雙音節動詞,如“研究”,后面常常直接加“者”,構成“研究者”。此時,“謂”的后面無需再加“賓”。“研究歷史者”雖然是正確的,但較少使用。如果想要補充“賓”,如“歷史”,最好先構成“VP+者”,如“研究者”,再把“賓”加在“VP+者”的前面,如“歷史研究者”。
(2)“發現組”的教學處理
“發現組”重在啟發學生主動發現“VP+者”的構詞規律。教師不直接教授構詞規律,而僅僅是向學生呈現相關詞組及由其變化而來的派生詞。呈現的內容同樣包括:“者”對謂賓的提取、“者”與雙音節的組配規律。為減少干擾因素,呈現只列出正確形式或最常用的構詞形式,不強調錯誤的構詞形式和少用的構詞形式[1]。在教學處理的過程中,教師保持沉默;若學生舉手提問,教師鼓勵學生“自己思考”,不回答任何關于“VP+者”構詞規律的問題。該組教學處理流程具體如下:
(PPT第1頁呈現,時間4分鐘)
他踢球 他唱歌 他獲獎 我殺人 我愛國 我捐款
踢球者 唱歌者 獲獎者 殺人者 愛國者 捐款者
(PPT第2頁呈現,時間4分鐘)
我研究歷史 我使用電腦 我表演節目
研究者 使用者 表演者
歷史研究者 電腦使用者 節目表演者
他挑戰極限 他翻譯文章 他經營公司
挑戰者 翻譯者 經營者
極限挑戰者 文章翻譯者 公司經營者
(3)“背誦組”的教學處理
“背誦組”不接受任何構詞法教學處理,僅僅被給予相同的自由學習時間。視覺呈現上,僅呈現“VP者”的正確構詞形式和常用構詞形式,不呈現錯誤構詞形式和少用構詞形式,不提示“者”是如何提取賓語的。教師操作時,不做任何講解,不回答任何關于“VP+者”構詞規律的提問,不干涉學生的學習方式。“背誦組”與“發現組”的區別在于,“發現組”擁有“VP者”詞匯的外部線索(主謂賓短語),從而便于發現構詞規律,而“背誦組”則只觀察相關派生語,缺少相應線索。當然,這并不能保證“背誦組”不會去“發現”規律,但這種“發現”較之于“發現組”要困難很多。經教師觀察,此時,有的學生抄寫,有的學生朗讀,有的學生默看。該組的具體處理流程如下:
(PPT第1頁呈現,時間4分鐘)
踢球者 唱歌者 獲獎者 殺人者 愛國者 捐款者
(PPT第2頁呈現,時間4分鐘)
研究者 使用者 表演者
歷史研究者 電腦使用者 節目表演者
挑戰者 翻譯者 經營者
極限挑戰者 文章翻譯者 公司經營者
(4)“對照組”的教學處理
“對照組”不接受任何的教學處理,由學生自然習得。
(5)小結
“接受組、發現組、背誦組”被試在“VP+者”上接受的教學處理時間相同,均為8分鐘。“對照組”未接受任何教學處理。為了將前三組與“對照組”區分開來,我們將前三組統稱為“有處理組”;將“對照組”稱為“無處理組”。
“接受組、發現組”被試接受了詞法規則的處理,“背誦組”未接受詞法規則的處理。為了將這三組進一步區分開來,我們將前兩組統稱為“有詞法規則處理組”;將“背誦組”稱為“無詞法規則處理組”。
四組的關系概括如下:

圖二 四組被試教學處理的情況
3.即時測試
為了解三個有處理組的學習情況,在教學處理環節結束后,我們立即進行了測試。測試方法同“前測”:使用紙筆測試,讓學習者使用“X者”構詞。為了隱藏實驗目的,測試內容包含教學處理中出現過的“X者”以及另外四個無關的生詞。對照組也在同一時間(即第2周)接受了相同的測試。在測試完成后,教師剔除非“VP+者”。
4.延時測試
為考察不同教學處理對被試長時記憶的作用,我們在第14周,也就是在教學處理完成的三個月后,對這四組被試進行了延時測試。測試方法亦同“前測”:使用紙筆測試,讓學習者使用“X者”構詞。同樣,為了隱藏實驗目的,“延時測試”中包含“X者”的產詞測試和四個無關生詞的測試。在測試完成后,教師剔除非“VP+者”。
四、結果與分析
我們統計了“VP+者”的正確使用頻率,并使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四組前測、即時測試、延時測試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如表1和圖三所示:

表1 四組前測、即時測試、延時測試正確頻次比較(單位:個/人)

圖三 四組前測、即時測試、延時測試正確頻次比較(單位:個/人)
(一)即時測試與前測的差異
即時測試是在教學處理完成后立刻進行的,因此,該成績反映的是教學處理的即時效果。我們將前測的正確使用頻次與即時測試的正確使用頻次進行了對比,發現了以下特點:
(1)即時測試條件下,不同的教學處理均產生了促進作用。
將即時測試成績與前測成績對比發現,“有處理組”的正確使用頻次顯著增加:“接受組”從3.42增至 10.33;“發現組”從 3.33增至 10.25;“背誦組”從 3.42增至 10.17。經方差分析,P值均小于0.05,表明前后兩次測試成績差異顯著。只有“未處理組”(即“對照組”)的前后兩次測試無顯著差異,P值大于0.05。這說明,教學處理方式盡管不同,但都對“VP+者”的即時學習起到了促進作用。
(2)即時測試條件下,不同教學處理的促進作用沒有顯著差異。
我們將“有處理組”的即時測試成績進行了方差分析,發現“接受組”、“發現組”和“背誦組”之間無顯著差異,P值大于0.05。正確使用頻率上,接受組為 10.33,發現組為10.25,背誦組為 10.17,單從數值也可看出三組非常一致。
再結合特點(1),我們可以概括出:不同的教學處理,即“講解規則”、“啟發規則”和“死記硬背”三種教學方式都能對“VP+者”的即時學習產生影響,并無優劣之分。
(二)延時測試與前測、即時測試的差異
延時測試是在教學處理完成的三個月后進行的,反映的是延時條件下的教學效果。對比延時測試成績的組間差異,發現,在延時條件下:
(1)“接受組”的持續效果最優。
三個“有處理組”中,“接受組”的正確頻次最高,為11.08,顯著高于其余三組,P值小于0.05。
(2)“發現組”的持續效果次優。
三個“有處理組”中,“發現組”的延時測試成績次之,正確使用頻次為7.33。與其余三組相比,兩兩組間差異顯著,P值均小于0.05。
(3)“背誦組”或無持續效果。
延時測試的正確頻次,“背誦組”4.25,“對照組”4.33。兩組組間無顯著差異,P值大于 0.05。
為了解不同教學處理的延時效果是持續增加還是有所下滑,我們又考察了縱向發展,將“有處理組”各自內部的前測、即時測試、延時測試三個成績進行對比。結果發現:
縱向發展上,三個“有處理組”中,僅有“接受組”在延時條件下的習得效果保持持續增加;“發現組”和“背誦組”的延時效果均減弱。這體現在只有“接受組”的正確頻率持續上升,從即時的10.33上升到延時的11.08。而“發現組”從即時的10.25下滑到延時的7.33,但仍高于前測的3.33;“背誦組”從即時的10.17下降到延時的4.25,但仍然高于前測的3.42。統計分析顯示,以上兩兩差異均顯著。
五、討 論
上述實驗清楚地顯示,在即時條件下,有詞法規則處理(接受式、發現式)與無詞法規則處理(背誦式)對二語者學習“VP+者”都有促進作用,且作用相當。但在延時條件下,兩種有規則的處理仍然保留促進作用,但無規則處理的促進作用消失;兩種有規則的處理中,接受式處理顯著優于發現式處理。
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在即時條件下,三個組的教學處理表現出相同的促進作用,但在這個“相同”之下,是否隱含著不同?另外,在延時條件下,三個組的教學處理表現出不同的促進作用,在這個“不同”之下,又隱含著哪些相同?
(一)聯結加工、激活加工與創造性加工
楊治良(2002)、梁寧建(2003)指出詞匯學習中存在“聯結加工”,即學習者的大腦在短時間內反復受到同一個詞的刺激,建立起該詞的形、音、義的直接聯結。Sokmen(1997)指出,刺激次數越多,這種形(或音)義間的聯結就越強。如果在詞匯輸入時,被試更多進行的是“聯結加工”,那么輸入什么詞,被試就建立起這些詞的形、音、義(或其中兩者)之間的聯結,不太可能激活相關的已學詞或創造出相關的未學詞。我們將這一認知過程概括為“輸入→拷貝→產出”,亦即“輸入什么就產出什么”。被試產出的詞匯中,與輸入語料一模一樣的這一部分詞匯,我們稱為“拷貝詞”。
在“聯結加工”的過程中還存在一種“激活加工”。(桂詩春,2002)如果在輸入詞匯時,被試在進行“聯結加工”之時還進行了“激活加工”,那么,被試不僅僅聯結了這些“輸入詞匯”的形、音、義,還激活了與這些“輸入詞匯”相關聯的詞法規則及語義系統。因此在產出活動中,被試不僅會產出與實驗輸入詞完全一樣的“拷貝詞”,還會產出實驗輸入詞之外的詞,亦即被試曾在其它場合見過、聽過或學過的詞。我們將這一認知過程概括為“輸入→拷貝/激活→產出”;并將實驗中沒有輸入的、但被試曾經在其它場合接受過輸入的這些詞稱為“激活詞”。
此外,在“聯結加工”和“激活加工”之外,可能還存在一種創造性活動(Stoffer,1995;Ellis,1985;Balteiro,2011),我們稱之為“創造加工”。即,被試不僅僅聯結了這些“輸入詞匯”的形、音、義,激活了與這些“輸入詞匯”相關的詞法規則及語義系統,還在這個系統范圍內創造出他們從未見過、聽過、學過的“新詞”。我們將這一認知過程概括為“輸入→拷貝/激活/創造→產出”。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新詞”,不是本體上所說的“新詞新語”,而是對學習者而言的,是指學習者從未接觸過的“新詞”。為了避免混淆,我們稱之為“新習得詞”。這些“新習得詞”,可能是我們漢語語料中存在的合法詞,也可能是漢語語料中從未有過的不合法詞。
(二)三種教學處理與三種認知加工的關系
被試產出的“VP+者”中,哪些直接來自于實驗的輸入(拷貝詞),哪些來自于實驗之外的輸入(非拷貝詞)?實驗之外輸入的“VP+者”中,哪些是被試曾經在其它語境中輸入過的,即他們曾經見過、聽過或學過的(激活詞)?哪些是被試從未接觸過的,即在實驗處理中才新出現的(新習得詞)?我們采用“先比對、再事后訪談”的方法,來區分出這三類詞。比如,被試A的即時測試答卷如下:
使用者、表演者、管理者、有意者、打球者、跑步者
具體操作步驟為:①比對輸入語料,將“使用者、表演者”劃分為“拷貝詞”。② 比對被試A的前測答卷,“管理者”已在前測中出現,故定義為“激活詞”。③將剩下的三個詞返還給被試本人,讓被試逐一判斷:“哪些是你曾經見過、聽過或學過的?哪些是今天測試中新出現的?”被試A將“有意者”判斷為“見過、聽過或學過的詞”,將“打球者、跑步者”判斷為“測試中新出現的詞”,故我們將“有意者”歸入“激活詞”,將“打球者、跑步者”歸入“新習得詞”。經統計,三類詞的比例如下:

表2 拷貝詞、激活詞、新習得詞的比例(%)
對比表1和表2,我們不難發現:
(1)在即時測試條件下,盡管三種教學處理對產詞的促進效果相當,但所產詞匯的來源不同:背誦組,基本全是拷貝詞(97%),僅有少量激活詞(3%),沒有新習得詞。與背誦組相比,發現組拷貝詞的比例降低,為81%;激活詞和新習得詞的比例增加,分別為13%和6%。與發現組相比,接受組拷貝詞的比例進一步降低,僅73%;而激活詞和新習得詞的比例進一步增高,分別為14%和13%。很顯然,詞法規則的清晰程度與產詞活動的創造性程度呈正相關:規則越清晰,產詞的創造性活動越多,復制性活動越少。
再與三種認知活動結合起來,我們發現,機械背誦主要促進的是聯結加工,少量促進激活加工,不促進創造性加工。而構詞規則不但促進聯結加工,也促進激活加工和創造性加工。
(2)在延時測試條件下,盡管三種教學處理對詞匯產出的促進效果不同,但上述正相關性依然不變;同時保持不變的還有,機械背誦對聯結加工的促進作用、構詞規則對激活加工和創造性加工的促進作用。
(3)無論是在即時還是延時條件下,與激活詞和新習得詞相比,拷貝詞的比例始終最高。可見,無論是哪種教學處理方式,聯結加工都是最主要的認知加工方式。
(三)深層加工與詞匯習得
由上分析可見,背誦式的學習方式雖然有助于二語者在短時間內聯結形、音、義之間的關系,記憶和產出大量詞匯,但這種聯結的穩固性很弱,難以抵抗記憶的消退。這是因為背誦方式帶有強制性和機械性,若不及時復習或強化,這種聯結強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動減弱甚至為零(楊治良,2002;王玉響、劉婭莉,2013),這一點與張金橋(2008)的實驗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與機械背誦相比,詞法規則建立在理解并創造性使用的基礎上。Craik&Lockhart(1972)、Craik&Tulving(1975)就曾指出過,對詞匯信息進行深層加工才是詞匯學習的有效手段。因為深層加工能加強形、音、義之間聯結的穩固性,有效地抵抗記憶的消退。Stoffer(1995)、Schmitt(2002)也指出,創造性活動是詞匯學習的重要策略。在派生詞的教學中,通過強調詞根詞綴派生關系引導學習者對詞匯進行深層加工,不僅能夠有效促進新詞的學習,又能有效地促進舊詞的鞏固(Oxford,1990);雖然其他策略也會或多或少地具有這樣的“雙重功效”,但這種詞根詞綴的學習方法的功效最為顯著。(Schmitt,2002)講解法正是通過講解構詞規則,引導學習者發現派生詞的構詞規則,實現對詞匯的深層加工,從而促進詞匯習得。
六、結 論
詞匯學習中存在“聯結加工”、“激活加工”和“創造加工”三種認知加工方式。聯結加工因未對所學詞匯進行深層加工,常常難以抵抗記憶消退的影響;而激活加工和創造加工,尤其是后者,是建立在對詞匯進行深層加工的基礎上,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記憶消退的影響,促進長時記憶。不同的教學方式對詞匯的三種加工方式的影響是不同的。教師清晰講解或者讓學生發現構詞規則都可以幫助學生對所學詞匯進行深層加工,因而大大促進了創造加工和激活加工,保證了學習效果,而講解法因其更加清晰而能夠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背誦法因未對詞匯進行深層加工,主要促進了聯結加工,少量促進激活加工,不促進創造加工,因而無法抵抗記憶的消退,雖能實現即時教學效果,但無長期功效。
七、教學啟示
第一,課堂詞匯學習很有必要。我們的實驗表明,無論是機械背誦式教學還是詞法規則式教學,只要在課堂上留出很少的一部分時間用于詞匯教學,就能明顯促進學習者的詞匯產出。
第二,大量輸入很重要。(Krashen,1982)實驗表明,無論是哪種教學處理,被試產出的詞匯中,絕大部分來自于實驗的輸入。這說明,輸入是輸出的前提。
第三,“X者”中,X的入詞規律(X的詞性、音節)不可或缺。清晰的詞法規則不僅有助于即時條件下的詞匯產出,更重要的是,還有助于抵抗時間推移對記憶的消退影響。因此,傳統的字本位教學,也就是以語素為本位的教學,是不應該被忽視的;詞根詞綴組合成詞的規則因其強大的構詞能力更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包括X的詞性和音節。
第四,增顯視覺輸入是促進詞匯學習的有效手段,如用“×、√”等符號強調構詞的規律。前人已有研究表明,使用增顯視覺輸入并和其他教學處理相結合能夠更有效促進詞匯的學習效果。(Doughty,1991;Williams,1999;Izumi,2002;Rott,2007;周榕、呂麗珊,2010;洪煒,2011)
注釋:
[1]在設計教學實驗時,本研究主要考慮減少“發現組”自學時的干擾因素,而未考慮負面語料對習得結果的影響,這也是后續研究準備改進之處。謝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
馮敏萱、楊翠蘭、陳小荷:《帶后綴“者”的派生詞識別》,《語言文字應用》,2006年第2期。
桂詩春:《新編心理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
洪 煒:《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近義詞習得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靳洪剛、章 吟:《“選擇性注意”與“差異效應”在漢語“得”字方式補語習得中的作用》,《世界漢語教學》,2009年第4期。
梁寧建:《認知心理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陸志韋等:《漢語的構詞法》,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
呂文華:《建立語素教學的構想》,《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茂春:《現代漢語“VP+者”成立的幾個條件》,《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王玉響、劉婭莉:《初級漢語綜合課教材詞匯的頻率與復現》,《華文教學與研究》,2013年第4期。
楊治良:《記憶心理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張 斌:《現代漢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張金橋:《漢語詞匯直接學習與間接學習效果比較——以詞表背誦法和文本閱讀法為例》,《漢語學習》,2008年第3期。
周 榕、呂麗珊:《輸入增顯與任務投入量對英語詞匯搭配習得影響的實證研究》,《現代外語》,2010年第1期。
Balteiro,I.Awareness of L1 and L2Word-formation Mechanis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Autonomous L2 Learner.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university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Didactics,2011(1):25-34.
Craik,F.and R.Lockhart.Levels of processing:a framework formemory research.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2(11):671-684.
Craik,F.I.M.and E.Tulving.Depth of processing and the retention of words in episodicmemor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75(104):268-284.
Doughty,C.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doesmake a differenc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1(13):431-469.
Ellis,Rod.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5.
Izumi,S.Output,inputenhancement,and the noticing hypothesis: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ESL relativization[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2(24):541-577.
Krashen,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xford:Pergamon,1982.
Oxford,R.L.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Boston:Newbury House,1990.
Rott,S.The effectof frequency of inputenhancements on word learning and text comprehension.Language Learning,2007(57):165-199.
Schmitt,Norbert.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In Vocabulary:description,acquisition and pedagogy,edited by Norbert Schmitt&Michael McCarthy.2002.
Shqerra,Nereida.The Role of Derivation and Compounding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MCSER Publishing,2014(4-2):117-121.
Sokmen.A.J.Current trends in teaching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In N.Schmitt&MceCarthy,eds.Vocabulary:Description,Acquisition and Pedag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Stoffer,I.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choice of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as related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University of Alabama: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1995.
Williams,J.Memory,attention,and inductive learning.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9(21):1-48.
Pedagog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Derivatives——Based 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VP zhe(者)”
LIU Yali&WANG Yuxi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 China;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CA 95616 USA)
Instruction on morphemes and word formation rul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vocabulary acquisition,as different pedagogicalmodels promote different lexical cognitive processing patterns(connection processing,activation processing or creation processing),and further influence the final acquisition status.This pedagogical research on the derivative“VP+zhe(者)”finds that:Both teachers’instruction and learners’self-finding of the formation rules can promote learners’deeper processing on vocabulary,which promotes activation processing and creation processing,and further promotes long-term memory.The clearer the instruction is,themore effective the acquisition is.Recitation,on the other hand,promotes connection processing,which only has instant teaching effect.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derivatives and provides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VP+zhe(者);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connection processing;activation processing;creation processing
H193.4
A
2221-9056(2017)09-1200-10
10.14095/j.cnki.oce.2017.09.004
2016-10-04
劉婭莉,四川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講師,語言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二語習得。Email:liuyali86@sina.com王玉響,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語言學系助理講師,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二語習得。Email:wangyuxiang@gmail.com感謝《海外華文教育》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文中不妥之處概由本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