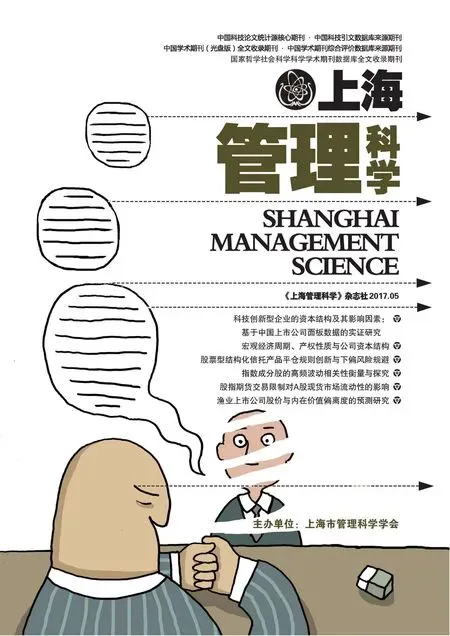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研究
——基于危機關聯度的視角
楊 芳, 余明陽(上海交通大學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研究
——基于危機關聯度的視角
楊 芳, 余明陽
(上海交通大學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企業打造一個優秀的品牌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時間,但僅僅是一場危機就足以將百年品牌毀于一旦。在此背景下,基于危機關聯度的視角研究了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于消費者感知品牌可靠性及品牌態度的影響。通過兩組實驗發現,對于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作用,危機關聯度具有調節作用。對于高關聯度品牌危機,企業自我揭露比外界揭露時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更好。另外,消費者的感知品牌可靠性在這一過程中起中介作用。該研究結論不僅有助于企業內部健全信息溝通機制,還可以為證監會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參考。
品牌危機揭露;危機關聯度;感知品牌可靠性;品牌態度
1 緒論
“十年植松柏,百年樹品牌”,企業打造一個優秀的品牌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時間,但僅僅是一場危機就足以將企業多年苦心經營的品牌毀于一旦。2016年,百度“魏則西事件”將百度競價推向風口浪尖,百度股價連跌8天;三星手機“NOTE 7”驚現“爆炸門”一事使得消費者信任和品牌信譽嚴重受損……此類品牌危機事件不勝枚舉。在社交媒體風靡時代,信息以光速進行著病毒式傳播,危機對品牌的破壞力更加巨大,而危機處理也變得愈加復雜,如何應對品牌危機已逐漸成為每個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必修課。
品牌危機應對策略已吸引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研究,如Dutta[1]基于危機來源屬性將品牌危機分為績效相關型和價值相關型來研究危機應對策略;Coombs[2]將企業危機應對策略分為否認、辯解和道歉三種策略;方正[3]基于品牌資產研究了產品傷害危機及應對策略對營銷變量的影響。
Sang[4]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在危機事件被媒體報道的情況下,企業如何選擇危機溝通策略,很少有學者研究企業主動應對危機策略的有效性。少量前人文獻研究表明,企業主動揭露危機且不使用說服性信息時,會產生積極的品牌態度和購買意愿[5-8]。
綜上,本文基于危機關聯度的視角研究了不同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作用。結果表明:對于高關聯度品牌危機,企業自我揭露比外界揭露時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更好;對于低關聯度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無顯著影響;消費者的感知品牌可靠性在這一過程中起中介作用。最后,本文也探討了該研究的理論貢獻和管理啟示,并對未來的研究給予方向及展望。
2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2.1品牌危機揭露方式:自我揭露VS.外界揭露
McGuire[8]于1961年基于預防接種理論 ( Inoculation Theory ) 提出了一種自我揭露的溝通策略,該理論指出猶如個體可以通過接種疫苗來增強免疫系統以抵御疾病,當組織采取主動的危機揭露策略時,可能會使信息的接受者產生“免疫”,當其真正面臨反面信息大量侵襲時,接受者便會主動防御負面信息的攻擊。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將危機自我揭露方式定義為企業通過召開新聞發布會、借助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企業自主運營的平臺主動向公眾揭露危機事件的行為,相應的外界揭露定義為由第三方媒體或利益相關者揭露危機而非企業主動揭露的方式。
企業自我揭露危機不僅可以凸顯企業勇于承擔責任的態度,而且可以有效防止媒體利用危機事件大肆宣揚甚至扭曲事件使企業受損[9-10]。其次,主動揭露危機可使新聞失去新鮮感,減少媒體報道的興趣和可能性。當企業主動揭露危機且比較可信時,媒體或其他相關利益相關者很難從相反或者不同的角度對危機事件予以報道[10-12]。
綜上,得出如下假設:
假設1:企業自我揭露危機比外界揭露時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更好。
2.2品牌危機關聯度:高VS.低
Coombs考慮危機的責任歸因,基于歸因控制點和故意屬性,將品牌危機分類為受害性危機、意外性危機和有意性危機三類;Dutta基于危機來源的不同屬性,將品牌危機分為績效相關和價值相關兩類;相應地,Votola & Unnava[13]把品牌危機分為與能力相關及與道德相關的事件;鄭彬[14]基于品牌危機是否由企業自身原因引起,將品牌危機分為主動性危機和被動性危機;Dawar[15]通過實證研究按照危機是否危及品牌資產的核心要素,將品牌危機分為核心要素的品牌危機與非核心要素的品牌危機。本研究借鑒Dawar和單從文[16]的分類方式,將品牌危機分為高關聯度品牌危機(與企業核心業務關聯度較高的品牌危機)和低關聯度品牌危機(與企業核心業務關聯度較低或無關的品牌危機)。
高關聯度品牌危機一般由企業的主營業務引起,與產品或服務質量存在缺陷相關,高關聯度品牌危機會降低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感知[17];Dutta & Pullig認為低關聯度品牌危機是由企業的非主營業務引起,一般與社會或者道德問題相關而非產品質量問題[18]。
Mittal[19]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當消費者對產品評價時,更加注重核心產品質量功能屬性而不是非核心的產品屬性。他通過實驗法證明,產品功能質量等高關聯度品牌危機與社會形象、價值觀等低關聯度品牌危機相比,高關聯度危機對消費者品牌感知、滿意度及購買決策等產生的影響更大。
綜上,得出如下假設:
假設2:對于高關聯度品牌危機,企業自我揭露比外界揭露時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更好,而對于低關聯度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無顯著影響。
2.3消費者感知品牌可靠性
不同的危機揭露方式對應著企業不同的危機溝通策略,德魯克在《管理》中指出,溝通是一種感知、溝通是一種期望。文榮認為感知的主體是溝通的承受者,是信息的受眾,感知的前提是基于理解[21]。
Reeder[20]通過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發現,人們在評價處理與能力相關的正向或負向信息,與處理非能力相關的信息相比有明顯的差異。高關聯度品牌危機主要與企業的產品質量及能力等相關,而低關聯度品牌危機主要與企業的社會形象、道德等相聯系,消費者在面對這兩種不同情形的危機時,可能會對品牌可靠性做出不同的評價判斷。而感知品牌可靠性可進一步影響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
綜上,得出如下假設:
假設3:消費者對品牌的感知可靠性在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的影響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框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研究模型
3 實證研究
3.1實驗1
實驗1操控了品牌危機揭露方式(自我揭露 VS. 外界揭露)和品牌危機關聯度(高 VS. 低)來驗證假設1和假設2。另外,本文參考了Eagly[22]的量表來測量消費者在這一過程中的感知品牌可靠性以驗證假設3。
3.1.1被試與實驗設計 被試是178名大學生,年齡分布在18~25歲,其中男士83名,女士95名。實驗1的自變量是操控的品牌危機揭露方式(自我揭露 VS. 外界揭露)這一組間變量,兩組每組各89名被試,調節變量是操控的品牌危機關聯度的高和低。
3.1.2實驗刺激物 考慮到被試者對材料的熟悉度及品牌的光環效應等因素,本研究選用虛擬的某酸奶品牌作為實驗1的刺激物。品牌危機材料參考Dutta并結合相關權威媒體報道文章改編而成。在“高關聯度品牌危機”組,被試閱讀的材料為“A品牌酸奶用奶粉勾兌發酵生產,公司為提高酸奶黏稠度添加了工業明膠等化學原料”;在“低關聯度品牌危機”組,被試閱讀的材料為“企業否認曾承諾將長跑募集的報名費用捐予貧困小學”。在“自我揭露”組,上述危機均通過企業官網主動揭露;在“外界揭露”組,上述危機均由第三方權威媒體報道揭露。除上述所述內容存在差異外,其他材料說明及長度均基本保持一致。
3.1.3實驗過程 首先,將被試隨機分成4組;其次,讓其閱讀A品牌酸奶的產品簡介及相關4段危機材料;然后,被試需要依次完成危機揭露方式和關聯度的操控選項、感知品牌可靠性量表以及品牌態度量表。問卷中的相關測項均采用Likert 5點量表測量;最后,要求被試填寫人口統計方面的信息。
3.1.4實驗量表 由于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和關聯度均為操控選項,故實驗1要測量的主要變量是消費者的感知品牌可靠性和品牌態度。
危機揭露方式操控檢驗的量表問題為“您閱讀的這條信息來源于企業自我揭露還是外界揭露?”,1表示“自我揭露”,2表示“外界揭露”;危機關聯度操控檢驗的量表問題為“您覺得此次事件與企業核心業務相關還是非核心業務相關?”,1表示“核心業務”,2表示“非核心業務”。
本研究參考 Eagly成熟的溝通可靠性量表,將感知品牌可靠性量表的4個題項設置為“A品牌在此事件中的表現說明了真誠/從這件事看,A是一個誠實的品牌/我認為A品牌很可靠/購買A品牌的產品我很放心”(M=3.09,SD=0.76 ),(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對于品牌態度的量表,本文參考Lafferty (2007),Kim & Han (2005),Mitchell & Olsen (1999),Dodds & Grewal (1991),等經典量表,品牌認知量表的3個題項分別為“我對A品牌的印象很好/我認為A品牌的產品物有所值/我認為A品牌的產品令人滿意” (M=3.00,SD=0.48 );品牌情感量表的3個題項分別為“我很喜歡A品牌的產品/我很信賴A品牌的產品/與同類產品相比,我對A品牌的產品有更大的興趣”(M=2.96,SD=0.50);購買意愿量表的2個題項分別為“如有需要,我會考慮購買該A品牌產品/在同類產品中,我選擇A品牌產品的可能性大” (M=3.00,SD=0.56),(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3.1.5實驗結果 操控檢驗。在正式實驗前邀請了60名研究生(女生32名,男生28名)分成4組,每組15人進行前測。對于危機揭露方式,自我揭露組93.3%的人回答正確,外界揭露組正確率為100%;對于危機關聯度,高關聯度組正確率為86.7%,低關聯度組正確率為93.3%,前測數據表明實驗操控成功。
正式實驗一共收集了178份問卷,其中“危機揭露方式”操控失敗問卷共計7份,96.1%操控成功;“危機關聯度”操控失敗問卷共計12份,93.3%操控成功。剔除上述19份問卷,實際有效問卷合計159份,實驗操控成功。
主效應分析。本研究采用單因素ANOVA來檢驗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主效用。將危機揭露方式(1=自我揭露,2=外界揭露)作為自變量,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作為因變量,實驗數據表明,相比于外界揭露組的被試(M=2.75,SD=0.353),處于自我揭露組的被試 (M=3.22,SD=0.350) 對品牌態度具有更加顯著的提升作用 (F(1, 157) =72.39,P<0.05 ),故假設1得證。
調節作用。本研究使用一般線型模型的單變量(Univariate)來檢驗危機揭露方式和危機關聯度對品牌態度的效用。將危機揭露方式(1=自我揭露,2=外界揭露)作為自變量,危機關聯度(1=高關聯度,2=低關聯度)作為調節變量,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作為因變量。分析結果 (F(1,155) =74.164, P<0.05) 顯示,危機揭露方式和關聯度交互作用顯著,即調節作用顯著。各組結果如圖2所示,可以看出:對于“高關聯度”組,自我揭露 (M自=3.39) 相比于外界揭露 (M外=2.55)對品牌態度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而對于“低關聯度”組,揭露方式(M自=3.05,M外=2.96) 對品牌態度影響差異不大,故假設2得證。

圖2 實驗1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影響的調節效應分析
中介作用。本文根據Zhao et al. ( 2010 ) 提出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同時參考Preacher & Hayes ( 2004 ) 和Hayes ( 2013 ) 提出的Bootstrap 算法,選擇使用PROCESS Model 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將危機揭露方式作為自變量,關聯度作為調節變量,感知品牌可靠性作為中介變量,品牌態度作為因變量,如圖3所示。在SPSS分析中,選用5 000作為樣本量,在95%的置信區間下,中介效應檢驗的結果 (LLCI=-0.463 8,ULCI=-0.180 8 ) 中不包含0。這一分析結果顯示,感知品牌可靠性中介效應顯著,且中介效應大小為-0.319 2。此外,在控制了中介變量感知品牌可靠性之后,自變量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不顯著,區間 (LLCI=-0.334 2,ULCI=0.023 9) 包含0,說明感知品牌可靠性中介效應顯著且是完全中介作用,假設3得證。

圖3 實驗1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影響的中介效應分析
3.2實驗2
實驗1選取的是消費品品牌A酸奶,為了進一步驗證實驗1的結論,增強其可靠性,實驗2選取了虛擬的制造業品牌。與實驗1類似,本研究操控了品牌危機揭露方式(自我揭露 VS. 外界揭露)和關聯度(高 VS. 低)來驗證假設1和2,通過測量感知品牌可靠性來驗證假設3。
3.2.1被試與實驗設計 被試是228名本科生及研究生,年齡分布在18~28歲,其中男士110名,女士118名。實驗2選用了2(品牌危機揭露方式:自我揭露 VS. 外界揭露)×2(危機關聯度:高 VS. 低)的組間設計。
3.2.2實驗刺激物 選用虛擬的手機品牌B作為實驗2的刺激物,將“高關聯度品牌危機”描述為“B品牌手機頻繁出現‘黑屏、死機、機身發燙等’問題”;相應的“低關聯度品牌危機”為“B公司總經理在評選活動中賄賂選票”。“自我揭露”組為企業主動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此事件;“外界揭露”組為該事件由第三方媒體報道揭露。除上述差異外,其他內容均保持一致。
3.2.3實驗過程及實驗量表 實驗2的過程與實驗1相似,量表題項除了刺激物更換為B品牌手機外,其他均與實驗1相同,在此不予贅述。
3.2.4實驗結果 操控檢驗。實驗2一共收集了228份問卷,其中“危機揭露方式”回答正確率為95.2%;“危機關聯度”正確率為93.4%。剔除上述操控失敗問卷24份(有兩份問卷兩項操控均失敗),實際有效問卷合計204份,操控成功率為89.5%。
主效應分析。與實驗1類似,本研究采用單因素ANOVA來檢驗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主效用。實驗數據顯示,自我揭露組的被試 (M=3.11,SD=0.685) 相比于外界揭露組(M=2.57,SD=0.616 ) , 其對品牌態度具有更加顯著的提升作用 (F(1, 202) =34.467,P<0.05),故假設1得證。
調節作用。仍采用實驗1的一般線型模型的單變量(Univariate)來檢驗危機揭露方式和危機關聯度對品牌態度的效用。分析結果(F(1, 200) =15.912, P< 0.05 ) ,表明調節作用顯著。各組結果如圖4所示,數據顯示:對于“高關聯度”組,自我揭露 (M自=3.25) 比外界揭露 (M外=2.36) 對品牌態度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而對于“低關聯度”組,揭露方式 (M自=2.96,M外=2.78) 對品牌態度影響差異不大,故假設2得證。

圖4 實驗2 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影響的調節效應分析
中介作用。仍使用PROCESS Model 4進行中介分析,如圖5所示。在樣本量為5 000,95%的置信區間下,0沒有包含在中介效應檢驗的結果 (LLCI=-0.6246,ULCI=-0.2509)中。數據顯示,感知品牌可靠性中介效應顯著,且中介效應值為-0.410 4。當控制了中介變量之后,區間(LLCI=-0.324 1,ULCI=0.073 4)包含0,即自變量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不顯著。綜上,感知品牌可靠性中介效應顯著且起完全中介作用,故假設3得證。

圖5 實驗2 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影響的中介效應分析
4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兩個實驗,研究了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實驗數據表明,其一,企業自我揭露比外界揭露時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更好;其二,對于高關聯度品牌危機,企業自我揭露比外界揭露時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更好,而對于低關聯度品牌危機,揭露方式對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品牌認知、品牌情感、購買意愿)無顯著影響。最后,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證明消費者的感知品牌可靠性在這一過程起完全中介作用。
該研究結論有豐富的理論意義。一方面本文引入了危機關聯度這一重要的調節變量,充實了品牌危機應對策略的研究。另一方面提出了“溝通即感知”的理念,加入感知品牌可靠性這一重要的中介變量,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角。
此外,這些研究結論有非常重要的管理啟示。首先,企業應建立健全危機應對機制,當發生高關聯度品牌危機時,應抓住時機主動向公眾公開道歉,并采取一系列補救措施以減少對品牌可靠性、品牌信任、購買意愿等的影響。其次,企業不僅要完善內部信息溝通體系,還要協調好和外界媒體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以便在品牌危機發生時可以自主選擇應對方式。最后,本研究對于中國證監會進一步完善修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機制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可以推進上市公司積極披露風險信息以避免目前存在的信息隱瞞等問題,推動資本市場和諧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對引導上市公司主動應對危機、維護良好的投資者和消費者關系具有借鑒意義。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處,如文中考慮到光環效應故使用了虛擬品牌作為實驗刺激物,未來可以使用真實的品牌以提高實驗效果的可信性。另外,文中只考慮了感知品牌可靠性這一中介變量,后續的研究可以探討其他中介變量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
[ 1 ] DUTTA S, PULLIG C. Effectiveness of corporate responses to brand crises: the role of crisis type and response strateg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12): 1281-1287.
[ 2 ] COOMBS W T, HOLLADAY S J. Communication and attributions in a crisis: an experimental study[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6, 8(4): 279-295.
[ 3 ] 方正,楊洋,江明華. 可辯解型產品傷害危機應對策略對品牌資產的影響研究:調節變量和中介變量的作用[J]. 南開管理評論, 2011, 14(4): 69-79.
[ 4 ] SANG Y L. Weathering the crisis: effects of stealing thunder in crisis communication[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6, 42(2): 336-344.
[ 5 ] CAMPBELL M. When attention-getting advertising tactics elicit consumer inference of manipulative intent: the importance of balancing benefits and investments[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995, 4(3): 225-254.
[ 6 ] MCGUIRE W.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ve and reputational defenses in immunizing and restoring beliefs against persuasion[J]. Sociometry, 1961, 24(2): 184-197.
[ 7 ] MCGUIRE W. Persistence of the resistance to persuasion induced by various types of prior belief defenses[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2, 64(4): 241-248.
[ 8 ] MCGUIRE W, PAPAGEORGIS D. The generality of immunity to persuasion produced by pre-exposure to weakened counter arguments[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1, 62(3): 475-481.
[ 9 ] ARPAN L M, POMPPER D. Stormy weather: testing stealing thunder as a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flow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journalists[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3, 29(3): 291-308.
[10] FENNIS B, STROEBE W. Softening the blow: company self-disclosure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lessens damaging effects on consumer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20(1): 109-120.
[11] ARPAN L, ROSKOS-EWOLDSEN D. Stealing thunder: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proactive disclosure of crisis information[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5, 31(3): 425-433.
[12] CLAEYS A, CAUBERGHE V. Crisis response and crisis timing strategie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2, 38(1): 83-88.
[13] VOTOLA N,UNNAVA R.Spillover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on brand alliances[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6, 16(2): 196-202.
[14] 鄭彬,衛海英. 品牌危機的內涵、分類及應對策略研究[J]. 現代管理科學, 2011(2): 91-93.
[15] DAWAR N, JING L.Brand crises: the roles of brand familiarity and crisis relevance in determin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4): 509-516.
[16] 單從文,余明陽. 基于危機關聯度的品牌危機應對策略研究[J]. 軟科學, 2016, 30(8): 97-100.
[17] DAWAR N, PILLUTLA M M. Impact of product-harm crises on brand equ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nsumer expecta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0, 37(2): 215-226.
[18] DUTTA S, PULLIG C. Effectiveness of corporate responses to brand crises: the role of crisis type and response strateg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12): 1281-1287.
[19] MITTAL V, ROSS J, BALDASARE W T, et al.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attribute-level performance on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9, 63(2): 88-102.
[20] REEDER G D, BREWER M B. A schematic model of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in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9, 86(1): 61-79.
[21] 文榮. 溝通是一種感知[J]. 商, 2014 (33): 1-1.
[22] EAGLY A H, WOOD W, CHAIKEN S. Causal inferences about communicators and their effect on opinion chang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36(4): 424-433.
TheImpactofBrandCrisisDisclosureonConsumerBrandAttitude—BasedonCrisis-relevancyPerspective
YANGFang,YUMingyang
(Antai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It takes lots of money and time for enterprises to build a honourable brand, while just a crisis is enough to destroy a century brand. Given this, we studied the impact of brand crisis disclosure on consumer attitude based on crisis-relevancy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of the 2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as to high-relevancy brand crisis, it was more positive to brand attitude ( brand cognition, brand emotion, purchase intention ) for self-disclosure compared with third-party disclosure. In addition, perceived brand reliability mediated this interactive effect.These results facilitate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sound intern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SRC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listed companies.
brand crisis disclosure; crisis relevancy; perceived brand reliability; brand attitude
F 274
A
2017-06-0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互聯網群體傳播的管控方案與社會引導對策研究(15AZD054)。
楊芳(1992—),女,陜西寶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品牌戰略與消費者行為;E-mail: fancyunique@163.com。
余明陽(1964—),男,浙江寧波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品牌戰略與企業戰略。
1005-9679(2017)05-01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