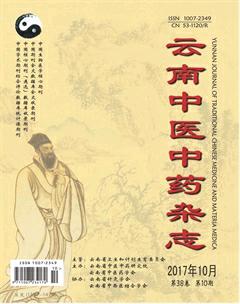向希雄教授兒科醫(yī)案2則
危艷青+向希雄
摘要:明代萬全自古提出小兒“三有余,四不足”,小兒肺脾腎常不足,肺脾不足無以固表則多汗,腎不足則可致遺尿,二癥又皆與心肝有余相關(guān),且就診患兒逐年增多,故二癥之醫(yī)案有記載之義,向希雄教授長期從事兒科醫(yī)學(xué)教研及臨床工作,臨證思路清晰且新穎獨特,辨證準確,用藥靈活,知通經(jīng)典,從醫(yī)30余年來,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jīng)驗,現(xiàn)將其汗證、遺尿醫(yī)案各選1則,與同道共勉。
關(guān)鍵詞:汗證;三有余,四不足;小兒遺尿
中圖分類號:R249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7-2349(2017)10-0102-02
向希雄教授現(xiàn)任湖北中醫(yī)藥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兒科主任,碩士研究生導(dǎo)師,從醫(yī)30余年,善于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兒科各種疾病,尤其擅長小兒呼吸系統(tǒng)、消化系統(tǒng)及泌尿系統(tǒng)的疾病。對小兒反復(fù)咳喘、厭食、腹瀉、汗證、遺尿、腎病綜合征以及紫癜等疾病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方法。筆者有幸追隨向希雄教授學(xué)習(xí),現(xiàn)選取向教授兒科醫(yī)案2則作如下闡述,以饗讀者。
1 病案1
患兒李某,男,5歲10個月。2014年4月16日就診。盜汗2年余。2年來患兒夜間汗出較多,以剛?cè)胨瘯r為主,家長訴患兒剛?cè)胨膬扇齻€小時內(nèi)大汗淋漓,伴磨牙、躁動不安,后半夜出汗量減少,喜俯臥位睡覺,另患兒平素大便2日1行,質(zhì)干,呈羊屎狀,偶予開塞露以助通便,小便可,無發(fā)熱、咳嗽、腹痛等不適,納食尚可。舌稍紅,苔白稍膩,脈滑數(shù)。診斷為汗證。治以益氣止汗通便。處以:太子參15 g,黃芪20 g,白術(shù)10 g,云苓15 g,陳皮10 g,法半夏6 g,薏苡仁15 g,白扁豆10 g,浮小麥15 g,煅龍骨30 g,煅牡蠣30 g,決明子15 g,火麻仁15 g,五味子6 g,柏子仁15 g,水煎劑5劑,日1劑。2014年4月23日復(fù)診,患兒夜間汗出減輕,以前胸、后背為主,磨牙明顯好轉(zhuǎn),大便較前好轉(zhuǎn),日1行,質(zhì)軟,小便可,納食欠佳,晨起偶伴噴嚏,流少量黃涕,余無不適。繼用上方加防風(fēng)6 g,神曲10 g,山楂10 g,連服2周以鞏固療效。
按:盜汗本屬陰虛,然向教授認識到小兒多肺脾常不足,自古明代萬全根據(jù)錢乙的五臟虛實證治,提出小兒“三有余,四不足”之說,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腎常虛;心常有余;肺常不足。”又在朱丹溪理論的影響下,提出“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觀點。脾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小兒生機旺盛,發(fā)育迅速,且臟腑功能不足,脾胃負擔(dān)比成人相對較重,加之乳食不知自節(jié),擇食不辨優(yōu)劣[1],因此小兒脾胃功能易于紊亂,而出現(xiàn)脾胃病,案中患兒大便干結(jié),2日1行,當(dāng)辨病位于脾胃而非大腸也。肺為華蓋,外合皮毛,開竅于鼻[2],小兒肺臟嬌嫩,肌膚不密,加之“脾常不足”,脾虛則不能散精于肺,而肺氣亦弱,衛(wèi)外不顧,故汗出較多。夜間磨牙、躁動不安,責(zé)之于心肝,小兒陰常不足,木火同氣,心肝之火易亢,腎陰之水不足,水不制火,心火炎上的生理狀態(tài),則表現(xiàn)為夜間磨牙、躁動不安。故本案患兒病位主要責(zé)之于肺脾,但與心、肝、大腸相關(guān)。方取六君子湯健脾益氣之意,又取參苓白術(shù)散補脾養(yǎng)肺之要,且以太子參取代原方之黨參,清補之意,滋而不燥,取其生津潤肺之功,并加用黃芪既可助參補氣健脾,又可益衛(wèi)固表而止汗。太子參、黃芪、白術(shù)補肺脾益氣而達到止汗之功,五味子、浮小麥斂汗,半夏、白扁豆、薏苡仁燥濕健脾,以防濕困脾胃而大便粘滯不爽,柏子仁、火麻仁、決明子潤腸通便,煅龍骨、煅牡蠣斂汗平肝安神,諸藥合用共奏益氣斂汗通便兼以安神之功,故此案患兒藥到病除,后加防風(fēng)固表,神曲、山楂健脾胃消食,繼服2周,病愈。
2 病案2
患兒夏某,女,7歲5個月。2015年5月7日就診。遺尿1年余。家長訴經(jīng)常遺尿,每日均遺,夜間難喚醒,白天小便正常,不伴尿痛,納尚可,余無不適。舌紅,苔中部黃膩,脈滑。診斷為遺尿,腎虛兼濕型。治以調(diào)補心腎,固澀止遺。處以:益智仁15 g,烏藥10 g,桑螵蛸10 g,炙麻黃6 g,菟絲子15 g,金櫻子15 g,枸杞子15 g,黃柏10 g,滑石15 g,通草6 g,遠志10 g,石菖蒲15 g,水少濃煎,服藥均應(yīng)在睡前2 h以上,服藥期間,囑患兒白天不宜過度玩耍,以免夜間疲勞貪睡,晚飯后注意控制飲水量,并囑家長臨睡前提醒患兒排尿,入睡后按時喚醒1或2次,從而逐步養(yǎng)成自行排尿的習(xí)慣[3]。服3劑,患兒舌苔轉(zhuǎn)為薄黃,夜間遺尿頻次減少,再服4劑,家長訴夜間喚醒患兒自行小便1次,方可入睡至天明不再遺尿,后來復(fù)診,加用茯神10 g,連服1周后,患兒遺尿病瘥,后隨訪未再復(fù)發(fā)。
按:遺尿是指5歲以上小兒睡中小便自遺,醒后方覺的一種疾病,為小兒常見病,輕重不一,病程不一,部分患兒纏綿難愈,治療困難,也有持續(xù)多年至青春期自愈者[4]。臨床反復(fù)發(fā)作,中醫(yī)治療本病有較好的療效[5]。小兒遺尿癥屬“遺尿范疇”,《素問·宣明五氣論》中已有“膀胱不約為遺尿”的記載。歷代醫(yī)家認為本病發(fā)生為先天稟賦不足,素體虛弱,腎氣不足,下元不固;或因后天失于調(diào)養(yǎng),肺脾氣虛,氣虛及腎,導(dǎo)致腎虛;或因肝主疏泄功能失調(diào)所致,肝主疏泄,可調(diào)暢氣機,通利水道,且足厥陰肝經(jīng)繞陰器,至少腹,若肝經(jīng)熱下注,可使決瀆開合失司從而引起遺尿;或心腎不交,水火不濟,心志不能下達于腎,腎虛不能主水,則膀胱不能固其水液[6]。綜上可見,遺尿一證,不僅與腎和膀胱相關(guān),同時涉及肺、脾、肝、心、三焦、小腸等臟腑[7]。正如《素問·經(jīng)別別論篇》曰“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diào)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jīng)并行。”《素問·靈蘭秘典論篇》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8]向教授認為遺尿一病本虛標實,且以虛證居多,本案患兒病程已久當(dāng)屬本虛,而苔中部黃膩,脈滑乃實證之征象,故本案即為本虛標實之證,治當(dāng)虛實兼顧。方取桑螵蛸散交通心腎之義,縮泉丸溫腎止遺之要,桑螵蛸補腎助陽,固精縮尿;枸杞子滋補肝腎,金櫻子固精縮尿,益智仁溫腎暖脾,固精縮尿[9],烏藥溫振脾腎氣化,使腎氣足,膀胱固,氣化復(fù)常,菟絲子補腎固精,遠志、石菖蒲、茯神開心竅、安心神與上列補腎藥同用,有交通心腎的作用[10];黃柏、滑石、通草清下焦?jié)駸幔焦沧嘟煌ㄐ哪I,固精止遺兼清濕熱之效。另有學(xué)者認為小兒遺尿是因為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控制能力下降所致,因此治療可以刺激神經(jīng)中樞為主導(dǎo)。麻黃所含的麻黃堿有興奮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作用,如大劑量使用能興奮大腦皮質(zhì)層和皮層下中樞,從而加強膀胱三角肌和括約肌的張力,使主動抑制排尿成為可控。此外,麻黃還能延緩睡眠深度,使其神經(jīng)活動處于激勵的狀態(tài),提高大腦對夜尿警覺點的興奮性,這同樣能增加膀胱三角肌和括約肌的張力,最終聯(lián)合作用強制神經(jīng)系統(tǒng)加強控制,避免遺尿的發(fā)生[11]。
3 結(jié)語
汗證、小兒遺尿均屬兒科常見病,且近年來患病率呈增高的趨勢,逐漸受到廣大家長和醫(yī)護人員的重視。向希雄教授認為汗證、小兒遺尿的發(fā)生皆與肺、脾、腎相關(guān),又與心、肝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其中汗證以肺脾為主導(dǎo),小兒遺尿以腎為主導(dǎo),這些也體現(xiàn)了小兒“三有余,四不足”的理論,向教授臨床在“小兒肺脾腎常不足,心肝有余”理論的指導(dǎo)下,根據(jù)每個患兒的具體病情,從補肺健脾益腎兼顧調(diào)心疏肝之法,辨治汗證與小兒遺尿,每獲奇效。
參考文獻:
[1]汪震,霍磊,梁媛《臨證指南醫(yī)案·幼科要略》兒科護理的思想及啟示[J].遼寧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2012,14(3):103-104
[2]孫廣仁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M].2版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07,2:108-109
[3]劉玉清,丁櫻丁櫻教授治療小兒遺尿經(jīng)驗介紹[J].天津中醫(yī)藥,2012,29(5):427-428
[4]翟文生,梁麗,楊濛小兒遺尿辨治八法[J].中國民族民間醫(yī)藥,2014,20(2):20-22
[5]汪受傳中醫(yī)兒科學(xué)[M].上海: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6,8:174-176
[6]崔芬芬,陳玉燕小兒遺尿癥中醫(yī)證治研究概況[J].陜西中醫(yī)學(xué)院學(xué)報,2014,37(3):103-104
[7]朱景善中醫(yī)兒科臨證心法[J].中國農(nóng)村醫(yī)學(xué),1997,25(3):5-7
[8]蘭生榮桑螵蛸散合縮泉丸配合針刺治療小兒遺尿78例[J].中醫(yī)兒科雜志,2012,8(3):46-47
[9]高學(xué)敏中藥學(xué)[M].2版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07,1:450-451
[10]上海中醫(yī)藥大學(xué)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教研組中醫(yī)方劑臨床手冊[M].上海中醫(yī)藥出版社,1973:239-240
[11]鄧潤民,陳志文麻黃治療小兒遺尿癥臨床療效分析[J].中國實用醫(yī)藥,2010,5(29):145-14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