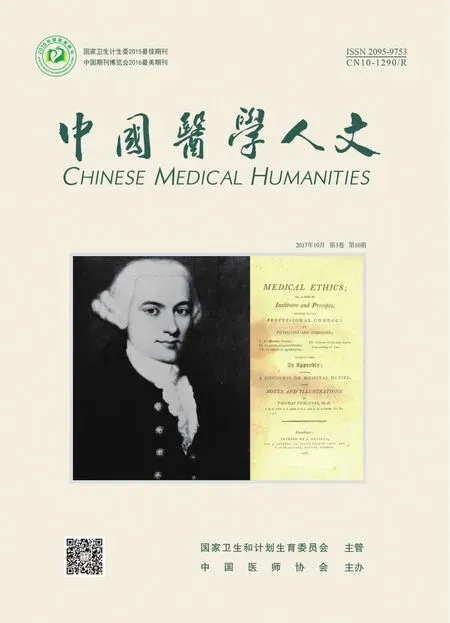如何有尊嚴地做醫生
——中國醫學人文大會人文對話
本刊記者/謝 姣
如何有尊嚴地做醫生
——中國醫學人文大會人文對話
本刊記者/謝 姣
2017年9月7-9日中國醫學人文大會期間,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原社長袁鐘主持人文對話欄目,與對話嘉賓就“醫生應該如何有尊嚴地生存”“良知如何影響從醫方向”“為什么當醫生就要當好人”等觀點展開對話,激烈的思想交鋒碰撞出絢爛的人文火花。本文將對話中的部分內容整理出來以饗讀者。
主持人:
袁 鐘: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原社長
對話嘉賓:
陸 軍: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
尹 梅:黑龍江哈爾濱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
江 西: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副院長
姚玉峰: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眼科主任
陳劍峰:北京正心正舉應用科學研究院院長
雷 方:河南科技大學副校長



袁 鐘:
200年前亞當·斯密寫了一本《國富論》,里面特別提到要怎么創造財富,他認為要充分的“利己”。但是“利己”出來之后,沖擊最大的就是“利他”。“利他”是我們醫療行業最大的一個特點,因而“利己”和“利他”的沖突帶來很多痛點,我想掙錢,但怎么有尊嚴地掙錢?我發現一些現象,不論是在一個國家里還是一個醫院里都有一個趨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不賺錢的部門,是要被忽視的。那么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醫院、醫生怎么有尊嚴地生存?
姚玉峰:
“利己”“利他”反映了我們這個行業中,個人或者說整個職業的一種矛盾沖突。首先我們回歸到個人,其實“利己”“利他”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命題。從這樣一個命題來說的話,德不近佛者不可以為醫,才不近仙者不可以為醫。醫生這個職業,對于“德”和“才”的要求很高,如果僅僅是謀生的話,為了你自己安寧,那就別從事這個職業。對于我自己來說的話,利己利他是始終存在的東西,在我利己的同時,我也能夠利他,而且心里是安寧的話,我覺得是最舒服的。
江 西:
談起怎么做一個有尊嚴的醫生,我可以自豪地說,在純樸的藏民族地區,醫生就是一個非常有尊嚴的職業。在藏區,人們把醫生當作佛和菩薩的化身,把醫生放在一個很高的地位。在藏區,只要醫生盡心盡力了,即使后期病人狀況惡化,甚至是死亡,他們也不會有任何的怨言,不會有任何的責問、傷害或者說是辱罵。我從醫35年,在我的身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所以我作為我們玉樹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的醫生感到非常自豪。
陸 軍:
由于工作關系,我所到醫院的數量應該不下500個。我自己深深感受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醫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無論硬件還是軟件,應該說是可以跟國際媲美,很多醫療技術不亞于國際水平。但是我們看到一個事實,我們忽略了醫學人文,由于醫學人文這只手不硬,導致了我們在很多方面不能夠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我們大家一致的口號是:患者利益至上,但是我們在實際服務當中,做到這點卻是很難。我個人覺得除了社會環境之外,當然有我們醫療衛生體制本身的責任,這種責任來自于政府,來自于醫院,同樣也來自于醫生本身。作為醫者,我們要把最大的愛,帶給患者,帶給他們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帶給了我們。
尹 梅:
醫學人文老師如果想讓你的課堂有吸引力,那么你一定要走進臨床。我走進臨床的時候,我也會對臨床的那些醫生們講,為什么做一個有人文情懷的醫生。其實我們經常說的醫術,是醫學技術和醫學藝術的合稱,醫學技術和醫學藝術相當于人的兩條腿,交叉并縱,只有技術一條路,開始沒有問題,走遠會累的。藝術幫你兩條腿走得更順暢,藝術對技術而言叫錦上添花。但是如果技術要是有一點差錯,或者是瑕疵的時候,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藝術會幫到技術,會做到雪中送炭。我在臨床做醫患關系的研究的時候發現在很多醫院里面,被投訴的醫生常常相對比較固定的,而且被投訴的常常不是技術水平最差的。所以某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服務技術和藝術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不可或缺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在我們的醫學人文隊伍還需要思考有多少人愿意去從事醫學人文這個領域的研究,能不能讓最好的人愿意加入到這個行列,也是我們這個梯隊,這個團體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雷 方:
醫院是不是為了掙錢,包括醫生,包括我們的尊嚴?我覺得一個醫院如果是為了掙錢,絕不是好醫院。一個醫生滿腦子是為了掙錢,更不是一個好醫生。其實我們現在對醫療行業有很多誤解,所有的醫院都想救死扶傷,幫助病人。其實我們的醫務工作,真的是很受人尊重,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生命科學,生命是無價的。在日本只有兩個職業被稱為先生——醫生和老師。既然別人如此尊重我們,我們就不光要有一個好的服務態度,關鍵還要有一個好的服務質量,能夠給病人解決真正的問題。因為陪著病人和家屬哭的醫生并不是一個完美的醫生,能讓病人和家屬不哭的醫生才是一個好醫生。所以我們出發點必須是好的,我們的技術必須是好的。
袁 鐘:
有一件曾經在整個社會引起過熱議的事情:我們在路上碰見一個人倒下,救不救?救了會不會被訛?這和醫療關系特別大,有些病人我們要去幫助他,我們還想到他會不會訛我,現在最糾結的不是不想幫他,不是不想救他,而是怎么保護自己?這就和醫療的初心有關系。隨著人們最初痛苦表達,和減輕痛苦的最初愿望,我們保護自己的時候如何幫助別人,這是很棘手的問題。
姚玉峰:
這樣命題既有假設性,又有現實性。我剛剛一直在想,一個人倒地的時候,我要不要去救。能不能解剖成這樣幾個要素。第一就是當遇到一個緊急情況的時候,個人要不要行動。要不要行動這里又分出了幾塊,其中就有問題的緊急性,比如說倒地,倒地后很從容的,那沒問題。如果倒地以后可能喪失生命,或者倒地以后一輛車即將開過來壓到他,這個情景就不一樣了。第二個就涉及這個人是否有應對這件緊急事的專業性。比如說在醫院里面,恰巧在我的邊上有比我更專業的人,那我也就變越權了。第三這里面沒有清晰的界限,最終涉及到一個社會評價力或者社會評判力問題。其實說得再白一點的話,倒地的人有可能訛你。為什么出現“訛”,我們對他的救助這種行為是符合常規判斷的,但是還會被訛。被訛的就涉及到社會評價,有沒有地方說理。當有地方說理,“訛”就不會存在。為什么需要法院,因為人類的社會事務其實是永遠不可能一刀切,需要有一個評理的地方,讓大家達成共識,這樣“訛”在社會上不被存在的,不被評價的。只有他們整個社會循環的時候,這樣的行為,社會不但不會讓你受到傷害,還會得到保護,這類行為就會變成正循環。
尹 梅:
其實透過這個事件揭示一個問題,整個社會民眾信任的滑坡。如果信任沒有了,那么我們的善良可能就要打折扣。所以最近網上有一篇文章,沒有底線的善良是值得推廣的。實際上它要有一個語境,這個語境就是語言的環境,那就是當整個社會信任都在滑坡的時候,你的善良可能就會給你帶來一些不應有的傷害的時候,你還會愿意一直善良下去嗎?我知道英國有一個諺語,“善是一種循環,愛是一種傳遞”。我看到地上躺一個人,猶豫救還是不救的時候,我想救的時候會不會給我帶來傷害,權衡利弊我選擇了離開,某種意義上我離開是不會受傷害的,但是從長遠利益來說我是受傷害的,萬一有一天我躺在地上的時候,經過身邊的人也不會救我。所以透過一個扶與不扶,我們能看到社會很多這樣的問題,每個人都在想保護自己的時候,只是保護了你的眼下利益,但是長久利益你也可能是一個受害者。
陸 軍:
我在這個領域已經38年了,面對比較緊張醫患關系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些問題。為什么會造成現在看病越看越貴,越看越難,政府有怨氣,醫院有怨氣,醫生有怨氣,護士有怨氣,老百姓有怨氣?歸根到底產生這種狀態有深層次的體制與機制的問題。我們側重了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就是放開來,放開來后大家就是要生存,要發展,要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要技術。但是忽略了一個問題,這個治療過程當中,如何去關注患者的感受,患者的利益和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和患者的良好的溝通。榆林孕婦跳樓事件一跳兩命,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僅僅怪家屬不對,僅僅怪醫院也不對,這真的是一種溝通不到位的問題。作為一個好醫生我們得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承受力,同時政府一定要給我們醫生以強大承受力的一個支撐。
陳劍峰:
實際上我們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把文化、人文和科學分開了,所以我們學生不了解人文當中的科學,科學當中的人文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得到知識,渴望得到智慧,因為我們要走向社會,要解決家庭問題、婚姻問題、戀愛問題、發展問題、學習問題,一系列的問題從什么地方來,人文是干什么用的,科學又是干什么用的。人文不是空的,他是能夠和科學互為前提,相互作用,類似于陰陽太極一樣的,缺一不可。做好領導,當好領導你必須懂人文,因為你的情懷,你的格局,都是建立在人文基礎上。
袁 鐘:
協和有一個專家,做了一個調查,全國136家醫院,八萬四千多醫護工作者,其中有25%的醫護人員給患者墊過醫藥費。其實我們幫助別人,也是在提升我們自己,也提升了我們的人生價值和幸福值。所以我相信醫生是最幸福的人。我們從事任何工作都是為了追求幸福,幸福是什么?是金錢?權力?地位?享受……《思想錄》說:“人的偉大——我們是如此看重人的靈魂,以至我們無法忍受靈魂受人蔑視,也無法忍受別的靈魂不尊重它。而人的最大幸福就在于這種尊重”,作為讀書人,醫生的“最大幸福就在于這種尊重”,無論在什么地方,醫生走在自己行醫的城市,認識醫生的所有人都會通過心靈的窗戶——眼神向醫生表達尊敬,當然也會表達疑惑、失望甚至蔑視,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治病救人中付出的結果。醫生本應該成為最幸福的人,在喚發利己的“經濟叢林”中,利他的人道主義者醫生受到強烈沖擊,于是探索“有尊嚴掙錢”的正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