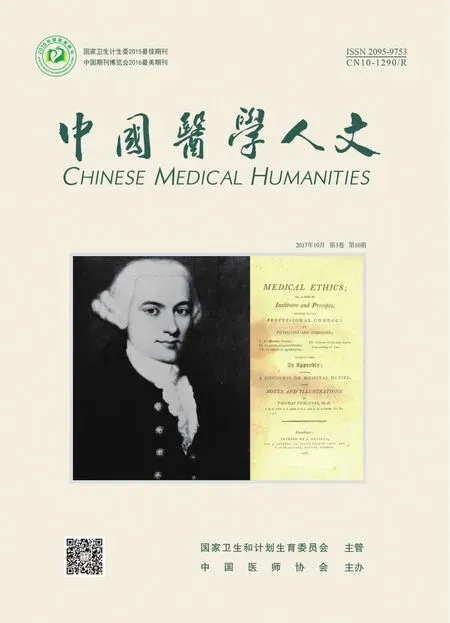面臨兩難困境 醫生如何抉擇
記者/李陽和
面臨兩難困境 醫生如何抉擇
記者/李陽和
在9月7日-9日召開的中國醫學人文大會上,由中國醫師協會人文醫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袁鐘教授、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張新慶教授等負責舉辦的“醫學新青年”分論壇成為會議的一大亮點。協和醫生拋出的案例,現場出演的情景劇,以及現實的熱點事件,引發了與會專家、學者激烈的觀點交鋒。圍繞特殊情境下“要不要檢查” “要不要搶救” “要不要手術”等臨床抉擇難題,臨床醫生、人文學者、法學專家及患者代表,從臨床醫學、倫理學、法學等多方面進行了深入討論和熱烈交流。
一個案例引發的討論醫生的專業判斷與患者需求發生沖突時怎么辦
一位女患者走進診室,對大夫說:“我腰疼有兩個星期了,擔心是椎間盤突出,聽朋友說應該做個CT。”大夫在問診和查體后,認為她的腰疼(沒有腿麻、疼的情況)可能就是肌肉韌帶勞損所致,告訴她:“你的情況沒必要做CT,況且CT本身有放射損傷,能不做就不做的好。”然而,患者并不聽大夫的,還是堅持要做CT。
按理,醫生可憑借專業知識、技能拒絕患者的不合理檢查要求,但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張新慶教授于2017年8月開展的“全國醫務人員從業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情況并非如此。調查問卷中,有一道問題是:當患者堅持要做在醫生看來沒有必要的核磁共振時,醫生會不會為患者開出檢查單?74.9%的醫生選擇了“會。但我會告訴他,自己并不愿意這樣做”;只有不足兩成(16.4%)的人表示“不會”。
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金話筒主持人蘇京平結合自己的治病經歷發表了看法。他對于醫生要聽任患者或者家屬的行為表示不解,“患者要想有好的治療效果和好的生活質量,就得遵醫囑、信醫生。醫患之間的信任非常重要,它是醫患共同往前走的前提”。
然而,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像蘇京平那樣想。如果遇到“不聽話”的患者,醫生如何應對才恰當?北京協和醫院基本外科主任醫師李秉璐教授認為很難給出確切的回答,關鍵是看醫生自己的資歷和患者的情況。“我剛畢業當住院醫生的時候,出門診面對這樣的病人,可能會按照他的需求來給他開這個檢查,因為我怕漏診,擔心自己給他的體格檢查不一定很徹底。按照我現在的年資,到底給他開還是不開?我會因人而異。有的患者來看病之前可能先‘百度’了,也可能聽到別人說因為做了CT檢查發現了腫瘤或者其他很嚴重的毛病,所以,他們想做個CT檢查預防一下。這個時候,我們要先做充分的溝通,告訴他這個檢查對身體有傷害,在此前提下,我有可能會給他們開CT檢查單。有的時候,病人其實需要治療的是心病,你按他的意思開了檢查單,他做完沒事就踏實了。對于大多數的病人,如果他們情緒很正常,沒有過多不好的想法,我會給他講明白病情,告訴他什么時候去做這樣的檢查。”
作者單位/健康報社
對于類似的問題,美國醫生給出的回答截然不同:2007年一項針對3 000名臨床醫生所做的調查顯示,超過6成的醫生選擇的是“不會”給患者開具這樣的檢查單。也就是說,美國絕大多數的醫生是堅持專業的合理性的決定。北京和睦家醫院的全科醫師Andrew Perrett認為,當患者對醫生的診療意見不接受時,醫生首先要判斷這個患者有沒有特殊性,然后再進行細致的溝通,爭取患者的配合。
一場情景劇引發的思考知情同意是否比搶救生命更重要
本來準備順產的孕婦肖夢瓔突然出現并發癥,需緊急搶救,梁護士長急著找到患者的丈夫李楠:“您愛人生命岌岌可危……現在需要您簽字,對她進行剖宮產急救手術!”
李楠難以置信,一個勁地說自己媳婦剛才還好好的,并念叨著,“我家里三代單傳,這回二胎又‘超’了個姑娘,我媳婦又快40了!不順產,我怕她再生就生不了了……”
張大夫從產房出來催促他盡快簽知情同意書,“現在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再生的問題,而是你愛人和她肚子里的寶寶能不能平安的問題!你懂嗎?”
在聽了大夫的病情介紹,以及護士長的勸說后,猶豫不決的李楠準備簽字,可孕婦在產房嚷著“我要自己生!我要自己生!”
我的書娟姨媽遠遠看見了她的背影。還是很好的一個背影,沒給糟蹋得不成形狀。書娟姨媽從外圍的人群撕出一條縫來到她的身后,被上萬人的汗氣蒸得濕淋淋的。姨媽伸出手,拍了拍南京三十年代最著名的流水肩。轉過來的臉卻不是我姨媽記憶里的。這是一張似是而非的臉;我姨媽后來猜想,那天生麗質的臉蛋兒也許是被毀了容又讓手藝差勁的整容醫生修復過的。
情況已非常危急,患者家屬簽了字,然而孕婦因擔心“剖了,就不能再生了”,仍死命堅持要順產……張大夫戴上口罩,毅然決然地說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強制手術!所有責任我來負!”
最終,經過大夫的全力救治,孕婦脫離生命危險,而胎兒因為耽誤了最佳救治時間沒能活過來……
這幕在論壇現場上演的情景劇,反映的是在緊急情況下醫生如何抉擇的問題。“這個戲并沒有演完,手術后,家屬在床頭悲痛不已,后面還會有什么,劇情沒有交待。如果患者一口咬定是醫生把孩子殺死了,去告醫生,那這個醫生的職業生涯很可能就此終結了。”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譚先杰教授坦陳自己的擔心,“我個人更帶有僥幸心理,就是如果我碰到這樣的事情,我希望遇到的患者及其家屬是通情達理的,我相信99%以上的患者是這樣的。也就是說,我們醫生做到了我們該做的一切,但結果并不如人所愿,這個時候,患者會諒解我們”。
是遵從患者本人的意愿放棄手術,還是依據醫學的專業判斷立即手術?北京大學醫學部劉奇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倫理難題,“從倫理學的角度而言,一方面醫者要搶救患者生命,維護患者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又不能違背了患者的自主決定權。但是,當生命權和自主權發生沖突時,生命權顯然更應該優先考慮”。
在產科,還可能遇到的一種情形是,患者家屬不愿意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字。針對這種情況,張新慶教授在2008年、2013年、2017年連續做了3次全國醫護人員狀況調查,問了同一個問題:假定一名危重病人急需手術搶救,病人家屬充分知情但仍然拒絕簽字,此時作為主治醫生應該怎么辦?有四種選項:第一,立即做手術。第二,放棄手術,采取保守治療。第三,做好準備,等待上級指示。第四,其他。調查結果顯示:5.0%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應“立即做手術”,80%的人選擇了“做好術前準備,等待指示”。
讓張新慶教授感到驚訝的是,從2008年第一次做調查,到今年8月進行第三次調查,過去了近10年,但醫務人員的選擇幾乎沒什么變化。這個現象引起他的思考,也引發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
在劉奇教授看來,大多數醫生選擇“做好準備,等待上級指示”,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緊急情況下,患者發病原因不清楚,個體差異很大,病情輕重也不一樣,且醫學是有局限性、不確定性的,這些都使得醫生在面對手術的時候,不得不考慮個人所要承擔的風險。”為此,劉奇教授給出的建議是,“面對這種情況,國內外通用的方法就是風險共擔,即讓患者和醫生共同承擔手術的風險。這就需要建立一種保護醫生、規避醫療手術風險的機制,如建立應急專家會診制度,以醫學共同體的方式做出相對正確的判斷,避免個人判斷錯誤。第二,建立醫療保險基金,分擔醫生個人風險。第三,加強科普宣傳,打消患者家屬術前簽字的疑慮。”
一則新聞事件激起的熱議
當救治有風險,如何以法律的手段保護醫生與情景劇“畫風”不同的是,在最近引起社會空前關注的陜西榆林孕婦跳樓事件中,是孕婦自己強烈要求改順產為剖宮產,但她的愿望沒能實現,最終悲劇發生。
有參會代表提出,榆林孕婦跳樓事件中,據現已披露出來的信息,孕婦馬某簽了授權委托書,被授權的丈夫是按順產簽署的知情同意,她本人后來極力要求剖宮產。此時,醫生是否應該遵從產婦剖宮產的意愿?
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睢素利教授回應說,患者即便已經簽了授權委托書,并不意味著她把權利委托之后自己就沒有自主權了。所以,醫生遵從患者本人的意愿是沒有問題的。從法律程序上來講,讓患者在委托授權書上簽一句話“撤回授權”,就什么事情都沒有了。即便沒有撤回,患者自己在清醒的時候做出的決定也是完全有效的。
然而,一些參會的醫生仍有疑慮:如果患者和家屬意見不統一,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選擇了做手術,沒有事當然皆大歡喜,但萬一患者死在了手術臺上,很可能就是一場醫療糾紛。“這個時候,對于醫生而言,道德和法律哪個重要?”
對此,南京醫科大學醫政與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黨委書記王錦帆教授指出,“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地方,醫生有這個能力去救人,但你不去搶救,你的倫理、法律底線就沒了。當然,醫生去搶救了,仍然沒能挽回患者生命,醫生是否要擔責?現在,有了‘尚方寶劍’——《侵權責任法》第56條明確規定:因搶救生命垂危患者的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近親屬意見的負責人批準,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即使患者家屬拒絕簽字也沒關系,但醫生要注意把整個溝通和手術的過程全部錄下來,包括和家屬談話的時候也要注意保留證據,以便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和保護。”

情景劇表演
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的張迪老師從患者自主性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如果患者有自主性,毫無疑問,按照《侵權責任法》第55條和56條的規定,應該尊重患者的自主性。那在什么情況下才能爭得患者家屬的同意呢?只有在患者缺乏自主性的時候,比如他是孩子,或者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病情嚴重到已經沒法做自主判斷了。”張迪進一步指出,“當然這個自主性不是說患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醫生在尊重患者自主性的同時,還應當考慮醫學指征,尊重醫學的專業判斷。”
北京協和醫院消化內科的吳東醫生表示,醫生通常會認定患者的最佳利益是讓他活著,但是有的患者出于宗教信仰或其他家庭因素的考慮,并不認同醫生搶救的決定。這個時候,醫生在進行醫療決策時,法律途徑一定要盡早介入,最好是請律師提前過來,以免出了事后陷入被動。
關于醫生“救還是不救”的道德困境,中國醫科大學出版社原社長、中國醫師協會人文醫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袁鐘教授更多的是從醫患信任和醫生職業特點分享了他的思考。聯系到社會上熱議的“老人倒地,救不救”的問題,袁鐘教授認為,多數人表示不敢救,因為我們的社會缺乏信任。同樣,在最應該講信任的醫療行業,我們的醫生面對需要搶救的患者時,也會糾結于“要不要救”,這背后的原因,有醫患信任的缺失,也與醫生的職業追求有關。
“盡管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法律,但不同的人在面對緊急情況做出的選擇并不一樣。有些醫生的信任資本是不夠的,在和患者打交道時,雙方都是高度警惕的。但是,從醫療行業的特點來講,醫生是高貴的職業,我們的醫生需要恢復我們的榮譽感、使命感。無論怎么樣,不要忘了初心,不要忘了我們為什么要當醫生。當然,我們的社會和法律也應保護醫生的善良,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支持、理解和包容。我去過很多的醫院,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是迅速搶救,但要注意保護好醫生,通常是找律師來,讓法律的支持跟上來。”袁鐘教授說。
(摘自《健康報》2017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