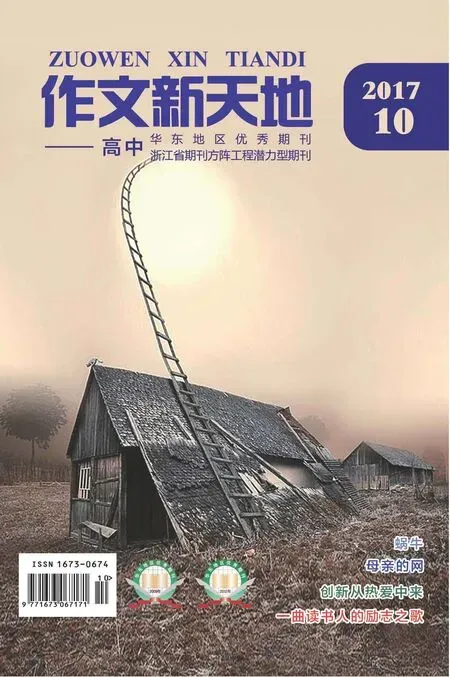蝸牛
◎吳偉偉 浙江省東陽中學
蝸牛
◎吳偉偉 浙江省東陽中學

有一回,在單位食堂就餐,我看打菜的阿姨是本地人,就用方言點了份“鴨肉”。排隊在我身后的同事是外地人,隨口順了句“蝸牛”。我乍一驚,隨即哈哈大笑。這位同事來本地工作已經多年,深諳兩地語言的差異,此番“指鹿為馬”,反倒令人覺察到了語音指向的多元化現象。
記得大導演李翰祥在其自傳《三十年細說從頭》里有過類似的記載。李翰祥生于遼寧錦西,曾于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修讀戲劇電影,1948年前往香港。餞別宴上,有個到過香港的朋友教了他一些入鄉隨俗的細節,于是就有了這樣的對話:
“在香港‘喝’茶叫‘飲’茶,吃飯叫‘塞(食)’飯。”
“干嘛塞呢,慢慢吃不好嗎?”
“慢慢吃,就叫慢慢塞(食)。吃面叫塞(食)面,面和上海的陽春面、北方的打鹵面都不同。黃色,細條的,因為堿落得重,所以吃著有點澀、有點硬。看電影和坐公共汽車一樣要買票,不過票不叫票,叫‘飛’。”
李翰祥追憶說:“我聽了直樂,記了半天,結果印象最深的還是‘飛’。票跟‘飛’實在差得太遠了,東三省有個地方叫‘北票’,豈不要叫‘北飛’?天橋晚期的八大怪之中,有個耍單杠的叫‘飛飛飛’,豈不要叫‘票票票’?”他當時所不知道的是,粵語里保留著大量的古漢語詞匯,比如“飲茶”和“食飯”;同時,香港也因受到英國長期殖民的影響,習慣粵語英語混用,將英文諧音變成粵語口語,比如管“票”叫“飛”,就是英文單詞“fare”的本土化表達。試想,對于前者,如果只是書寫成漢字,在理解上并不會出現任何偏差;對于后者,如果將英文單詞原樣呈現,只要翻檢英漢字典同樣可以迎刃而解。之所以容易造成誤解,根源全在于聽者以既有的語言系統套用陌生的語言系統,而忽視了一時一地一事的特殊性。
語言學家周有光的《語文閑談》中有一則叫做《近音的干擾》,提到:“‘納粹’(Nazi)和‘小豬’(Nasser,瑞典語)近音,因此‘納粹’運動始終難以在瑞典開展。‘元帥 ’(Marshal)和‘馬 歇爾 ’(Marshall,人名)同音,因此美國在戰后有‘五星上將’而沒有‘元帥’。”每一種傳統文化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影響力,總是偏于靜止凝滯而排斥流動變化的。因此,對于外來文化基本上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一套,停留在器用層面而難以深入骨髓,一旦抵觸則棄若敝屣,毫不吝惜。至于內部文化的嬗變,有時候為了避嫌或者忌諱,干脆只是改個名號,譬如喚“錢幣”為“阿堵物”之類,換湯不換藥,其實并沒有觸及事物的本質。
除了地域文化的差異會造成誤聽,知識涵養的不足同樣會導致誤解。如明代馮夢龍《笑府》:
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為“糕”也,曰:“夏雨如饅頭。”或又疑為夏禹也,曰:“周文王象塔餅。”(《行令》)
“春雨如膏”,是形容春天的雨水可以像脂膏一樣滋養農作物。這個詞語,大概源自《左傳·襄公十九年》:“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歷史既然久遠,孳生引述必定眾多。偏偏接酒令的聽后生疑,則其學問功底可想而知,他將錯誤的信息傳遞下去,即使后面的人想要撥亂反正,也只是回天乏力,徒喚奈何了。
又據清代小石道人輯《嘻談續錄》,有個《堂屬問答》的故事:
一捐班不懂官話,到任后,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并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小。”上憲曰:“我不是問什么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官忙站起來答曰:“卑職小名狗兒。”
“捐班”在清代是指不通過科舉考試而向官府捐納銀錢換取官職的人,一般來說其學問功底與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官員是有著比較大的差距的,因此對于以“溫柔敦厚”雅言為基礎的官話,難免有種“兵遇上秀才”的感覺,茫然不知所謂。“風土”是指風俗習慣與地理環境,“春花”是指越冬后的魚種,“紳糧”是指地方上有地位有財勢的人,“黎庶”是指民眾百姓。盡管捐班在上司面前“對答如流”,態度極盡誠懇謙卑,無奈驢唇不對馬嘴,令人啼笑皆非。事實上,根據專家考證,在清代即便是捐班,也要經歷考察試用期,方可如正途出身者一般受“差遣”。為此,大部分捐班都會大搞“題海戰術”,惡補“應試技巧”,以便盡快熟悉官場規則,為從仕鋪好一條坦途。這個故事,估計來自那些深深厭惡捐班的讀書人的杜撰,對不學無術的嘲諷,實際上也從側面印證了語音與文字的多重對應關系。
對于人事如此,對于自然也是如此。人們依靠敏銳的洞察力,發揮豐富的想象力,為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一一擬定專屬的名字,并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范,其中就有“擬聲”,比如雞、鴨、鵝、貓、蛙之類,無不根據動物本身的叫聲予以命名。還有一些鳥兒,因為其生活習性和生理特點與同類的差異,更是得到了文人們的眷顧和垂青,被賦予了廣泛而深遠的文化意義。比如,固化杜鵑的叫聲為“不如歸去”,寄托在外漂泊的游子的思鄉之情;固化“鷓鴣”的叫聲為“行不得也哥哥”,表示行路的艱難和對離別的凄愴傷感。甚而無生命的風聲雨聲,因為特定環境的觸發,稍經點染,也無端地多了一層人文關照。據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之二“郎當曲”條: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也。”明皇愧且笑。
因為安史之亂,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曾避難蜀中。回京途中,聽到駝馬的鈴聲,引起了一種不確定的聯想,這本是作為“梨園祖師”的一種藝術敏感。而宮廷樂師黃幡綽不改其俳諧本色,利用諧音加以諷諫,點到即止卻力勝千鈞。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所以楊貴妃稱他為“三郎”,這個專屬的昵稱,代表著一段逝去的美好回憶。至于“郎當”,據明代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的解釋,就是“敗事”。“三郎郎當”的意思,乃是暗指唐明皇耽于安逸,終于國破,而今“好了傷疤忘了疼”,念念不忘的卻是滿載珍寶以備時時把玩,此種故態復萌,可不就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么?
由于漢語不是音節書寫的語言,在其長遠的發展過程中便產生了不同的表現形式,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當屬同音異形詞。同音異形詞的存在,有時候會給民眾生活帶來一些的困惑與不便。
據明代馮夢龍《古今譚概·無術部第六》“琵琶果”條:
莫廷韓過袁太沖家,見桌上有帖,寫“琵琶四斤”,相與大笑。適屠赤水至,而笑容未了,即問其故。屠亦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賞極,遂廣為延譽。
枇杷、琵琶屬于同音異形詞,袁太沖的朋友因為寫了別字,結果貽笑大方。
細細追究起來,枇杷和琵琶都是聯綿詞。對于聯綿詞,鄧廷楨《雙硯齋筆記》卷三指出,“泥于其形則岨峿不安,通乎其聲則明辨以晰”。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九《通說上》也說:“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換言之,對于這兩個詞,固然不能通過析字的方式分辨內涵,卻能夠因為讀音的相近而推斷出在意義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枇杷,在蘇軾的《惠州一絕》中被稱為“盧橘”,因為其葉子形狀似樂器“琵琶”,所以又多了“枇杷”這個名字。另外,比如“縹緲”與“飄渺”,“嬋媛”與“潺湲”之類,都只是為了適應各自的描摹對象變化了形體,而其內核則幾乎沒有變化。
其實,在精于屬對、嫻于修辭的文人們看來,同音異形詞的存在,令語言的意義與類別更加豐富嚴謹,給了他們馳騁文思的絕好載體。在唐代高彥休《唐闕史》中有一則非常著名的故事:
優孟師曾見于史傳,是知伶倫優笑,其來尚矣。其開元中黃幡綽,玄宗如一日不見,則龍顏為之不舒,而幡綽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漆城蕩蕩,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后兒坐也。”上為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孔子)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唐代以懿宗誕辰為延慶節,舉辦各種節目加以慶祝。李可及在皇帝和眾人面前表演了一段類似于相聲的《三教論衡》,分別拿佛、道、儒三教的創始人來開涮,調侃他們是婦人。看得出來,李可及是博覽群書,并做了精心準備的,他所立論的正是三教的原典,用以自圓其說的方式便是善用同音異形詞。“敷座而坐”,即結跏趺坐,是一種互交二足,將右腳盤放于左腿上,左腳盤放于右腿上的坐姿。“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意思是說自己最大的憂患,便是自己的身體,這是苦難的根本所在。“我待價者也”,是以出售美玉為譬喻,希望得到統治者的信任,進而施展自己的才能。結果“敷座而坐”被訛作“夫坐兒坐”,“有身”被訛作“有娠”,“待價”被訛作“待嫁”,距離本來面目甚遠,與人們的習慣認識相悖,產生了極大的喜劇效果。
浮白齋主人《雅謔》有一則《園外狼》:
石中立為員外,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同列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吾儕反不及此!”石曰:“然。吾儕做官,皆員外郎,敢比園內獅子乎?”眾大笑。
鐘伯敬《諧叢》有一則《汗淋學士》:
王平甫(王安國)學士軀干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劉攽)曰:“君所謂汗淋學士也!”
陳皋謨《笑倒》有一則《爭坐位》:
瞎子、矮子、駝子三人吃酒爭坐,各曰:“說得大話的許坐第一位。”瞎子曰:“我目中無人,該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長)人,該我坐。”駝子曰:“不要爭,算來你們都是侄輩(直背),自然該讓我坐。”
以上三則,無不是利用漢語的諧音修辭,借助同音異形詞對事物進行非常態解讀,使語言更具有了活潑的生趣,使生活也多一層詩意。“園外狼”表達了對“人不如獸”的憤怒和自嘲,“汗淋學士”表現了對胖子夏天容易出汗的戲謔,“爭坐位”化劣勢為優勢,在敏捷應對中體現了群眾的智慧。正如柏格森在《笑——論滑稽的意義》中指出的那樣:“當一個表達方式原系用之于轉義,而我們硬要把它當作本義來理解時,就得到滑稽效果。”

現在我們進入信息時代,語言在與時俱進上更是不遑多讓,而網絡語言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源自同音異形詞,比如稱“工程師”為“攻城獅”,稱“教授”為“叫獸”,稱“主角”為“豬腳”,稱“悲劇”“喜劇”為“杯具”“洗具”等等。大家明知其錯,仍將錯就錯,以訛傳訛,樂此不疲地使用與轉發,將此作為新新人類的一種身份象征。其中的利弊得失,見仁見智,一言難盡。
但或許,我們可以溫故張大春在《認得幾個字》的自序里說的一段話,來客觀地審視我們的語言和人生:
“小孩子識字的過程往往是從誤會開始的。利用同音字建立不同意義之間的各種聯系,其中不免望文生義,指鹿為馬。倘若對于字的好奇窮究能夠不止息,不松懈,甚至從理解中得到驚奇的快感以及滿足的趣味,或許我們還真有機會認識幾個字。否則充其量我們一生之中就在從未真正認識自己使用的文字之中‘滑溜’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