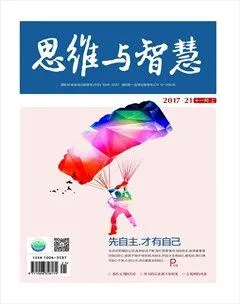靜與躁
葉春雷
道家哲學,首先是“躁”或者說“動”的哲學。老子說:“反者道之動。”按照這個觀點,“動”或者“躁”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靜”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道家哲學承認事物的運動是永恒的,所以才有“反者道之動”這樣高度抽象而精確的命題。事實上,當孔子站在河邊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時候,他實際上也是在坦承物質世界的永恒運動呀!
但是,老子又強調,“致虛極,守靜篤”,并且明確指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按照老子的思想,靜統帥躁,這是沒有問題的。莊子在《繕性》中言:“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寧極”四字,可謂對“靜”最佳詮釋。
蘇東坡被貶黃州,月夜泛舟赤壁之下,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這個感悟是老子式的。他看到了物質世界變動不居的特性,所以才會在遭遇人生重大變故(“烏臺詩案”)的關口,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適應新形勢、新變化。這種調整,個人的感覺,是老子“靜為躁君”這一思想的一次成功運用。外在物質生活是變動不居的,有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謂“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就是外在物質生活的“躁”的集中體現。但是,蘇東坡的偉大,是用內心的“靜”來制外在的“躁”,強調“靜為躁君”,這就是他接下來說的后半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從“躁”的觀念看,“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赫拉克利特);從“靜”的觀念看,河流永遠是河流,不會消失。就這個意義言,“靜為躁君”,微觀物質世界雖然一刻不停地在變動,但宏觀物質世界卻永恒存在。蘇東坡感悟到了這一點,活著的信心也就更足了。所謂“一蓑煙雨任平生”,就是這種坦然自信心態的表現。
“以靜制動”因此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非常高妙的人生哲學。當老子將“重為輕根”與“靜為躁君”并置時,我感覺,在老子的想法里,“靜”是重的,“躁”是輕的,所以“靜”才能勝“躁”,才能統帥“躁”。中國文化非常注重一個人的“靜氣”,“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是清代三朝帝師翁同龢的一副對聯。“靜氣”就是一種沉穩勁健之氣,與一個人的“躁氣”也就是虛浮之氣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說,“靜為躁君”,就是要消除人的“躁氣”,錘煉人的“靜氣”。“躁氣”就像天上的云,輕飄飄的,沒有分量,所以有躁氣的人在做人上就沒有根蒂,老子因此說:“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君”是什么?“靜氣”。人失掉了“君”,做事做人就沒有定準,恣意妄為,無邏輯可言,這樣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大家的認同?因此老子在第四十五章接著說:“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今天的中國社會,因為處于一個大變革時代,一個劇烈的轉型期,各種思潮沖突尖銳,表現在人心上,就是“躁”得厲害。“躁”有其好處,那就是古人說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最怕的是一潭死水,一個聲音。正因為有各種思潮的交流碰撞,才會有真理的火花閃現。所以,當代社會,不怕“躁”,但是需要用“靜”來統帥“躁”,遏制“躁”的負面影響。這個“靜”,個人以為,不是墨家的“尚同”,而是儒家的“和而不同”。承認每個人生命的獨立價值,允許每個人發表自己的想法,無論那想法是成熟的還是不成熟的,而又在法律的框架內和平共享身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彼此和諧相處。這就是“和而不同”,這就是“靜”的最高境界。
事實上,當我們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時,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魏晉人對個體生命獨立性的尊重。王羲之在文中寫道:“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你可以選擇“靜”的人生,我可以選擇“躁”,這里面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同樣可以獲得人生的快樂。魏晉人不愿將人生圈定在一個固定的狹窄的圈子里,他們希望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是不受羈絆的,這種想法是多么好。雖然我們肯定老子的“靜為躁君”,肯定人的內心的靜氣,肯定人心應該有的那份沉穩厚重,但是,在人的外部生活中,我們并不提倡“槁木死灰”。我們希望人的外部生活是活躍的,豐富的,富有變化的。所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應該是我們的一種自覺的追求。我們羨慕西方文化的冒險精神,許多科學上地理上的大發現,都源于這種冒險精神,源于外在生活的“躁”,源于對運動的天然愛好,我們中國人同樣可以做到。所以,外在的物質生活無妨“躁”一點,多在外面走走看看,多體驗;內在的精神生活無妨“靜”一些,少點對名利的貪欲,多點對生命本質和尊嚴的體悟和尊重。這樣一來,既做到“靜噪結合”,又做到“靜噪有別”“以靜制躁”,真正如蘇軾所言:“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以動襯靜,那靜是何等恢弘而博大?
按照孔子的說法,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靜噪豈可偏廢?乃自制對聯一副,以為結束:
靜噪本一體,唇亡則齒寒。
(編輯 之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