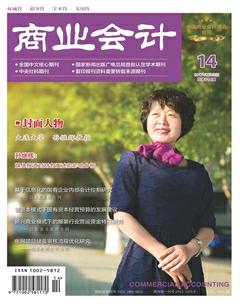公司治理中風險投資者與創始人的控制權之爭:以雷士照明為例
王先鹿+李楠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812(2017)14-0055-02
摘要: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財務投資形式,越來越受到上市公司投資者的青睞,特別是遇到資金難題時。然而風險投資帶來的結果并不確定,作為一種追逐利益的行為存在相應的風險。近年來經常發生的風險投資人與創始人之間的沖突也證明了這點,對這個現象的深入研究和探討對避免投資管理風險、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具有現實意義。文章以雷氏照明企業為例進行分析,對創始人與風險投資者之間存在的沖突和矛盾展開討論,以期為企業治理提供相應的風險規避策略。
關鍵詞:雷士照明 創始人 風險投資 控制權
一、引言
作為企業資金來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風險投資不僅能為企業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還能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動力。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風險投資在我國興起,這種投資的介入對于解決當時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資金難題有重大意義,直接推動了民營企業的治理和改革進程。
雖然風險投資作為在民營企業變革中的重要推動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與之相應的企業家和風險投資人之間的問題、沖突不斷(顧乾坤、范博宏,2012)。雷士照明企業的控制權爭奪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創始人與風險投資人之間爭奪控制權的行為中,反映出了民營企業在改革調整中出現的問題。本文將重點從民營企業治理與風險投資關系的視角,為民營公司的治理完善以及與風險投資的治理關系提供一些初步的啟示。
二、事件回顧
1998年底,吳長江與另兩位股東以100萬元的注冊資本創立了雷士照明。2005年,雷士照明出現了股東之間的利益糾紛,另兩名股東要求用8 000萬元把自己所持股份轉讓給吳長江,也即吳長江獲得企業全部的股權。由于需要吳長江支付巨額現金給兩位創始股東,企業一下子陷入了資金周轉的難題中。全體經銷商出面相救,局勢瞬間反轉,結果是吳長江重新坐鎮雷士,其他兩位股東轉讓股份離開雷士。
2006年8月,軟銀賽富的投資者向雷士照明注入了2 200萬美元,吳長江為了募集資金與軟銀賽富、高盛簽訂了一系列“對賭協議”, 2010年5月20日,雷士照明以每股2.1港元的發行價格順利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交易,募集資金近15.3億港元。軟銀賽富成為雷士照明第一大股東,股份比例為30.73%,超過吳長江29.33%的持股份額。
2012年5月25日,雷士照明發布公告,吳長江先生因“個人原因”辭任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董事會所有委員會職務,并辭任公司全部附屬公司的一切職務。非執行董事、賽富亞洲基金創始合伙人閻炎被選為董事長,來自施耐德的張開鵬任首席執行官。大部分媒體和相關人士認為,這次驅逐應是來自公司資本方——軟銀賽富,吳長江被資本方“逼宮”讓位,是資本方通過驅逐創始人來控制企業。
2012年12月,吳長江引入德豪潤達,德豪潤達斥資16.5億港元收購吳長江手中雷士的股權,吳長江將自己手中11.81%的雷士照明股份出售給德豪潤達,此時德豪潤達持股已達到20%,成為雷士照明的第一大股東。2013年6月,吳長江被任命為執行董事,時隔兩年重返董事會,吳長江雖然再次被任命為CEO,重新執掌雷士,但已今非昔比,其擁有雷士的股權已被稀釋到2.54%,事實上,吳長江已經從一個創始人逐漸變成了雷士的“打工者”,兩者的矛盾也由此引發。
2014年8月8日,雷士照明發布公告稱,因吳長江的不當行為影響公司經營,已通過決議罷免吳長江先生的首席執行官職務,不當原因主要指出吳長江利用公司內控漏洞,故意繞開董事會,精心策劃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行為,至此,經過了數次股權變動,吳長江終究還是遺憾收場。
三、風險投資對雷士照明公司治理的影響
(一)對股權結構的影響
對公司而言,要進行良好的治理,股權結構是必須考量的部分,如果股權結構的集中程度太高,可能會使得公司無法讓控制權以及現金流權這兩者實現統一,作為創始股東,其有可能會出現損害外部股東的權益而讓自身獲利的念頭,也可能出現以公謀私的現象。對于雷士照明而言,在風險資本未曾入股之時,吳長江作為創始股東,完全掌握著公司的股份,此時的股權結構極為集中。而隨著一系列的風投機構入股其中,吳長江所擁有的股份占比逐漸減少,這使得該公司的股權集中狀況得到了一定的緩解,逐漸實現了股權多元化,也讓吳長江的權力受到了制約,從而能夠有效地改善公司的治理情況。然而,在上述過程中,控制權的爭奪又會不可避免地產生。
(二)對董事會的影響
風投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到所投資公司的治理中去,而最為常用的手段則是進入所投資公司的董事會。以雷士照明為例,風投機構在該企業的董事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能夠有效地參與到決策層面,實現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的監督,而這種方式對于減少風投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是有益的,并能使委托代理成本有所減少,最終改善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風投也會以自身的利益為考量做出決斷,這又會讓其他股東以及創始股東的權益被削減,所以需要雙方互相制約。
(三)對管理層更迭的影響
對于企業而言,其戰略層面的具體執行是由管理層所決定的,因此,后者的行事對于企業運營而言至關重要。風投機構在進行企業控制權的爭取過程中,還會制訂出相應的選拔制度進行管理層的任命,從而讓后者的管理能力得到增強,同時可從多個方面對管理層進行監督,若是管理層的行事不能與風投機構相契合,則可能出現被彈劾罷免的情況。對于雷士照明,在風險資本未曾進入時,吳長江就是該企業的一把手,長時間以來一直以“一言堂”的形式進行獨斷的管理,在此過程中,其管理的手段主要是發揮自身的人格魅力。但是,風險資本進入該企業之后,吳長江不但股權受到日益削弱,同時其管理風格也與新的管理制度難以契合,依舊保持原有的獨裁模式,甚至數次蔑視董事會的決定以及公司規程,而這種做法已違背了風投機構的治理原則,因此,吳長江終究只能遺憾出局。endprint
四、結論與啟示
從雷士照明的案例不難發現,吳長江對雷士照明的控制權旁落風波本質是風投機構與企業創業者之間為取得最終企業控制權而進行的博弈過程。對于風險投資者,其不但能從資金方面對企業進行支持,解決后者的資金困境,還能讓傳統民企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然而,民企在引進風投之時,需要清晰地察覺這一舉措將帶來的潛在風險:圍繞企業控制權出現的斗爭以及拋售股份謀求個人利益等問題。通過分析,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總結:
(一)控制權的爭奪根本目的是為了讓企業能夠進一步發展。對于企業而言,引入風投的確可以讓企業的資金問題得到暫時緩解,而創始人則需要付出所持的部分股權,因此,控股權旁落這一危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對風險投資以及企業創始人而言,二者的控股權爭奪本質上是企業控制權的爭奪,因而二者需要秉承著對所有股東負責的理念,即便是在進行權力爭奪時,無論何者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都不該因為自身利益而讓全體股東遭受損失。
(二)控制權的爭奪伴隨創投雙方對企業利益的考慮。對于投資巨頭而言,投資于目標企業的主要目的是獲得高額投資回報,獲得控制權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獲得高額投資回報,并積極參與到監督治理企業中,對董事會和管理層都產生重大影響,以保護自身利益。因此除非另有目的,無論風投是否獲得控制權,風投股東應當將企業經營管理權交給創始人,只有創始人才是企業文化的創造者和延續者,其主要職能在于參與治理,做好監督和風險控制,保護自身利益。
(三)當風投股東爭取控制權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企業,不可避免地會和創始人股東之間產生摩擦和斗爭,這就不再是公司治理的問題,而是企業控股兼并問題。創始人如不采取合理保護措施,必然會失去企業,但是創始人進行股權爭奪也應當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而不能利用關聯方交易等方式以損害全體股東利益來維系自己利益。在雷士照明案例中,創始人吳長江和風投進行控制權爭奪過程中,為了維系自身利益,利用關聯方交易損害了公司利益進而損害了股東的利益,失去了基本的誠信義務,在此過程中,雖然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各組成部分并沒有發揮作用,所有重大關聯交易都沒有經過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沒有察覺,會計也沒有盡到監控披露的義務,產生了不可扭轉的錯誤決策。
參考文獻:
[1]蘇振華.論機構投資者介入上市公司治理[J].浙江社會科學,2002,(02).
[2]王蘭芳.創業投資與公司治理:基于董事會結構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11,(07).
[3]張慕瀕.機構投資者崛起、創業股東控制權博弈與公司治理[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3,(04).
[4]陳亦新.創始股東與私募投資者的控制權爭奪分析[D].山東:中國海洋大學,2013,(05).
[5]沙敏.雷士照明控制權之爭對創業者的啟示[J].現代企業,2015,(09).
[6]文風.社會資本視角下創始人與投資人控制權博弈——基于雷士照明控制權之爭的案例分析[J].商業會計,2014,(1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