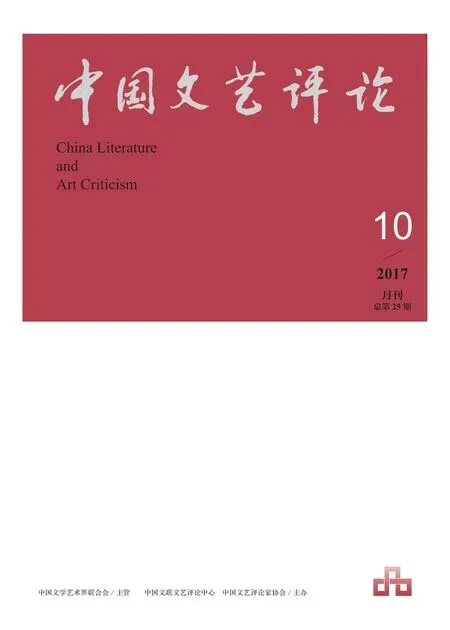變革時期中國搖滾樂的社會學重審
張慧喆
變革時期中國搖滾樂的社會學重審
張慧喆
本文嘗試從社會學角度重審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搖滾樂常常被講述和探討的“顛覆性”問題。深入分析中國搖滾的藝術形態和創作群體,會發現它深深裹挾在社會主流思潮之內,融合化生了多種社會文化元素,接納吸收了在社會變革之時被溢出結構之外的邊緣族群,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中國搖滾樂及其社會子場域的生成。中國搖滾樂作為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社會新興邊緣場域,可以說是社會結構在發展變化過程中所進行的一次自我調整,體現了社會自身容納變革的彈性,并在變革時期起到了整合社會場域、彌合社會裂痕的作用。
中國搖滾 變革時期 社會學 社會場域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曾在中國大陸音樂界、文化界以及普通聽眾中掀起巨浪狂潮,那個時代涌現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至今活躍在人們的記憶中。它最主要的特征通常被認為是反叛性、宣泄性,是隅居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異質性。實際上,以上特征僅僅是它與主流話語、外來文化、市場思路等對話過程中被摘取和高光顯示的標簽。如果將這些作品放在正發生著激烈更新的文化語境中進行深入解讀,就會發現搖滾樂同樣隱藏著對于多層面文化形態的融合借鑒;按照這一思路,若將參與搖滾樂創作的群體進行社會學的場域分析,會得出與先前關于搖滾樂的“反叛的青年亞文化”話語相異的結論——即搖滾樂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子場域,在社會基本場域發生整體性結構變革的背景下,起到了接納社會異質個體、維系社會層級斷裂、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一、中國搖滾樂的誕生場:變革時期
中國搖滾樂經歷了大致這樣一個發展歷程。它醞釀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廣州地區出現大陸第一支輕音樂隊“紫羅蘭”和位于東方賓館的全國第一個音樂茶座;破土于北京地區1980年成立的第一支樂隊形式的表演團體萬里馬王,乃及1984年中國第一批搖滾樂隊如崔健的七合板樂隊、丁武的腹蝗蟲樂隊開始進駐北京地下Party圈進行小規模的聚集性演出;爆發于1986年崔健在“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演唱《一無所有》、1990年搖滾樂隊組團登上各類大型舞臺,直至1994年魔巖三杰和唐朝樂隊舉行“中國樂勢力”紅磡演唱會;分流于1995年三里屯酒吧一條街出現,以及其后live house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城市各個角落,為搖滾樂回歸小型現場提供恰當的契機;常態于今天“中國搖滾樂”這個僵化類型軟化變形為實驗、民謠、爵士、金屬、電子、后搖等等不一而足的更加細分的音樂形態中,而那些搖滾音樂人有的化身為紅火熱鬧的音樂真人秀節目中的“幕后功臣”,將搖滾音樂元素融入各色歌手的改編演唱之中。可以說中國搖滾樂數十年的跌宕起伏全程伴隨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它誕生于劇烈的社會變革,得益于變革之時激烈碰撞的社會思潮和開放思路,同時也歸寂于市場經濟轉型之時自身的因循舊制。
任何社會子場域,包括藝術場,均受制于社會元場域即經濟政治場的基本規則,這是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關于場域理論的基本判定。在布爾迪厄看來,行動者及其在社會中的所在位置彼此勾連,就形成了“場域”,而社會中根據分工不同而包含的許許多多的子場域,如文學場、科學場等等。雖然布爾迪厄承認這些子場域在一定程度上有自身的邏輯和規律,但是它們都需要遵循整個社會成立的基本思路,才有可能參與社會運行的游戲。同理,中國搖滾樂的出現并不完全是藝術界和音樂界自身變革的美學邏輯,而是子場域的變化發展與外部的社會環境整體變革形成了契合關系,從而完成了這一藝術符號變革的合理合法性塑造。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政治經濟基本場域的變革以及文化場域的自主化趨勢構成了中國搖滾樂誕生發展的根本動力源。
1、政治經濟二元場域促使搖滾樂市場生成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之中,始終處于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當中。在這一段關乎革命的歷史中,中國社會的場域構成、思想氛圍、話語體系都相對單一。政治訴求對于文化藝術活動的制約和規范力度處于高位,在中國近現代音樂發展史上,從學堂樂歌、工農革命歌曲、外國革命歌曲、再到群眾歌曲的興起和風靡,都與當時內憂外困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這些音樂類型的進行曲式、合唱形式、莊重旋律、飽滿情緒適合于激起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熱情,因而受到創作者和接受者的青睞。
直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表明,全國的工作中心將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經濟建設。政治場域從而不再是唯一的社會基礎場域,經濟場域同樣開始在文藝活動的價值評判中起到賦值作用。因此,當市場要求多樣化的藝術作品以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文化需求,中國唱片總公司的一元壟斷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被廣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國唱片總公司廣州分公司、北京百花音響器材廠等單位的多元競爭態勢所取代,音像行業開始了市場化探索。音像市場的大片空白促使大量人力和資源開始流向此領域,內地音像公司的數量從最初的幾家在短短幾年之內激增到幾百家,同時盒帶發行大幅度增長,各種音樂類型都有了被嘗試和創新的機會,搖滾樂正是在此契機之下進入市場。當中國音樂圈還不知“搖滾”為何物之時,許多創作者在偶然接觸到這一西方流行音樂形式之初,就被吸引而開始模仿創作。正是由于搖滾樂對年輕群體的天然吸引力以及它有著較大的市場適應彈性,英國流行音樂社會學家賽門·弗瑞茲(Simon Frith)曾將搖滾樂定義為“為了擴大年輕人市場同時性消費行為所制造的音樂”。因此作為文化商品,中國改革時期經濟場域賦值權力的上升給搖滾樂提供了足夠的交易空間,由此實現了搖滾樂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大規模擴張。
2、文化場域自主性助推搖滾樂藝術實踐興起
20世紀80年代初期,與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還有文化體制改革。一些文化試點單位逐步進行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模式,實際上就是當時在美學文藝界占據主導地位的“自主性”和“向內轉”兩種話語的制度層面實踐,也就是文化場域自主性的生成。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藝術院團紛紛開始根據大眾趣味招聘演員,自主編排劇目、自主決定演出形式等,直接影響了內地音樂活動中表演形式和創作方向上的轉變。
首先在表演形式上,專業藝術團體“走穴”活動風行。“走穴”演出面向大眾,大眾趣味自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演出內容,這對流行音樂的誕生和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力,其中就包括了搖滾音樂。一些專業藝術院團的歌手演員開始自行組織樂隊,翻唱歐美搖滾曲目,如崔健、劉元等的七合板樂隊,王芳、肖楠等的眼鏡蛇樂隊;還有一些院團會帶上本不屬于院團的臨時演員參與走穴活動,如曹平曹均兄弟、何勇等都是在跟隨走穴的過程中正式開始他們的搖滾演出。正如曹平回憶,他們走穴演出時常常演唱披頭士的歌曲,“其實人們根本不管我們唱什么,就是要那個熱鬧勁兒。”可見大眾趣味對院團演出形式的制衡。
其次,在創作方向上,20世紀80年代的流行音樂在獲取更多聽眾群體、占有更大市場份額的動力驅使下,主動汲取和融合了多種音樂文化形態中的不同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創作類型有三種,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群眾抒情歌曲的延續和拓展、外來流行歌曲的扒帶翻唱以及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的現代化演繹。第一種類型如《祝酒歌》采用了新疆民歌節奏特點,《邊疆泉水清又純》從唱詠時節景致破題,轉而歌頌了軍民之情;第二種如各大音像公司蜂擁而出的翻唱合輯;而第三種則以電視劇《四世同堂》的主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為肇始,以《南腔北調大匯唱》演唱會和專輯為代表,嘗試將傳統戲曲進行交響曲化和電子音樂化的改編。這種多層社會文化互滲融合的初級形式為此后搖滾樂進行更加深入的文化互融提供了有益的嘗試。
整個社會從意識形態到場域權力的變化,是中國搖滾樂在藝術特征上滲透多層文化形態、在創作群體上融合多個社會族群的思想土壤和政策基礎。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對于真理的獨尊性和排他性的強調轉變為要求多樣化、表達自我和追求共識,為多元融合的藝術創新提供了思想上的萌芽。而搖滾音樂恰是一種融合了多元音樂風格和特點并且需要不停汲取新的音樂元素進行自我顛覆和更新的音樂種類。另一方面,社會場域的結構性調整使原先與政治場域的關系較為松動的行動者大量溢出原先所在的場域,他們必須重新尋找社會位置,由此獲得社會空間里的生存權力和身份認同。而一個新興場域能夠接納這些場域溢出者,搖滾音樂圈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社會結構的打散重組,這些接納溢出者的新興場域必然由一些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行動者構成。以上兩方面形成了中國搖滾樂從藝術形態到創作族群兩個方面對社會不同文化形態與階層的融合與滲透。
二、 多元融合的藝術特征順應社會結構重組的整體趨勢
上文提及,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內地流行音樂的創作方向是多種社會文化的多元互滲。雖然彼時這種嘗試還僅僅停留在一種文化融合的初級形態,存在著不少瑕疵——譬如它延續主導文化的同時保留了其教化意味;它吸納了港臺和西方流行歌曲的曲式結構、模仿其演出方式,致使大量翻唱出現,并沒有發展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創作個體精神氣質的原創音樂語言;還有用流行音樂技法融合傳統或者民族音樂元素的“新戲曲”模式,卻在商業鏈條的推動下淪為流水作業——但這種初步的融合嘗試為此后流行音樂進一步化生多層文化形態積淀了一定的創作平臺和聽眾基礎。而后,搖滾音樂將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民間文化相融合,在表達未來愿景的同時不忘反思過往,在訴求精神內涵的同時輔之以大眾化的表述方式,并且試圖模糊當代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的界限,創作出一種屬于當下的民間文化形式。不同文化形態的多元融合在搖滾音樂中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1、主導文化中滲透精英意識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導話語是著力唱頌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以及強調未來與希望。而這樣的情緒同樣成為搖滾音樂中一股強大的創作潮流,其情緒表達主要呈現為兩種方式。
方式之一是對紅色歌曲進行電聲改編,如1992年侯牧人出版的專輯《紅色搖滾》,崔健的歌曲《南泥灣》等。其中《紅色搖滾》里有一曲搖滾版改編的《國際歌》,后經唐朝樂隊的再版而傳唱度甚高,甚至成為中國搖滾史上的一個有關“搖滾精神”的標志性符號。而實際上,這兩個改編版本基本一致,只是以電聲樂器代管樂,將原曲的中慢板提速,而在曲式結構、和弦走向、和聲編排等方面并未做改變,尤其《紅色搖滾》版本在第三段采納了原曲的美聲與民族唱法相融合的合唱方式。因而,《國際歌》搖滾改編版本中,原曲所表達的追求全人類幸福的愿景、激發共產主義的信仰與希望等主旨得以保留,只是由于樂器音色的調整,使原曲的肅穆色調在改編版本里變成了激進昂揚。而這種色調上的調整恰恰使歌曲更加適合于改革時期的樂觀積極的時代風潮。與之相似,崔健曾引發軒然大波的改編版《南泥灣》,同樣反叛意味并不濃。雖然崔健刪去原曲結尾處的一段歌詞“又戰斗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范/咱們走向前/鮮花送模范”,消解了原曲唱頌革命英雄的初衷,但是,作為一首歌曲的部分構成,僅僅歌詞的簡單改變其實無法扭轉曲風、主題的走向。這首歌曲從配器到演唱均采用了當時非常主流的流行音樂表達,崔健的演唱所用并非現今大眾所熟悉的毫無圓潤飽滿可言的嘶啞唱腔以及偏離正常發音方式的吐字方式,而更接近于當時流行音樂常用的氣聲唱法,整首歌顯得優美隆重。因此,歷史意義的抹平實則讓這首歌回到了唱詠自然風光的變遷和生活光景的好轉這一主流話題。因此,這些改編的紅色歌曲并不是對原曲的顛覆,而是用流行音樂的技法編排對早先歌曲義涵的再次激活。
方式之二是從較遠的歷史中發掘組織民族信念的母題,這種風格由唐朝樂隊開啟,他們的《夢回唐朝》在歌詞意境上采用大量文言語詞營造古典詩意,在唱腔上吸納京劇甩腔、念白等技巧,在編曲配樂上用中國傳統音樂句法書寫吉他連復,從而設定了全曲的古典氛圍,而西方曲式在作品中的作用則是加強中國傳統藝術意境,展現出唐之盛世的大氣恢宏。后來如穴位樂隊、超載樂隊、鄭鈞,直至二手玫瑰、子曰樂隊等,都有過相似歌曲意象的創作,或者在創作中運用大量的中國古典或者民族音樂元素。這些歌曲可以說共同構成了最早的流行音樂“中國風”。
由此可見,彼時中國搖滾樂與主導文化一樣表達了對于改革新形勢和中國歷史與未來的歌頌。只不過,搖滾樂在接納主導文化為其主題內容之一的同時,并沒有讓樂觀的贊頌和理想化描繪壓倒現實生活當中不可避免的疑慮以及精英立場的文化反思,呈現出精英文化與主導文化的共融。崔健的《一塊紅布》是其中代表。這首歌中塑造了處于主導性位置的強力集體和處于從屬性位置的弱勢個體兩個形象,分別用明亮高亢的小號織體和代表了個體化意志的人聲織體表達。人聲與小號形成對比式復調,在豐厚纏綿的多線條織體中“我”和“你”之間的關系呈現得愈加親密而復雜。兩者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強權與弱勢、控制與被控,而是一種復雜的沉迷、依戀、卻時時矛盾痛苦的狀態。紅色符號、政治元素的確常常成為崔健作品中予以解構的對象,但是在解構之后,崔健通常不會遺留一片價值的廢墟,而是重新在這些渣粒中建構起一個關于理想、希望、自我實現的價值體系,實現對公眾的引導和啟蒙。同樣,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搖滾樂出現了大量述說集體性理想的作品,如臧天朔的《孩子、太陽、世界》、呼吸樂隊的《走過人間輝煌》、黑豹樂隊的《愛的光芒》等,這些歌曲針對極速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出現的被拋置于各個場域邊緣的族群出現的迷茫與焦慮,試圖給出療救的藥方,而這藥方的藥材就出自主導文化,那就是對于未來的堅定信心,只是以新的音樂形式作為藥引,并嘗試了不同以往的熬制手法,將主導文化的主題與精英文化的反思相結合。不論是從革命歷史中重新建構民族信念,還是從傳統文化中獲取身份認同,他們都落腳于一個主題,那就是與主導文化相一致的對于民族未來的愿景。
2、精英文化中采納的大眾文化模式
由于西方啟蒙思想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和知識話語最重要的理論預設,因此文學藝術創作的其中一個內在要求是用精英話語啟發大眾民智,因而當時呈現出精英與大眾的相互對立和隔絕。然而在正常情況下,許多具體的藝術文本中,會同時包含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元素,兩者之間的壁壘在極大程度上來自人為建構。而80—90年代中國搖滾樂卻由于它精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雙重屬性,從一開始就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最早開始了市場經濟下的大眾文化生產實驗。若對這一現象進行審美化解讀,就可以理解中國搖滾所包含的精英文化特征諸如主體性、批判反思性、創新性等,都是在大眾文化生產鏈中得以傳播和形成的。張楚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
張楚的作品中,歌詞是構成其藝術特色的最重要元素,但是作為音樂作品,歌詞必須由恰當的音樂語言表達與襯托,而張楚簽約魔巖文化期間出版的兩張專輯《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和《造飛機的工廠》都是個人書寫與團隊運作相合作的產物。歌詞和旋律是張楚的創作,是作品中精英意識的主要載體,而編曲部分則由賈敏恕及其團隊完成,架構起這些作品能夠被大眾接受的基本悅耳度。因此,張楚的作品就出現了口語化詩歌風格的歌詞、念白式的平淡旋律與精巧細密的編曲之間的差異化對比。比如第一張專輯中的《螞蟻螞蟻》一曲塑造了一個隨遇而安的小人物,天下之大他就是一只毫不起眼的螞蟻,空揣著幻想(想一想鄰居女兒聽聽收音機/看一看我的理想還埋在土里),感到生活總不那么盡如人意(冬天種下的是西瓜和豆粒/夏天收到的是空空的歡喜),雖然羨慕蝗蟲的大腿、蜻蜓的眼睛、蝴蝶的翅膀,但也只能接受自己生來纖細的四肢和黢黑的皮膚,含著艱辛和夢想走過生命之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了四季/五谷是花生紅棗眼淚和小米)。張楚用螞蟻為隱喻延展出他對于普羅眾生的生命通感。與他大部分歌曲特征一致,這首作品同樣是詩意滿滿但是旋律簡淡甚至隨意,而編曲團隊用雷鬼音樂的節奏音型整合起散亂的音符,使這首歌在音樂上具有了整體可聽性。可貴的是,《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這張專輯中,編曲團隊深刻了解了張楚的個人特質并且用相對個人化和詩性自由的編曲方式予以匹配,同時以簡單清透的配器讓張楚不突出的聲線從和弦中得以顯露,不爭奪張楚歌詞的優勢。如此恰當妥帖的融合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還有很多,譬如黑豹樂隊、汪峰與鮑家街43號樂隊,以及有著獨特中國文人色彩的校園民謠,顯示了文藝作品以藝術價值為導向實現商業價值的可能性。
3、民間文化的當代延續
傳統意義上的民間文化指的是由社會底層民間自發形成的、以自娛自樂為目的的文化形式。在大眾媒介鋪蓋社會行為和交往的當下,由于民間文化所賴以生存的鄉土社會的分崩離析,民間文化正呈逐漸消亡之態。然而,有學者認為,大眾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成為民間文化的當代延續,因為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并不是徹底分離的兩種文化形態,而是“斷裂與延續并存。斷裂了的是文化語境,是生產方式,是具體的文化形式,是消費方式,也是意義的再生產方式;延續著的是人類對生命力、對自由的永恒追求,其相通之處在于相同的資源,在于不同文化主體共同的精神需求,在于享用不同產品時相似的價值取向。”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認定的,不論大眾文化“采取一種多么扭曲的方式,它們會對集體的希望和幻想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在優秀的大眾文化文本中,常見到來自民間文化的給養。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搖滾樂對民族民間音樂元素的融合運用以及作品中表達出的重回鄉土社會的愿望顯示出它與民間文化的一脈相承。
這批音樂人以及他們的作品中有著顯而易見的民間音樂傳統。多位搖滾音樂人譬如何勇、劉效松、吳桐、王勇等等都來自民族音樂世家或民族器樂專業,他們也多在創作中傾向于使用民族樂器營造一種傳統意境的當代回響。何勇《鐘鼓樓》中有三弦、張楚《螞蟻螞蟻》中有笛子、崔健《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中有古箏。
雖然如此,單純的音樂元素的拼貼并不能實現這些作品深層文化含義及文本類型從大眾文化向民間文化的轉換,更重要的是音樂人是否表達出回歸鄉土社會的愿望和立場,以及作為民間民眾一員的集體訴求。同時期的西北風歌曲同樣采納了民間音樂的樂器伴奏、發聲方式、調式旋律等,甚至北京搖滾樂在誕生之初,曾因為與“西北風”歌曲有著相似的音樂元素,因被統一歸入“西北風”之中。但是,“西北風”不能被認為帶有民間文化色彩,而是一種在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由文化精英創作的富有民間藝術形式特征的大眾文化類型。“西北風”歌曲無論在音樂上還是歌詞內容上都呈現出某種矛盾性。它一方面追求鄉土色彩的配器和調性,音色蒼涼,旋律悲愴哀傷,另一方面卻同時貫穿著充滿歡樂律動的迪斯科節奏;歌詞內容上,常常直接再現以北方農民為主體的現實生活,指出生活的艱辛和貧瘠落后,看似發自民眾的聲音,而后通常轉向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和的對未來的信心與希望,以及對于民族和國家這個集體形象的依戀。因為“西北風背后的作曲家不是一個小眾,而是一群人,是一個在當時即將跨入精英主流的群體。它唱出的是這個群體在80年代這樣一個經濟、政治和文化各個領域都在多樣化轉型的時代中的思考。”與之相對,只有在承認鄉土社會、體認社會進程之焦慮感的基礎上,對于農耕音樂元素的拼貼運用才具有民間文化的實質性意義。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有大量無法進入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分工或者大眾媒體生產鏈中的群體淪為社會邊緣,其聲音被掩蓋。與西北風創作者站在廢墟之外的觀察不同,搖滾樂的創作者無法將自己從社會的廢墟中分離出來。中國搖滾的主創中可以分出三個群體,無論是體制邊緣人、游蕩者或者跨界藝術家,他們始終是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廢墟里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學藝術史教授巫鴻認為,人們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對城市廢墟進行記憶和描述,一種是“把城市作為一個美學課題——作為思考和憧憬的一個外在對象;另一種則是將自己置身其中,不斷以自身的經驗體會城市的消隕。”從20世紀90年代搖滾樂中常常表現出的不得不生長在他們并不信任的城市和相對應的文化工業當中的失意與憤然,到現如今從中國搖滾中分化出的城市民謠,這些一脈相承的音樂人對鄉土社會的憧憬依然存在,他們在音樂傳播路徑上依然依賴于類似鄉土社會中民間文化的口耳相傳。只是在作品里,這種向往很多時候不再是憤世嫉俗的咒罵、背向而行的躲避,而是變成了一種以平和之心去理解的可能性,存在于被文化改造了的城市空間。
三、多層重組的創作群體構成穩定性新興子場域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搖滾樂對于多種文化形態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于本身創作群體的多樣性。借用布爾迪厄的習性和場域概念,可以按照他們經由體制培養、家庭環境、教育背景的不同而在社會場域當中所處的不同位置,將其分為三個群體。這三個群體在社會結構發生整體變革的背景下,從原先的社會位置脫離,重組成為了一個新興的搖滾音樂場域。
第一個群體是體制的邊緣者。他們大多是專業藝術團體的從業者或者從業者的子女。得益于家庭和工作環境,這一群體在大陸范圍內最早接觸到西方流行音樂和搖滾樂,因而成為中國搖滾最早的生產者,并構成了早期中國搖滾最重要的版圖。如崔健和劉元曾在北京交響樂團分別擔任小號手和薩克斯手,臧天朔曾在北京歌舞團擔任鍵盤手,劉效松和張永光都曾是北京京劇院的打擊樂手,竇唯也曾考取石景山青年輕音樂團的歌唱演員,而何勇、高旗、常寬、吳珂、虞進、汪峰等音樂人均出生于樂團家庭。改革開放初期,體制方面的改弦更張裹挾著這些游走于體制邊緣的音樂人進入了市場浪潮,演員們在走穴演出的過程中逐漸對文化市場和大眾需求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可以說在文化體制改革開始之初的幾年時間內,體制內的藝術團體與游走在團體邊緣的族群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限,他們互為輔助、彼此認同。前者認可后者的對西方流行音樂的學習、對表演形式的突破,后者也得益于前者的舞臺、器材以及學習材料上的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來自于體制的庇護。正如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的許可讓崔健得以在1986年的“百名歌星演唱會”上演唱《一無所有》,李谷一的默許維持了眼鏡蛇樂隊的創作與演出,王健則為張楚的創作公開背書。只是后來這個過程及其影響被忽略了,從而造成了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搖滾的片面理解。
其次是“城市的游蕩者”。他們多是一些自由音樂人,也就是北京本地浸淫在搖滾圈的無業、無學或者半失業社會青年以及懷揣音樂夢想來到北京的外地音樂人。他們的家庭、教育和政治背景并沒有提供給他們較多的文化資本或者政治資本,因而得益于彼時變動的社會結構,經濟場域的上升、城市化的影響,通過后天的習得技藝以及在城市游蕩間獲得的市場敏感度,從而在場域中獲得位置并施加影響。譬如高考失利的唐朝樂隊吉他手劉義軍,在每天長達十數小時的嚴苛練琴過程中,摸索出用電音吉他模擬琵琶、古箏等中國傳統樂器句法特征的演繹方式;而黑豹樂隊和指南針樂隊兩支流行搖滾樂隊的市場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各自的樂隊經紀人郭傳林和王曉京以及他們對市場動向的把握。
此外還有“跨界的藝術家”。指的是原先擁有一定的社會場域位置,而后跨界進入搖滾音樂圈的音樂人。首先包括一批在校期間投身音樂領域的高校學生,如徐曉峰、陳戈、沈黎暉、宋柯、高曉松、洛兵等,他們都曾嘗試音樂創作,有的后來開始拓展搖滾樂的市場、完善產業鏈條,創建并發展了如草莓音樂節、麥田音像、阿里音樂等產業品牌。其次還有一些在專業音樂院校學習期間組織搖滾樂隊、進行演出甚至出版專輯的學生,他們的專業多是古典音樂或者民樂演奏,可以稱之為搖滾樂界的“學院派”,如汪峰與鮑家街43號樂隊、輪回樂隊等。憑借較強的專業音樂素養,“學院派”樂隊擴展了當時中國搖滾比較單一且類型化的音樂表達模式。如專輯《鮑家街43號》中將經典搖滾三大件的配器方式與爵士、藍調、節奏布魯斯音樂形式完美融合,使他們在北京搖滾音樂圈中初次登場就驚艷四座。第三是一些跨界藝術家,包括陳底里和穴位樂隊、最早入住北京東村的左小祖咒等。他們在搖滾樂領域的實踐通常與其他藝術種類的實踐同步進行,使搖滾樂的音樂表達方式更加多元。
以上中國搖滾樂的三個創作群體,由于成長環境、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的差異,因而在社會場域中處于不同的位置,有著不同的音樂創作理念和風格,體現著行動者所在的社會階層所給予的長時間的生活經歷和所接觸的生存狀態在他們身上所積累下的習性。他們選擇融合在一個完全外來的、陌生的音樂大類——搖滾樂中,致力于創造一種不同于原有在政治場域支配下的主流文化藝術場域中的編碼原則,從而構成了一個新生的社會子場域。
社會學者于長江在考察圓明園藝術群落時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80年代末開始,由于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思想潮流的變更,北京等大都市已經自然而然地在向多樣 化(diversi fication)、多 元 化(pluralism)發展,呈現為一種都市性(Urbanism)和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社會,原有的處于人們視線之外的非主流群體開始浮現、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正如上文的分析,北京搖滾樂這個新出現的邊緣場域中,實際上容納了多種不同的非主流人群,有在體制變更之時被“溢出”體制之外的邊緣族群、始終以個體為單位脫離體制庇護直接面對整個社會的游蕩者、也有分散在大學校園這個相對獨立而獨特的環境中的非主流青年。雖然這些群體在基本的社會條件上彼此相異,但是在一個新出現的邊緣領域中,他們找到了身份認同,原先分散性的個體被容納進一個社會場域中,由此進入了社會結構。他們所保有和傳遞的依然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或其變體,從而形成新的社會粘合劑,避免分裂和不穩定因素。這是社會結構自身所有的容納變革的彈性。這恰恰說明20世紀80年代文化藝術界看似發起了一場激進的顛覆,卻最終被社會順利消化甚至維持了社會平衡的原因。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場域系統所發生的急劇的整體性變革并不是自下而上從新興場域或者亞文化行動者發起的,而是原本屬于絕對支配性場域的政治場域自上而下自反地進行。它賦予經濟場域以權力并使之成為可以與自己相較的基礎場域。其他場域如文化場域、藝術場域、學術場域不再需要唯一而嚴格地遵循政治場域的規則,經濟場域開始在其中起到賦值作用,規則開始松動。在巨大的場域系統變革之下,來自于創建搖滾樂子場域的顛覆性被場域系統的整體性變革消解了。搖滾樂這個由不同的非主流群體、分散的個體融合而成的新興邊緣場域在社會激變中、在一個社會由同質性社會轉向分散性社會的過程中,起到了類似于社會中間階層的“安全閥”作用。中國搖滾樂的發生發展及其所體現出的藝術界變革與社會容納機制之間的關系,能夠給如今再一次走向變革的中國社會以持續的啟示,值得深入的追蹤和探討。
張慧喆: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講師
(責編: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