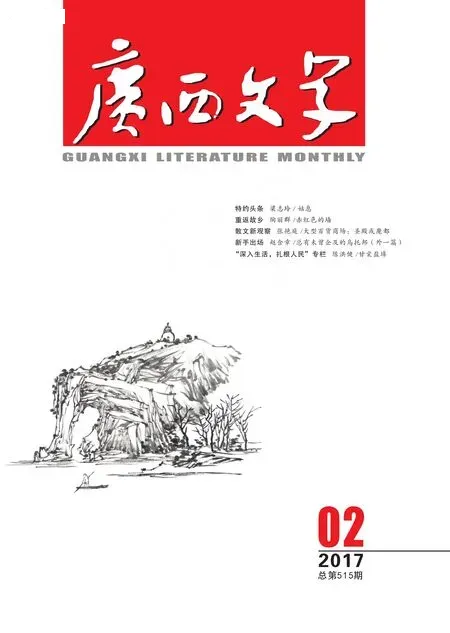劉月潮小小說(shuō)二題
劉月潮/著
耳朵跑了
夏天,不,整個(gè)夏天,我竟聽不到一丁點(diǎn)聲音。耳朵忽然逃離我的身體。之前耳朵跟我提過(guò)多次,它不想再聽人的說(shuō)話聲,我周圍的人沒一句真話。我老把耳朵的話當(dāng)耳邊風(fēng),當(dāng)成玩笑話,假話鬼話耳朵都得聽,這是耳朵的本分。真沒想到耳朵突然跟我翻臉,玩失蹤了。
耳朵扔下我跑了。失去聽力,聽不見人說(shuō)話聲,但我能想得到,周圍的人仍天天在醉心地說(shuō)著假話鬼話。對(duì)這些謊言鬼話,耳朵早聽厭了生煩了,我卻沒生一點(diǎn)厭煩之心,反而天天跟著一塊說(shuō)。
丟了耳朵,我的世界忽然安靜了。我知道耳朵再也不會(huì)回來(lái),它早聽不慣人的那套假話、鬼話,也討厭它的主人——我這個(gè)滿嘴說(shuō)著假話、鬼話的人。在說(shuō)這些假話鬼話時(shí)我也有過(guò)不情愿,可我能說(shuō)真話嗎?這世上人人說(shuō)慣假話、鬼話,早已聽不得真話。我怎么也做不了安徒生童話里說(shuō)皇帝光著身子的孩子,那個(gè)孩子來(lái)到人世間后還是一張白紙,如果白紙涂滿字后就不會(huì)說(shuō)出揭穿謊言的真話。
耳朵不懂人世間道理,我要跟大家打成一片,還要活得像樣點(diǎn),不跟著大家一道說(shuō)假話、鬼話就會(huì)真的變成大家眼中的活鬼。
耳朵害慘了我,我只看見人嘴巴一張一合,卻聽不見他們到底在說(shuō)啥。
我的嘴巴在很多場(chǎng)合不敢出一點(diǎn)聲音,害怕說(shuō)錯(cuò)話,生怕我的話不對(duì)別人的路子。我只好時(shí)不時(shí)地點(diǎn)頭裝裝樣子。
后來(lái)在單位弄砸了好幾件事,我再也裝不下去,索性跟大家挑明我是個(gè)聾子,啥也聽不到。還拿出醫(yī)院診斷書,診斷我得了嚴(yán)重的焦慮癥、強(qiáng)迫癥、臆想癥,還有要命的耳鳴,它們一齊合謀奪走我的聽力。在醫(yī)院,我不斷向醫(yī)生強(qiáng)調(diào)我耳朵跑了,醫(yī)生說(shuō)這就是典型的臆想癥。
周圍的人都曉得我喪失聽力,成了聾子。從一個(gè)有聲世界跌進(jìn)無(wú)聲天地,再也沒人主動(dòng)同我說(shuō)話,我連跟人說(shuō)假話、鬼話也不可能了,我成了被遺忘的人,成了局外人。
我忽然安靜下來(lái),喜歡成天窩在家里。妻子梅艷得知我成了聾子,目光虛虛地望了我一眼,又飛快地跳開。我和梅艷結(jié)婚許多年,還沒有孩子,到底誰(shuí)的原因一直沒弄清。兩人平日各忙各的,越過(guò)越生分,有時(shí)晚上回到同一屋檐下已是深更半夜。
我們都像客人似的,把回家當(dāng)成走親戚一般。閑了下來(lái),我才感到自己真正回家。每間房墻角都結(jié)了蜘蛛網(wǎng),網(wǎng)了一些叫不出名的蟲子。我就像是網(wǎng)上一只垂死掙扎過(guò)的蟲子。
開始打掃屋子,我用掃把清掃蛛網(wǎng)時(shí),大大小小的蜘蛛四處逃散,它們很快又會(huì)在某個(gè)角落結(jié)網(wǎng)。這么多年我也被網(wǎng)住了,沒有掙脫過(guò)生活的束縛。
梅艷回到家后,眼睛一亮,瞬間又暗下來(lái)。我心頭也暗下來(lái),這個(gè)家還是原來(lái)的家,但我和梅艷再也回不到從前的好日子。
對(duì)著墻角又結(jié)起的蛛網(wǎng),我一天天胡思亂想著。成了聾子,我遠(yuǎn)離生活軌道,大家都還在滿嘴謊言,假話鬼話連篇,我在一旁連聽的資格也沒了。我心中不免有些失落,說(shuō)了這么多年鬼話,好像早已上癮,歇下來(lái)后我只好跟自己說(shuō),假扮跟不同的人說(shuō)。我好像還能同大家一樣,活在一個(gè)滿嘴謊言、鬼話連篇的世界。
夏天快過(guò)去了,我突然聽見知了的叫聲。我嚇了一跳,以為出現(xiàn)幻覺。我還聽見汽車?yán)嚷暋⑷说恼f(shuō)話聲……天啊,我怎么忽然恢復(fù)了聽力,聽見這個(gè)世界的聲音……
我的耳朵悄悄地回來(lái)了。耳朵跟我說(shuō)離開我其實(shí)也很后悔,它在外面浪蕩了很久,就是沒遇見一個(gè)說(shuō)真話的人,它對(duì)人算是徹底失望,所有人都一個(gè)屌樣,它又能投奔誰(shuí)呢?它想盡快結(jié)束這種流浪的日子,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到我身上,做回我的耳朵。
秋天了,我的痛苦在一天天加深,不敢跟任何人講我突然恢復(fù)聽力的事,沒準(zhǔn)大家以為我之前是故意的。我就索性裝聾作啞,裝聾作啞也有它的許多好處。
所有人都以為我還是個(gè)聾子,說(shuō)話也從不避著我,我曉得了許多人的秘密。包括妻子梅艷。梅艷跟人通話再也不避我,時(shí)常在電話里跟男人調(diào)情,還跟一個(gè)叫昊的男人定期私會(huì)。有好幾次,我差點(diǎn)上前掀翻梅艷,想狠狠揍她一頓。最后關(guān)頭我還是強(qiáng)忍住,如果恢復(fù)聽力的事一旦露了馬腳,我就會(huì)變成大家的公敵。
除了人人滿嘴鬼話、假話的世界,還有一個(gè)被大家一心刻意隱藏起來(lái)的世界,這個(gè)隱蔽的世界就像地心深處黑暗的王國(guó),我一次次偷偷摸摸闖進(jìn)這個(gè)可怕的暗藏的世界。楊娜跟張平時(shí)常暗中勾搭在一塊,背后鼓搗些小動(dòng)作。局長(zhǎng)沈陽(yáng)跟副局長(zhǎng)孫少立表面客氣,暗中較勁互相提防,孫少立甚至幾次設(shè)下陷阱想扳倒沈陽(yáng),沈陽(yáng)時(shí)時(shí)小心提防才一次次躲過(guò)去。沈陽(yáng)、孫少立都背地里受賄,送錢的都是經(jīng)過(guò)他們多年考驗(yàn)的老板,一條繩上的螞蚱。主任王偉叫情人買內(nèi)衣,發(fā)票卻開成單位辦公用品。陳誠(chéng)負(fù)責(zé)局里做標(biāo)語(yǔ)這塊,他總是要吃一倍回扣……
大家眼皮底下看得到的是一個(gè)世界,還有另一個(gè)看不到的世界。這兩個(gè)世界一個(gè)比一個(gè)可怕,我卻像上了癮,在這兩個(gè)世界來(lái)來(lái)回回穿梭。 耳朵也幾次提醒我,這樣下去只怕我再也回不了頭。
我真的回不了頭。雖然我早恢復(fù)了聽力,但他們把我當(dāng)成聾子,眼中好像根本沒有我這個(gè)人似的,有時(shí)就當(dāng)著我的面說(shuō)那些見不得人的壞事。
我發(fā)現(xiàn)這么多人的丑事,這個(gè)潛藏著無(wú)數(shù)秘密的世界讓我太害怕,卻又讓我像一個(gè)躲在暗中窺探的人,內(nèi)心又一天比一天興奮。再這么裝聾作啞下去,我覺得自己有一天真的會(huì)瘋掉。
局里開年終總結(jié)表彰會(huì),特地請(qǐng)來(lái)分管的王副市長(zhǎng)。局長(zhǎng)一口一個(gè)尊敬的王副市長(zhǎng),二十多分鐘講話,局長(zhǎng)就恭敬地說(shuō)了二十多遍。我實(shí)在忍俊不禁,在臺(tái)下忽然笑出了聲。也許我憋得太久了,不想再裝聾作啞。果然所有人的目光都齊聚在我身上。我厭倦了被人無(wú)視的日子,索性站起身來(lái)說(shuō)個(gè)痛快:局長(zhǎng)這么尊敬王副市長(zhǎng),可幾天前你還在電話里跟人說(shuō),都是王禿子攪渾了水,從中渾水摸魚……
王副市長(zhǎng)禿頂,老百姓都喊他王禿子。我的話一下子驚翻了會(huì)場(chǎng),誰(shuí)也沒想到我扔出這么一顆炸彈。
還是局長(zhǎng)沈陽(yáng)反應(yīng)快,他連忙大吼一聲,說(shuō)李守誠(chéng)是個(gè)聾子,他得了強(qiáng)迫癥、臆想癥,就是個(gè)精神病患者……快,快把他控制起來(lái),送精神病院。
旁邊的人一擁而上,扭住我。我拼命地掙扎,喊叫:我耳朵回來(lái)了,早恢復(fù)了聽力,王副市長(zhǎng),我說(shuō)的可是真話……
看來(lái)真是個(gè)精神病患者,趕快送精神病院,好好治療。不過(guò),我要批評(píng)你們,對(duì)職工關(guān)心不夠……王副市長(zhǎng)發(fā)話了。
我被送到精神病院,成了一位精神病患者,我看見墻角結(jié)著蛛網(wǎng),蛛網(wǎng)都蒙著灰塵。我又被網(wǎng)住了。在精神病院里,我又發(fā)現(xiàn)了第三個(gè)世界:這些精神病患者在一遍遍地說(shuō)著真話,在說(shuō)著自己心底的話。耳朵說(shuō),他們是世上最有勇氣說(shuō)真話的人。
過(guò)馬路
章正光是在路邊忽然跟王世達(dá)分手的。
兩人說(shuō)笑著從賓館出來(lái),肩碰肩穿過(guò)一條林蔭道,秋風(fēng)一陣陣刮過(guò),密匝匝的樹葉在頭頂上不安分地抖動(dòng)。
林蔭道走到頭就是車來(lái)車往的大馬路,穿過(guò)馬路再往前走十幾米遠(yuǎn)就到了他們培訓(xùn)的會(huì)議室。
過(guò)馬路時(shí),章正光左右望了一眼,看見十幾米外馬路上才橫著斑馬線,忙轉(zhuǎn)身走過(guò)去,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世達(dá)有沒有跟上來(lái)。世達(dá)正要橫穿馬路,停在路邊,側(cè)著身子,背對(duì)他,在等身后走過(guò)來(lái)的一群培訓(xùn)班女學(xué)員。都是一個(gè)系統(tǒng)的,這群女學(xué)員里有不少他倆的熟人。還有他一直暗地里喜歡的楊瑩瑩。他跟楊瑩瑩開過(guò)幾次會(huì),參加過(guò)幾回培訓(xùn),楊瑩瑩對(duì)他不冷也不熱。
章正光咧嘴笑了笑,他一向遵守交規(guī),從不亂穿馬路,拿生命開玩笑。有回他跟幾個(gè)同事出差,大半夜出來(lái)找吃的,看見馬路對(duì)面有家粉店沒有打烊,幾個(gè)同事互相看了一眼,一下子躥過(guò)馬路。章正光卻去找有斑馬線的路口,硬是繞了一個(gè)大彎才過(guò)到馬路對(duì)面。同事們一碗粉早下了肚,都笑正光是個(gè)五好市民。
章正光踩上斑馬線時(shí),王世達(dá)也正領(lǐng)著這群女人直穿馬路。王世達(dá)一個(gè)勁地同身邊的楊瑩瑩有說(shuō)有笑,中間還有意無(wú)意瞟了他一眼。
章正光剛走過(guò)斑馬線中間,一輛小車為避讓馬路中間王世達(dá)那群人,來(lái)不及剎車,竟斜著朝他沖來(lái)。小車車速極快,章正光還算反應(yīng)快,也還是連滾帶爬地撞上人行道。撿了條小命。小車擦著他腳跟駛過(guò)去。
章正光驚出一身汗,傻呆呆赤著一只腳站在人行道上,大口地喘著氣。他抬起手摸著腦袋,腦袋還好好的,摸摸自己的臉,又狠狠地?cái)Q著腮幫子,疼痛使他確信自己還好手好腳地活著。
小車急剎住了,司機(jī)探出頭,見沒傷著人,就一聲不吭地開車一溜煙地跑了。
王世達(dá)打頭跑過(guò)來(lái),一只被車輪碾壓得變形的鞋子,被王世達(dá)拎在手上。那只走樣的鞋子就成了王世達(dá)的戰(zhàn)利品。王世達(dá)把鞋子摜在地上,拍了拍他肩膀說(shuō),正光,以后可不能一個(gè)人冒冒失失過(guò)馬路,有大部隊(duì)要跟著大部隊(duì),跟著大部隊(duì)走才是安穩(wěn)的。
王世達(dá)說(shuō)完回到女人中間,大家都笑哈哈地瞅著他,說(shuō)只要人沒事,犧牲一只鞋子算不了什么。楊瑩瑩也笑嘻嘻地望著他,那嘴角微微向上好看地翹著,滲出一絲嘲諷,說(shuō)這只鞋子可是正光的貴人,正光一準(zhǔn)做了虧心事,鞋子在替你受過(guò)。
大家都很開心地笑起來(lái),扔下正光一起簇?fù)碚f(shuō)笑著走向教學(xué)樓。
只剩下他站在人行道上,章正光覺得自己成了頭案板上被宰殺后褪光了毛的死豬,難堪、羞辱、懊悔……他這頭死豬又被人開膛破肚,掏光了內(nèi)臟。
穿上那只變形的鞋子,章正光右腳像套上了腳鐐,高一腳低一腳地走進(jìn)教室。學(xué)員們的目光頓時(shí)齊齊地粘在他身上,他怎么也甩不掉,活像一個(gè)罪犯,不安生地坐在審判席上等著大家審判。
那個(gè)上午章正光的心根本不在課堂上,培訓(xùn)老師講什么,他一句也沒聽進(jìn)去。大家也都不怎么專心,都時(shí)不時(shí)地瞟他一眼,都來(lái)瞧他的稀罕,好像他是個(gè)活死人,活該被車子輾死,卻沒死成,像個(gè)活鬼還活在人世上。章正光心里委屈死了,難道他守規(guī)矩多繞些路去走斑馬線就成了跟大家不一樣的人?還有那個(gè)他喜歡的楊瑩瑩,也一直用怪怪的眼光瞧他。
下課時(shí),章正光第一個(gè)出了教室,把同學(xué)們甩在后頭。那只變形的鞋子一點(diǎn)兒不合腳,拖著他的雙腿,讓他抬不起腳。下樓時(shí)他索性脫下鞋子,重重地拎在手上,下到一樓大廳再穿上鞋子。
來(lái)到馬路邊,他喘了口氣,心虛地望了一眼右邊十幾米遠(yuǎn)的斑馬線,過(guò)馬路走斑馬線遵守了多年,如今卻要拋棄它。章正光遲疑了一下,還是抬起腿,右腳落到馬路上像觸電似的又縮回頭,他穩(wěn)了穩(wěn)身子,左腳慢慢地落在馬路上,他心里才踏實(shí)些。他活像一只鴨子沒入車流里。馬路頭一回讓他無(wú)比生疏。
從后面過(guò)來(lái)的同學(xué)見到令人好笑的一幕:馬路上車多人多,正是下班高峰期,章正光笨拙地驚慌地躲閃著各種車輛,像個(gè)才學(xué)會(huì)走路的孩童。
大家都齊刷刷地站在路邊,看著章正光慌亂地過(guò)馬路。
大家都覺得有趣,這章正光一離開斑馬線,都不懂得怎樣過(guò)馬路了。
就在大家替他松了口氣,章正光挪到馬路邊上時(shí),還是被一輛疾馳而來(lái)的電動(dòng)車撞倒在地。
撞人了。馬路上車輛頓時(shí)亂成一團(tuán),馬路邊的同學(xué)頓時(shí)像一尾尾魚游向章正光。
章正光被同學(xué)們抬上急救車。臨上車時(shí),章正光忽然清醒過(guò)來(lái),竟惦記著那只變形的鞋子,他讓王世達(dá)找來(lái)鞋子,放進(jìn)急救車?yán)铩?/p>
章正光右腿腓骨骨折。住院期間,同學(xué)們相約著去看望他好幾回。痊愈出院后,全班同學(xué)特地為他舉行了一場(chǎng)聚會(huì),大家觥籌交錯(cuò),慶祝他新生,他重新回到大家中間。楊瑩瑩還滿臉?gòu)尚叩貫樗艘皇赘琛?/p>
過(guò)馬路時(shí),章正光再也不走斑馬線,而是直穿馬路,他很快跟大家一樣,像水底的魚自在地穿行在車流里。那只變形的鞋子一直被章正光藏在鞋柜里,它就像把快刀,把他的人生切成兩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