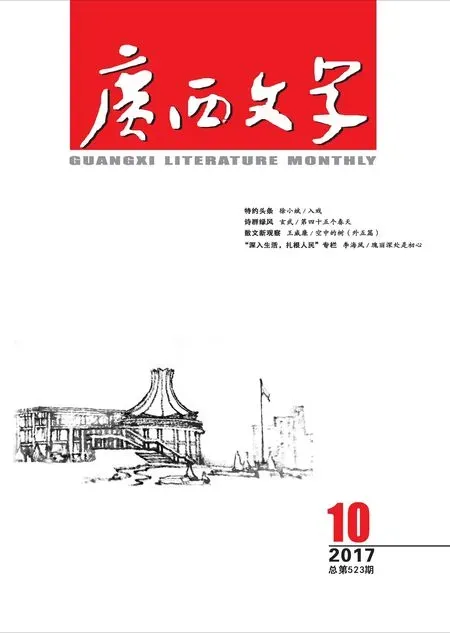空中的樹 (外五篇)
王威廉/著
空中的樹
鄰居的陽臺上有一棵樹,恰好在我書房窗外的視野里,因此我便天天看著這棵樹生活。發呆與冥想,憤怒與平靜,這棵樹都陪著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能看到這棵樹,取決于這座樓房的格局。我住的是小戶型,鄰居是大戶型,因而他們房子的陽臺也像是艦船的尖頭一般,向前迎去,迎住了暗潮洶涌的空無。那陽臺在我的窗外的左側,并不擋住我的光,但我的正前方擺放著電腦,我以正面姿勢看到的是液晶屏幕,一個電子世界的入口。我們已經把大量的時間消耗在那個屏幕里,我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關機或停電的時候,我們發現那只是一面黑色的、幾乎沒有反光的鏡子。我們自以為抵達了另一個世界,但我們的目光只是觸碰在這樣的冷冰冰的表面上,我們的眼睛不會撒謊,因此,我們的眼睛會感到異常的疲憊。疲憊的時候,我只能不看屏幕,在墻壁和屏幕之間的空隙,我望出去,望到的就是那棵樹。
那棵樹像是一面破碎的旗幟,每一片葉子在風中瑟瑟發抖,仿佛在不斷堅持,有時,無風的時候,它的葉片紋絲不動,仿佛已經死去。
無論如何,那是一棵空中的樹,我看不見它的樹根,只看見它在陽臺的護欄上探出來的部分,在那部分的后邊,什么也沒有,只有無窮盡的白光。看著它,總讓我有種如臨深淵的感覺。看得久了,我時常覺得我變成了它,正如我學會了法術,可以變成一棵空中的樹,然后望著遠方的薄霧。我很想把自己的枝葉伸展到薄霧的上邊,每一片葉子都是我的眼睛,因而我可以看清薄霧上方的空無。
鄰居家養狗,是一只淡黃色的拉布拉多犬,看上去已經很老了,不只是因為體型龐大,更因為它很少亂叫,只是站在樹下,安靜地望著陽臺外的空無。它學會了植物的方式。據說,狗看到的世界,沒有顏色,是黑白的,像是那種很古老的黑白電視機。我小的時候,只有那樣的電視機,但那時的新奇感不亞于現在使用觸屏手機。現在,看完一部黑白的藝術電影,都感到夠嗆,那種黑白竟然那么不自然,讓人疲憊,耗費了大量的想象力去補充畫面。但狗的世界,永遠都是黑白色的。世界一定就是彩色的嗎?看來也未必就是真理。那么,狗看到的空無和人類看到的空無,是否一樣呢?狗能感覺到樹的空無嗎?
不管狗有多大的智慧,狗的出現,的確讓這棵空中的樹變得不再那么寂寞。這是真的。因為我時常變成那棵樹,所以我能感到樹的內心,樹因為狗的存在而稍感放松。
除了狗,還有它的同類:小區里長著許多高大蔥郁的樹,但這棵空中的樹凌駕在自己的同類之上,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嗎?它俯視自己的同類,會感到孤獨嗎?我變成那棵樹的時候,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氣,因為那并不是一棵樹應該待的位置,于是便要付出更多,才能與世界達成平衡。
這棵樹對我而言,愈加重要。它像是一名雖敗猶榮的戰士,守在空無的前線。假如沒有這棵樹,我的視線只能完全與空無相接,那與現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樹的枝干、細碎的樹葉,把空無切割成不同的形狀,我想那就是美。所謂美,便是對空無的巧妙遮蔽。但美的極致,又是一定要通向空無的深淵的。美,是空無的一種卓越的形式。
我們都有凝滯的時刻。凝滯的時刻有空中的樹來陪伴,是一種幸運。我經常相信,我的凝滯,只有這棵空中的樹才能明白。因為,我難道不是一個生活在空中的人嗎?我的雙腳踩的是樓板,樓板的下面住的是別的什么人,我的雙腳踩的并不是真正的大地,只是一大塊懸空的樓板。我的雙腳和樹的根須一樣,被圍困了。圍困樹的是一個巨大的花盆,圍困雙腳的,是看不見說不清的事物。因而,這種圍困就像我望向樹的目光,我的目光里隱含著探詢與疑惑嗎?
這是一棵空中的樹,一棵和我在空無中共生的樹。
丟失的身份
恐怕沒有幾個人意識到,與身份證匹配次數最多的一個詞語竟然是“丟失”。每次在使用身份證過后,總有好心人提醒你:拿好你的身份證啊,小心別丟了。而丟失身份證的故事更是時常縈繞耳邊。某某朋友把身份證丟啦,你打電話過去安慰,朋友的憤激訴說讓你覺得他已經掉進了悲慘世界。你的安慰反而在激發著他的憤激,他說:我寧愿再多丟幾百塊錢也不愿意丟掉身份證!這么一場對話在你的心里就會種下恐怖的種子:
丟什么都好,就是不要丟掉身份證!
我有段時間就把身份證放在錢包里,和一些亂七八糟的卡放在一起,我為了生活的方便,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時候就需要身份證了,沒有身份證,你將無法向別人說明你是誰。你所說的話沒有身份證的確認只是小丑的謊言。你說得越多,辯解得越急切,身份證的意義就越突出,這個時候,身份證簡直如同救世主一般了。我把身份證放在錢包里,就是想在這種突然出現的情況下能夠獲得有力的突圍。但是熱情的朋友是不會答應我這么做的,“因為這樣太容易丟失了!你怎么能把身份證和公車卡、打折卡什么的放在一起呢?”我有些支吾了,我說:“都是一樣大小的卡片,放在一起好保管。”這樣的回答只會讓朋友更加生氣,“這怎么能一樣呢?!”
都是一樣的卡片,卻也是等級化的管制呢。不得已,我只好把身份證放在抽屜里,還上了鎖,以防某只突然出現的老鼠叼走了它。
不過事情變得更加復雜。身份證是安全了,可我的心卻懸了起來,我預感到那種難以辯解的困境遲早就會與我遭遇。果然有一次,我和幾位朋友正好路過一家博物館,便想進去看看,但是人家問我們要身份證,他們說:“現在博物館雖然免費了,但是卻一定需要參觀者出示身份證。”我和另一個沒帶身份證的朋友便被阻隔在了外邊,這時我懊悔了起來,一個封存起來的身份證和丟失了的身份證似乎沒什么區別。但我沒有放棄對面前困境的反抗,我開始和博物館門口的工作人員聊天,希望用花言巧語來軟化他們的清規戒律。他們的態度有所軟化,但是身體的姿勢卻依然牢固,我突然想起錢包里其他的卡片,便掏出自己的名片遞了過去。對方拿著我的名片端詳了好久,突然笑了起來,笑得很復雜,難以揣測,笑完后他竟然放我們進去了,不過他要求我們交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因為不是很貴,我們便也妥協了,順利地克服了身份證缺席的困境。
這件事情的教訓是深刻的。即使有時候沒有身份證也能辦成一些事情,但是你必須付出額外的代價。一個人的一生假如有了太多額外的代價,那便成了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生活將變成生鐵的枷鎖,讓你主動伸出脖子,并自己戴好它。這是一個無底的陷阱。
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仔細端詳著身份證,這個小卡片并不比其他的卡片更漂亮,相反,那種凸面鏡下照出的人臉有著古怪的神情,仿佛是在劫難逃的囚犯。這也的確詮釋了身份證的固有含義。
我的身份證至今未曾丟失,我為此慶幸不已也為此小心翼翼,我覺得最好的辦法便是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奇數的日子帶著身份證,而偶數的日子鎖好身份證,這樣便能把風險降低到原來的二分之一。若是這樣都不能避免一些困境,那么這就是無法回避的命運了,必須像個有尊嚴的人那樣去面對它。當然,如果發揮我們的想象力,我們可以預計在不久的未來,身份證肯定會死亡,但它的幽靈會永生,它會變成電子芯片之類的東西,在你剛剛來到這個世界的瞬間就已經植入了你的身體內部。
這樣一來,身份證便永遠和“丟失”脫離了關系,但不得不實話實說:沒有比那更恐怖的事情了。
診斷眩暈
早上起來突然感到頭有點眩暈,那種感覺很奇妙。身體明明是穩穩當當的,但是眼前的景物似乎在晃動,這樣的情況我以前倒是經歷過一次,不過那次是地震,是世界真的在震動。但是這次,瞬間過后,我發現世界安若磐石,一動不動,動的只是我的意識。就這么起床,然后總覺得頭昏沉沉的,似乎沒睡夠,但掐指一算,整整八個小時,絕對睡眠充足。
記得書上提過,眩暈和頭昏是兩種感受,但是大部分都混為一談。我曾經也是混為一談的,但是我在一天的時間內都完全搞清楚了,的確很不一樣,但有時又覺得似乎還是有相通之處的。畢竟,都是對正常意識的攪亂。
生病對于除卻腦袋的其余肢體來說,很簡單,可以認為就是肉身的毛病。但是大腦的問題就復雜很多,身體與意識混雜在了一起,難分難解,是物質的毛病更多一些還是意識的問題更大一些,那絕對不是能夠輕易分辨出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才是一個既唯物又唯心的混合體。
服了藥,躺下,閉上眼睛,自我的黑暗內部在旋轉;睜開眼睛,人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整個世界圍繞著這個點在旋轉。受不了了,爬起身來,靠著墻壁緩緩走動,整個世界都在一個大轉盤上,一切固定的事物都煙消云散了,就仿佛直觀體驗到了地球的自轉。
突然間想到,沒有比頭暈更令人絕望的身體癥狀了。暈不像疼痛,有一個尖銳的對立面時刻提醒著一種關注,暈是緩慢的,難以覺察的,待你感到不適的時候,你已經率先成為某種情緒的俘虜。你會以為你的不適并非來自身體,而是來自一種難以捉摸的心情。你需要自我審視,去找出問題所在,甚至,像是在教堂的懺悔,久遠以前的過錯都需要重新被檢索一番。這是慢性的折磨,不會在遭遇之際就挫敗你的勇氣,它是魔鬼的低語,先扮演出一副勸人多多休息的偽善,你以為會有勞作后的愉悅等待著你,但是后來你會發現,只有一種混沌和不辨方向的狀態像是福爾馬林溶液一樣的浸泡你。絕望就此真正誕生,一絲一縷,從世界和心靈的深處升起,而后又把根須悄悄隱藏起來。找不到根源,病灶就無法治愈,在眩暈與昏沉的交替中,你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厭世者。
孩子的喚醒
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和這個陌生的小男孩待在這里。我們不說話,甚至很少去看對方,周圍是下午四點鐘的陽光和空無一人的寂靜。這里是某個居民區的“秘密花園”,一些石桌石椅和鍛煉器材安靜地蹲在這里,像是已經在土地下面生根發芽。在不久的剛才我走進這里,像是個入侵者,打破了某種固有的和諧,為了讓波動慢慢沉淀下來,我盡量讓自己變得安靜。
我坐在石椅上,看著小男孩在破舊的秋千上蕩來蕩去。他的身影一會兒進入了從樹葉縫隙中透露出的光斑,一會兒又讓光斑在地面上完全呈現出來,像是一個變幻莫測的魔術師,讓人感到有一點點眩暈。他的雙手緊緊抱住秋千右側的繩索,而小小的頭就埋在雙臂的中間。我看不見他的小臉,他的臉一直面向著腳下此起彼伏的地面,像是成年人在發呆或是思考的樣子。但我覺得他肯定不會在發呆,更不會在思考,他只是在觀看,享受著看的幸福。他不會感到乏味。乏味,這是一個成年人世界的詞語,它沒有具體對應的事物,只是出自一種精神的錯覺。毫無疑問,人類的詞語世界要大于人類的生存世界,那些多余的詞語泡沫并不是飄浮在渺渺高空,而是沉淀下來,構造了新的元素。它們自我指涉,自我繁衍,到最后我們不知身在鏡中還是鏡外。就如“乏味”,這個詞比我們能夠體會到的更加“乏味”。
小男孩有規則的鐘擺運動,像是一種神秘巫術的催眠,它伴隨著“吱呀吱呀”的單調聲響,把我帶到了時間之外的某處。我不是神秘主義者,但我深深知道我腦海中的觀念像是我無法躲避的透鏡,世界穿過它呈現在我眼中的時候發生了改變,而我無法復原最初的影像。由此我學會了懷疑自己,我有時更傾向于相信身體的感覺而非思考的結論。就像此刻,我的身體有著前所未有的放松,它不是處在一種享受之中,而是它失去了享受的欲望,因此它變得無比寧靜,無比透明,仿佛風都可以穿身而過。我來到了無始無終的混沌當中,我想到了“天人合一”這個中國古代的理想生命方式,但我覺得“天”對于我而言卻是那么陌生,更別談與之“合一”了。我感到的只是歷史與時間從一個人生命中的暫時隱沒,它們暫時帶走了那些強加給生命的壓迫、焦慮、煩躁、雜亂與悲劇。生命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但是卻感到輕盈和清爽,有飛翔的沖動,可更多的是意識中并非虛無的空白。
我迷戀這種感覺。我相信每個人對時間的體驗都是獨特的,這種“獨特”對于他人而言自然是神秘的,也是將自身與他人分離的重要因素。我執拗地相信:這種“獨特”關乎個人的存在,“獨特感”越強的人,存在意識也越強。假如真有一種完美的“個人寫作”,那我覺得就是有著強烈存在感的文字。只有寫出自己內心的獨特與豐盈,才能通過閱讀與溝通豐富他人的生命體驗,才能讓個體與個體之間發生深刻的精神關聯,從而把個體的人和整體的人類在更高的意義上緊密聯結起來。——原諒我這樣去議論和說明一種感覺,實際上即使沒有這些意義,我也從本能上迷戀這種感覺。這種時間之外的感覺,讓我想起詩人博爾赫斯筆下那些時間之外的玫瑰,散發著奇異和幽暗的芳香。
我不知道小男孩此刻對于時間的感受,但我猜測他是處在時間之外的,至少是處在時間的邊緣上。他穿著紅色的拖鞋,上面沾滿了灰塵,我卻并不覺得那是一種“臟”,或許世上就沒有臟的事物,“臟”只在人的心里。可是成年人的世界卻是由一堆判斷和定義構建的,這些外在于我們的透明卻真實的東西我們稱之為什么?社會?那么時間又是什么?除了物理學上的定義,我覺得它幾乎就是人的存在本身!除了社會建構出的時間概念,對于個體的人來說,幾乎不可能對時間作出準確的說明,甚至是進一步的感知。因為個體的有限在永恒的無限面前所說出的任何話語,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沉默的加深。即使我們不談永恒,僅僅談論身邊的事物,比如四周的樹木,它們存在的歷史都遠大過人類。我想起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一篇小短文《巨人樹》,他在面對這些從遠古洪荒年代幸存下來的大樹時被深深震撼,他在文章結尾這樣寫道:“在踏進森林里去時,巨人樹是否提醒了我們:人類在這個古老的世界上還是乳臭未干,十分稚嫩的,這才使我們不安了呢?毫無疑問,在我們死后,這個活著的世界還要莊嚴地活下去,在這樣的必然性面前,誰還能作出什么有力的抵抗呢?”有人說美國作家缺乏歷史意識,我不明白他們所說的歷史意識究竟是怎么樣的,但我所認同的歷史意識就是斯坦貝克這樣的:直接穿透了人類為自己建構的歷史,而觸及了高于人類存在的整個宇宙。“宇宙”在人類的文化論述中并非總是一個大而不當的“虛妄之詞”,它和我們的文化關系比我們設想的要密切得多。最起碼,它提供了一個大于人類歷史的尺度,當我們從人類歷史的源頭穿越而出的時候,或許才是從另外的角度真正深入地進入了歷史。
一個下午都在聆聽自己的自言自語,周圍顯得很不真實,像是虛擬的空間,像是我轉身離去就再也無法尋覓的神秘之地。我多么珍惜此刻的一切,我多么慶幸小男孩讓我體驗到了此刻的豐富與無限。在時間的裂縫中我暫時超越了我自己,盡管我知道無論怎樣的超越總會“小于一”,但畢竟大于其他任何個別的事物。這些奇怪的想法小男孩不會知道的,但我感謝他作為一個單純而抽象的理想之人的象征,喚醒了我對生活、世界、他人和童年的無限熱愛。
探測周圍的岸
在南方的夏季寫作,有著強烈的抵抗意味。此刻的陽光如同帝國最強盛的耀眼時分,喧囂的萬物考驗著一個作家的耐心與耐力。作家余華談及他早年在夏季的寫作,那是在封閉的房間內正襟危坐,鋪開稿紙,揮汗如雨,怕汗水打濕稿紙,就用毛巾把右手和筆都纏繞起來。這樣的情景現在想來還真有些激動人心的感覺,寫作看起來變成了一種苦修,但卻是逃避炎熱的最好方式。要是在八月描述寒冬大雪的場景,會不會因為過于投入而渾身打起冷戰來?就像是福樓拜寫完《愛瑪》后服毒自盡,自己的身體也出現了極度惡心的中毒癥狀。的確,寫作召喚著一個全新的世界,但并非是一個理想的世界。
談論寫作本身往往是危險的,因為寫作不是一種現實的職業,而更多的是一種秘密的職業,一種精神上難以拭去的胎記。甚至,某些特殊的寫作癖好就像是隱私一樣令人羞于啟齒。想起巴爾扎克那無與倫比的大肚子,每次寫作他都要向那個皮肉構成的大袋子里傾瀉無數杯劣質咖啡,讓寫作成為一種略顯古怪的有些神經質的強迫性運動。而大詩人里爾克在晚年卻經常要依靠通靈術與“幽靈”交談而寫作,將寫作這個行為中的神秘主義因素發揮到了極致。
我在這里愿意談及的不是這樣的寫作,我要談論的是一種對寫作的刻骨“仇恨”。葡萄牙詩人佩索阿在《惶然錄》中寫到的有關寫作的文字,是讓我最感到揪心的文字:
“對于我來說,寫作是對自己的輕賤,但是我無法停止寫作。寫作像一種我憎惡然而一直戒不掉的毒品,一種我看不起然而一直賴以為生的惡習。”
請原諒我這樣的斷章取義,似乎佩索阿成了中國語境中那種郁郁不得志的傳統文人,但實際上佩索阿只是個小職員(甘心如此,正如卡夫卡), 他從不懷“匡扶社稷、懸壺濟世”之心,他只是覺得他寫得不夠好,卻仍然在寫,只是因為寫作讓他的存在變得沒那么墮落,但這樣反而成了對寫作的一種玷污(一種偉大的寫作難道僅僅是讓自己顯得沒那么墮落嗎?)如果你過分珍愛一件事物,那么你將無法容忍它身上任何一點兒的雜質;同樣,如果你過分珍愛一件事物,你必將失落,必將幻滅,因為這世間本沒有完美的事物。
佩索阿這樣結束道:“是的,寫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會失落,因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不過,不像河流進入河口是為了未知的誕生,我在失落自己的過程中沒有感到喜悅,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拋到了沙灘上的淺池,淺池里的水被沙吸干,再也不會回到大海。”
引文的第一句話,很顯然是佩索阿對自己的一種清醒的安慰,也是眾人普遍的生活感受:一種不可逆轉的失落過程。但更打動我的是后面的話,盡管字里行間全部由隱喻構成,不好理解,但卻充滿了對寫作的最為本質的也是最為絕望的認知:那就是坦然面對了作者的必然死亡,而作品雖然也只是一種虛空,卻畢竟在世界上留下了微弱的印跡,就像是被細沙過濾后的海水一樣。這種看法在詩人奧登悼念偉大的葉芝的時候,表達得更為清晰:
因為詩不能讓任何事發生:它活著
在它自身構筑的峽谷中,官僚們
從未想去干涉,它漂蕩在南方
從孤立的農場和繁忙的悲痛,
到我們信任和死守的粗野小鎮;它活著,
是事件發生的一條道路,一個出口。
是的,無論如何,詩歌必將活著,寫作也必將活著,或說寫作在試圖創造一種長存于世的“活著”。只有這樣的想法才能激勵我的寫作,給我生活與生命的勇氣。在接近比自己更為永恒的事物時,人才能在不斷地失落中去保持住自身的平衡。就目前而言,我尚年輕,寫作這樣的致力于語言與世界的活動,讓我的內心充盈著某種不為人知的幸福感。但是我卻早已做好了準備:在數十年后,曾經困擾佩索阿的也必將困擾我。
卡內蒂(Elias Canetti,——我不得不再次引用,因為這里談論的是寫作,眾多的大師都比我更有資格)說:“在這里,而非別處,你被允許寫作。”一句驚心動魄的簡單話語。與其說限定了一個作家的存在,不如說限定了一個人的存在。什么是這里,而什么又是別處?又是誰在允許?我感到深淵正在我的身后豎起,而我所需要做的正是用寫作去探測自己周圍的虛空。當我的根須生長得足夠長,我想,總有一天我能夠碰觸到可靠穩固而又適宜生長的岸。
我無力改變的事物越來越多
我無力改變的事物越來越多。我是在家的樓頂上想到這些的。廣州的夏天由于過于漫長讓人產生了一種時間凝滯的錯覺。太陽西沉,黑夜涌現的時分,假如有風,站在樓頂上會感到世界還活著,還在呼吸。這個散發著巨大熱量的世界,像是一團模糊不清的星云,孕育著一些不知名的恒星和行星。我站在如外星般雜亂的樓頂,可以看到廣州的標志——“小蠻腰”觀光塔,它的特點就是吸引你不斷凝視它,卻一無所獲。當黑夜越深,“小蠻腰”的光就越亮,反復提醒我處于黑暗之中,像是那些被黑暗所庇護的事物一樣。可我,總是懼怕著那樣的事物。
也許是因為我改變了一些事物,所以我才發覺我無力改變的事物越來越多。改變一件事物,就是要進入事物的核心,在那樣的過程中自己也不得不被或多或少地改變。這種自身的改變,加劇了精神深處的無力感。我時常被無力感所困擾,就像我站在樓頂上眺望不遠處的馬路,街燈亮起,呼應著四面八方明晃晃的車燈,仿佛生活才剛剛開始,其實這不過是一場幻覺。我已經無法區分這是出自自己心底的幻覺,還是出自生活的客觀的幻覺——假如真有這種分野存在的話。
如果在夜色更加濃密的時分,比如午夜,站在樓頂上,還會有一番更加細膩的感受。也許,我什么都不曾改變過,因此才變得越來越無力,就像缺乏鍛煉的肌肉。在緩慢蠕動的生活之流里,我們變幻著自己的位置,也許位置不同,本質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人的存在是如此玄奧、如此多變,以至于是如此悲傷。這樣的悲傷,讓我想到自己是個人,而不是別的什么事物,而且只能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即便是最親近的人,我也不是他們,他們更不是我。這種想法不知道更能安慰人,還是更能傷害人?
樓下的小餐館,過了午夜愈發熱鬧起來,人們大聲吵嚷著,有時還會摔碎酒瓶,令人聯想起一場場不堪入目的街頭斗毆事件。我對此非常好奇:經歷了十幾個小時的白天生活,那種被殘酷壓榨、為了生存奔波忙碌的生活,并不能壓垮人類,即便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依然在內心隱藏著力量,而后在酒精的誘惑下那種力量傾瀉而出,突然從奴隸變成了斯巴達的猛士,會不會令他自己都暗自吃驚?也許這種吃驚只是一瞬閃過,他就被這種自己發出的力量所裹挾,抵達了一個自己的理性從未想過的地方。的確,誰沒有過那樣的時刻呢?我在生活最乏味的時候不也懷念那樣的時刻嗎?盡管那樣的時刻痛苦遠遠多于快樂。
我眺望著樓下的一切,我深感無力。我無力改變的事物越來越多,也許是因為我經歷的事物越來越多,而我的有限性正在凸顯出來。我在許多個夜晚眺望著樓下的一切,不管是“小蠻腰”還是小餐館,我都能體驗到與它們深深關切的感受。我當然去過“小蠻腰”,也去過那些小餐館,因此我有時可以用記憶去體驗,但更多的時候,用想象便已足夠。我體驗著那種與它們、與很多事物共存于世的感受,然而,它們畢竟外在于我,遠離于我,是如此冷漠,我不得不再一次被無力感所深深折磨。
這就是所謂的“孤獨”的深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