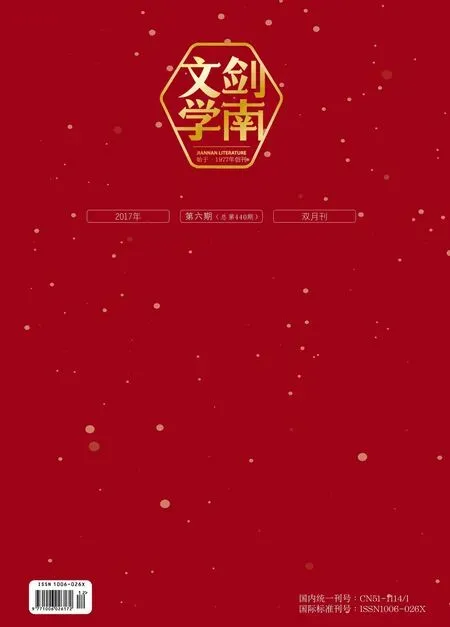多重視野下的人性復蘇
□ 伍立楊
長篇小說《大瓦山》以牛巴馬日的死為故事切入點,以科考大學生艾祖國和牛巴史麗的愛情為主線,掃描了“文革”前后發生在瓦山坪公社的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故事,是一個時代視野的濃縮回放。小說運用極具張力的個性語言,詼諧、夸張而極具諷刺地披露了特殊歷史背景下人們生活的艱難。作者以詩意的筆觸,向世人展示了彝族文化的神奇和大瓦山的神秘;以時代民族的視野,表達了作者對人性光明的深刻贊美,召喚人性的復蘇。
小說語言的個性拓展
小說《大瓦山》的語言是極具個性和張力的,其詼諧和夸張以及表達的精確和收到的效果,可以說是對當下小說有限表達空間的積極拓展。如描寫曾是國軍軍犬的大黃出場時的片段:“只因周老大在人群之中多看了它一眼,從此它便跟了周老大。”解放后周老大帶大黃去剿匪無功而返后:“總之剿匪失敗罪過全在大黃身上。剿匪隊曾想將大黃處死,以啖其肉,全靠周老大的人格魅力和手上的殺豬刀才保住了大黃的一條狗命,于是大黃更加盡職盡責,并且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多生多育,這么多年下來,全區上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狗男狗女都是大黃的狗子狗孫。”再如:“地球人都知道牛巴馬日與曲柏的仇恨”,等等。
看似詼諧夸張的語言,表達極其深刻精準,又充滿了極度的諷刺。“艾祖國想再到醫院去看牛巴叔叔,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得趕在天亮之前離開家,避開所有認識他的人和不認識他的狗,躲回大瓦山上去”。很多語言,不僅是最為客觀、直接的小說場景描述,也是別致而深刻的本性揭示,以及精彩的對比諷刺。
多重視野的生動刻畫
長篇小說《大瓦山》,從時代視野、民族視野和地域視野入手,為我們繪制了一幅經緯縱橫的特殊空間。小說的主要故事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鋪開,一直到后來的包產到戶,雖然是一個偏僻的小小的瓦山坪,可它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風云變遷。文中涉及“批斗大會”等很多真實的歷史事件,涉及“牛豬配種”的荒唐史料,涉及成昆鐵路全面開工建設中 “南瓜生蛋”的感人往事。
豐富的民族民俗文化信息,是小說《大瓦山》的另一大特色。小說花了大量的篇幅來展示民族民俗文化,為塑造小說人物性格和小說故事發展起到很好的鋪墊作用,如彝族人取名時“一般老大叫阿依,老二叫阿嘎”,彝族的超度儀式,“生彝”“黑彝”的概念,桿桿酒,待客風俗,喪葬習俗,串門的禁忌,彝族年的來歷,爬花房及婚俗,送祖靈儀式,火把節由來等等描述。小說的地域視野也很明顯,文中描繪的大瓦山,不僅有鳳池、魚池、花池、干池的美麗傳說,更因為作者的深情講述,使大瓦山始終散發著一股神秘、悠遠的氛圍。
人性光明的復蘇回歸
作為清朝皇室后裔的艾祖國,跟隨老師王大江來到大瓦山搞科考,但由于牛巴馬日的意外 “死亡”,從此就再也沒有離開。一開始,想走不能走;到后來,有家不能回。在艾祖國父親同事的指引下,艾祖國僥幸躲過了北京的清理運動,但又因與牛巴史麗和克其等人的愛恨糾葛和利益糾紛,又戲劇性地被卷進了瓦山坪大大小小的風波。本是一個文弱的書生,卻不得不經歷一波波殘酷的事,幸而有牛巴史麗、俄著娜瑪等人幫助,艾祖國帶著周老大的殺豬刀,帶著自己的信念,劈荊斬刺,終于“殺”出了一條活路,最終扛起了一個殘破的家庭,獲得了真正的愛情,修筑了令后人敬仰的愛情天梯。
有時代的洪流,有個人的恩怨,有民族的差異,時代的脈搏,如此境遇走出來的艾祖國,更彰顯著人性的堅毅和光明。
阿卓因為遭到莫曲柏頭人的多次侮辱,以至瘋了以后一輩子都在堅持“去地里檢查莊稼”的主業,后來照看阿妞的豬兒(艾人民)才短暫地忘記了此事。當豬兒陪伴克其后,她又撿起了自己的主業。由此可見,曾為奴隸的阿卓所遭受的深重苦難和新生命帶給阿卓的巨大希望。直到后來,阿卓被艾祖國弄上了大瓦山,遠離了瓦山坪,和女兒牛巴史麗、孫兒艾人民、艾瓦山生活在一起,阿卓才丟掉了主業,甚至完全恢復了正常。包括克其最終的負罪自焚和臨終懺悔,作者在揭露苦難的同時,更深刻地贊美著永不磨滅的人性光明。
離家出走多年又不忘大瓦山的艾人民改名換姓,把自己的女兒以大瓦山紫云峰為名取名任紫云,艾瓦山的兒子也以紫云峰為名取名艾云峰,而且以記者和第一書記的身份重新相遇在大瓦山,一同走上愛情天梯,回到那個特殊的家。小說如此結尾,這不僅是作者戲劇性的安排,更預示著冥冥之中的人性復蘇和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