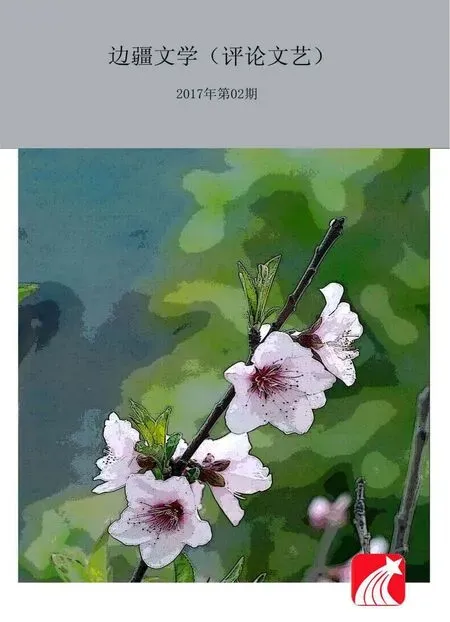在語言深處撫慰疼痛的陽光
——評張永剛的新詩集《飄動的云》
劉建國
在語言深處撫慰疼痛的陽光——評張永剛的新詩集《飄動的云》
劉建國
我曾經在許多的心靈境遇里去觸碰這樣一個能指:如果在語言深處去撫慰疼痛的陽光,那會是一次怎樣的靈魂震顫?為此,我曾小心翼翼地在語言的罅隙里去打撈透過指縫的陽光,并用一種莫名的心情去孵化和喂養它們,希望它們能蛻變成一群精靈,在我心靈的洪荒之地精耕細作。但艱辛的汗水滴落出的卻是對語言的失望和痛恨。因此,我常常逃避這種語言的困境,并想徹底忘卻了它們。在讀完詩人張永剛的新作《飄動的云》(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時,我突然有了一種釋然,因為我數次觸碰的那個能指,在他的詩里獲得了最好的解答。語言,這個曾經讓我失望和痛恨的東西,在他詩篇里的化作一道道風景和萬般柔情。
《飄動的云》一如既往地延續他含蓄和雋永的創作風格,但在前兩部詩集《永遠的朋友》和《歲月深處》的基礎上更能顯示出他的“詩心”:在語言深處撫慰疼痛的陽光。在對他前期的詩歌評論里,就有中肯的說法:“現代生存困惑是衡量一個詩人是否真能置身于五光十色的現代生活之中,去敏銳地感受現代社會的一種尺度。張永剛在他的詩里充分地展示了這種彷徨無定的生存情境,體現出對現實生活的執著審視和選擇。”只不過,《飄動的云》把對彷徨無定的痛苦體驗上升為對一個陽光世界的撫慰。詩歌,永遠都是在語言的深處經過無數次的陣痛以及在陣痛蛻變的涅槃式升華中產生的。在面對今天詩歌“沒落”的時代乃至整個文學“沒落”的時代,很多評論語言也變得無所適從,甚至無所事事。但我個人認為,無論在任何時代,詩永遠是詩人對世界的深層體悟以及對自我靈魂的觸碰甚至救贖。也許在很多人眼里,“詩”是無關緊要的,這從某種層次上印證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浮華和喧囂。借用另一位曲靖詩人的話來說,就是:“詩歌對文化精英、乃至文化知識界人士、普通老百姓都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文化精英、乃至文化知識界人士、普通老百姓這些階層的生活里不能沒有詩歌。詩歌可以考驗一個民族的良心,詩歌可以考驗一個國家的良知。沒有詩歌的國家是野蠻的、原始的乃至崩潰的。缺少詩歌的國家,人民會更加愚昧。”其實,詩從產生那天開始,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承擔了不同的外在使命和內在堅守并形成了詩的糾結和詩人的糾結。詩的糾結導致對詩的認識在理論層面形成了延綿不絕的爭議,也由此產生了不同的理論觀點。詩人的糾結表現為外在使命和內在堅守對詩人的擠壓和撕扯,這使得詩人常常陷入困惑與痛苦之中。也許在理論上可以去設想外在使命和內在堅守的均衡性,但一旦真正達到了均衡,可能詩歌就喪失了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也就不存在詩的糾結和詩人的糾結。外在使命和內在堅守在普遍意義上永遠不會是均衡的。“最關鍵的是,詩人將生活訴求置于心靈還是作為外在的責任來承受。前者是一種人生境界,后者則是一種寫作態度。”仰望人類的詩歌天空,在對繁星燦然感慨的同時,我們依然會一如既往地把目光投向堅實的大地,并不斷向地平線延伸……因為,這一切孕育了詩人的情感,并且賦予了詩歌的生命和質感。
用語言的指尖撫慰那縷疼痛的陽光
可以說,詩人張永剛一直倚重內在的堅守,正如他所言:“我努力重視提筆之前心靈的感覺和律動,力求將生活融入內心,以構建詩意的生存方式。”這種堅守讓他在詩里不有意去描摹生活的苦難與疼痛,而是用語言的指尖去撫慰生活的苦難與疼痛,并把這種苦難和疼痛升華為詩意化的存在:“我在風中聽到箴言/我在語言的指尖/領悟了風聲/我將文字趕進天空/群鳥一樣飛過/讓原野突然安靜/心也空寂”(《風聲》)。所以,讀他的詩,總是能獲得一種語言深處的優美感以及心靈的凈化:“陽光普照 如酒力遍布全身/這種時刻 一切皆已注定/那些埋伏的風/那些不飛的鳥/盡情享受溫暖 一聲不吭/用無形的手將時間制服/來自神祗的公平 如云飄過/讓許多事物深受感染 發出聲音/讓那些琴弦 被歌唱的柔情軟化/又在指尖的波浪中 突然繃緊”(《訴說》)。時間和空間在文學語境中總會形成千姿百態的幻化。在《訴說》里,作者用豐滿的筆觸,在語言的指尖感受著四季輪回對心靈的震顫,優雅而又那么深邃,時間和空間在這里被反復折疊,又被反復打開。情感的律動,在神性般的光芒中被浸泡和洗滌。
把寫作當作詩意化的生存方式,這種態度本身就令人敬佩。在當代的詩歌界,更多的詩人是把寫作當作是對語言的把玩,當然,我不否認他們的作品也帶著情感,也能顯示出對世界的體悟。但是,把對語言的排列組合放在詩歌寫作的首位是不應該被肯定的。正因為把寫作當作詩意化的生存方式,他的作品幾乎都保持明亮與陽光,盡管那縷陽光是疼痛的陽光:“黑色的精靈/穿過夜/在我的手里留下文字/在我的手里/放上蠟燭/讓我感覺顫動/來自輕柔的奔跑/讓我同時聽見/一陣小雨的低語/讓我知道/黑暗的背后/必有光走過/流光溢彩的瞬間/必有神庇護”(《精靈》)。
讓低語的花在語言深處綻放
“花”這個意象,在中國詩詞里出現得實在太多太多,它對中國人心靈的影響程度遠非量化可比。當然,也許可以說,在每個詩人心里,“花”都是以千姿百態的心靈觸摸去感悟世界的。詩人張永剛也有太多的“花”語,這與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意象是不謀而合的。“花”雖多,但中國古今的詩人對花的描摹都各有別致,詩人張永剛也是這樣的。“花”是什么?他用自己的心靈去感悟。呈現在《飄動的云》里,“花”是情感的催化劑,更是整個世界,因為,無處不在的是——讓低語的花,在語言深處綻放:“手在音樂中間/如花開放”(《一個日子》)、“更加明亮的花瓣/飄上枝頭/將無邊夜色/變為清晨”(《聽雨》)、“如果看到雪花/你要告訴我”(《如果看到雪花》)、“一杯咖啡/帶著花/在平安之夜發出光芒”(《平安夜》)、“你的氣息/如一朵遲來的玫瑰/開在發際”(《兩輪圓月》)、“問候和祝福/來自寧靜的臺階/帶著花/一朵正在盛開的玫瑰/讓高樓俯下身子/長久凝視/讓光伸出雙手/輕輕托起/它溫順的顏色”(《臺階》)、“你是一枚果實/被上帝派往春天/你是一種花/開在風的發際”(《果實》)、“你靜守安寧/一如花朵/悄無聲息”(《表達》)、“最美的花剛剛盛開”(《色彩》)、“你將兩個季節/用花妝點/讓花朵燦若繁星/布滿了/天空下的大地”(《兩個季節》)、“我在風的內心/遙想花朵容顏/正被清晨的夢指點/在一朵新鮮的云彩下面/靜靜開放”(《兩個季節》)、“我知道你的問候/在某個早晨/在我的窗邊/喚醒所有的花/并使陽光開口/和我輕輕說話”(《春天的鳥》)、“你讓安靜的花/輕輕落下/讓激情的紅均勻展開/仿佛夢幻時刻/迎候天使的盛典/花香飄近/如秀發臨風/拂過聆聽的渴望”(《長椅》)、“你用清靈的花朵/告訴我/春天已經來臨”(《春天來臨》)、“你近在咫尺/位于節日中心/用無邊的花朵隱藏自己”(《節日的夜色》)、“讓我知道遠方很遠/天空無比清麗/花朵與花朵/連在一起”(《春節》)“野菊燦爛/將開放的沖動/隨身攜帶/它以柔克剛/在神的手中改變了夏季”(《一張照片》)、“這些花朵帶著風/將黑色的幕掀開”(《舞臺》)、“誰讓花瓣的顏色/連綿起伏/漫過墻壁/無形的手臂/穿過回味的拐角/誰讓一幅畫中的景象/花繁似錦/春天透過紙背/花香彌漫內心”(《一幅畫》)、“所有的花伸出手指/將另一朵花捧起”(《平靜的時光》)、“一塊頭巾/花朵一樣打開/讓果實向你靠近”(《秋日》)、“看你清唱如花/開遍水邊空地”(《明澈的水》)、“芳草青青/雜花生樹”(《在秋天的高處》)、“驀然回首/如驚鴻一瞥/目光的花朵連綿不絕”(《風輕輕走來》)、“任花朵如夢/開在靜夜的枝頭”(《燈光的大門》)“最美的花開在路上”(《遠處的雨》)、“我手執鮮花/穿過大片夜色/靠近你”(《跨年》)、“讓季節含苞/花朵一樣滿懷激情/即將開放”(《感受內心》)、“花蕾突然低語/綠葉面容清亮”(《明亮的早晨》)……在這里,時間仿佛是靜止的,詩人用指尖扒開那疼痛的陽光,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花”的繽紛世界。
談到詩歌里的“花”,我經常會想起陳之藩《時空之海》中的那句話:“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再讀《飄動的云》時,我對這句話有了更為深切的體驗。詩人張永剛在詩集里直接以“花”為題的不多,但透過這些詩篇,我們能感受到他那深沉的生命情懷。在《油菜花開》里,作者表達了人生的惆悵和無奈之情。對家鄉的眷戀,對親人的思念,怎能不引起詩人的感慨?雖然回家的路途并不遙遠,但經常連假期都沒法好好休息的他,一年又有幾次能從容回到故土去陪伴親人呢?他只能以故土最具代表性的油菜花來抒發自己的情懷。春天來臨,作者自然會想到家鄉無邊無際的油菜花,但作者不直接寫春天來臨,而是“知道春天已經來臨”,“知道”一詞,暗含了作者內心的期盼和更多的無奈之情。接下來繼續用“知道”來表達這種情感:“知道這些日子/路上與心中的擁擠/知道我用思念/跨過年/跨過冬與春的分界/讓冷暖集于內心/眼前分明亮著/互相叮囑的話語”。游子思鄉,在中國的文學世界里,總會觸及心靈深處那難以回避的傷痛,所以,作者才會說:“一生總有一景最為孤寂……當我低聲清唱/可有一朵/于萬花叢中/與我輕輕應和”。惆悵和無奈已經到了極致,但詩人對詩歌寫作的追求:“我愿意讓幾乎所有作品都盡量保持著明快的境界與節奏,以印證個人信仰對時代意蘊柔弱而綿密的整合力量”,導致他必然懷揣著惆悵和無奈繼續前行:“春天的風送來消息/將牽掛的事情一一告知/我知道旅途漫長/花開似錦/在夜色的邊緣讓我安寧”。在以“雪花”為題的幾首詩里,作者沒有去刻畫“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的意境,也沒有去抒發“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失意,而是從內心出發,描摹對雪花純潔品質的向往和對人間溫暖的渴求:“寒冷退開/春意提前到達/潔白的原野無比安寧/雪花開滿遠方/最為純潔的一朵/落在我心里”(《雪花簇擁》)、“在一顆心落下的時候/讓它的溫暖、有力擋住了/北方強大的/整個冬季”(《如果看到雪花》)、“清靈的花朵/面容俏麗/徐徐飄落/停在我的夜里/讓我的夜晚/聽到低語/讓激動與寧靜/覆蓋整個節日/以及節日之外/你送給我的/所有時間”(《雪花》)。在《兩朵花》里,作者把大地之花和雪花融合在一起,體現宇宙萬物生生相息的生命規律。這種對生命的期待和吝惜還有他的《等待花朵》、《初冬的玫瑰》、《有一種花》等。生命情懷,在文學意義上是指作者對自身生命的體悟和以及由此發散到對宇宙萬物的情感體驗。在《飄動的云》里,詩人總是以他那靈動的心,撫慰著人生和世界。
在情感與想象深處走進語言的煉獄
再平凡不過的生活場景,通過詩人情感的滋潤和想象的觸發,在語言的行距中,總是能孕育出豐富的詩意,這不得不令人贊嘆。田間地里的勞動場景以及水稻和樹林等等,到了詩人筆下,就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生活實在。《割草》描摹了天還未亮就和叔叔推著老式推車去割草的經歷。在這里,艱辛被恐懼淹沒:“有一刻我再次彎腰/將一只熟睡的鸛驚起/它突然的叫聲/擊碎無邊的寂靜/毛骨悚然/在看不見的風中/令我強烈戰栗/余悸草野般寬廣/綿長”。在《拉車》里,上山的艱辛本來就對當時還未成年的詩人難以承受了,何況還有下山的危險在后面,所以詩人不得不感嘆:“怎樣將一輛農村的手推車/拉下滇東的大山/讓一天的勞動/在我們的家門口結束/那是我長久的擔憂/它在我的記憶深處/有力地顛簸著/那種難以抑制的速度/在車子后面/我們不得不走過的地方/揚起了長長的灰塵”。《勞動》一詩顯示了詩人在20世紀70年代那個特殊的時代里在學校勞動的獨特感受:“在那些課程邊緣/我們開始種菜……我們埋頭施肥澆水/以勞動的名義/命令菜地交出它的果實/就像老師/以課程的名義/命令我們交出期末的答案/他想讓我們用一種/更為可靠的方式/在那個難以生長的時代/整整齊齊長大”。這種詩意化的存在表述,還有《水稻》《地邊》《旱季》《樹林》等等。作為一個創作者和理論研究者,我始終佩服他在情感、想象和邏輯表述之間獲得的難得的詩歌寫作勇氣:“服從于心靈的寫作對于寫作者本身而言并不挑剔,甚至人為的選擇都是多余的。……可見,在一個自由的心靈世界里,你所感受的,你所書寫的,其境界,絕對超越了你所生存的時空,絕對要為你的現實居所鍍上一層精神的陽光。”不經過情感與想象的洗禮,不走過語言的煉獄,誰能吟發出在心靈深處的那曾經經歷又難以磨滅的記憶。
在中國文化的心理情結里,故土與親人總是一種無法解開的羈絆——始終,人首先為情物,不管是顯赫者還是卑微者。當然,落實到詩歌理論的解讀層面,要把它解釋清楚可能很困難,正如詩人所言:“決定一首詩歌優劣的理性判斷往往是無效的”。在《飄動的云》里,詩人抒寫了對自己故土的深情留戀:《彎子》《以且》《板橋之一》《板橋之二》《鐘山》《大地坪》《羊洞腳》《金雞》《長底》《樂巖》《多伊樹》《青草塘》《大營》《牛街》《富樂》《羅平》《一條路》《回板橋》《春天的羅平》等。故土的溫馨,令人魂牽夢繞,最終只有那條路去連接:“一條路/從曲靖通往羅平/那是滇東的東邊/我最平常的旅程/讓我不斷往返/用盡一生的時間”(〈一條路〉)。更能打動人心靈的,是那懷念無邊的情愫:《父親》《那一天》《離別父親》《思念》《大風》《百日》《草色如煙》《荒草》《青苔》《柏樹》。這十首詩,是詩人在其父親去世后寫下的。可以想象他在寫每一首詩歌時內心的悲催和眼瞼掛著淚花的情景……情到至深處,語言便顯得蒼白無力,這就是語言的煉獄,但他卻能夠在這語言的煉獄里去傳遞他那赤誠的孝子之心:“我知道你充滿了等待/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你等待無邊的事情/自己到來……一場漫長的病/把你的身體/和心/粗暴地綁架/你走了一生的那條小路/在原來的山上蜿蜒/有一小段/閃閃發亮/站在屋檐的下面就可以看到/但此時的屋檐/已經屬于想象/近在咫尺的地方/用心才能走到”(《父親》)、“我打開家門/期待父親/等我回來//大雪突然停下/在我的車子周圍/風折回了/原來的地方/不再說話”(《那一天》)、“一座山突然壓在心上/亂云蒼茫/夕陽點亮燈籠/血色的光/走在高高山上/鳥在火中起舞/鳥用火/照著您去的地方/看不見歸程”(《離別父親》)、“這個日子/你離開的腳步清晰可見/印在我們心上/一條路/走向高處/在一個終點停下/將你和時間留住……你的語言長久停留/透徹我們的耳膜/直入肺腑/使我好想答應/同時喊出/那個久違了的詞語/父親”(《百日》)。
那縷疼痛的陽光,在語言深處被以靈魂的溫度時時撫慰,這就是《飄動的云》。
【注釋】
[1] 張永剛.滇東文學:歷史與個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264.
[2] 云南北鴻.詩84首[M].香港:類型出版社,2014:101.
[3] 張永剛.飄動的云[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2.
[4] 張永剛.飄動的云[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2.
[5] 陳之藩.時空之海[M].臺北: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6:8.
[6] 張永剛.飄動的云[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3.
[7] 張永剛.歲月深處[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6:3-4.
[8] 張永剛.滇東文學:歷史與個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222.
(作者系曲靖師范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