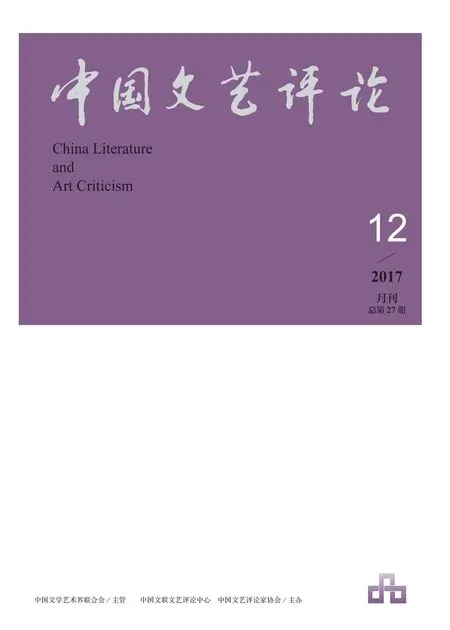信息時代科學與藝術互動的三種模式
黃鳴奮
編者按:縱觀文藝發展史,文藝的每一次創新和發展,都能看到科技的重要力量。當今時代,科技與藝術更呈現出緊密聯系、互相滲透的態勢,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對于這一論題,本刊自創刊以來就給予了充分關注。本期刊發一組文章,對相關前沿問題進行探討。
信息時代科學與藝術互動的三種模式
黃鳴奮
在人類由傳統社會走向信息社會的過程中,科技助力藝術創造震撼,體現了二者相輔相成的一面。藝術為科技迅猛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所震驚,通過作品加以渲染與批判;科技理性對藝術感性加以制約,人工智能顯示出取代人類從事藝術活動的趨勢,科技實力裹挾藝術精神,則體現了二者彼此博弈的一面。科技 藝術 信息時代如果親臨奧地利林茨電子藝術節或參觀北京今日美術館的相關展覽,我們會為科技與藝術聯姻所造就的輝煌而震撼。相反,如果觀看人造人、隱身人、換靈人、克隆人等題材的科幻電影,我們可能領悟到人類對科技失控這一預期的震驚、憂慮與警惕。當藝術瞄準科技走火入魔的危險大張撻伐時,科技正以其不可阻擋的迅猛發展沖擊傳統藝術觀念和藝術格局,甚至對整個社會形成震懾之勢。可以說:上述涉及科技與藝術關系的震撼、震驚與震懾并存,是人類從傳統社會走向信息社會的特有標志。
一、震撼:科技對藝術的助力
藝術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之間存在某種一致性。盡管達爾文等進化論者將人類藝術溯源于動物的性選擇,但在創造性的意義上,藝術是人類所特有的。盡管比較心理學家發現某些動物也能使用(甚至制造)簡單工具,但在運用工具、制造工具的意義上,科技也是人類所特有的。以語言為標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造就了人腦中作為自我意識依據的第二信號系統,從而使作為藝術之心理依據的模仿和表現成為可能。以文字為標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提供了對于藝術的外延和內涵進行深度思考的媒體條件,從而促進了最初的藝術觀念和藝術理論的誕生。以印刷術為標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建設了作為藝術共享平臺的大眾媒體,從而使藝術生產、藝術傳播和藝術鑒賞走上了大規模市場化軌道。以電磁波為標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實現了藝術共享的電子化、遠程化、視聽化,為讀圖時代的到來導乎先路。以計算機為標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將藝術發展納入網絡互聯、智能集成的軌道,使藝術在世界范圍的跨平臺流動成為常態。盡管作為其支持條件的科技(主要是信息科技)經歷了諸多變化,不論在哪個時代,藝術總是訴諸人的心理,通過影響包括知、情、意在內的心理過程而發揮其社會功能。離開了人的心理,無從詮釋藝術的奧秘。
1. 藝術追求震撼
既然藝術訴諸人的心理,那么對人的心理影響越大的藝術作品、藝術活動或藝術角色,就可能獲得越高的評價。循此以推,震撼性效果便順理成章地變為藝術的目標,因為它的含義正是大到非同小可的心理影響。人們用“震撼”頌揚雪萊《西風歌》、艾略特《荒原》之類詩歌,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之類小說,《紅旗渠》《李四光》之類戲劇,《辛德勒的名單》《唐山大地震》之類影片,《天下兄弟》之類電視劇,《復興之路》之類大型音樂舞蹈史詩,《見證與銘記——南京大屠殺》之類空間展示藝術,或贊美其視覺形象直達心靈,或肯定其內涵的深厚、對比的強烈、立意的驚世駭俗,或者稱頌“平靜中的震撼”“瑣細與平實中也有讓人震撼的內容”。
從信息論的角度看,藝術對震撼性效果的追求至少包含以下三重意義:一是訴諸感官,讓人們接觸到新鮮而強烈的刺激;二是訴諸心靈,通過展示匪夷所思的因果聯系打破人們的心理定勢;三是訴諸肢體,讓藝術活動給參與者帶來非同尋常的反饋。如果感官作為分析器難以應對紛至沓來(甚至如大潮般涌至)的強烈刺激,如果心靈作為處理器難以按常規及時解析新穎海量的信息、或者發現了遠超出其慣性思路的聯系及意義,如果肢體作為效應器難以操控自身所處的奇異環境,人們就會體驗到震撼。這是震撼的三重意義,也是以源于科技的信息處理系統為參照對藝術效果的闡釋。
在不同類型的藝術中,生成震撼效果的方式不同。例如,美術作品的震撼更多來自畫面的大氣磅礴,音樂作品的震撼更多來自旋律的回腸蕩氣,文學作品的震撼更多來自情節的起伏跌宕,戲劇表演的震撼更多來自故事、表演和舞臺特效的集成,影視藝術的震撼更多來自宏大畫面、超強音響與人物命運的相互交織,互動藝術的震撼更多來自驚險情境的經歷。
2. 科技助力藝術創造震撼
科技與藝術都植根于人性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們分別是人類“做得到”與“想得到”的代表。人類能夠運用工具制造工具,這是“做得到”的基礎;人類能夠運用語言反思自己的存在,這是“想得到”的基礎。對于前者的概括與升華產生了科技,對于后者的概括與升華產生了藝術。不論“做得到”或“想得到”,都以已經做到、已經想到為基礎,以未曾做到、未曾想到為引領。這說明科技與藝術都只能放在歷史發展中來定位。
人類曾有科技與藝術融而未分的時代。原始人引吭高歌,就其發聲而言是技術,就其傳情而言是藝術,當時都包含在技藝之中。最初的藝術工作者——游吟詩人是從善于歌唱者發展而來的,最初的科技工作者——工匠則是從善于伴奏者發展而來的(骨笛、弓弦、石鼓等考古遺存曲折地反映了他們之間的聯系)。伴隨著社會分工的推進,科技更多朝實用發展,藝術更多朝娛樂發展。在多數情況下,科技將無用變成有用,藝術將有用變成無用,進而宣布“無用乃大用”。
科技與藝術是人類把握世界的兩種方式,既相互區別,又彼此助力。科技對藝術的貢獻之一,就是協助創造震撼性效果。擊鼓而歌,其情愈壯;編鐘齊鳴,廟堂回響;泰山刻石,文辭高遠;燈光閃亮,驚艷登場……這類例證不勝枚舉。直至今日,科技(特別是信息科技)仍然有助于實現藝術對震撼性效果的追求,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它們提供了多樣化的呈現方式,可以讓藝術家所構想的情境通過相應數碼設備得以亮麗展示;二是它們揭示出海量信息之間各種潛在的聯系,其組合效果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三是它們創造出精彩的互動場景(如主題公園等),讓人們得以親力親為、樂此不疲。或許可以說:在第一重意義上,立體聲比單聲道震撼,三維電影比二維電影震撼,街機比掌機震撼,大型數碼娛樂比桌面數碼游戲震撼;在第二重意義上,超文本比線性文本震撼,隨機藝術比固化藝術震撼,新媒體藝術比傳統藝術震撼;在第三重意義上,交互性藝術比靜觀性藝術震撼,群體性藝術比個體性藝術震撼,冒險性藝術比日常性藝術震撼。當然,以上只是就總體而論,并非對個別作品加以比較。
概言之,藝術試圖引導人擺脫日常生活的束縛,見平常所未見之景,識平常所未識之人,悟平常所未悟之理,歷平常所未歷之情。就此而言,科技確實大有用武之地。奧地利林茨電子藝術節之所以能夠在新媒體藝術領域標領風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借助科技力量展示藝術勝境。例如,荷蘭藝術家尼斯(Marnix de Nijs)《爆炸視圖2.0版》(Exploded Views 2.0)是一個交互性裝置,讓訪客在物理上穿行于視聽城市景觀之中,為在大屏幕上投射出的交互性影像所震撼。德國藝術家亨克(Robert Henke)及其學生梅爾茨(Christoph M?rz)的《波場綜合體之作》(Works for Wave Field Synthesis)旨在探討音響在空間中的傳播。它運用由192個計算機控制的揚聲器組成的環路,形成陣列。通過高級算法算出送達每個揚聲器的信號,可將大量虛擬音源置于環路內外的任何地方,從而使處身其間的人們獲得獨特的聽覺感受。最震撼的是將音源定位于聽者的頭部時所產生的效果,這種體驗是無法用其他技巧獲得的。以上兩件作品分別獲得交互性藝術組、數碼音樂與音響藝術組榮譽獎(2013)。
3. 震撼的反思
根據《國語·僖公二十三年》記載,周景王將鑄無射鐘,單穆公表示反對。在單穆公看來,這口鐘(或者這組鐘)體積過大,音域過低,制作起來勞民傷財,即使制成,其演奏會導致聽者產生從感官不和到心靈狂亂、再到行為失當的種種弊端。這表明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已經對樂鐘的震撼性效果加以反思,從邏輯的角度表明“藝術追求震撼”這一命題的局限性。
顯而易見,單穆公所持的標準是和諧,不僅包括感覺、心靈與行為的和諧,而且包括社會意義上的和諧。他的觀點至今仍有啟發意義。如果刺激超過一定限度,那么,震撼不僅無法使人產生愉悅,而且可能對人的感官、心靈與肢體造成傷害。例如,快速變動的電光可以用來渲染氣氛、營造震撼的效果,這對成人來說或許是“司空見慣渾閑事”,但對尚未適應這種刺激的兒童來說并非如此。1997年12月6日,日本曾因上映根據任天堂游戲軟件改編的電視動畫片《袖珍怪獸》,發生數百名兒童“光過敏中毒”的事件。有鑒于此,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電光技術的影響。推而廣之,將科技引入藝術領域,不應片面追求震撼性效果,而應堅持以人為本、節之有度的原則。
順便說明一下:人的感官、心靈與肢體對于刺激都有一定適應性。刺激雖然強大,作用時間長了就無法再喚起先前的震撼反應。從積極的意義上說,這是人對于自身的一種心理保護。如果長期接受外界強烈刺激的影響,又始終做出相同靈敏度的反應,那么人們很可能受到身心上的傷害。因此,主動降低感受性,不失為非線性系統的明智選擇。從消極的意義上說,如果藝術借助高科技的助力而一味“狂轟濫炸”,那么很可能使人變得麻木,心理受到扭曲。正因如此,人們對于藝術不只是期盼“驚濤駭浪”,也喜歡“小橋流水”。不過,在另一些情況下,人們又希望用新的震撼來打破常規。例如,法國戲劇理論家阿爾托(Αntonin Αrtaud)曾將戲劇和往日巫術的力量相比,提出:“事實上,我們想使之復蘇的是一種總體戲劇,在這種觀念中,戲劇將把從來就屬于它的東西從電影、雜耍歌舞、雜技,甚至生活中奪回來。我們認為,分析性戲劇與造型世界兩者的隔離是十分愚蠢的。軀體和精神、感官與智力是無法分開的,何況在戲劇這個范疇,器官在不斷地疲乏,必須用猛烈的震撼才能使我們的理解力復蘇。”由此看來,和諧與震撼是兩種相生相克的美學觀念。
二、震驚:藝術對科技的批判
與震撼相類似,震驚與外界強烈刺激相關。不過,其重點不在這類刺激撼動人心的作用,而在于人自身的內部心理體驗,特別是因期待落空而感到緊張、害怕或興奮。例如,倘若對重要事物的存廢、規模與特征的認知被證明是大謬不然,對重要事物所懷的情感被證明是價值倒錯,為影響重要事物而貫徹的意志被證明是適得其反,我們就體驗到震驚。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科技以加速度發展,為其后涉及全世界的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生物革命準備了條件。這些革命都意味著原有的思維定勢、社會范式被突破,其影響往往超出人們的預計,由此帶來了各種不同意義的震驚。這種震驚作為沖擊波進入藝術領域,一方面帶動了藝術觀念和藝術手段的更新,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某種反彈,當代藝術在科幻場景中對科技的批判往往就導源于此。這種批判每每以制造更大的震驚的方式出現,試圖引發人們對于科技負面影響的警覺。這類震驚有時可能轉化為噱頭,導致人們見怪不怪的心態。
1. 科技帶來震驚
與震撼相類似,科技所帶來的震驚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渠道起作用:一是通過奇異物品的發明,讓人從感官上覺得異乎尋常,“怎么會有這樣的東西存在”;二是通過奇異因果的揭示,讓人從心靈上覺得不可思議,“怎么會是這個樣子”;三是通過奇異反饋的引入,讓人從肢體上覺得身不由己,“怎么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對于第一種渠道,麥克盧漢提供了下述實例,旨在說明電光渲染(而不是活字印刷)的字母在19世紀末所引發的震驚。終身致力于印刷術研究的沃爾德(Beatrice Warde)這樣自述看廣告的經歷與感受:“那天晚上我進場看電影遲到了。我在路上看見兩個腿腳畸形的埃及體的字母Α……它們像音樂廳里一對滑稽演員一樣手挽手地以明確無誤、昂首闊步的姿勢迎面走來。我告訴你我遲到的原因原來如此,你會感到奇怪嗎?我看見字母底下的襯線仿佛被芭蕾舞鞋拉在一起,以至于使那些字母活生生地像是芭蕾舞明星在跳足尖舞……經過4000年必然是靜態的字母表的歲月之后,我看到其中的字母能在時間這個第四維度里做些什么:這就是‘流動’或運動。你完全有理由說,我像受到電擊那樣感到震驚。”
關于第二種渠道,20世紀中葉有過不少和第五次信息革命相關的例子。德國的本斯(Max Bense)帶領其學生利用算法和計算機程序創造出可以和著名畫家媲美的作品,許多不明就里的欣賞者在發現真相后震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懷申鮑姆(Joseph Weizenbaum)想開發一個“聰明”的計算機程序,結果出乎意料地創造出一個可信的人物。他深為這個名為Eliza的智能體在其不知情的同事中所引發的心理反應而震驚,因為他們將它當成真人傾訴衷腸。懷申鮑姆于是寫作了《計算機權力與人類理性》(1976)一書,向世人發出警告。
關于第三種渠道,宇航實驗室可以作為例證。雖然我們可能在夢中從高處跌落,也可能經歷在電梯里極速下降、在游樂場乘摩天輪過最高點后陡然俯沖,但失重現象主要發生在軌道上、太空內或遠離星球等異常情況下。科學家可以通過建造實驗室來模擬上述條件,給身臨其境的人們帶來震驚級的體驗。某些頭腦精明的人從中看到了商機。例如,英國維珍集團與縮比復合材料公司共同研發的太空船二號飛行器成功試飛,揭開了商業失重體驗的大幕。
2. 藝術制造更大的震驚
在手段的意義上,科技主要是人類認識與改造物質世界的工具,藝術主要是人類認識與改造精神世界的工具。在內容的意義上,科技主要是成體系、可傳授的知識,藝術主要是創造性、不可傳授的本領。在本體的意義上,科技主要定位于物質產品的生產,藝術主要定位于精神產品的生產。這樣說當然不是否定各種過渡形態的存在,如藝術科技與科技藝術等。在某些情況下,科技性與藝術性都被當成是衡量產品特征和水準的尺度。科技中可能有藝術,正如藝術中可能有科技那樣。如果某種科技能夠巧妙地以有序應對無序,便體現出某種藝術性,像相對論公式、宇宙常數、智能寫作程序等都是如此。如果某種藝術能夠實在地將無序變成有序,便體現出某種科技性,像可以批量生產的藝術品、詩詞格律、戲曲程式等都是如此。
如果科技愿意為藝術服務,比如為藝術觀察提供參考系、為藝術構思提供數據庫,或者是為藝術傳達提供工具與材料,那就產生了藝術科技。如果科技企圖將藝術對世界的把握納入自己的發展軌道,那就產生了藝術科學。如果科技企圖與藝術聯手發揮影響,那就成了藝術科教(電影中的科教片可以為例)。如果藝術愿意為科技服務,在科技推廣中發揮作用,那就成了科普藝術。如果藝術企圖與科技聯手進行探索,那就成了科技藝術。如果藝術企圖矯正科技的發展方向,避免科技走火入魔,那就成了科幻藝術。
正是在科幻情境中,藝術企圖制造更大的震驚。不論是現實的科技或擬議的科技,都給了藝術想象以某種基點和方向。反過來,藝術家同樣根據自己對現實需求與未來遠景的把握進行預測。二者相互融合,彼此促進,其結果通過具體藝術作品的構思展示出來。在科幻作品中常見的情況是:藝術家從自己所知的科技出發,運用類似于歸謬的方法加以演繹,將某種科技取向推向極端,使之和現有的倫理規范發生沖突,由此制造出比科技震驚更大的藝術震驚。這種傾向在世界科幻小說鼻祖雪萊夫人那兒已經顯示出來。她所創作的《弗蘭肯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的故事》(1818)既利用當時生物學已經積累的知識作為構思根據,又以天馬行空的想象超出其時生物學所處的水平,圍繞人造人講述了一個頗為悲催的故事。這部長篇小說自20世紀以來多次被改編成電影。此外,從美國《來自天上的聲音》(The Voice from the Sky,1930)和《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1933)、英國《換靈人》(The Man Who Changed His Mind,1936),到印度《印度超人克里斯》(Krrish,2006)、日本《蘋果核戰記2》(Machina,2007)、美國片《人造士兵》(Cyborg Soldier,2008)和《超能敢死隊》(Ghostbuster,2016)……有大量作品是順著瘋狂科學家遭受懲罰的路子構思的。
3. 震驚的反思
“科技震驚”至少包含了兩重含義:一是科技作為主體所蓄意制造的震驚,二是科技作為對象使人感到震驚。前者重在動機,可能和科技為傳播而謀求轟動有關。后者重在效果,可能和科技的發展之快、亮點之多、影響之大、規劃之宏偉相關,褒貶義兼備。介于二者之間的是科技工作者因反思所體驗到的震驚,即中介性震驚,像核科學家在看到自己制造的原子彈爆炸的結果之后所感到的震驚就是如此。
與此相類似,“藝術震驚”至少包含了兩重含義:一是藝術作為主體所蓄意制造的震驚,二是藝術作為對象使人感到震驚。對于前者,本雅明格外看重。他認為震驚(shock)是現代人所具有的一種普遍的社會感受和體驗,也是現代藝術作品的一種美學風格或追求。震驚體驗的產生與現代人經驗的貧乏和貶值有著密切的關系。本雅明一方面希望通過拯救貧乏和貶值的經驗來救贖藝術和現代人的心靈,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極力地推崇現代藝術的震驚體驗,希望從中發掘革命的潛能。對于后者,我們既可以從人們對與自己同時代不熟悉的各種藝術的心理反應觀察到,又可以援引人們對先前時代所留下的具有難以想象的水準、形態或風格的各種藝術的心理反應作為例證。由于藝術工作者自身的反思而體驗到的中介性震驚同樣是存在的,可能見于其作品引發了匪夷所思的反響、回顧早先創作時發現差異之大等場合。
令人感興趣的是科技和藝術互動對震驚的影響。“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本是詩圣杜甫的自嘲,若移以論當今時尚,似乎也頗為適合。以“宅”自詡的異次元藝術愛好者是如此,那些以奇異研究贏得搞笑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也是如此。對于當事人來說,博取震驚也許是一種劍走偏鋒的成功。對于外界人來說,感到震驚或許是一種心理挑戰。沒有這樣的博弈,人生便寂寞了許多。繼之而來的往往是視野融合。沒有這樣的融合,社會便生分了許多。
三、震懾:科技對藝術的發威
與震撼、震驚相比,筆者所理解的震懾具有下述特點:刺激物即使不在感官所把握的范圍內,仍然使人意識到它的威力所在;人們雖然能夠以自己的心靈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系,卻無力改變其發展趨勢或結果,即使明知這種趨勢或結果與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馳;當事人所采取的行動雖然能夠獲得某種正反饋,但比起大環境的負影響來顯得無足輕重。當下流行的網絡用語“細思恐極”可以用來概括震懾所產生的心理效果。科技目前在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震懾正是這樣起作用的。縱使我們到了周邊沒有什么人造工具的荒山老林,仍然逃不出科技的手掌心,這不僅是指衛星早已籠罩全球,也是指我們的身體早已打上了科技的烙印——從十月懷胎到長大成人,沒有一個環節少得了科技的介入。縱然我們知道科技是把雙刃劍,但也沒有辦法不用它,這不僅是指所有生活資源和生產資源都離不開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的要素,也是指如果不抓緊開發科技就無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落后就要挨打。縱使我們可以經營自己所處的微觀環境并獲得某種自由感,但在宏觀背景下,基于科技的全景監視早已無孔不入。如果說藝術通過烏托邦想象公開向瘋狂科學家叫板,那么,科技則通過引領社會變遷來重塑藝術。前者更多訴諸某種幻覺、預測,帶來純粹心理上的不安與疑慮,后者則更多見于行動、變革,造成實際生活中的沖突與矛盾。不過,科技對于藝術的發威、震懾或制約,與其說是一種赤裸裸的暴力,還不如說是一種“含蓄的震懾力”。它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 科技理性對藝術感性的制約
科技與藝術是人類把握世界的兩種方式。科技傾向于將世界有序化,譬如,工具是可以被制造的,知識是可以被驗證的,規律是可以被揭示的。藝術傾向于將世界無序化,譬如,佳作是神來之筆,靈感是不可捉摸的,天才是偶然產生的。正因如此,人們常說科技是理性的(為思辨邏輯所左右),藝術是感性的(為情感體驗所支配)。這并非否認理性對于藝術、感性對于科技的意義,只是就它們的主導取向而言。
科技與藝術分別將求真與求美作為自己的旗幟。雖然人的心理過程具備整體性,但求真更多地和認知過程相聯系,求美更多地和情感過程相聯系。科技研究必須排除偏見,避免用主觀想法取代客觀驗證。藝術創作則必須張揚個性,以情動人。科技研究有可能將冷靜當成一種肯定性品質,正如藝術創作有可能將熱情當成一種肯定性品質那樣。科技研究如果需要熱情的話,那只是由于科技工作者必須擁有與其研究相適應的內生性動機,并不是指將某種情感投射到其研究成果上。藝術創作如果需要冷靜的話,那只是由于藝術工作者在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時必須考慮所使用的傳播手段的特性、所面臨的接受對象的特點等因素,并不是指應當消除其創作成果的情感性。
人類離不開科技,正如離不開藝術那樣。盡管如此,現代社會畢竟以科技為第一生產力,因此,不論以GDP、從業人員或者經費額度、利潤規模為指標來衡量,科技所占有的地位都是藝術所無法相比的。科技理性往往有條件轉變為主流意識形態。那些脫離科學常識的藝術創意受到科技理性的嚴肅批判,被當成是迷信。在科技理性興起之后,神話與傳說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因為它們是不可由同行復制并檢驗的。科技并不是以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為目標,而是實實在在駕馭自然力。因此,當科技昌明之際,神話就銷聲匿跡了。與之遭受類似擠壓的還有仙妖、魔法、玄幻之類精神產品。這是現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2. 人工智能對藝術角色的取代
藝術歷來被視為人類特有的活動、才能或產品。盡管如此,進入信息時代之后,不僅是那些需要學徒吃苦耐勞的藝術復制環節逐漸被相對輕松的數碼加工所取代,那些需要真人演員通過涉險展示勇氣與才華的角色逐漸被數碼特效所取代,并且,那些本來仰仗天才、靈感、直覺、頓悟的領域也漸漸為人工智能所蠶食。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就不斷嘗試用計算機創作美術、音樂、文學等作品,談論“機器思維”“電腦創造性”等問題。如今,相關程序不斷完善,機器人作者已經逐漸在新聞寫作、動漫生成中獲得應用,智能化圖像軟件也已經逐漸在建筑設計等領域獲得推廣。
人工智能可否取代由人類所扮演的藝術角色?目前眾說紛紜。盡管如此,若和以計算機為龍頭的信息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相比,如今科技已經對藝術形成了一邊倒的震懾態勢。倘若說網絡時代承諾“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信息時代則宣稱“智能體都可以成為藝術家”。前者洋溢著烏托邦情調,后者蘊含著惡托邦風險,因為許多人類藝術工作者可能因此下崗。
目前的人工智能還處于由人設計和應用的階段,雖然在感知、記憶、應對、決策等方面顯示出某種與人類智能相似的特征,但既沒有自身需要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動機、態度,也沒有獨立意志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因此,人工智能在藝術領域仍然是人類的助手而已。不過,許多人早就預言上述局面發生根本變化的“奇點”。這種質變是否會真的發生,只有歷史發展才能回答。我們傾向于將有關“奇點”的宣傳視為科技對整個人類社會的震懾來理解,藝術領域所感受到的壓力不過是這種震懾的一種表現。當然,藝術工作者可以通過將自己轉變成為掌控人工智能的新型藝術家來尋找出路,變壓力為動力。
3. 科技實力對藝術精神的裹挾
科技與藝術互動的態勢取決于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做,并非所有事情都能想(存在被指為“腹誹”“犯意”等危險)。所謂科技倫理、藝術倫理正由此而來。在我國以經學為主導的傳統社會中,倫理性是對于科技與藝術的共同要求。封建倫理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學東漸等原因而瓦解,“民主”與“科學”成為20世紀新文化運動爆發以來的社會訴求。在“以美育代宗教”“言論自由”之類觀念的引導下,藝術逐漸實現了現代轉型。此后,現代意義上的科技與藝術聯手,共同為打造社會主義文明服務。
在這一期間,全球化作為浪潮在世界范圍內洶涌澎湃,逆全球化在同樣范圍內激起浪花。如今,科技與藝術互動的平臺已經不限國家,甚至也不限于區域性國家聯盟,而是聯合國這樣的世界性組織。科技交流更多被當成硬實力輸出,藝術交流被當成軟實力輸出,通過藝術展示科技實力(或者通過科技展示藝術實力)則構成了巧實力的一種形態。不論電影大片或視頻游戲,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運作的。這類文化產品通常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不僅推廣了其意識形態,且展示了其科技水準,在精神層面對被輸出國家的觀眾形成了某種震懾。由于上述心理影響存在于娛樂過程中,因此人們未必覺察得到它的存在,這正是巧實力的妙處。
藝術起源于交往,其精神實質是自由,生命力在于創新創造。在科技實力的裹挾下,藝術的交往功能可能被扭曲,自由精神可能萎縮,創新創造可能走上歧途,表現為雖然應用高新科技卻只生產出炫目鏡頭,講述的仍是老套故事(甚至是無稽之談),不僅無助于人類形成和鞏固命運共同體意識,反而可能加劇當下不同文化與文明、不同民族與種族、不同國家與國際組織間的對立和沖突。在這樣的情況下,重申藝術所應負的社會責任便是順理成章之事。
綜上所述,科技與藝術的互動在歷史上由來已久,其形態受制于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科技嶄露頭角,不僅促進藝術走上信息化、數字化的道路,而且協助藝術創造它所期待的震撼性效果。與此同時,藝術出于人文關懷等原因對科技的高速發展表達憂慮,通過在科幻情境中制造震驚的方式提醒世人保持對科技負面作用的警覺。科技理性對于藝術感性的制約、人工智能對于藝術角色的取代、科技實力對于藝術精神的裹挾,則體現了科技對于藝術的震懾。藝術與科技之間的博弈對信息時代的社會心理來說堪稱舉足輕重,因此值得深入研究。當然,我們希望這種博弈是非零和性質的。
黃鳴奮: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史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