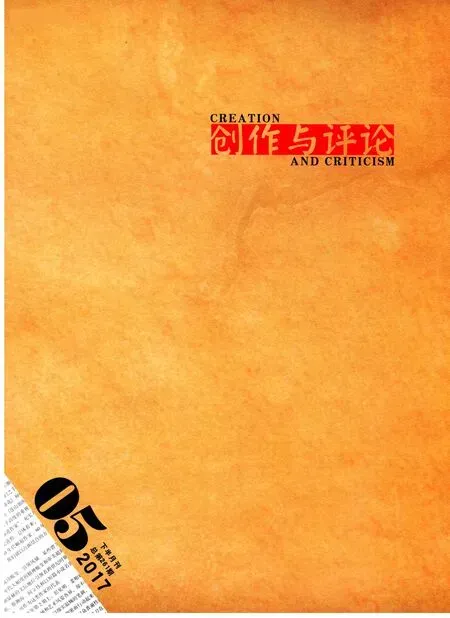融歷時性梳理與共時性探討于一體的學術建構
——劉起林訪談錄
○張露
融歷時性梳理與共時性探討于一體的學術建構——劉起林訪談錄
○張露
一、“紅色文學”研究應有怎樣的學術聚焦
張露:在對您訪談前準備資料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您新出版的學術專著《紅色記憶的審美流變與敘事境界》在2015年連續獲得了兩個全國性獎項。10月份獲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第十五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12月份又入選中國文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的“中國文藝評論2016年度優秀作品”,成為全國獲得這個獎項的9部著作之一。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請您談談您研究“紅色文學”的來龍去脈與學術思考。
劉起林:“紅色記憶”題材創作研究是我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紅色記憶的審美流變與敘事境界》是在結項成果的基礎上調整和深化而形成的。在研究“紅色記憶”審美方面,我碰到的最大問題是在國家課題已經申報下來之后,還不斷地被探問為什么要研究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色彩相當強的選題。在我看來,“紅色記憶”無疑是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集體記憶,“紅色文學”則是當代中國文學最為重要和豐富的創作題材,因此選擇這樣一個選題并沒有什么特殊性。我們過去曾批判過極“左”思潮在創作領域搞“題材決定論”,那么,現在我們在學術研究中,就同樣不能搞“題材決定論”,關鍵在于怎么去研究。
在當代文學學術領域,“紅色題材文學”的成果是相當豐富的。20世紀50—60年代的創作同評論初步確立了“紅色文學”的價值秩序,80—9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產生了不少帶質疑、否定色彩的論著;21世紀以來的多元文化語境中,對“紅色經典”的討論與爭鳴更呈現出全面展開之勢。但不少研究者往往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或全盤肯定與維護,或全面否定甚至排斥,顯示出研究者自身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我看來,文化多元的根本意義不在于能輕易找到擊敗異己立場的理論武器,而在于能獲得一種“八面來風”的思想啟迪和廣泛吸納的價值資源。所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超越20世紀中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對立思維模式,既具備開放、兼容的學術胸襟,又秉持一種在深刻體察基礎上的辯證、持衡立場。基于這種思想觀念,我選擇對“紅色記憶”這個相對客觀、中立的學術切入點,來審視當代文學史上豐富而復雜的相關審美形態,闡發其形成路徑、意義機制、價值底蘊和內在局限,從而建構起一種對于當代“紅色記憶”審美的富有學理性的理解。
張露:那么,您對“紅色記憶”這個概念本身是怎么理解和界定的?這種理解與界定又給您的研究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劉起林:綜觀中國當代文學史我們可以發現,“紅色題材”實際上是一個隨歷史發展而不斷擴充其內容范圍的創作領域,研究者卻往往忽略了從學理層面根本性地思考如何對其進行科學界定,以至“紅色題材文學”研究的范圍本身也顯得頗為混亂。我認為,這種科學界定需要以“紅色題材文學”所依托的歷史事實為基礎才有可能形成。
在20世紀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現代化的大背景中,領導人民進行了艱難曲折的階級革命和民族戰爭,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后又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事業。這種由共產黨所領導、以革命意識形態為基礎、以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為目標的社會演變和民眾奮斗史,構成了20世紀中國的“紅色記憶”。從社會文化視野來看,關于“紅色記憶”的外延大致存在著三種界定。
其一,從“紅色革命”是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社會政治運動、“紅色記憶”則是“對紅色革命的記憶”這一原初性含義出發,將“紅色記憶”界定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中國現代史上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與斗爭,時間范圍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這種思路來認定的“紅色記憶”審美成果,應該包括“革命歷史題材”和“戰爭題材”兩類創作。
其二,從“紅色政權”“紅色江山”開創、鞏固和建設的思路出發,將中國現代史上的“紅色革命”和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都劃歸“紅色記憶”的范疇,時間段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之前。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紅太陽”熱、“毛澤東”熱到21世紀初風靡一時的“唱紅歌”,都是既有革命戰爭年代的紅色歌曲,又有更多的20世紀50-70年代歌唱共產黨、歌唱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歌曲;在對“紅色英雄人物”的宣傳中,從劉胡蘭、董存瑞到黃繼光、邱少云直到雷鋒、焦裕祿,都被作為宣傳的對象;歸納十七年文學的“紅色經典”時,也是既包括革命歷史題材和抗戰題材作品,又包括小說《創業史》《山鄉巨變》和電影《英雄兒女》等表現新中國斗爭與生活的作品。這些社會文化和文學現象背后的思想依據,都在于對“紅色記憶”的上述理解。
其三,將“紅色記憶”視為一個不斷延伸的歷史動態結構,把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民眾追求獨立富強、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全部社會實踐,都作為“紅色記憶”來看待。根據這種思路,不少宣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報告與論文,都將“紅色精神”與“核心價值觀”“紅色精神”與“中國夢”融為一體進行闡述,從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再到“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航天精神”,全部被納入同一視野中進行解說。
以上三種界定中包含著兩個基本要素,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是以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為主導。從這個角度看,將戰爭年代或毛澤東時代劃歸“紅色記憶”范疇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領導中國經歷著由革命文化為主導向執政文化、建設文化為主導的社會轉型,政治上由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轉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經濟上由生產關系的公有化為中心,轉向以生產力的發展為中心;社會生活由階級斗爭為綱轉向和諧社會建設。在這個轉型期,社會文化呈多元化發展態勢。但即使如此,不斷增添著新內涵的“主旋律文化”卻與過去的“紅色文化”一脈相承,所以,“主旋律文化”也應屬于“紅色記憶”的范疇。基于這種原因,我“紅色記憶”的概念認同內容涵蓋更全面、更具歷史發展眼光的第三種界定。
“紅色題材文學”從本質上看是一種現實主義文學,以第三種概念界定為基礎,我們就可以在共和國歷史的整體視野中,從“紅色記憶”這種創作資源出發來對相關創作進行重新梳理。首先在總體框架上,認同與謳歌20世紀上半葉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時代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斗爭與生活的作品,均可納入研究的視野;以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生活為表現對象的創作中,在“主旋律文化”引導下的部分也可涵蓋于內。其次,超越現實生活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史傳統分類法,從“紅色記憶”內涵的歷史流變出發來觀察相關創作,我們可以區分出對戰爭年代革命往事的追溯,對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生活的謳歌,對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革、轉型狀態的考察三種類型,這樣,“紅色記憶”審美也就可以概括為“革命往事追溯”“建設道路謳歌”和“變革時勢考察”三種敘事境界。
張露:我研讀您的《紅色記憶的審美流變與敘事境界》時有一個問題感到相當疑惑:你在對“敘事境界”的歸納和區分中專門將“創傷記憶審視”作為了一種類型。我們一般都認為“紅色文學”“紅色經典”都是歌頌“紅色歷史”“紅色文化”的,兩相比較,您的這種學術框架顯得相當獨特。請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劉起林:“紅色題材文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性難題,是如何處理以革命進程中的錯誤與創傷為審美對象和思想主題的創作。這類作品與我們對“紅色題材文學”屬于“頌歌”型的通常理解不一致,但確實又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巨大存在,因此,我們視而不見是不可能、也是不應當的。
總體看來,人類歷史上的任何重大進程都是既有勝利與輝煌、也有坎坷與失誤的,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斗爭同樣如此。它給革命事業和革命隊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給歷史當事人帶來了沉重的犧牲與傷痛,特別是歷史錯誤的承受者,更有可能存在精神上難以化解的委屈與失落感。即使革命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歷史當事人在激情洋溢地投入之后再辯證地回味往事、考量得失,心中往往也會產生付出巨大代價后的缺失與遺憾感。更為吊詭的是,如果歷史當事人以正面參與者的身份和高度認同的態度投入某項革命運動,事后卻發現那不過是一場歷史的錯誤,精神心理的創傷與荒謬感就更是在所難免了。甚至“紅色記憶”本身,也會因歷史的前行和記憶的規律而不斷出現價值評判、情感傾向的轉變與位移。正因為如此,在“紅色記憶”的豐富內涵中,必然會存在種種意味復雜的“創傷記憶”。
在當代“紅色記憶”審美的歷程中,“創傷記憶”有著豐富的藝術表現。十七年文學中那些“干預生活”、在新時期“重放的鮮花”,就是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瑕疵”及其所導致的心理創傷的揭示與批判。20世紀80年代,展現革命歷程中的“創傷記憶”成為思潮性的創作現象,眾多“反思文學”作品都站在革命誤區承受者的立場,來品味歷史創傷、總結經驗教訓;揭示“黨史”“軍史”重大問題與內在矛盾的創作,也出現了如黎汝清《皖南事變》之類的優秀作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將革命事業的輝煌與誤區、喜悅與創傷融為一體進行表現更成了普遍的趨勢,《歷史的天空》將描述紅色英豪成長和揭示根據地內部矛盾融為一體,《戀愛的季節》對20世紀50年代初的“青春加革命”眷戀、認同與慨嘆、剖析兼而有之,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證。既然“創傷記憶”屬于“紅色記憶”的歷史與文化構成中不可忽視和抹煞的重要存在,那么,傾訴與反思這種“創傷記憶”,就是對“紅色記憶”意義正值的有力的豐富、深化與拓展,將其納入“紅色記憶”審美研究的范疇,也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不過,我并不認同將各種解構“紅色革命”、否定“紅色文化”的創作都看做是“創傷記憶”書寫。“紅色記憶”作為對中國紅色革命的感受與認知,在根本價值立場層面隱含著一種對“紅色革命”和“紅色文化”的認同態度,所謂“記憶”中對經驗過的事物的識記、保持、再現或再認,就包含著置身其中、也就是作為革命隊伍一員的心理態度。所以,“創傷記憶”的審美主體應該秉持一種“療治”創傷、健全和完善革命肌體的精神立場。比如,王蒙小說的“少共”情結和“布禮”心態、張賢亮《綠化樹》中的《資本論》閱讀和“走向紅地毯”場景,都昭示著一種“置身其中”的精神姿態;與此相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描寫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政治生活,但作者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敵對性的暴露、控訴立場,所以,前者應納入“創傷記憶”的范疇,后者則不能歸入。這二者之間的差異與對比,相當清晰地體現了“創傷記憶審視”的外延邊界。
總之,以“紅色記憶”為根本出發點,遵循客觀事實的存在形態及內在邏輯,我們完全應該在“革命往事追溯”“建設生活謳歌”和“變革時勢考察”之外,將“創傷記憶審視”也納入研究的視野。這樣,相關研究才能超越各種不同方向的觀念至上、立場唯一的學術思路,以“理解比評價更重要”的思想態度,創新性地建構起一種全面性與辯證性兼具的“紅色題材文學”研究的思路與框架。
二、“跨世紀文學”的學術構想
張露:相對于《紅色記憶的審美流變與敘事境界》這種歷時性梳理和共時性探討兼顧的學術框架,您的另外一部學術專著《勝景與歧途:跨世紀文學的多維審視》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共時性展開的特征。但《勝景與歧途》出版后也反響良好,獲得了上一屆、也就是“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請談談您對“跨世紀文學”的相關思考。
劉起林: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展開的是一種創作跟蹤性質的研究,所以對文學發展狀況相當熟悉。當我回過頭來,對我一直共時性觀察的學術對象進行一種歷時性的梳理和全局性的歸納、總結時,我發現學術界的一些判斷和提法并不符合客觀呈現的文學事實。所以,我在《勝景與歧途》中貫穿了一個基本想法,就是希望以中國文學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的發展與轉型生態為觀照對象,捕捉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要現象和關鍵問題,將具體個案剖析與全局態勢考察、文本內涵解讀與意蘊生成機制探尋結合起來,實事求是、論從史出地探討這一時期的文學領域到底呈現出怎樣的精神走向、審美得失和內在文化邏輯。
具體說來,學術界對20世紀90年代后的中國文學,習慣于以“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來界定與區分。在我看來,這種界定簡明扼要,局限性也相當明顯。首先,這種界定起源于文學評論界對文學創作按年代所作出的粗略概括,并不具備深厚的學理根基,也不是對定型的文學歷史時期的歸納與總結,因此不是嚴謹的文學史概念。其次,從客觀歷史事實看,20世紀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都與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共名”狀態存在著巨大差異,但這兩個階段內部具有明顯的歷史連貫性,并未出現可劃分為不同時期的顯著標志,“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的概念卻使它們之間人為地構成了巨大的“斷裂”。所以,在新型文學格局已基本確定、文學面貌已較為全面展開之際,重新理解和闡釋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間的中國文學就顯得很有必要。
從民族歷史發展的高度看,近現代中國始終處于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民族文化也處于相應的轉型狀態。其中又可區分為以追求獨立、解放為主線的“革命文化”階段和追求富強、文明為主線的“建設文化”階段。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革命文化”并沒有隨之結束,而是以“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和“撥亂反正”的新旗號,延伸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新時期”。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社會才真正步入由政治本位到經濟本位、由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將崇高與世俗兼收并蓄的“建設文化”狀態。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間的中國文學,就處于這樣一種以社會與文化轉型為基礎的、向新型文學生態與審美格局演變的狀態。所以我認為,如果從文學發展與時代文化整體格局關系的角度,以整個社會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設文化”轉型的客觀實際為歷史和理論基礎,將20世紀90年代“新時期文學”終結與轉型的狀態,和21世紀前10年新型文學面貌與審美格局逐漸形成的階段,作為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歷史進程來考察,并以“跨世紀文學”的概念來統馭和界定,也許能夠更準確而深入揭示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價值內涵、審美文化特性及其歷史文化意義。
以上的梳理說明,《勝景與歧途》雖然章節框架所顯示的是一種共時性展開考察的格局,內在的學術思路卻蘊藏著強烈的、甚至是很深厚的歷史眼光,其實是處于一種共時性展開和歷時性追溯相結合的思想狀態。
張露:您在《勝景與歧途》中選擇了四種創作現象作為重點論述對象。您認為,從文化底蘊的角度看,“跨世紀文學”最值得關注的當屬歷史文學的異軍突起和持續興盛;從作家隊伍及主體精神建構的角度看,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現象應為知青作家群的精神分化;從審美價值和思想文化影響的角度看,“百年反思小說”構成了足以與中國新文學史上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相抗衡的優秀作品群;“跨世紀文學”最具圖書市場效應的,則是“官場小說”。應該以這些文學現象為關節點,才有可能充分地呈現“跨世紀文學”多元共生的創作態勢和審美格局。我覺得這種將文本審美建構與文化生態考察融為一體的思路很有層次感和立體性,那么,通過這種考察,你覺得“跨世紀文學”表現出哪些基本特征?
劉起林:我認為,因為中國文化呈現出全方位轉型的狀態,對于“跨世紀文學”也不能僅僅從文本出發,而應該在審美文化的開闊視野中來觀察和理解。從這樣的視野來看,“跨世紀文學”表現出以下方面的重要特征。
在審美意蘊建構方面,“跨世紀文學”表現出多元發展和多向度精神跨越、審美深化相融合的特征。“主旋律文學”方面,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小說”彰顯著呼喚體制變革的思想激情;“跨世紀文學”中,張平的《抉擇》和《國家干部》、周梅森的《人間正道》和《中國制造》、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和《省委書記》等作品,則表現出從激情呼喚向深切批判的跨越與轉變。“官場小說”方面,“新寫實小說”意在惟妙惟肖地勾勒凡俗之人在權力網絡中卑微、無聊、爾虞我詐的日常生態;“跨世紀文學”中,王躍文的《國畫》和《蒼黃》、閻真的《滄浪之水》等作品則從人生品質蛻變、精神心理困苦、生命意義迷茫等深層次出發,揭示出中國社會官本位生態中典型的人生命運與人格特征。在反思20世紀中國歷史方面,80年代的“新歷史小說”和“跨世紀文學”中的“百年反思小說”,藝術內蘊和審美風范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種差別表明,“跨世紀文學”確實對既成藝術思路構成了極富精神跨度的境界拓展與審美深化。
在審美資源發掘和精神思路選擇方面,“跨世紀文學”體現出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的特征。新時期文學中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直到“新歷史小說”,都存在話語基點單一、思想主題“共名”的特征。“跨世紀文學”中,從莫言的《檀香刑》、鐵凝的《笨花》、張一弓的《遠去的驛站》等近現代歷史反思類作品,到賈平凹的《秦腔》、王安憶的《啟蒙時代》、蔣子龍的《農民帝國》、鄧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等當代生活審視類文本,直到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范穩的《水乳大地》、楊志軍的《西藏的戰爭》等邊緣敘事類作品,審美內蘊建構都是以揭示中國的社會歷史本相為旨歸,力求將西方文化、中國當代現實主義傳統和中國傳統乃至民間文化等各種審美資源融為一體,在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基礎上進行一種自創新境式的藝術創造。
在歷史演變趨勢方面,“跨世紀文學”呈現出藝術形態豐富性與文化精神不成熟性并存的特征。“跨世紀文學”呈現出各種思想立場、題材類型、審美境界和藝術技法的創作“眾體皆備”的景觀。甚至“十七年文學”革命現實主義的思路,也有劉白羽的《第二個太陽》、魏巍的《地球上的紅飄帶》出現;20世紀80年代“傷痕文學”的敘事境界,也有老鬼的《血與鐵》、潘靖的《抒情年代》、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問世。但文化精神的不成熟性也多方面地表現出來。不少引起廣泛關注的作品均褒貶不一、反差極大。賈平凹的《廢都》、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王躍文的《國畫》、莫言的《檀香刑》甚至出現了帶有“事件”性質的爭論。大量被推崇為“經典”“大師”“高峰”的作品一旦進入具體的文本分析,就顯出難以經受多方位檢驗的平庸之態。長篇小說“茅盾文學獎”面對“官場小說”“盜墓小說”等新型文學形態的“叫板”,也顯得捉襟見肘,似乎“理屈詞窮”。在探索性創作中,作家們立意糾正當代文學“假大空”的弊端,卻步入了“邪祟”“病態”的境界;立意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卻走向了民間的“藏垢納污”之處;力求回歸中國傳統審美境界,卻戀上了傳統文化的陳腐趣味。所以,“跨世紀文學”雖然思路活躍、類型豐富,卻眾體雜陳、良莠難分,而且各種思想路線之間難以達成價值共識,出現了許多看似輝煌的“幻景”和貌似正道的“歧途”。
總的看來,“跨世紀文學”已經突破各種固有的審美與文化模式,卻還處在走向成熟的歷史過渡性狀態之中。這種歷史過渡性狀態,正是中國社會從20世紀“革命文化”向21世紀“建設文化”的歷史轉型在文學領域的表現。
三、在創作跟蹤評論與專題學術研究之間
張露:您曾經是有一定影響的評論家,以研究當下的長篇小說和文學思潮著稱,但從您的著作來看,您已經完全進入了對文學史特定領域的專題性研究,具有很強的學理性和“學院派”色彩。請問您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有什么感受?
劉起林:我最初確實是從文學評論起步的,碩士期間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研究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的,當時還產生了一些影響,后來也一直沒有間斷對長篇小說和文學思潮的跟蹤研究。但讀博士以后,我又增添了一個“疏離當下”、學理性較強地展開當代文學專題研究的學術空間。這種轉變本身自然是我自己認真思考后的選擇,談到感受,從社會層面看最主要的應該是一種不無尷尬的矛盾性。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有意回避“評論家”這個稱號,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所謂“評論家”,就是“我出了本書,你給我說幾句好話吧”;或者“那個著名作家新出的書其實很‘臭’,你寫篇文章把它罵一頓吧”;或者是評獎時“你要給我投票啊!”在這種狀態中跑跑顛顛,看起來很風光,其實時過境遷后就會發現自己沒有真正結實的學術成果。所以我很想把“評論家”的帽子遠遠地拋到身后。等到我轉而寫“學院派”研究性質的文章、往“學者”的方向靠攏時,卻又不時會有人說:“你寫些那樣的東西有什么用,根本沒人看!出本書還要自己掏錢!”雖然對“自己掏錢”的事往往可以用“我有課題經費”來加以抵擋,但論文發表、專著出來之后連自己可能都不會再讀一遍,卻也是“學院派”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事實。甚至某些學者自身也難耐“坐冷板凳”,顯得“沒有才氣”“沒有社會影響”之苦,有些學術同行聽說我曾經“做文學評論”而與許多作家熟悉,往往會倒過來羨慕我過去的狀態。是耶非耶,得乎失乎?可以修改一句名言來解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求仁得仁,自己心安就可以了吧。
張露:當前的文學評論實際上是相當豐富的,評論文章在報紙、刊物、網絡乃至各類官方文件中“全面開花”,五花八門的評獎、排行榜也以學術或媒體權力的方式參與到了文學評論之中。但人們對于文學評論的狀況還是普遍地不滿意。您認為當前的文學評論最缺乏的是什么?對于創作跟蹤評論和專題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您又有什么看法?
劉起林:就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而言,我認為,文學評論是以學術的方式參與當下的社會文化建設,學術研究則是對各種文學與文化現象進行貫通來龍去脈的考察與探討,二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就學術研究而言,當代文學研究面對的是一個“現在時”狀態的學術對象,在這個研究領域中,資料的收集、積累和儲備作為學科發展的基礎性工作雖然相當重要,但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資料本身的查找其實并不繁難,對資料的深入研讀與具體感悟以及由此形成的問題意識實際上才更為緊要。問題意識的生長點,應該就存在于活生生的、不斷變化的文學創作和社會文化實踐之中,所以,學術研究不感受當下創作的活力,就很容易固化、僵化自我的思維和視野。反過來,人們對當前的文學批評狀況普遍不滿意,我認為關鍵在于,眾多文學評論性質的判斷與言說都缺乏充分的學理性和真正的歷史感。大量“我認為如何如何”之類的評論與判斷,其實是缺乏對“所以然”的深度闡釋的,而且放到較長的歷史時段中去看那種評論與判斷到底是否深刻和準確,從評論者到被評論對象再到廣大受眾,也大都是沒有充分把握的,于是,許多文學評論就成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表演和“作秀”。所以在我看來,深刻的問題意識,以及問題確立和闡述的學理性和歷史感,在當前的文學評論中相當缺乏。正因為如此,我所希望自己形成一種將專題研究和創作評論的優長融為一體的學術建構。
張露:劉老師,您在來河北大學文學院工作之前,曾經在長沙、上海、杭州和廣州等多個城市學習或工作過,我們還知道您對湖南老家的文學界情況比較熟悉。您專門研究湖南文學的學術新著《“文學湘軍”的跨世紀轉型》又即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請您就這方面的情況向我們做一些介紹吧。
劉起林: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還是湖南師大中文系的碩士生,就參與了湖南文學界的不少活動,開始了對“文學湘軍”的研究,也因此結識了湖南文學界和學術界的眾多師友。湖南文學研究由此成為我學術研究的起點。后來,我由于求學和工作的原因輾轉于全國各地,個人學術興趣也產生了巨大變化,但湖南長沙始終是我時常重返的一個“根據地”。我的《“文學湘軍”的跨世紀轉型》所論述的作家們,就都在我的湖南師友群體之中。遙遠的湘江水靜靜流淌,河風吹老少年人,我關注“文學湘軍”不覺已20多年了。當初湖南文壇的“中堅”們已逐漸進入了創作的“尾聲”階段,那些和我一樣的“初出茅廬”者也大多完成自己的高峰之作,水過中流日過午了。所以也到了該對我的湖南文學研究做一個總結的時候了。
《“文學湘軍”的跨世紀轉型》這本書所著重論述的,實際上是湖南文壇繼20世紀80年代古華、莫應豐、葉蔚林那一代之后的一個代際創作格局,以及由這一代作家的創作所構成的湖南文學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跨世紀”歷史進程。如前所述,我認為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余年之間其實是相通性遠遠大于差異性的,這20余年共同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跨世紀文學”時期。《“文學湘軍”的跨世紀轉型》就是我對“跨世紀文學”的學術思路進行深化和細化的一種“個案研究”。我這本書依舊是縱向追溯與橫向剖析相結合,既從歷史宏觀的角度,揭示“文學湘軍”跨世紀格局的來龍去脈、歷史定位;又以實力派作家的創作為坐標,闡明“文學湘軍”在跨世紀轉型過程中的特征與成就。我希望形成一種在史料和歷史邏輯層面梳理湖南文學60年、從內涵與價值底蘊層面講清“文學湘軍”跨世紀20年的學術境界,使這部專著成為我建構“跨世紀文學”學術判斷的一份“田野調查”。
這本書所研究的對象都是對我情深誼重的師友,但按照我曾戲言的“思想無禁區,理論無權威,學術無頂峰”的研究原則,我秉承一種有理有據、直言無諱的言說姿態,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以學理性和建設性兼具、有見解有啟發為學術宗旨,其他方面則顧忌較少。好在湖湘文化向來崇尚實事求是,師友們又諳熟我的個性與為人,我的這本書也不是嚴格意義上排座次、定優劣的文學史,所以言長說短應當也無所妨礙。
張露:最后我們想了解一下你未來的研究計劃,不知能否透露一點相關信息?
劉起林:《“文學湘軍”的跨世紀轉型》出版以后,我的下一部著作是《當代歷史文學的主體意識與文化精神》,已經與人民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然后我將以當代抗戰題材小說作為研究對象。這樣,“古代史題材創作研究”“‘紅色記憶’審美研究”和“抗戰史敘事研究”,共同構成了我對當代“歷史題材創作”的系列研究。“歷史題材創作”和“跨世紀文學”兩個系列研究,就是我目前能確切地講出來的大致研究框架。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