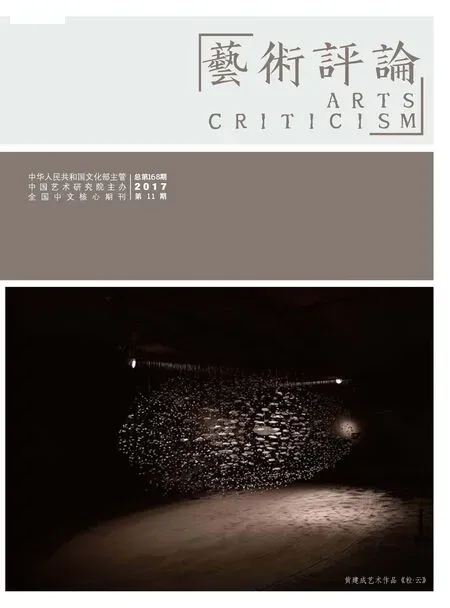數字媒體影像時代的未來書寫
——中美科幻電影的賽博空間與賽博格身體的文化想象
陳亦水
21世紀之后,隨著電影特效技術的日新月異與智能時代的到來,賽博空間(cyber space,亦稱“網絡空間”)和賽博格(cyborg,亦稱“人機一體化”)被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這些1960—80年代的舊詞匯,大量活躍于當代主流科幻電影的創作之中。
冷戰時期,好萊塢科幻電影迎來了第二個黃金時期,一系列以太空旅行為題材的科幻電影作品成為經典之作。相比之下,21世紀主流科幻電影則以賽博空間和賽博格身體為主要表現對象,更具有未來面相,而這些充滿后人類主義色彩的科幻元素,不僅與西方科技文明的發展保持同步,還是歷史上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和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當代延續。
而反觀近年來中國科幻電影的未來書寫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西方的文化邏輯與價值系統中進行創作的。在此意義上,厘清賽博空間、賽博格在西方流行文化語境下的演變過程,有助于反觀中國科幻電影創作的文化邏輯,進而為中國科幻電影創作尋找突破西方為中心話語體系的可能性。
一、美國意識形態的賽博格銀幕化身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觀察,當代科幻電影對于賽博格身體的塑造,不無明顯地呈現出一種對于性別、種族、民族、宗教、階級等等意識形態身份的重塑狀態。這一重塑狀態直接將現實的文化身份問題,引向了一種后人類主義式的、關于未來的文化身份想象。
作為一個技術術語,“賽博格”指涉的是一種“自我調節的人機系統”(selfregulating human-machinesystem),亦即人機合成體。最早提出“賽博格”假設的是美國數學家、控制論之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他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論》(Cybernetics)一書中,通過邏輯嚴謹的數學推演方式設計出自動機器人的控制系統,維納的機器人是建立在“信息(information)—反饋(feedback)”的控制系統之上,而“研究反饋的任務需要建立在工程學設計和生物學研究的共同合作基礎之上。信息、檢測和傳輸信息技術的研發,則需要工程師、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所有學科研究人員共同努力”。維納認為,人、動物、機器沒有本質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科幻電影的創作。不過,在大眾文化領域里,1930年代的早期科幻片尚未從B級片定位和恐怖片類型中獨立出來,正如《科學怪人》里的弗蘭肯斯坦仍以中世紀的怪物為主要原型,西方科幻文學作者與電影人,尚未認識到弗蘭肯斯坦這個科技與野獸雜糅體身上所具有的強大的未來魅力。
但在政治領域中,美國政府努力地將弗蘭肯斯坦強大的未來魅力付諸實踐。1960年代,美蘇大國太空爭霸賽期間,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試圖在軍方支持下,試圖通過機械、藥物等技術手段對人體進行拓展,以增強宇航員身體性能,使其變成一個“自我調節的人機系統”,以適應在太空環境下無負擔地生存、作業,同時對蘇聯方面展開軍事行動。
美國好萊塢的科幻電影的第二個黃金期,恰恰誕生于美蘇太空爭霸賽如火如荼的70年代。美國導演喬治·盧卡斯,充分認識到弗蘭肯斯坦這一未來屬性,于是他將這頭中世紀怪獸從30年代的恐怖片類型中“解放”出來。1977年,盧卡斯制作了影片《星球大戰》,故事里可以在外太空行走、具有超強戰斗力的帝國沖鋒隊暴風兵,就是美國軍方研制的賽博格身體的銀幕化身,極具濃厚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
美國后現代女權主義人類學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理論上將賽博格身體的后人類主義討論,引向了一條推翻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反叛道路,旨在強調“女權主義—社會主義”身份政治的建構問題。她在《賽博格宣言》里宣布,一個賽博格統治的后人類時代業已到來。所謂賽博格身體,是一種“控制論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一個“生物體與機器的混合雜交物,是一種社會現實,也是一種虛構的創造物。”哈拉維認為,賽博格身體是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身體,而女性身份恰恰是在于父權制度下被壓迫的一種性別認同,她由此推論,賽博格時代將帶來一種新型的權力統治與反抗壓迫的關系,這需要全球婦女實踐的參與。時至今日,“賽博格電影永恒的主題,是關于控制的科學事業”,人機雜交體承擔的是一種反烏托邦修辭,抒發的是“與器官移植、輸血和外科移植手術失敗的類似焦慮”,表達的是“基于現代醫學科學的緊張,更直指生化科技或許是無法超越身份/認同的后人類”。盡管在西方電影中,賽博格主題的確以西方科技的(反)烏托邦面目出現,某種程度上治愈著西方人對醫學生物科技的恐懼,例如“蜘蛛俠”系列電影中發生變異的蜘蛛俠、“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中的具有特異功能的變異人等等,但經過一套完整的“超級英雄拯救地球”的好萊塢文化邏輯的編碼,“現代醫學科學的緊張”與“外科手術失敗的類似焦慮”,巧妙地轉化成為某種“充滿費勒斯中心主義幻想的福特主義模式”,無不彰顯了美國資本與軍事力量。
不難看出,賽博格理論在理論層面上具有反主流文化的激進特征,但現實中的美國科幻電影對于賽博格身份的塑造方式,則體現著美國主流文化價值觀念。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后,銀幕上的這些賽博格身體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表現為“脆弱的、后現代模式的,因為它們遭受著不斷的爆炸”。這是當代美國反恐意識形態在大眾文化領域的顯影,直接投射出美軍與伊斯蘭世界軍事對抗的挫敗和焦慮。例如,美國漫威電影工作室第一部獨立投資、制作完成的大電影《鋼鐵俠》(2008)里,主人公托尼·史塔克第一次試驗鋼鐵俠戰服成功之后,便穿上它瞬間降落到中東地區的伊拉克、干掉了幾名恐怖分子,作為賽博格的銀幕化身、美國最受歡迎的超級英雄之一,鋼鐵俠第一次亮相就旗幟鮮明地宣布了他的身份立場:全球范圍內打擊中東恐怖分子,捍衛美國與全人類的世界和平。
此外,還有影片《源代碼》(2011)中在伊拉克反恐作戰中腦死亡的、肉身不完整的海軍陸戰隊員,依靠電腦聯線人體的交感神經系統,一次次地“回到”開往芝加哥的列車爆炸之前的時刻,其靈魂進入車上一名陌生乘客的肉身,繼續開始他“生前”在現實維度的反恐任務;《阿凡達》的主人公,也是一位人類身體有缺陷的殘障人,同樣也是依靠電子交感技術重組,在充滿“交感幻覺”的虛擬現實潘多拉星球中成為一名能跑會飛的阿凡達戰士;還有《極樂空間》(2013),將未來設定為一個地球內外兩極貧富空間,窮人在地球上開礦、生產,為生活在太空的空間站里的富人提供補給,地球上的男孩成為一名依靠生化控制系統操作的超強機甲人,他依靠后腦勺嵌入的機械交感系統而控制全身的金屬骨骼,使之能夠以一敵百……無論是開往芝加哥列車上的平民乘客,還是異星上的阿凡達,或是貧窮的“地球人”機甲人,都是各種形式上的賽博格人類身體,而這些在人類肉身基礎上的賽博格身體的重組,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人類肉身自身缺陷不足,進而完成了對當代美國文化身份的重組,以及對主流價值觀的修復和再次肯定。
二、賽博空間影像的反烏托邦思潮之退場
世界電影特效技術的日新月異與科幻電影創作的發展,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首先,電影史論界將1976年《星球大戰》的制作年稱為“特技效果的新生”(電影正式公映于1977年);其次,1999年沃卓斯基兄弟(姐妹)導演的《黑客帝國》,以360°擺放照相機的方式拍攝的“子彈時間”(bullet time)這一攝影技術的成功運用,標志著科幻電影上升至一個新的歷史臺階;最后,2007年,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電影《阿凡達》,全面提升了動作捕捉和虛擬攝影的特效技術的水準,其誕生年份被譽為“3D電影元年”,引發了全球觀影風潮,使之成為一部青史留名的佳作。
科幻電影技術對于虛擬現實空間影像的表現力的不斷進步,都旨在詮釋“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生活”,千禧年之后的世界科幻電影創作,在銀幕內外高調宣布著一個指向未來人類現實生活的賽博空間時代的到來;賽博空間從此成為科幻電影中主要展現電影特技的奇觀場域。
在賽博空間正式登場之前,從空間塑造上來看,美國科幻電影空間的文化表達主要以大航海時代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為主。當代后殖民理論的學者們認為,《星球大戰》開啟的70年代好萊塢科幻電影黃金期中,類似于“星際迷航”“星球大戰”“異形”等系列電影的空間想象方式,表露出美國人對于“第三世界”領土及其種族與文化,實際存在著某種“矛盾的帝國主義”(ambivalent imperialism)情結,故事中的星際聯盟、星際艦隊、生化軍隊等人類為主體的社群,對于外星人通常采取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入侵行為,以防止異類的自然進化。這些未來書寫方式,某種程度上隱含著對于“異形”(alien)身份的想象方式,直接來源于美國本土社會對于黑人等有色人種的外來移民的恐懼和排斥心理。以星際開拓為主題的美國好萊塢科幻片中,對于地外太空的空間想象和宇宙英雄身份的認同方式,有著歷史上的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傳統和現實中的種族主義文化邏輯在其中。
直到1980年代,隨著個人計算機在西方社會的普及、互聯網技術的發明與電腦游戲玩家文化的流行,賽博格人機混合技術的概念,催生了“賽博空間”(cyber space)的誕生,為科幻文學寫作與電影創作帶來了一個關于未來空間的全新想象。其中,賽博空間中的賽博格身體,成為這一時期賽博朋克流行文化的主題,其身份政治之復雜性,理論上為科幻文學和電影創作打開了更廣闊的文化空間。
1984年,美國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出版了反烏托邦科幻小說《神經浪游者》(Neuromancer),他定義賽博空間是一種依靠計算機模擬出來的“交感幻覺”(consensual hallucination),推動了文學和藝術界的“賽博朋克”(cyberpunk)運動。所謂賽博朋克文化,指的是“一群生活在反烏托邦未來的高智商罪犯,生活并困在一個由技術所統治的人口過剩與都市退化的世界。這個世界由計算機無限的力量所控制,同時,廣闊的計算機互聯網絡也為高智商罪犯們提供了新的空間。通過計算機進行時空旅行是罪犯們的家常便飯,他們在這個電腦化的未來里依靠竊取和買賣信息和虛擬貨幣為生”。這種具有反烏托邦色彩的未來書寫,正是20世紀80年代科幻文學的主題。
那么,如何分辨賽博格與人類身份呢?當維納的賽博格設想把人類、動物、機器三位一體地視為一個有機運行系統時,就已經將人類身份推向了被質疑的位置。幾乎與維納創造“控制論”的同時,服務于英國軍事情報系統的計算機之父與密碼學家阿蘭·圖靈(Alan Turing),開始研究人工智能機器與人類身份的區別;1950年,他設計出來家喻戶曉的“圖靈測試”(The Turing test)。美國后人類文學評論家凱瑟琳·海爾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們如何成為后人類》一書中提出,圖靈測試是一種存在悖論的分辨人機身份的方案,因為它所證明的是“扮演和再現身體的疊加,再也不是一種自然的必然性,而是一種因情況而定的生產,這是一種由技術決定的關于身份的生產,并且不能從人類主體中分離開來”,無法脫離于人類主體的分辨方式,卻反身證明了電腦或者人工智能的無法分辨性,更重要的是它與人類難以區分,正如難以從根本上劃分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性別身份一樣。海爾斯進一步指出,在知識爆炸的時代里(20世紀的最后十年),相反,人類的肉身只是后人類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信息和人性一樣,擁有“具身化”(embodiment)的特征,例如它依附于物態的實體,可以被毀滅卻不能被復制,一個后人類和人工智能一樣,在接收了外界信息之后,可以在自身內部形成了一個“信息反饋回路”(informational feedback loop),這樣一來,所謂自我就成了一個具有流動性的、多種形態的實體。海爾斯用了這樣一個比喻后人類身份的特征:“當你凝視著電腦熒屏上向下滾動的閃爍的光標時,無論你具體屬于哪種實體的身份認同,你便已經成為了一個后人類了。”
在西方科技史上,圖靈測試的出現,被人們追加為后人類時代的到來,這也是《銀翼殺手》(1982)、《人工智能》(2001)、《機械姬》(2015)等科幻電影中反復出現的賽博格身份認同主題,然而這些影片中的關于賽博格身體的文化政治表述則大相徑庭。
美國導演雷德利·斯科特拍攝的賽博朋克色彩濃厚的影片《銀翼殺手》,根據反烏托邦科幻小說巨著《仿生人夢見電子羊了嗎?》改編,講述一名生活在核爆之后的都市警察抓捕仿生人的過程中,卻發現自己可能是一名仿生人的故事。創作者將人類與仿生人身份的討論,上升至美國文化主體中的自我與他者身份異質性雜糅的反思維度。故事里,人類警察主人公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員,表現為一個充滿現代科技文明與美國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創傷的身體;影片里的仿生人(即賽博格)也沒有簡單地被視為外來移民與少數族裔的化身“外星人/異形”(alien),而是旨在反思自我與他者之間不可分割的文化雜糅特性。
在今天的主流科幻電影創作中,賽博空間的表現力極大地推動了科幻電影創作在影像與敘事上的雙重革新。《阿凡達》中藍色的奇異潘多拉星球、人類與克隆納威人之間依靠電子交感傳輸系統進行溝通的大膽想象,如今已成為展示視覺影像奇觀的想象力的基本來源。人們對于想象力的影像實踐方式,必然離不開數字虛擬技術的電影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從地域空間的塑造與文化身份的建構來看,賽博空間與身體的想象與創造,在世界電影工業生產中已成為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邏輯的定勢思維,延續著“賽博格”詞匯誕生之初的冷戰意識形態,成為這個電影“賽博格帝國”內在的文化主導策略。
隨著冷戰的結束,曾經在《神經浪游者》《銀翼殺手》等反烏托邦科幻小說中不斷出現的賽博格身份認同困境,在近幾年的科幻電影中被表現為一種積極、向上、肯定美國社會主流文化價值觀的面相。這是千禧年之際的《黑客帝國》和2007年的《阿凡達》對于賽博空間的主要表達主題。賽博空間看似為科幻電影創作打開了一個更廣泛的空間,但是正如美國科幻電影研究者凱文·羅賓斯(Kevin Robins)清醒的批判,在大眾文化生產中,賽博空間所帶來的烏托邦視覺建構方式帶有強大的欺騙性,一個基于現實的仿真世界誕生了,新技術看似可以為人類創造一個新的烏托邦世界的可能、讓人類以為賽博空間創造出來的仿真世界意味著對現實世界的某種解決方案,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視覺文化讓人類變得更加厭倦舊事物和陳腐之物。在此意義上,《黑客帝國》系列電影并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反烏托邦科幻作品,而是一種以反烏托邦的科幻敘事手法,對主流文化及其統治結構進行認同。除了第一部《黑客帝國》(1999)具有人類身份覺醒、底層反抗獨裁統治的激進意味之外,在《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2003)和《黑客帝國3:矩陣革命》(2003)里,人類生活的現實錫安與“母體/矩陣”(Matrix)統治的反烏托邦現實和烏托邦賽博空間,其實都是母體/矩陣所設計出來的程序。換言之,在“黑客帝國”系列電影中,革命被想象為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是修復和改良統治階層的內在設定。北京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學者戴錦華教授近年來十分關注科幻電影,在針對《黑客帝國》的解讀中,她強調:“雖然現在在數碼特效上相當用力,但在故事的選擇、結構的編織上都有點弱,包括故事深度、角色深度,乃至科學幻想的深度,則進行了玄學化的處理”,三部曲系列進而從一個賽博朋克文化的反烏托邦科幻傳統的反思,最后逐漸淪落為“反叛的領袖與統治的集權者其實是朋友,壓迫與反抗是結構好的游戲”的模式,人類反抗者最終選擇與計算機握手言和、擁抱科技文明。從沃卓斯基兄弟(姐妹)對于賽博格身體的塑造方式來看,人們想象革命的方式與反烏托邦敘事,本質上是反—反烏托邦式的、反—反主流文化激進革命的。所以,人類與母體/矩陣最后達成了協定,也就消解了賽博朋克反烏托邦科幻寫作傳統內在的反主流文化的激進力量,最終達成了對主流社會及其統治機制的認同。
《黑客帝國》系列對于賽博朋克文化的改編方式與賽博空間的未來書寫策略,在21世紀之后的科幻電影中不僅繼承了下來,還在“后9·11”時代語境下,轉變為一種反恐演習的虛擬訓練場,在包括《源代碼》在內的影片里成為宣揚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陣地,1980年代的反烏托邦科幻文化創作傳統就此退場。
三、中國科幻空間與未來身份定位
從當前為數不多的中國科幻電影創作中可以發現,中國科幻電影創作中的賽博格虛擬現實空間的想象與文化參照,始終以西方科幻電影為準繩。
在科幻電影的塑造方面,中國人對于地球的關注度在某種程度上要大于美國科幻電影。相應地,中國科幻電影對地表之外、架空現實的賽博空間的表述力,則相對羸弱很多。更重要的是,賽博空間的想象能力指向的是一條通往未來人類生存空間的想象之路,中國電影則整體呈現出創造力方面的匱乏,取而代之的只是一味地追求科幻空間的視覺奇觀效果,反而使得地外空間、賽博空間的文化坐標曖昧不明,這些架空現實的虛擬空間所定位的文化身份位置,也因此語焉不詳。
例如,影片《長江七號》里唯一呈現宇宙空間的方式,是小狄躲在黑暗的衣柜里,依靠不明的外星生物所散發出來的全息影像才看到了地外星系的整體面貌,這既可以看作是一種賽博格虛擬現實空間,也可以讀解為是小狄與長江七號進行心靈感應之后看到的視覺幻象;《臥龍崗》里的外星人珠子返回星球的空間展示方式,是一個經過了純色處理的黃色的異度空間,同樣,它既可以視為賽博空間,也可以看作是人類與瑪雅人相告別的精神空間;還有影片《拯救愛情》里洞穴般的藍色T星球,以及《詞與物》中封閉的“異托邦”空間等,中國電影人對于賽博空間的想象,總呈現出一種被動、封閉或者曖昧不明的狀態。
自晚清以來,西方科技、工業與文明對中國人而言意味著一種可以帶中國脫離當時民族國家恥辱的先進文化事項,中國啟蒙知識分子對其寄托了擺脫民族危亡與屈辱境地的希望。西方先進的科學理念與文化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重塑中國民族性格與國家身份的可能。在中國科幻電影創作中,我國電影人對于西方科技文明,延續了晚清以來的極大的快樂憧憬;對于賽博格身體人機合成狀態的身份混雜的處理方式,也充滿了樂觀、肯定的自我認同,而這種身份混雜的自我認同狀態,內在地包含了對西方科技文明的他者認同。
中國科幻電影中的賽博格身體,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人類/中國身體與機器/西方科技文明的合成體。最終,該合成體的后人類特征的中國文化身份表述方式為缺乏反思力的,對賽博空間、虛擬現實以及地表之外的空間的無限向往。
例如,香港科幻電影《女機械人》(1991)、《超級學校霸王》(1993)等塑造的賽博格身體,所謂人機合成體表現為一種由身份錯亂而引發的搞笑噱頭,既傳遞出“九七”回歸之前“香港文化焦慮與身份想象的緊張”,更體現出香港在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中文化身份的無根性。在同時期大陸拍攝的科幻電影,如《兇宅美人頭》(1989)、《合成人》(1988)以及《毒吻》(1992)等,盡管體現出對于西方科技文明與生化技術的恐慌心理、具有一定的反烏托邦色彩,但從創作者對于賽博格身體的塑造方式及其身份想象來看,這些影片無意探討未來科技文明時代的中國身份定位,賽博格人類僅作為一種身體奇觀而展示,旨在刻意營造某種恐怖氣氛,以最大程度挖掘娛樂價值。隨著中國人快樂地擁抱西方科技、成為其忠實信徒之后,中國科幻電影很快陷入了對影像的奇觀化呈現之中,文化身份的位置也因此難以定位。
千禧年之后的合拍片時代里,無論是《公元2000》(2000)里的人工智能,還是模仿美國科幻電影《人工智能》(2001)里的機器人造型的《機器俠》(2009),或者是《未來警察》(2010)與《全城戒備》(2010)中人機混合體的超能警察形象,以及《長江七號》(2008)中的外來科技寵物狗塑造,同樣無意于在賽博格身體上寄托某種關于未來身份的想象與文化定位,而是不斷地將賽博格詮釋為西方科技文明的符號,描繪的是一副擁抱高科技文明的快樂烏托邦情景。
關于賽博空間與賽博格身體的后人類影像塑造,是一種在西方科技文明觀念體系之下,建構未來西方文化主體性及其身份定位的方式。但在中國電影人的創作之中,一方面是一味地追求效法好萊塢人機合成體的視覺奇觀,而落入了西方文化主體性身份的他者認同之中;另一方面,后人類主義的影像實踐也被想象成一種解構主體性的策略,用以定位“第三世界”地區邊緣化的身份位置。例如,臺灣學者甚至提出了“賽博格—臺灣”的說法,認為“臺灣本身并無固定、完整內容,而是不斷生成、具有復雜即身性的流動過程。如果有所謂的臺灣主體,它也是一種缺乏本質與內容的賽博格主體”。的確,諸如為數不多的臺灣科幻電影《騷人》(2012)中的“網絡建國”設想與世界青年集聚在山谷中迎接世界末日的狂歡景象,還有根據法國作家馬歇爾·埃梅的短篇科幻小說《穿墻人》(2007)改編的同名科幻片里困在虛擬現實情境中的主人公們等等,都通過賽博空間的影像表達,塑造了一個充滿流動性的“賽博格—臺灣”身份,潛在地表征了某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式的臺灣未來身份危機。
然而,和其它具有解構性質的后現代理論一樣,例如后殖民、酷兒理論等等,后人類視域下的賽博格身份討論有著自我邊緣化、逃避現實身份困境的特征,作為一種策略,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的賽博格身體的形象塑造方式,本質上缺乏一種具有建構意義的、直面現實和想象未來的動力。
四、關于中美科幻空間與身份的文化差異
縱觀中美科幻電影對于賽博空間與賽博格身體的表現方式可以看出,美國科幻電影自有一條清晰的“科學—政治—軍事—流行文化”領域互融共進的發展脈絡,然而中國科幻電影,則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因想象力匱乏而文化身份曖昧不明的狀況。但是,如果撇開中國科幻思維的西方文化影響,可以發現中國的科學觀、科幻觀與西方的科技文明導向有著本質區別。
首先,根據中國地緣文化認同的本土思維模式,中國人自古以來以“華夷之辨”為地緣文化認同之基礎,進而對“四海之外”的空間展開想象的。
前現代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天—地—人”合而一體的宇宙觀,在中國電影創作中有著深刻的影響。例如,在取材于“鬼吹燈”系列小說的影片《九層妖塔》(2015)里,創作者對外星人身處的空間與身份形象,進行了中國式本土化的創作:外星人所寄居的超越地表的空間,不僅不像好萊塢科幻片那樣處于地表之外,反而在地球內部的洞穴之中;妖塔的奇幻空間塑造方式,也取材于前現代中國原始民俗文化的審美特征。這和同時期美國好萊塢科幻片對于“外星人來自外太空”的想象方式,在空間的想象層面上有著根本區別。影片里,中國創作者將外星人與中國少數民族身份進行了聯結,并且根據現實中的少數民族差異性文化,創造了一個名為“鬼族”的外星人族群,它既是外星人,又是中國這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分支。
同樣,在影片《美人魚》(2016)里,超越地表的空間,也是高度內在于地球之中的。無論是影片中的日本研發出來的殺海豚的生化科技,還是西方學者追蹤史前神秘海洋生物過程中使用的高科技手段,都在影片里被塑造成一種負面的、具有諷刺意味的科學主義價值觀念。這些刻畫超越地表空間的、對未知生命體進行想象描繪的影片,同時也溢出了科幻類型片的范疇,為中國電影之于未知空間的想象開辟了一條亟待拓展的創作小徑。
其次,中國“天—地—人”的宇宙觀,表現出來中國人看待人類與地外空間關系的另類視角,理論上在中國科幻空間的塑造方面大有作為。
對于西方人來說,土地即是地球,正如好萊塢科幻電影《星際穿越》(2014)所呈現出來的西方科技文明的空間觀念那樣,看護土地、守候地球的取向在影片中被視為保守、落后的農民身份(即墨菲的哥哥),而大膽地朝向太空冒進、在其它星系中開拓殖民地空間的行為,則塑造成激進、富有冒險精神和承擔人類物種使命的宇航員身份(如庫伯和女兒墨菲),影片無不以“好萊塢式的發展主義、以科學來拯救科學災難的邏輯而勝出”。對于中國人而言,這一空間的想象邏輯則恰恰相反,中國人某種程度上更傾向于人類家園的守望者,而非朝向地球位置空間以及地表之外開荒破土的殖民者,而這正是好萊塢科幻電影中所有意和無意忽略的空間觀念。
再次例舉《美人魚》中的人類與海洋空間關系的呈現方式,其中半人半魚的身體既已包含了身份雜糅的特質,一方面,時空不明的地域空間與歷史年代“彌散著一種歷史觀念和精神特質,將懷舊的兩難和宿命的疑惑集于一身”,標著了香港電影人關于故鄉與他鄉的“后九七”時代里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美人魚作為人類的他者,與依靠未來科技文明而拼湊的賽博格后人類人機合成體不同的是,這種非人類的他者身份的塑造方式,主要是通過清理歷史上人類與海洋生物的共存關系而指向的是一個關于環保主題的未來人類文明想象,具有對人類世代生存的土地/地球與超越地表的地域空間進行重新描繪的可能性。
最后,關于賽博空間與賽博格身體的未來書寫,中國科幻電影創作目前在這一方面本質上仍處于空白狀態。無論是對于計算機文化的反思力、賽博空間的建構力還是賽博格銀幕化身的身份政治的想象力,中國電影人都急需擺脫晚清以來對于西方科技文明的盲目崇拜思維,進而立足本土文化科學觀念進行科幻電影創作,在21世紀人工智能時代里發出不同于美國好萊塢的中國自己的聲音。
結語
從目前關于未來賽博空間的影像塑造方式與文化身份表達來看,占主導地位的仍是美國好萊塢電影中表露出的當代反恐意識形態與美國精神的文化邏輯。一方面,美國科幻電影有著基礎牢固的反烏托邦科幻文學寫作傳統;另一方面,隨著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對流行文化話語權主導能力的增強,當代美國科幻電影幾乎改寫了1980年代賽博朋克文化的反烏托邦政治立場,轉而宣揚當代美國反恐意識形態。
反映中國科幻電影無論是外太空及的宇宙探索,還是關于虛擬現實空間的塑造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處于缺席狀態,只是一味地效法好萊塢科幻電影的創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本土空間與文化身份的表述能力。但是,中國科幻電影對于超越地表的空間塑造方式,仍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中國式的科幻思維模式的特點,這潛在地包含了一種非西方式的描繪未來圖景的影像與敘事可能性。這急需當代中國電影人,對于當前西方科技文明的發展格局,以及整個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化進程,在技術現狀、政治視野和文化立場方面進行深度分析和全面判斷,才能在21世紀之初的后人類思潮復興之際,準確定位中國本土空間與主體性文化身份位置,進而提供一個關于整個人類未來空間與政治身份的新的未來想象。
注釋:
[1]Mike Featherstone, Roger Burrows.“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Mike Featherstone, Roger Burrows Ed.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Press, 1996:2
[2]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5:vii.
[3]事實上,《星球大戰》的片名就取材于當時美國軍方公布的《戰略防御倡議》,這是一個針對蘇聯可能對美國發動大規模洲際導彈攻擊的戰略防御系統,最終目的是為了抵擋蘇聯的核彈,俗稱“星球大戰”計劃。
[4]Donna J. Haraway.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ilan: Feltrinelli Press, 1995:3
[5]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哈拉維的理論創建對未來人類身份想象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但顯而易見的是,她對于賽博格身體的思考脈絡及其后人類時代的斷言,尚未考慮到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遠未完成,有些不發達地區甚至尚未開始;再加上經濟全球化趨勢,一方面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貨幣、商品貿易、信息傳播的流通速度加快乃至同步,另一方面,也加劇了世界地緣格局內部的貧富分化與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這都使得哈拉維所構想的后人類時代里的新型壓迫與反抗關系的革命前景,顯得略微簡單與樂觀。
[6]Fran Pheasant-Kelly, “Cinematic Cyborgs,Abject Bodies: post-human hybridity in T2 and Robocop”, Film International, Vol. 9, No. 5 Nov 2001:62.
[7]Anne Allison, “Cyborg Violence: Bursting Borders and Bodies with Queer Machines”,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6, No. 2. May, 2001:244-249.
[8]陳亦水. 尾巴的恥辱:中國電影科幻空間的科玄思維模式與身份困境[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 2015(6):114.[9]游飛、蔡衛. 電影新技術與后電影時代[J]. 當代電影.2000(4):66.
[10]馬良. “凍結時間”特技攝影的歷史發展和演變[J].影視制作. 2010(7):34-37.
[11]Ericka Hoagland and Reema Sarwal.“Introduction: Imperialism, the Third World,and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Ericka Hoagland and Reema Sarwal ed. Science Fiction,Imperialism and the Third World. Jefferson:McFarland & Company Press. 2010:7.
[12]在現實中,所謂“異形”(alien)恰恰是辨認“非美國人”的官方詞匯,美國移民局用來標識那些所有居住在美國國土內、非美國公民的外來人身份的詞匯,包括外國留學生、訪問學者或者教授,以及擁有永久居住權的綠卡持有者等。
[13]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Books Press. 1984:51.
[14]賽博朋克是80年代之后的反主流文化科幻寫作主題,內容往往圍繞網絡、電腦、黑客等等,以展現一個反烏托邦的黑暗未來。
[15]Katie Hafner and John Markoff: Cyberpunk:out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1:9.
[16]圖靈測試內容為一系列簡單的問答對話,測試者需要根據被測試者的回答情況,判斷后者的人類或電腦身份;問答對話結束后,當超過30%的電腦回答讓被測試者相信是人類時,則電腦通過圖靈測試。2014年,俄羅斯科學家研發的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stman)聊天程序成功通過了圖靈測試。
[17][18][19]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xiii, 49, xiv.
[20]Kevin Robins. “Cyberspac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Mike Featherstone, Roger Burrows Ed. 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Press, 1996: 135-154.
[21]戴錦華:《雪國列車》中的階級憤怒與反抗[OL],2014-07-14,1905電影網。
[22]戴錦華. 科幻電影研究專題[OL]. 北京大學系列講座,2015年9月—12月。
[23]戴錦華. 未來的維度[OL]. 2016-11,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當代寫作研究中心的演講,騰訊文化。
[24]Sophia Siddique Harvey, “Mapping cyborg bodies, shifting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anxieties in Cyber Wars”, Chinese Cinemas, Vol. 3, No. 1,2009: 53.
[25]林建光. 導論一[A]. 林建光、李育霖主編. 賽伯格與后人類主義[C]. 臺中:臺灣中興大學出版社,2013. 8.
[26]在英文中,土地與地球的表達通常是一個單詞“earth”。
[27]許荻曄. 戴錦華:現在年產幾百部電影,有價值的還不及年產100部時[OL]. 澎湃新聞網. 201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