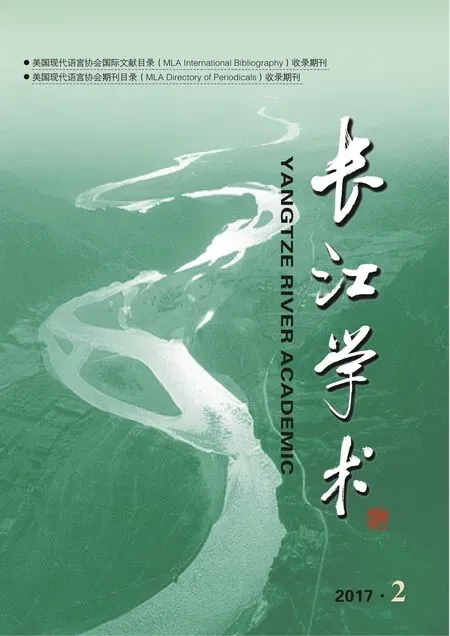日本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
黃念然 高 越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日本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
黃念然 高 越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就其傳播特征看,一、以“重譯”、“轉譯”、“節譯”、“轉述”等為基本方式;二、日本“納普”文藝理論和“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成為譯介重點;三、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文藝的“觸媒”作用。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對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如福本和夫的“理論斗爭主義”、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識論”、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等的吸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建構了政治和大眾的關鍵兩極,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這些都為當下中國文藝理論界進一步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問題提供了反思的基礎。
日本 馬克思主義 文藝理論 傳播 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問題一直是文藝學界關心的核心問題之一。回望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中國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建構,具有明顯的革命實踐性、倫理意識形態性,政治氣候的變化常常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與前行的晴雨表。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了中國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接受視野和闡釋模式上的偏狹,但往往又語焉不詳。如果從中國譯介、傳播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分析、總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不僅可以引領我們重回歷史現場,還能對問題的癥結有更清晰的認知。日本作為西方近現代思想向中國傳播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傳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學界譯介與傳播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方式及其選擇性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規約著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文學的基本方向及其主要理論建構方式,并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探索與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學理上進行清理與剖析,對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這一重大課題仍然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作用。
一、中國學界傳播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特點
晚清以來,日本作為中國借鑒西方思想的一個重要中繼站,其重要性已為有識之士所深知。如張之洞很早就認識到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一個簡便途徑在于翻譯日本書籍,他說:“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譯西書不如譯東書。”在翻譯日文書籍之外,清末民初中國赴日留學生也逐年增加。據李喜所根據有關資料統計,赴日留學大致情形是:1896年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10000人;1909年3000人;1912年1400人。這期間,中國留日學生創辦了許多雜志,如《開智錄》、《譯書匯編》、《國民報》、《新民叢報》、《游學譯編》、《新小說》、《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直說》、《女子魂》、《白話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醒獅》、《民報》、《復報》、《云南》、《音樂小雜志》、《法政雜志》等等。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密切關注歐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日本進步思想界先后成立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社會民主黨、平民社等組織,創辦了《勞動世界》、《平民新聞》、《社會主義》、《真言》、《光》、《新紀元》、《獨立評論》、《社會主義研究》等許多以介紹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為主要內容的進步刊物。象片山潛、幸徳秋水、堺利彥等著名學者,不僅積極舉行各種演說會、讀書會、研究會、談話會宣揚社會主義,還親自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幸徳秋水和堺利彥合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二章(載于《平民新聞》1904年11月3日)。從1906年開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及著名社會主義理論家李卜克內西、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文章在堺利彥創辦的《社會主義研究》得到全文譯載,開始在日本社會和思想界迅速流傳。中國早期留日學生對風行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于1900年成立了譯書匯編社。該社不僅選譯日本學者所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刊登中國留學生的翻譯文章,如1901年1月《譯書匯編》1、2、3、6、8期連載的日本學者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以及1903年2月刊登的留日學生馬君武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等。到1904年前后,這股引進和譯介日文社會主義著作的熱潮幾達高峰,“這一階段出版界出版了許多留日學生翻譯的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書籍。像矢野文雄的《新社會》,幸徳秋水的《廣長舌》、《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近世社會主義評論》,島田三郎的《社會主義概論》、《世界之大問題》,西川光二郎的《社會黨》和《世界大同主義》等,幾乎是當年,有些甚至幾個月內就被譯成中文了。”作為同盟會機關刊物的《民報》也成了譯介社會主義思潮的重要陣地,先后刊發了朱執信(署名蟄伸)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宋教仁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署名勥齋)等重要文章。中國留日學生同日本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互動交往也逐漸密切起來,像梅景九、張繼等留日學生經常參加幸徳秋水等人組織的日本社會黨的各種會議,而幸徳秋水、北一輝等日本社會黨人也參加了張繼、劉師培等人組織的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活動。大致來看,中國學界傳播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通過日文以“意譯”、“重譯”、“節譯”、“轉述”或“轉譯”等方式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就是依據日文本并參照英文本譯出的,其中,日文本是由《星期評論》編輯部戴季陶提供,英文本則由陳獨秀借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再如,《民報》“第1號的《進步與貧乏》、第8號的《無政府主義之二派》、第11號的《虛無黨小史》、第16號的《巴枯寧傳》等是節譯自亨利·喬治、久津見蕨村、煙山專太郎等人的著作,而第2、3號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第3、7號的《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國之革命》和第5號的《萬國社會黨大會史略》等,都是直接譯自不久前出版的日文報刊”。前述宋教仁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一文是直接根據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大杉榮發表在《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的同名文章翻譯并略加修改后而成的。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之哲學》、《面包掠奪》,以及《共產黨宣言》第一章部分內容和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等等,也都是通過日文轉譯刊登在劉師培創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上。
其二,帶有明顯的片斷化、零散化的特征。以《共產黨宣言》的譯介為例。1903年2月上海《新世界學報》上刊登的日本學者福井準造著、趙必振翻譯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只是簡單介紹了馬克思撰寫《共產黨宣言》的緣由并摘錄其中的部分段落。馬君武于同年發表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只在文章最后羅列的參考書目中提到《共產黨宣言》。1906年朱執信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中所摘譯的主要是《共產黨宣言》中的十大綱領,實際上是《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節譯本。
其三,誤讀現象嚴重。由于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借助上述的“意譯”、“重譯”、“節譯”、“轉述”或“轉譯”等方式,因此在資料占有的純粹程度、全面與否、翻譯的信達程度、文筆優劣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由此而引發的學習與運用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誤讀、誤解以至歪曲也就在所難免了。比如,在對社會主義的介紹中,就有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同于經濟史觀的。如《晨報》上譯載的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的文后總結中就直接說:“馬克思的歷史觀,已如上述,普通稱他為唯物史觀,我想稱他為經濟史觀。何以有唯物史觀的名稱呢?因為他說明社會上歷史的變遷,注重在社會上物質條件的變化。何以我又想稱他為經濟史觀呢?因為他說明社會上歷史的變遷,注重在社會上經濟條件的變化。總而言之,觀察社會的變遷,以物質的條件,再適切說起來,以經濟的事情為中心,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觀的特征了。”像梁啟超的《中國之社會主義》、劉大鈞的《社會主義》、周炳林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么樣運動》等文章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等同于經濟革命論或經濟決定論的誤解也比比皆是。
總的來看,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譯介,主要以日、俄譯本為藍本或中介,具有非常明顯的理論的橫向移植性和來源的間接性,在闡釋馬克思主義時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選擇性傾向非常明顯,這些特點也反映在中國文藝界對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與傳播中。
二、中國文藝界譯介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的基本特點
其一,“重譯”、“轉譯”、“節譯”、“轉述”仍然是中國文藝學界譯介與傳播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方式。如魯迅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就是根據從日本學者昇曙夢的譯本重譯而出。正如魯迅所言,這本《藝術論》出版時“算是新的,然而也不過是新編”,因為魯迅所譯的《藝術論》在內容上實際又混合了盧那察爾斯基的《實證美學的基礎》一書的基本內容,在不解處則“參考茂森唯上的《新藝術論》(內有《藝術與產業》一篇)及《實證美學的基礎》外村史郎譯本”。在魯迅所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集《文藝與批評》中,這種根據日文譯本的情況同樣非常明顯。其中,第一篇《為批評家的盧那卡爾斯基》“是從金田常三郎所譯《托爾斯泰與馬克斯》的附錄里重譯的”,而金氏又是從世界語的本子譯出,“所以這譯本是重而又重”。第二篇《藝術是怎樣發生的》則是魯迅“從日本輯印的《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中杉木良吉的譯文重譯”,至于第四篇《托爾斯泰與馬克斯》與第五篇《今日的藝術與明日的藝術》則“都從茂森唯士的《新藝術論》譯出”。魯迅所翻譯的作為蘇聯關于黨的文藝政策的會議紀錄和決議的重要文獻的《文藝政策》同樣是根據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輯譯”而重譯的。正是由于這種譯介中的橫向移植與理論來源的間接性(多以日、俄譯本為藍本或中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就出現了創造性詮解與誤讀并行的傳播景觀。
其二,日本“納普”文藝理論和“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成為譯介重點。這突出表現在中國的左翼文藝運動中。以藏原惟人為例,其《意識形態論》(馮憲章譯,現代書局1930年7月)、《再論新寫實主義》(吳之本輯譯,現代書局1930年5月)、《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和無產階級》(吳之本輯譯,現代書局1930年5月)、《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的路》(吳之本輯譯,現代書局1930年5月)、《理論的三四個問題》(胡行之輯譯,樂華圖書公司1934年1月)等都進入到中國學者視野中。日本左翼學者專門研究“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論著也一同譯介進來。如屠夫二郎輯譯的岡澤秀虎的《新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發達史》(新興文藝社1930年7月)、青野季吉的《普羅列塔利亞藝術概論》(新興文藝社1930年7月)、片綱鐵兵的《普羅列塔利亞小說作法》(新興文藝社1930年7月)、橋本英吉的《普羅文學與形式》(胡行之輯譯,樂華圖書公司1934年1月)、小林多喜二的《新興文學的大眾化與新寫實主義》(馮憲章譯,現代書局1930年7月)等。
其三,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文藝的“觸媒”作用。如徐懋庸曾把日本的文藝論著比作化學上的“觸媒”(catalyst)物質,并提及了日本學者本間久雄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中的唯物辯證法對他所起過的“觸媒”作用。他說:“從《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我認識了社會進化的鐵則,從《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我解悟了唯物辯證法的公式……這些道理,都是這本書不曾講到的,但我卻由此旁通了。所以我說這書是‘觸媒’,它影響了我。”
三、左翼文藝運動對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吸納
從思想來源來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興起的左翼文藝運動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早期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像郭沫若、周揚、胡風、茅盾、成仿吾、李初梨、馮乃超、蔣光慈等左翼文藝理論家,既是中共黨員,也有留日經歷或背景。他們或參加創造社、太陽社、未名社等進步文學團體,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大多親自參加了譯介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活動,由他們倡導與發動的左翼文藝運動打下了深刻的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烙印。其對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吸納,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福本和夫的“理論斗爭主義”。福本和夫的福本主義深受盧卡奇、柯爾施等人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福本和夫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曾追隨柯爾施學習馬克思主義并通過柯爾施結識盧卡奇,后者還贈之以《歷史與階級意識》。福本和夫強調“理論斗爭主義”,追求一種純粹的無產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主張嚴格區分純粹與不純的革命意識與革命分子,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從想象性的觀念而非具體的現實出發,忽視了無產階級面臨的具體問題而埋頭于理論原則的發展與運用,在階級斗爭中重視知識分子的領導而忽視民眾的作用。后期創造社成員直接吸收了福本主義理論的早期源頭——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吸收了列寧的階級意識理論,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的全面批判以及文學與革命實踐的直接統一。創造社同魯迅及太陽社等的幾次大論戰都打上福本和夫“理論斗爭主義”的鮮明烙印。以二十代后期創造社的“方向轉換”為例就可以明顯看出。1927年的《洪水》半月刊圍繞郭沫若《馬克思進文廟》一文進行討論,先后刊登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第3卷第25期)和《文藝戰的認識》(第3卷第28期)、郁達夫(筆名曰歸)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第3卷第26期)和《在方向轉換的途中》(第3卷第29期)以及毛尹若《馬克思社會階級觀簡說》(第3卷第28期)等文章,初步開始了創造社在文藝與政治上的“轉換方向”,其雜志辦刊風格也從“純文藝的雜志”轉變為提倡革命文學的“戰斗的陣營”。1928年,成仿吾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方向轉換”宣言《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宣稱:“我們遠落在時代的后面。我們在以一個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為主體,以它的‘意德沃羅基’為內容,創制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的’語體,發揮小資產階級的惡劣的根性……我們如果還挑起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的責任起來,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換一句話,我們今后的文學運動應該為一步的前進,前進一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受福本斗爭思想的影響,成仿吾在稍早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對文學趣味論也作了一概的否定,認為“趣味是茍延殘喘的老人或蹉跎歲月的資產階級,是他們的玩意”,將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陳西瀅等人的生活基調和文藝創作都視為“以趣味為中心”,認為這種文藝“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而李初梨也引用成仿吾對“趣味文學”的批判,對魯迅作了這樣的階級定位:“他在這里,一方面積極地,抹殺并抗拒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意識爭斗,他方面,消極地,固執著構成有產者社會之一部分的上部構造的現狀維持,為布魯喬亞汜當了一條忠實的看家狗!”并最后判定魯迅“對于布魯喬亞汜是一個最良的代言人,對于普羅列塔利亞特是一個最惡的煽動家!”郭沫若則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將魯迅直接定位為封建余孽和反革命:“第一,魯迅的時代在資本主義以前,更簡切的說,他還是一個封建余孽。第二,他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還不曾確實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說他是根本不了解辯證法的唯物論。”“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2.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識論”。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識論”主要是受列寧的《怎么辦?》一書第二章《群眾的自發性與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啟發而形成的。在1926年9月發表的《自然生長和目的意識》一文中,青野季吉用“自然生長”和“目的意識”亦即“自發性”和“自覺性”兩個概念,強調必須把無產階級文學從自發階級提高到自覺階段。在他看來,就像列寧所說的那樣,“無產階級自然生長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社會主義的意識,是從外部灌輸的”,因此,他相信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在文學領域灌輸目的意識的運動”。應該說,青野的“目的意識論”在看到文學的階級性的同時又忽視了文學的自律性,割裂了文藝社會效果與藝術效果的有機統一。青野的這些思想也深刻影響了李初梨。他于1928年發表的《自然生長性和目的意識性》一文,從內容到形式幾乎是的青野《自然生長和目的意識》一文的翻版,而且同樣引用了列寧的相關論述。在李初梨看來,無產階級意識可分為自然生長的無產階級意識和目的明確的無產階級意識兩個部分,前者是指“勞動大眾底自然的覺醒”后自發形成的無產階級意識,而后者指革命的知識分子投身到普羅列塔利亞運動中通過廣泛的政治運動和文化思想批判實踐而形成的一種社會主義意識。這后一種自覺的無產階級意識乃是“戰斗的唯物論及全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主義的意識”,相比普通勞苦大眾的那種萌芽狀態的、摻雜著粗淺唯物論或經驗論的無產階級意識甚至工會主義意識,它要純粹得多,因此,推動革命的中堅力量只能是革命的智識階級,成熟的無產階級意識只能在革命知識分子中產生,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只能在清理掉思想的雜質后才能得以形成。我們可以看到,創造社成員同各個文學派別與社團的大論戰,都同這種無產階級“純化”運動有著密切的關聯,他們的文學宗派主義與極端的文學階級論同他們所接受的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而且對后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是日本左派理論家藏原惟人在福本主義受到批判之后綜合“拉普”推行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和傳統現實主義的藝術特征而提出來的,其理論核心是強調“明確的階級觀點”和“對于現實的客觀的態度”和嚴正寫實的手法。藏原惟人于1928年5月在“納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機關刊物《戰旗》創刊號上發表的《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之路》一文由太陽社的林伯修譯成中文后,以《到新寫實主義之路》為題刊登在《太陽月刊》1928年7月停刊號上,其中的“無產階級現實主義”一詞被置換為“新寫實主義”。這篇文章對無產階級現實主義作了性質上的界定,不僅嚴格區分了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即浪漫主義),同時還嚴格區分了新舊寫實主義。在藏原惟人看來,理想主義是漸次沒落的階級的藝術,寫實主義則是漸次勃興的階級的藝術;布爾喬亞寫實主義和小布爾喬亞寫實主義都是舊的寫實主義,而普羅列搭利亞作家“對于現實的態度,是徹頭徹尾地客觀的現實的”,并且他們“不可不首先獲得明確的階級的觀點”,因此,“普羅列搭利亞”寫實主義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寫實主義。藏原惟人的這些闡述新舊現實主義的特點和關系、界定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性質的論著,對創造社和太陽社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如創造社的李初梨于1929年初發表的與茅盾辯論的長文《對于“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底抬頭,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文學運動底新階段》的第八節《形式問題》中,就對藏原惟人表示了贊同,他不僅根據林伯修的譯文大力加以推介,而且明確提出:“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至少應該作為我們文學的一個主潮!”又如,太陽社成員錢杏邨所倡導的“無產階級現實主義”和“力的文學”,其理論來源既有蘇聯“拉普”派成員佐寧的《為了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更多則來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寫實主義之路》和《再論通往無產階級現實主義之路》等文章,以至于他在和茅盾的論戰中被魯迅調侃為“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1929年太陽社成員蔣光慈赴日養病期間還專程拜訪藏原惟人并從其處借到佐寧的《為普羅寫實主義而戰》等書籍。1930年1月,吳之本又翻譯了藏原惟人的《再論新寫實主義》。同年五月,藏原惟人的一系列研究“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并接連譯載在太陽社書刊的論文結集為《新寫實主義論文集》出版(吳之本譯,上海現代書局1930年),由此可見當時左翼運動對他的重視程度。
四、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影響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從思想譜系或話語形態上來看,主要有歐洲馬克思主義思想話語、俄蘇馬克思主義思想話語和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想話語三大系統。這三大話語系統之間錯綜復雜的交織和演化,以及中國學界對它們的選擇性吸收,深刻影響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相較之下,魯迅、茅盾、瞿秋白、周揚、馮雪峰等人的革命現實主義批評與俄蘇思想話語系統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而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等人的激進化的革命批評話語同日本思想話語系統的聯系更為密切。就后者而言,從二、三十年代的“文學革命”論爭,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到五、六十年代的文藝大批判,都同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與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早期文藝界圍繞對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與傳播初步建立起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系的一些重要支柱,這些都對后來的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高度重視文學的階級性和政治功能。這一點在錢杏邨、郭沫若、李初梨、王獨清等人的文藝理論探討與批評實踐中可以清楚看到。像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和《藝術家與革命家》及化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馮乃超的《冷靜的頭腦——評駁梁實秋的〈文學與革命〉》及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當時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文章,都高度重視文學的階級性和文學的社會使命,認為文藝可以“組織生活”、“創造生活”和“超越生活”,呈現出鮮明的“左傾”傾向以及將文藝簡單化的特點。總的來看,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幾乎全盤接受藏原惟人新寫實主義文藝觀念,同時又照搬馬列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從革命功利主義的立場闡釋了無產階級文學的性質、目的、綱領、任務并將之付諸文學批評實踐。其基本理念就是:作家應運用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來認識世界,觀察世界,表現世界;世界觀與文學創作之間被理解為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文學作品的內容等同于作家的觀念形態或思想傾向;文藝的基本功能被理解為政治“宣傳”和“煽動”;革命口號式的標語文學也應給予高度評價。正是由于對日本“納普”理論的簡單理解,創造社主要成員在其批評實踐中都或多或少地犯有左派幼稚病,從簡單的階級論視角出發對魯迅、茅盾、葉圣陶等人的文學創作進行發難并給予了不公正的評價,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十年文藝思潮進行了革命化的簡單化的分期(如錢杏邨將之分為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以及五卅運動以后工人階級力量顯現三個時期)。我們還不難發現,通過對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與傳播,“五四”運動時由“科學”、“民主”、“人性”、“國民性”等概念組成的話語群落開始為“革命文學”、“黨的文學”、“工農兵文藝”、“國防文學”、“文藝大眾化”、“意識形態”、“傾向性”“反映論”、“政治性”、“階級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內涵和外延完全不同的話語群落所替代,在文革時更為“兩結合”、“工具論”、“文藝黑線”、“五把刀子”、“寫真實”、“寫本質”等概念或術語所覆蓋。
2.提倡文藝大眾化。文藝大眾化問題與二十年代普羅文學的發生、發展相伴隨。創造社和太陽社對蘇聯及日本普羅文學的大力宣傳直接引發了國內文藝理論界對文藝大眾化問題的關注與熱烈討論,并開啟了馬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建設的重要一極。與晚清白話文運動和“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不同的是,創造社和太陽社在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增添了新的思考維度即革命性,這同“五四”的思想啟蒙有著質的區別。像成仿吾的《革命文學的展望》一文中所集中討論的無產階級文學要怎樣“獲得大眾”的問題;沈端先在《文學運動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提出的普羅藝術運動的當前任務是“大眾化”和“化大眾”相結合的觀點;陽翰笙在《文藝大眾化與大眾文藝》中提出的努力使“歐化文藝”加速度地大眾化的號召;鄭伯奇在《關于文學大眾化的問題》中對大眾心理特質和大眾文學性質的分析,等等,都是從革命的視角,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去關注大眾生活和解決大眾化中的難題。其進步意義在于它為無產階級文學的語言實踐辨明了基本方向——為大眾、寫大眾、大眾寫逐漸成為文藝大眾化的主導策略并成為延安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先聲;其消極影響則在于將日本“新寫實主義”的創作要求簡單化為只能描寫那些“最重大、最主要、最使人感激、最多數人利害”的事件,而且必須“站在社會及集團的觀點上去描寫,而不應該采用個人的及英雄的觀點”。
總的來說,中國學界對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傳播,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左右了后來中國文藝發展的基本方向,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探索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影響突出表現在:它通過其譯介中鮮明的選擇性傾向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中國形態確定了政治和大眾的關鍵二極。就政治一極而言,由于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傳播,急于將其從“知識傳播”的層面推到革命文學理論指導思想的地位,缺少相應的過濾和必要的吸收與消化,因而其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往往是并存的。它基本規范了中國二十世紀革命文學的進程,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政治決定或主宰文藝的基本格局,也使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呈現出鮮明的政治批評的特點,甚至產生很多負面影響。比如,太陽社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與宣傳,固然由于在當時白色恐怖加緊情勢下對革命性、政治性、階級性的不加選擇的引進、運用與發揮而情有可原,但在文學事業中造成的客觀后果仍然是十分嚴重的。從理論上講,太陽社在譯介過程中還沒有真正意識到并解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現實主義創作是否發生矛盾及如何解決矛盾的問題,從批評實踐上講則開啟了文學批評中打棍子、扣帽子的不良風氣。這在太陽社對魯迅、茅盾諸人的不公正評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就大眾一極而言,這些譯介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大眾化有著正面的積極的推動作用。它們不僅提供了左翼革命文學關于“文藝大眾化”論爭的主要理論基礎,也為“左聯”的文藝大眾化實踐提供了思想資源,同時直接或間接地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關“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結合”以及“知識分子改造”等表述提供了理論支持,為建設中國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與此同時,在開啟大眾一極的同時,對于文藝大眾化實踐,又缺乏對高于實踐的理性邏輯的深度思考,即只求理論趨同于現實,對文藝大眾化的現實活動本身也必須努力上升為某種理論的考量甚少,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俗化為一般認知的弊端非常明顯。所有這些都給后來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帶去了負面影響,也給當下中國文藝理論界進一步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問題提供了反思的基礎。
Japan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uang Nianran Gao Yu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Japan’s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 is featured with retranslation,indirecttranslation and selectivetranslation ofJapaneseversions ofMarxisttheories,withthe emphases on Knapp’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Japanese Proletariat literature,and with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atalytic role of basic Marxistprinciples.The China’sthe left-wing’s absorbing early JapaneseMarxisttheory of literatureand artsuch as Aono Suekichi’s theory of objective and consciousness,Korehito Kurahara’snew realism and so on helped to construct two crucial poles of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however,while leading to some negative influence,these provide basis of reflection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Japan;Marxist;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Dissemination;Sinicization
責任編輯:汪樹東
黃念然(1967—),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學研究。
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11&ZD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