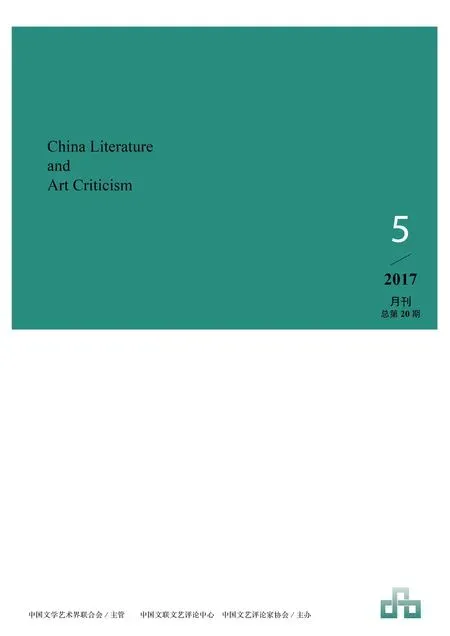多元共生、賦魅效果與混合現實:科幻影視視野中的游戲
黃鳴奮
多元共生、賦魅效果與混合現實:科幻影視視野中的游戲
黃鳴奮
以游戲為題材的科幻影視,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其以藝術為主導發展起來,在對游戲及相關現象的描寫和構想中表現出深刻的人文關懷。在社會層面,它們矚目生物人、機器人和外星人等智能生物并存的假定性情景,構想了多種充滿惡托邦情調的游戲;在產品層面,它們揭示了數碼時代街機游戲、單機游戲和網絡游戲使人心亂意迷的影響;在運營層面,它們觸及了游戲過程中虛實世界相互滲透、真實世界彼此進入、分化世界多方博弈的現象,展示了走向混合現實的發展趨勢。
科幻影視 游戲 共生 賦魅 混合現實
在科幻的視野中,游戲往往不僅是剩余精力的發泄、自由意志的顯示或者娛樂訴求的滿足,還是社會批判的切入點、科技反思的著眼點、人性蛻變的關捩點。時至今日,科幻本身已經形成了科幻文學、科幻美術、科幻影視、科幻游戲等分支。其中,以游戲為題材的科幻影視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與如今網絡上常見的游戲直播不同,科幻影視主要以藝術為主導發展起來,在對游戲及相關現象的描寫和構想中表現出深刻的人文關懷,如社會層面多元共生的憂思、產品層面賦魅效果的揭露、運營層面多重現實的反思等。下文所舉的例證中,若不加特殊說明,指的都是科幻電影。
一、 社會層面:多元共生的憂思
從社會的角度看,游戲是擺脫現實身份束縛的自由活動,經常給參與者帶來快感,因此可能被劃歸為娛樂。盡管如此,自從人類社會劃分為彼此對立的群體、種族、階級、階層之后,初民中流行的共享性娛樂在很大程度上為對抗性娛樂所取代。游戲參與者喪失了平等的地位,某些人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自由活動沾染了濃烈的血腥氣。不論是至今仍有遺跡可考的角斗場,或者是被概念化的“貓鼠游戲”,都為我們展示了對抗性娛樂的這種特征。現代社會基于人生而平等的觀念為游戲劃定了清晰的倫理底線。以此為指導,即使是高度對抗性的游戲,也不允許建立在有意傷害他人性命的基礎上。在科幻視野中,未來社會的游戲呈現出烏托邦和惡托邦的兩極分化。如果人們將來不僅擺脫了社會對立、進入大同世界,而且擺脫了生活重負、不為分工所束縛,那么,真正體現自由精神的游戲將成為全體社會成員都有條件參與的普遍性活動,共享性娛樂因而得以流行,并為增進彼此福祉發揮作用,這是烏托邦。如果人們將來不僅仍為社會對立所束縛,而且比當下更為冷血或嗜血,企圖通過游戲來獲得更寡廉鮮恥甚至肆無忌憚的自由,那是惡托邦。若就實際所能看到的科幻影視而言,幾乎都屬于惡托邦類型。下文以參與者的身份為根據,將它們區分為生物人游戲、機器人游戲和外星人游戲三個子類。
1. 生物人游戲
生物人游戲是主要由人參與的游戲。它在科幻電影中的出場,也許一開始就是悲劇性的。被科學家造出來的人應農夫的小女兒瑪莉婭之邀玩朝湖里扔野花的游戲,但當花扔光了時,他以為女孩也會浮在水面,遂將她扔到水里。看到她淹死了,他沮喪地走開。這是美國片《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1931)為我們展示的悲慘場景。
如果說上述影片中村民們對瑪莉婭的不幸寄予同情的話,那么,意法合拍片《第十個受害者》(The 10th Victim,1965)中的各國觀眾卻是冷漠或狂熱地接受電視所轉播的殺人游戲。參與者由電腦隨機派位,分別扮演追捕者和受害者,在羅馬展開對抗。這類影片緊張刺激,層出不窮。例如,西德電視片《百萬游戲》(Das Millionenspiel,1970)將在被指定幫派追殺的情況下連續存活七天作為參與者贏得百萬德國馬克大獎的條件,描寫整個國家都在觀察電視上的追捕,某些人欣賞,某些人反感。美國電影亦不乏其例:(1)在《過關斬將》(The Running Man,1987)中,2017年美國在世界經濟崩潰之后成為獨裁的警察國家,對所有文化活動加以監視。政府通過電視轉播各種真人秀節目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其中有一個是由冷血的希利安主持的“賽跑者”。它在風格上模擬古羅馬的角斗士,要參與者在廣闊的區域中逃避傭兵的追殺,爭取由國家開恩的一線生機。(2)根據《天地逃生》(Gamer,2009)的構思,玩家在社區游戲中控制他人(將被選中的人當成“人物”),從蓄意傷害,直到用真正的武器在指定區域內進行由電視轉播的戰斗。(3)總名為“饑餓游戲”(The Hunger Games)的四部電影(2012,2013,2014,2015)標志著殺人游戲題材的高峰。除上述國家外,俄羅斯也推出了類似作品,像《暗殺游戲》(Maf ya: Igranavyzhivanie,2016)就是一例。其創意在于:被參與者集體認定為殺手的人都死于其所懼怕的事物或情境。我國的《復仇直播》(2015)就題材而言同樣屬于這一類型,但所直播的游戲在技術上缺乏含金量,風格則是喜劇性的。
除大眾媒體(主要是電視)所轉播的殺人游戲之外,科幻電影還描繪了其他類型的生物人游戲,如美國《五重奏》(Quintet,1979)中未來冰河時代垂死的人類所進行的死亡游戲,《人肉炸彈》(Timebomb,1991)中政府創造殺手所開啟的貓鼠游戲,《人類清除計劃》(The Purge,2013)中政府主導的旨在減少人口數量的滅絕游戲,加拿大《黑夜時刻》(The Dark Hours,2005)中暴力性侵犯者為報復醫生強迫對方及其親人參加的噩夢般的游戲,等等。美國電視劇《無敵金鋼》(The Six Million DollarMan,1973)1975年11月2日播出《我們的跑動后衛之一失蹤》(One of Our Running Backs is Missing),描寫了足球賭博所導致的綁架案。作為土星獎最佳科幻電影,美國《滾球大戰》(The Rollerball,1975)所描繪的是旨在滿足人們嗜血欲望的殘酷比賽(體育游戲)。類似的影片有同年出品的美國電影《死亡賽車2000》(Death Race 2000,1975)等。
2. 機器人游戲
“機器人游戲”至少包含三種可能的含義:讀為“機器+人游戲”,指將原先由人進行的游戲搬到機器平臺上;讀為“機器人+游戲”,指機器人自娛自樂的游戲;讀為“機器+人+游戲”,指著眼于人機互動的游戲。現階段科幻影視常見的是第三種意義上的機器人游戲。
早在1897年,由法國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執導的短片《小丑與自動化》(Gugusse and the Automaton,1897)就出現了機器人形象。其后的科幻電影陸續塑造了工業機器人、軍事機器人、宇航機器人、執法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等形象。1973年,美國《西部世界》(Westworld,1973)率先將娛樂機器人應用當成題材,背景定位在未來成人娛樂公園達洛斯。它所設立的三個主題世界都由類人機器人提供娛樂,游客可以任意對待他們,即使使之死亡,他們也總能在次日活過來。園方希望這樣的娛樂能夠持之以恒,但類人機器人不僅悄悄發生變異,而且走上了反抗之路,導致娛樂公園不得不關閉。在美國《幻世追蹤》(Vice,2015)中,商人朱利安設計了終極度假勝地“幻世”(VICE),顧客在那兒可以和類人居民玩最粗野的游戲,機器人同樣每晚重啟以清除當日的記憶。盡管如此,仍有一個機器人由于偶然的機遇保留記憶并形成了自我意識,打死了朱利安。
這兩部影片都涉及商業化交互性娛樂的倫理問題。在娛樂業,設立影片中所描寫的那一類游樂場或度假勝地,讓游客去那兒放縱自己,這在倫理上是允許的嗎?機器人固然是生物人所發明、制造并批量生產的,但人類是否應當尊重“它們”轉變“他們”之后所應享有的權利呢?如果機器人不僅具備人的外形,而且擁有與人類似的心理,人類卻只是將他們當成異類看待,只是因為他們在構成身體的材料上與自己不同,便鄙視和虐待他們,甚至以殺戮為能事,這樣的局面能夠維持下去嗎?根據《孟子·梁惠王上》的記載與看法,“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當年以土偶象征活人埋進死人墓中,究竟是導致后來形成以活人殉葬的惡劣風氣、以至于孔子要咒他們斷子絕孫,或者是用替代品殯葬挽救了生殉者的性命、以至于孔子要反駁對這種做法的質疑呢?類似的爭論可以為《西部世界》和《幻世追蹤》的解讀提供參考系。譬如,用機器人充當可讓人任意對待(包括殺戮)的招待員,是為社會沖突提供了一種替代性解決辦法(宣泄人們的心理郁結)而值得肯定,或者是為社會暴力提供了一種示范性教唆途徑而應予譴責呢?類似問題都值得思索。
在以機器人游戲為題材的科幻電影中,美國驚悚片《未來世界》(Futureworld,1976)所選取的是另一種角度。它描寫機械人樂園重新開張,兩名媒體記者應邀前往考察,結果發現園方克隆游客(其中包括各國領袖)送入社會,以圖控制世界的大陰謀。影片中的克隆體的生產基礎由電子機械轉移到生物科技,關注取向從游樂場內部轉向外部世界,引導人們從化身或代理的角度思考生化機器人所可能發揮的社會作用。這部影片使人想起12世紀流傳于日本的佛教言論集《撰集抄》關于巧匠師仲將所制造的機器人送入社會扮演不同角色的描寫,以及今天在移動互聯終端中比比皆是的智能程序,還有游戲玩家對角色的操控,等等。未來智能機器人既可能根據覺醒了的自我意識而行動,也可能僅僅根據操控者的授意而行動,同時還可能根據多種意志、意愿以及情景性刺激的誘導而行動,這無疑增加了多元共生時代社會互動的復雜性。
3. 外星人游戲
外星人是科幻電影的重要題材。有關想象大致沿著下述思路展開:將宇航視為地球人轉變為外星人的途徑,將地外智能探索、外星自身危機和宇宙環境變動等當成外星人前來地球的契機,將地球人想象成外星人后裔(或者相反)。所謂“外星人游戲”至少包括如下不同含義:讀為“外星+人游戲”,指地球人在外星上所參與的游戲,地點就在外星;讀為“外星人+游戲”,指外星人所參與的游戲,事件發生在地球上;讀為“外星+人+游戲”,地點可能在不同星球之間切換。
在第一種意義上,美國《無限拘禁》(Slave Girls from Beyond Inf nity,1987)將兩個少女置于異星,構思了她們所邂逅的活死人軍隊制造者與之進行的貓鼠游戲。英國電視系列劇《神秘博士》(Doctor Who)系列一的第七集《無盡的游戲》(The Long Game)將地點定位于公元20萬年人類第四帝國時代的太空站,描寫此處人類都被改造成電腦,夢想能進入第500層生活,其實是中了外星人設下的圈套。
在第二種意義上,美國《人們》(The People,1972)主人公阿默森到邊遠地區支教,發現自己所面對的是因母星遭到自然災害而被迫移民地球的外星人群體。這些人曾被地球人當成巫師而遭到虐殺,幸存者不僅不敢使用自己的超能力,甚至不敢接受阿默森所提議的所有玩笑、游戲與活動。相比之下,美國《鐵血戰士》(Predator,1987)描寫了強勢外星獵手在中美洲對地球人加以跟蹤、耍弄與虐殺;其續集(Predator2,1990)定位于1997年,題材仍然是外星獵手和地球人玩貓鼠游戲,地點改到洛杉磯。
在第三種意義上,美國電視片《ALF事業》(Project: ALF,1986-1990)描繪了Melmac星球上的人玩的游戲Bouillabaisseball。它是以海產品為球的冰上游戲,可稱為“海產什燴球”。美國《獵人獵物》(Hunter Prey,2010)描繪了來自兩個不同星球的人在第三個星球的貓鼠游戲,事件涉及他們各自的母星。
現階段的宇航科技、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都還未能證實(或證偽)外星人的存在。因此,外星人純粹是人類通過想象為自己設立的他者。與此相應,“外星人游戲”實際上是地球人游戲的映射。例如,美國作家康奈爾(Richard Connell,1893-1949)的短篇小說《最危險的游戲》(The Most Dangerous Game,1924)受當時流行于非洲和南美的大獵物狩獵的啟發而寫作,描寫來自紐約的一位獵手跌下游艇,游到加勒比海的一個孤島,在那兒成了一個俄國貴族的獵物。與此類似,美日合拍的電視片《最后的恐龍》(The Last Dinosaur,1977)將巨獸獵人(big-game hunter)當成主人公。美國電視劇《不可思議的綠巨人》(The Incredible Hulk,1977)第三季中的《陷阱》(The Snare)也是受這一短篇小說影響而創作的。美國電影《無限拘禁》(1987)將上述故事的背景轉移到外星人世界,據此構思了作品的基本框架。在這類作品中,地球人所面臨的社會矛盾、謀生技能和應對策略等要素都映射于和外星人的關系。
在社會構成的意義上,科幻世界以多元共生為特征,真人與類人、原版人與克隆人、純種人與變種人、機器人與電子人、地球人與外星人等并存而互動。上述電影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人們對相關社會沖突的憂思。不論是人造人無法恰當把握游戲場景而造成無辜者死難,還是電視媒體出于提高收視率、轉移注意力等動機而轉播各種殺人游戲,或者生物人與機器人在游樂場玩無節制游戲、異源生物在不同星球進行貓鼠游戲,都彌漫著某種惡托邦情調。我們與其相信類似事件將來一定會發生,還不如認為相關影片展示了事物發展應當避免的某種可能性。
二、 產品層面:賦魅效果的揭示
在科幻視野中,游戲不只是活動,而是可定型生產的產品。這一意義上的游戲可以追溯到玩具的起源。玩偶至遲在距今約五千多年的古埃及就已經出現。古波斯、古希臘、古羅馬等古文明都有玩具出土。我國的陶制玩具、響鈴、風箏、七巧板等都堪稱歷史悠久。科幻影視中的游戲產品繼承了淵源有自的玩具傳統,美國《勇敢者的游戲》(Jumanji,1995)中吐出異象改變玩家人生的棋盤、其續集(Zathura,2005)中打印卡片言事成真的跳棋便是很好的例子。美國電影《魔力玩具盒》(The Last Mimzy,2007)構想了游戲產品的新來源:外星人將高科技手段偽裝成玩具,以求影響地球兒童。這類想象并非全無現實基礎,因為我們確實已經進入科技化、電子化、數碼化游戲產品流行的時代。在豐富多樣的游戲產品中,科幻影視對于街機游戲、單機游戲和網絡游戲格外關注,而且對其賦魅效果予以前瞻性思考。
1. 街機游戲
最初的電腦游戲出現在美國高校實驗室的大型機上(1962)。197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生開發出太空戰模擬游戲《星際飛行》(Spacewar)的投幣版《銀河游戲》(Galaxy Game),為街機游戲開了先河。當年晚些時候,美國工程師布什內爾(Nolan Bushnell)為一家名為Nutting Associates的教學儀器公司開發出大批量生產的街機游戲《計算機空間》(Computer Space)。從此,這類游戲逐漸在酒吧、游樂園等場所流行開來,并成為科幻電影的描繪對象。例如,美國《陰陽魔界》(Twilight Zone: the Movie,1983)由四個短片組成。其中,出現在《這是好生活!》(It's a Good Life!)的人物安東尼便喜歡玩街機游戲。很奇怪,他拍拍游戲機就能干擾電視所播出的場景。
美國《最后的星空戰士》(The Last Starf ghter,1984)簡直就是街機游戲的宣傳片,所描寫的是玩家羅根受發明者邀請進入游戲對應場景,因此暢游太空,在外星人領航員格里格訓練之后成為打敗帝國、拯救星盟的英雄,受邀協助重建。他們駕駛自己的槍星號回到拖車公園,格里格向其家人及鄰居講述了羅根的英雄事跡。其弟弟受到啟發,想走哥哥的道路,開始玩《星空戰士》。相比之下,美國《逃離魔幻腦》(Arcade,1993)則包含了對街機游戲消極影響的警覺和批判的話。它提出了兩個超乎目前街機游戲實際可能性的問題:相關產品能夠應用真人腦細胞嗎?游戲玩家的靈明會被困于其間嗎?這部電影對它們的答案都是肯定性的。根據其描寫,某計算機公司為使所開發的游戲中的壞蛋更加真實,將一個被其母親打死的小男孩的部分大腦細胞用在他身上,由此推出名為“游樂場”(Arcade)的街機游戲。這款產品導致一些玩家失蹤或喪命。主人公歷盡波折,好不容易才取得開發上述游戲的程序員的幫助,將朋友從虛擬囚禁中解救出來(但同時也釋放了惡棍小男孩,留下隱患)。
2. 單機游戲
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隨著蘋果電腦和PC先后問世、多媒體技術日益成熟,電腦游戲產品逐漸從大型機、街機向臺式機、手提電腦、掌上電腦、平板電腦和嵌入式計算機遷移,社會上對游戲成癮危害性的擔憂不斷增長,這成為相關作品構思的契機。
根據美國電影《六度戰栗》(Brainscan,1994。又譯《腦波掃描》)的描寫,少年布勞爾獨自生活在已經過世的雙親留下的房子里。他經小伙伴介紹接觸到一張神奇的游戲光盤,晚上運行后體驗到殺人的刺激,而且,第二天他從電視新聞中得知被自己所殺的男人真的死了。他驚懼地想洗手不干,但有人將第二張光盤寄來,脅迫他再玩,布勞爾已經分不清虛實,被游戲中的魔術師所擺布……還好他醒來后發現先前的經歷只是夢。第二天,他將光盤帶到學校展示,但魔術師出乎意料地出現于光盤播放前,說明先前的經歷又不是夢。這種亦幻亦真、撲朔迷離的描寫雖然不無夸張之處,但從總體上吻合電子游戲所產生的心理效果。事實上,電子游戲之所以使人著迷,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通過人機互動提供了行為主義心理學所說的操作性條件反射。游戲場景設置明明是虛擬的,玩家的行為卻可以獲得確實可感的反饋,這令人欲罷不能。
與通常安裝在游樂場運行的街機游戲不同,單機游戲滲透到廣闊的社會空間,因為其載體(磁盤、光盤或磁光盤)可以相當方便地復制。俄羅斯影片《超能游戲者》(Na igre,2009)據此構想了如下情節:季馬等年輕人在電子競技中獲勝,贊助商給他們每人一張超能游戲“反恐精英”光盤。他們看了之后變成超能戰士(代價是電腦燒了)。開發商要他們干壞事,先是去爭奪鈀元素,為此殺人(代價是自己人也死了一個)。這樣的超能戰士可以通過看游戲光盤大量制造。因此,季馬等人面臨這樣的抉擇:是毀了這些光盤,還是創造一支超能游戲大軍并統治世界?這些青年因此分裂。季馬本人所選擇的是前者,其同伴博士和揚選擇的是后者。開發商要把十萬張光盤從水路運到外地去賣,季馬去攔截,但遭到博士和揚的綁架。這兩個家伙準備將他和船一起炸掉,還好季馬逃了出去,在女友幫助下襲擊游戲基地。博士、揚殺死開發商后想逃跑,但遭季馬阻止,最后為官方特種兵所逮捕。《超能游戲者2》(Na igre 2. Novyyuroven,2010)講述的是獲得全國電子競技冠軍的幾個年輕人卷入沃特斯公司陰謀的故事。這家公司以組織電子競技為名義培育自己的武裝力量,企圖從政府手中奪取核力量控制權,推廣具備激發超能力的光盤就是實現野心的途徑。
上述影片問世的時代,始于1986年的電子競技已經風靡全球,不僅作為正式的體育賽事為官方所認可,而且已經變成不少年輕人的職業選項。雖然還沒有某種游戲光盤能夠使玩家獲得超能力,但電子競技確實有使人的心理能力定向化、專門化的功效。以此為背景,《超能游戲者》觸及了玩家在游戲之內的角色扮演和在游戲之外的社會擔當之間的關系。
3. 網絡游戲
多用戶地牢游戲(Multi-User Dungeons,MUD,1979)的問世標志著網絡游戲的起步。從那時以來,由于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迅速發展等原因,網絡游戲由附庸蔚成大國,引發廣泛社會關注,并從社會現象轉變為科幻題材。
網絡游戲具備比街機游戲和單機游戲更廣泛的共享性、更靈活的可塑性、更豐富的擴展性。正如曾經流行一時的口號“網絡就是新生活”所展示的,移動互聯網絡不只是媒體,而且是具體可感的生活空間,在科幻界看來,網絡游戲也不只是尋常的文化產品,而是居住著各種生命體的世界。關于網絡虛擬生物的科幻電影就是這樣產生的。例如,在意法合拍的《超靈境界》(Nirvana,1997)中,虛擬現實游戲設計師杰米發現自己陷于兩難境地:一方面公司催著要交貨,另一方面游戲主要人物梭羅因遭受電腦病毒侵襲而有了感覺(自我意識),對無休止的打打殺殺感到厭倦,要求消滅它的存在。他開始從其雇主的服務器上刪除這款游戲,以免梭羅再痛苦。這樣,游戲就無法按計劃在圣誕節發布了。自從妻子麗莎離開自己之后,杰米一直感到壓抑。他黑入公司服務器之后,處于虛擬現實之中。網絡為保護自身,投射出杰米的父親與麗莎等虛擬呈現,試圖在黑客記憶中形成閉合回路以燒毀其大腦。杰米成功擺脫種種幻象,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目標上,這就是找出公司的賬號。他突然豁然開朗,成功刪除了梭羅,接受了麗莎離開自己的事實。
網絡游戲和單機游戲一樣有令玩家上癮的危險。對此,日本《網絡殺人游戲》(Avalon,2001)有所反映。它將令年青人如癡如狂的模擬戰斗游戲場景稱為傳說中亞瑟王及其圓桌騎士長眠的美麗小島阿瓦隆。在另類宇宙中,許多人被誘惑到那兒,作為單一或結伙的玩家襲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敵人以及對立用戶。贏者可以得到賽點或可兌換現金的游戲幣,這讓熟練玩家有條件以此為生。當他們的大腦與游戲直接交互時,阿瓦隆對玩家施以有效的精神束縛,使許多人因此得了緊張癥。游戲包含了悖論:它是迷人的,但若過度,玩家就會因大腦受損成為廢人。類似的現象見于美國喜劇片《熱浴盤時光機》(Hot Tub Time Machine,2010)。其中的雅各布宅得不行,一把年紀還整天沉迷在電子游戲里。
當然,對于游戲產品的作用不能籠統地否定。在我國臺灣出品的《黃金島歷險記》(1996)中,電子游戲機迷朱事丁因玩所拾到的電腦光盤而被吸入游戲世界,和游戲中的人物打斗。父母和哥哥在尋找他的過程中意識到親情的重要性,改變了過去對他不管不顧不體貼的態度,冷漠的家庭趨于和睦,結果是喜劇性的。在美國《安德的游戲》(Ender's Game,2012)中,天才兒童經過游戲訓練成長為艦隊司令,并通過游戲對抗消滅了對地球構成威脅的異星蟲族。這些都是對游戲產品正面作用的肯定。從藝術構思的角度看,游戲產品成為某些科幻電影組織情節、塑造人物的切入點。例如,美國《異星兄弟》(The Brother from Another Planet,1984)中的外星來客幫地球人修好游戲機,展示了他善良熱情的一面;《記憶裂痕》(Paycheck,2003)的主人公詹寧斯在被迫清除特定時段記憶之后從填字游戲的剪報找到自己事先留下的提示,從而啟動讓可能危害人類的未來預測機器自毀的觸發機制。
三、 運營層面:混合現實的構想
時至今日,游戲不僅作為活動、產品而存在,而且已經融入環繞著我們的環境,并作為我們適應環境的方式而發揮作用,被廣泛應用于兒童教育、職場提升、心理治療、軍事訓練、消費經濟等領域。它大致可以分為真人游戲、電子游戲和混合游戲三大類。相比之下,真人游戲主要在現實空間進行,電子游戲主要在虛擬空間進行,混合游戲則跨越現實空間和物理空間的界限。第三類游戲的技術基礎是方興未艾的混合現實(MR)。在科幻影視中,我們可以發現范圍更為廣泛的現實混合,其表現主要是虛擬世界相互滲透、直實世界彼此進入、分化世界多方博弈。
1. 虛實世界相互滲透
關于真人進入計算機化虛擬世界的描寫,在美國《電子世界爭霸戰》(Tron,1982)中就已經出現。這是第一部探索虛擬現實理念的主流影片,并因率先采用計算機動畫而名垂史冊。它描寫了發明家、軟件工程師弗林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化身潛入計算機系統尋找對手剽竊證據。在西班牙《睜開你的雙眼》(Abrelosojos,1997)中,以愛情游戲為樂的主人公西薩見到夢中情人,為此和前女友發生糾葛,兩個女子居然可以相互切換,這正是虛擬現實夢境的奇跡。加拿大驚悚科幻片《感官游戲》(eXistenZ,1999)不僅描寫了基于虛擬現實游戲的多重現實,而且揭示了相關游戲公司之間的競爭。在影片中,還有一群現實派反對這些公司,因為它們使現實變形。英國《夢魘迷宮》(The Kovak Box,2006)則描寫科幻小說作家落入陷阱,變成作品中的角色,進入夢魘般的游戲。我國《神奇》(2013)將情節重點設置于游戲測試員進入虛擬世界之后和虛擬姑娘之間的戀情上;《時光大戰》(2015)所關注的是超級玩家穿越到虛擬的游戲基地之后如何為追回被偷獵的時光而戰斗;《瘋狂電玩城》(2017)則設想游戲設計師董安進入虛擬空間拯救作為試玩者被困在那兒的上司安娜。
在科幻影視中,與真人進入游戲虛擬世界相比,描寫游戲虛擬角色進入現實的作品數量較少,但也有一些。例如,美國《時空悍將》(Virtuosity,1995)構想了警用訓練機中的殺手進入現實作惡的情節。《電子世界爭霸戰》(Tron,1982)的續集《創-戰紀》(Tron: Legacy,2010)寫七年后的事情,重點之一是游戲里野心勃勃的獨裁程序想沖出來。它向程序軍團發表演講,讓它們殺向現實世界,但沒有成功。印度《超世紀戰神》(Ra.One,2011)所描寫的游戲中的魔王卻如愿進入了現實世界,不僅追殺玩家普拉提,甚至還殺了其父親(這款電玩的設計師)。普拉提只好從游戲中召來超級英雄勇者對抗它,結果魔王與勇者同歸于盡。
若論虛實世界雙向滲透的話,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電視片《邪惡電玩帝國》(How to Make a Monster,2001)。據其描寫,由于恐怖游戲的開發者將先進的人工智能芯片插入主機,加上閃電的意外影響,使得本用以讓玩家體驗虛擬實境的動作捕捉套裝變成現實環境中的活物。它和虛擬世界中的怪物彼此感應,對人類用戶大打出手,殺死了這款恐怖游戲的三名開發者。為了消滅它,人們必須同時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作戰。
2. 真實世界彼此進入
真實世界彼此進入至少有三種可能:一是平行世界之間的穿越。例如,日本柴田一成執導的《真實魔鬼游戲》(Real Onigocco,2008)根據山田悠介的同名小說改編,構思來自兒童常見的捉迷藏或抓人游戲,以平行穿越、滿街狂奔為特色。這種穿越不發生自然位置上的變化(穿越前后都在日本同一時代、同一地點),變化原因主要在于社會位置(最高統治者換人,發布了除掉姓佐藤的人的命令),由此弄得人心惶惶(心理位置變化)。二是不同空間之間的穿越。例如,在美國《像素大戰》(Pixels,2015)中,外星人接到地球人發送到太空中關于街機游戲的錄像資料,以為地球人要向他們宣戰,就反轉過來將游戲中的吃豆人、蜈蚣等實體化,將它們派來攻打地球人。美國總統在軍隊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只好請童年時代的街機戰友、高手布倫納等出馬應對。布倫納如今是上門裝平板電視的工人,想追求其客戶帕頓中校(她剛剛被丈夫拋棄),卻因身份差異被拒絕。不過,在聯手對付8像素外星人的過程中(帕頓是負責提供激光炮等專用武器的專家),事情有了轉機。三是不同時間之間的穿越。如美國《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以1964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當下迪士尼樂園和劫難之后明日世界為背景,揭示了主人公歷盡劫難的感悟。
3. 分化世界多方博弈
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代表了數碼現實開發中兩種相反的取向,亦即引導用戶走向具備沉浸性、想象性與交互性的虛擬世界,或者以批判性、自覺性與獨立性為特征的現實世界。所謂“混合現實”(MR)則是它們的統一或折衷。在多倫多大學工業工程系米爾格拉姆(Paul Milgram)等人給出的定義中,“混合現實”是指虛擬性連續體介于完全真實和純粹虛擬兩極之間的任何定位(1994),包括靠近真實環境的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靠近虛擬環境的擴增虛境(Augmented Virtuality)。雖然有不少人同意他的分類,但日本混合現實系統實驗室公司山本博之卻表示反對。他認為不應從區分主次的角度來考慮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混合或結合,“增強現實”與“擴增虛境”之間沒有清楚的界限。因此,他主張直接使用“混合現實”這一概念(1999)。我們傾向于將混合現實理解為沉浸性與批判性、想象性與自覺性、交互性與獨立性之間的統一,2016年熱播的美國電視劇《西部世界》(The Western World)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這部美劇所描寫的事件發生于未來以生化機器人充當招待員的游樂場(主題公園)。對于園方來說,為游客所提供的一切幾乎都是虛擬的,不用說假山、山寨版小鎮,連外觀與真人無別的招待員也是假人。園方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的開發、管理與經營活動都是基于批判的、自覺的、獨立的思考。對于招待員來說,他們感覺自己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現實的,從飲食起居住行,到被罵被打被殺。園方不僅為他們安排了活動場景,而且將特定角色的記憶植入其大腦中,因此,他們沉浸在園方所設定的情境中無法自拔,將園方通過想象為自己設定的腳本當成自己真實的生活經歷,以為園方通過無縫移動通信下達的交互性指令就是自己的獨立意志。對于游客來說,他們將這家主題公園所提供的服務當成混合現實來接受,其心理定位在純屬虛擬和全然現實兩極之間移動。他們越是從虛擬的角度看待這些服務,就越有可能無所顧忌地放縱自己的欲望;他們越是從現實的角度看待這些服務,就越有可能根據社會規范約束自己的言行。這部美劇從園方、招待員和游客三方博弈來展開敘事,最終歸結于生化機器人的覺醒,亦即其心理實現了指向批判性、自覺性和獨立性的質變。在此之前,他們被園方所控制,以為游戲空間就是自己的生活空間;在此之后,他們擺脫了園方的控制,要為自己開拓真正意義上的生活空間。作為觀眾,我們可以從現實的角度將這部美劇當成是某種諷喻(因為控制、反控制和失控是真實生活中的常見現象),也可以從虛構的角度將這部美劇當成是某種前瞻(因為由生化機器人提供服務的游樂場畢竟還沒有問世)。
我們不僅可以從科幻影視的視野分析游戲,也可以反過來做,由此產生了新的選題“游戲視野中的科幻影視”。從后一角度看,下述現象是值得注意的:(1)游戲被某些科幻影視作品作為題材來源。例如,《超級馬里奧兄弟》(Super mario bros,1993)、《坦克女郎》(Tank Girl,1995)、《毀滅戰士》(Doom,2005)、《超級戰艦》(Batteleship,2010)、《波斯王子:時之刃》(Prince of Persia:The Sands of Time,2010)都取材于同名游戲。《極度深寒》(Deep Rising,1998)是與游戲并行的科幻怪獸電影。反過來,《阿凡達》(James Camerons Avatar: The Game,2009)是與同名電影(Avatar,2009)并行的游戲。《最終幻想:圣子降臨》(Final Fantasy VII Advent Children,2005)則與先前的角色扮演視頻游戲《終極幻想7》(Final Fantasy VII,1997)相銜接。(2)游戲可以充當科幻影視情節設計的參照系。例如,法、美合拍驚悚片《源代碼》(Source Code,2011)采用了與游戲類似的通關設計,描繪瀕死的史蒂文上尉如何利用生前最后八分鐘積累經驗,最終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又如,美國《但丁密碼》(Inferno,2016)設計了類似于尋寶游戲的線索。(3)游戲可以充當科幻影視情節的組成部分,為塑造人物、豐富內容服務。例如,美國《千鈞一發》(Gattaca,1997)描寫游戲明星作為遺傳工程所造就的精英莫羅幫助純種人弗里曼實現夢想。在《黑客帝國3:矩陣革命》(The Matrix Revolutions,2003)結尾,建筑師在公園中遇到了先知,說她玩的這場游戲太危險了。先知說要改變就會有風險。在《時間規劃局》(In Time,2011)中,小混混要同主人公威爾玩“清零”游戲,威爾勝了他,才逃過一劫。這類內容雖然只是細節,卻增加了作品的意蘊。類似的例子有加、英、美、日合拍的《裸體午餐》(Naked Lunch,1991)、日本《殺戮都市》(Gantz,2011)等。(4)游戲可以引導觀眾對科幻影視進行鑒賞。例如,我們可以將美國《香草天空》(Vanilla Sky,2001)之類科幻懸疑電影和猜謎游戲類比,把握其構思的巧妙,尋找釋疑解謎的路徑。有一些影視作品雖然以“游戲”為標題,也有某些科幻成分,但主要情節和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游戲無關。例如,《火花游戲》(Sparks,2013)以隕石輻射導致某些受其影響人產生超能力為前提,構想了超級惡棍與超級英雄之間的種種沖突;《幻體:續命游戲》(Self/ less,2015)以跨越身體的意識移植為背景,講述身患癌癥的老富翁采用科技手段重返青春、開啟不死模式。這兩部美國影片標題中的“游戲”都是漢譯時加上的,意圖似乎是讓觀眾不要將其中的科幻內容看得太認真——“火花”是影片主角斯帕克斯姓氏的意譯,此人的超能力來得莫名其妙;“續命”是將自己的意識通過醫療過程傳輸到他人身體上,這種做法顯然既為人倫所難容,又缺乏科學根據(至少在現階段是如此)。
20世紀中葉以來,由于以計算機為龍頭的信息革命的引領,游戲產業嶄露頭角、標領風騷,成為創意經濟的重要支柱,相關產品在社會生活、文化交流等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們對其影響毀譽不一,對其前景同樣眾說紛紜。科幻影視將游戲納入自己的題材范圍,以前瞻性或推謬性思維展示其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并依據編劇、導演和制片人等相關人員所持的社會規范、審美理想和價值觀念予以評價,客觀上起了激濁揚清的作用,具有教化功能。除此之外,游戲題材的科幻電影至少還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將游戲本身當成哈哈鏡或照妖鏡,通過科幻展示人性、人情、人心的隱秘,或者引發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具有認識功能;二是將科學假說、技術設想等作為游戲和科幻彼此溝通的結合部,具有交流功能。正因為如此,這類文化產品值得深入研究。
黃鳴奮: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史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