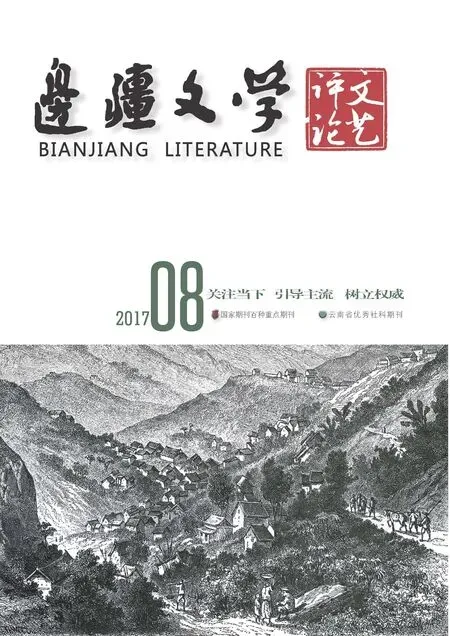兒童文學的疼與癢
尹宗義
兒童文學的疼與癢
尹宗義
兒童文學是用兒童的眼光看世界,用兒童的心靈感受生活,用兒童的語言講故事。它喚醒童心,激起童趣,激發好奇心與求知欲。但現實中的兒童文學作品,種類繁多,但精品不多,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太少;即使是那些非常暢銷的兒童文學作品,在光芒背后也有不少陰影。原因何在?童薇菁認為,一些兒童文學作家“缺乏對生活的體察,缺乏對孩子性格的關注,無法創作出真正的兒童喜歡的作品。”(《創作兒童文學先要弄清孩子要什么》)
從兒童文學發展脈絡來梳理:過去,傳統的兒童文學作品思想教育色彩太濃,削弱了趣味性、可讀性;現在,兒童文學作品的商業化氣息太濃,工夫花在詩外(包裝、插圖、印刷、炒作等)。特別是一些非兒童文學的作家涌入,為搶占兒童文學市場的一席之地,創作了一些主人公雖是孩子,但語言、情感、思想還是成人的作品;雖然他們憑借原有的名氣,確保所謂的兒童文學作品也能暢銷,但沒有童心的創作,只是模仿孩子的口吻,除了滑稽可笑外,真能留給孩子的東西并不多。
一、思想的外殼與內涵
在中國特有的文化思想土壤里孕育的兒童讀物,比如朱熹的《小學》、肖漢沖的《龍文鞭影》、程允升的《幼學瓊林》等,以教化為主要目的;誕生于黑暗現實的兒童文學作品,關注苦難,批判現實,比如:張天翼的《禿禿大王》《金鴨帝國》、陳伯吹的《阿麗思小姐》、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深陷政治斗爭愈演愈烈的泥潭,許多兒童文學作品成為政治附庸,淪落為政治家教化孩子的工具,文學色彩蕩然無存。
擺脫了教化與政治色彩,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一些作家為了占有市場,一心想創作出暢銷的兒童文學作品,便竭盡所能地取悅兒童,讓兒童獲得短暫歡愉,卻忘記了肩上的使命——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比如:楊紅櫻作品雖然比較暢銷,但只能算是“商業化的暢銷”,并非是“文學的暢銷”,因為她的“作品文學味淡,文學表達不夠深刻、細膩,作品缺乏審美高度和永恒性,人物性格卡通化,故事結構‘圖像化’,其作品的閱讀‘通俗化’,缺乏文學閱讀應有的深度和難度。”
為了取悅兒童,一些兒童文學作家專注于孩子癡迷的話題,比如:魔幻、征殺、游戲、競爭、背叛、戀愛、欺騙……兒童文學的禁區在一步步地被打破。比如:比較暢銷的《查理九世》,一套共21本,擺在書店最顯著的位置。但作品的文字比較陰森,常常描寫幽靈,死尸,殺人魔團體,人骨教堂等等血淋淋的場景——“他們在這里把人秘密殺害,剝下來的皮肉當飼料,神不知鬼不覺的就把尸體處理掉了,這個房間就是殺人房。”讀這樣的句子,成年人都感到不寒而栗,那么,對于孩子的身心,必然產生負面的影響。
從兒童本位觀的角度分析,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充滿童心、童情、童趣,著重于兒童性格和精神的重建。兒童文學應該有禁區,對性經驗、暴力事件、網絡游戲、消極頹廢等等不適合兒童的身心健康的內容,必須回避,更不能著力渲染和描寫。另外,一些隨意篡改經典名著,無論是大話名著,還是水煮經典,都一味追求時髦、麻辣,故意制造搞笑、幽默,根本不顧及原著的精神意蘊。如果讓孩子讀這樣的讀物,不但領略不到經典名著的文學與文化的獨特魅力,而且孩子的心靈還會被污染。這種文化污染,很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長。
閱讀楊紅櫻的《一只會笑的貓》,在折服于作家豐富想象的同時,也感覺作家通過一只會笑的貓竭力張揚個性——因為其他貓不會笑,他們就看不慣笑貓,看見笑貓笑就生氣。所以,笑貓就不跟他們來往,甚至下結論:“在我的同類里,我并沒有好朋友。”其實,笑貓也沒有真正異類朋友——雖然京巴狗“地包天”每天都在電梯口等著它,整天陪著它,但它心里很看不起京巴狗,嫌棄京巴狗口臭、記憶不好。作家這樣教孩子與人相處,難道沒有錯嗎?孤立的絕對的個性是有弊端的,必須與共性辯證統一起來,才能真正促進人性健康發展。
雖然反對兒童文學淪落為思想性、教育性、階級性的工具,但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娛樂性、消費性、市場化、個性化。過由不及,都是不正常的。只有機地將兩方面結合來,在輕松有趣的閱讀中,讓孩子潛移默化地受到思想、品德方面的啟發和教育,以及情感、情操、精神境界等方面的感染和影響,最終幫助孩子健康成長。
二、作家的模仿與童心
“兒童文學言說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成人對兒童的訓誡性言說,成人對兒童的想象性言說,游戲精神下兒童的自我言說。”如果作家是以訓誡孩子的方式創作,就不可避免地注入成人思想,必然削弱了孩子天性中的愛游戲、愛求知、愛趣味、愛幻想的內容。總之,兒童文學說理太多,離兒童的距離就更遠了。
如果作家憑借自己的童年記憶,加上實現的觀察,通過想象、聯想,俯下身子,試著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眼睛去看世界,以兒童的心靈去體驗生活。但由于這些作家并不是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家,沒有一顆真正的童心——只有一顆人為培養起來的假童心,只善于裝萌,裝幼稚,裝可笑,拿腔捏調地模仿兒童口吻講故事,流露出矯揉造作的孩子氣和娃娃腔。就像一些少兒電視節目主持人,一大把年紀了,還裝童音,裝幼稚,裝萌,只會讓人感覺滑稽可笑,渾身起雞皮疙瘩。
成人創作兒童文學作品,主要是從自身的童年回憶入手。這些內容對于作家來說,印象深刻,寫起來得心應手。但是,作家如果一直采用這種方式創作,必然會犯情節雷同的錯。比如:曹文軒的小說,總喜歡寫主人公經歷各種各樣的苦難,堅強地成長起來的。讀《青銅葵花》時,孩子會被葵花不幸人生感動,同情不止;再《阿雛》,悲憫之心上就形成了一層免疫膜,對阿雛失去雙親的痛,不再像葵花失去親人那樣疼痛了。如果這樣的情節,這樣的感情再循環下去,免疫就不再是一層膜,可能變成一層厚厚的繭子。
敘說童年經驗,滿足自身回憶意愿,流露私人情緒。從當下兒童接受的角度看,生活狀態不同了,價值觀改變了,過去的主旋律是否還能在孩子心里奏響,還是一個未知數。曹文軒喜歡寫悲傷和苦痛的童年生活,并認為“兒童文學苦難閱讀不可缺”。其實,從趨利避害的本能看,沒有人會追求苦難。苦難本身并不是財富,并不值得炫耀。只是處于苦難人樂觀地辯證地認為苦難也不是壞事,自我安慰,自我激勵罷了。生活在幸福懷抱里的孩子,真的讀得懂苦難人生與悲慘生活嗎?從傳遞正能量的使命看,過多灰色的東西,對于孩子的健康成長,也是極不利的。比如:《阿雛》的灰色元素——沒有人在意阿雛父母的生死,民眾的麻木讓阿雛從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不信任別人的種子。又比如:《甜橙樹》《紅葫蘆》等作品的憂郁的色彩——童年的孤單、父親是遠近聞名的大騙子。如果作品是一面反光鏡,負能量的東西折射出來的還是消極的,并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遵循負負得正的原理。灰色的東西太多,還會沖淡兒童文學是快樂的文學的色彩,變成悲愴文學、死亡文學,與生命文學就越來越遠了。
真正算得上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家,葆有一顆純正的童心,不但能俯下身子,還能用心、用情觀看、聆聽、感悟兒童的心靈顫音,以審美的姿態去書寫兒童世界的喜怒愛樂。這樣的作品,用真情打動孩子的心,用美去陶冶孩子的靈魂,對他們進行情感教育、愛的熏陶。最富有愛心、童心的冰心,創作的通訊系列《寄小讀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兒童文學的一部代表作。“《寄小讀者》各個方面的抒寫,給孩子們以感人的愛的教育,使他們從小就得到愛的泉源的滋潤,體味人世間最美好的感情。”她以溫潤清麗的文字,以“愛的哲學”為內涵,通過作品進行“愛的教育”,對“五四”以來的少年兒童成長起用是不可估量的作用。《寄小讀者》的成功,源于冰心熱愛孩子的心,源于她始終懷有一顆童心。
三、內容的時代感與前瞻性
大江健三郎說:“許多人都認為是生活在現在,生活在當下,其實不然,我們吃飯、工作、行走、寫作,都是為未來做準備。”作為兒童文學的主要讀者——孩子,他們不僅活在當下,更應該活在未來。他們現在只是經大人的身體這個通道,來到這個世界,通過成人的世界走向未來。如果孩子閱讀的只是作者的童年生活——過去的生存狀態,這些內容與活在當下的孩子不僅存在較大的距離。讀者的生活基礎與情感元素與作品的思想內容沒有相似性,閱讀時否能產生共鳴,還值得商榷。比如:曹文軒憑借豐富的童年經驗,創作了一部部好作品,塑造了一個個生動形象的兒童人物。他們雖然性格不一,卻與作者的童年經驗與成長背景息息相關。《草房子》里的桑桑養了一群鴿子,其樂無窮。但是,能捧著《草房子》讀的孩子,又有幾個人喂養過鴿子,能從作品中真正感受到童年的樂趣;今天,寫情書的浪漫已經遠去,孩子們不可能再體驗帶大人傳情書的事。桑桑傳情書時的使命感,又有多少孩子能真正讀懂?
相對于生活經驗欠缺、間接接收能力有限的孩子,作品內容呈現的最好是當下生活,盡可能與孩子的生活在一個頻道上。兒童文學作家最應該多創作反映當下孩子生活的作品,應該真誠地走向兒童世界,直接去感受孩子們的生活,了解他們情感、思想,創作出接地氣的作品。比如: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黃蓓佳在創作《你是我的寶貝》時,專門來到南京的培智學校跟孩子們相處,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零距離接觸,才能更好地零距離創作,才能創作出真正適合孩子閱讀的作品。再比如:鄭春華創作《非常小子馬鳴加》時,專門到小學“蹲點”,連續半個月每天和孩子們一起做操、吃飯、上課。鄭春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孩子們上課做小動作她看得一清二楚,下課后她就和孩子交流,了解他們的心理。有了這種貼近孩子的態度,才能真正創作出孩子們愛看的作品。所以,少年兒童出版社副總編輯周晴強調,兒童文學要從孩子中來,到孩子中去。如果兒童文學作家真的走進留守兒童,走近二孩家庭,走進應試教育,或許就能創造一批真正反映孩子當下心聲的好作品,深受孩子的歡迎。
一些作家不但沒有豐富的童年經驗可寫,又不愿意深入孩子當中感受孩子的生活,只是坐在電腦前,寫虛擬的世界、虛擬的童年和虛擬的快樂生活。這樣的作品,如果脫去商業化的外套,剩下的只是瘦骨嶙峋的身子,最終該自行消亡。也有一些作家,知道現在的孩子受玩手機,喜歡打游戲,于是從中去挖掘創作素材,充分運用短信內容、網游話題、網絡惡搞、QQ微信聊天的記錄,再加上一堆流行的符號,一部作品就應運而生了。這樣的作品,雖然與孩子的生活同步,但導向不好,即使暫時暢銷,但良心何安啊!
兒童文學作品不但要關注當下,而且更要具有前瞻性。《窗邊的小豆豆》雖然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但在兒童教育理念方面具有前瞻性。小林校長充滿愛的個性化教育和小豆豆父母有原則的、寬厚的愛,以及來自同學之間的互助互愛,不僅給小豆豆營造了一個幸福的、無憂無慮的童年,引導他健康成長,而且像一把鑰匙,為解決教育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參考,且為現代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兒童文學的內容故事可以過去式,但蘊含在其中的成長精神、發展軌跡、愛的傳遞、正能量的光芒,必須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對于兒童文學作家來說,不僅是一位有愛心、童心的作家,也應該是一位懂得教育學、兒童心理學的“老師”,能肩負起促進孩子健康成長的使命,完成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的教育任務。
說起兒童文學的前瞻性,不得不說一說兒童科幻作品。在科幻的世界里,暢想著未來的生活,展望著明天的世界。但主旋律應該是培育孩子的美好夢想。比如:王功恪的兒童科幻小說《小博士漫游科學王國》“以多元的解讀角度、經典的講述模式、美好的主題關注兒童的夢想,關注中國兒童的未來,成為兒童科幻小說有力的參照坐標,這對當下兒童文學的創作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小博士奇奇”形象相對于“史努比、圣斗士、蠟筆小新、米老鼠”,更具有正義、陽光、博學、聰慧、自強的鮮明色彩,更能激活中國孩子夢想。
由于孩子的生活世界相對局限,更多的時間被束縛在教室、家庭,對于更寬闊的空間,比如天空、高山、海洋、河流、工廠、田野等,相對陌生。因此,兒童文學作家要描寫更寬闊的世界,給孩子自由想象的空間,承擔起開拓孩子視野的使命。
面對兒童文學的疼與癢,我們都可能束手無策,即使暢所欲言,也只是隔靴搔癢。但是,如果能清楚認識到兒童文學的疼與癢,至少在親子閱讀時,可以更好地引領孩子選擇性閱讀;在幫助朋友的朋友推薦閱讀書目時,也可以做到心中有底氣。或許僅此而已罷。
(作者單位:云南省昭通市教育局)
責任編輯:臧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