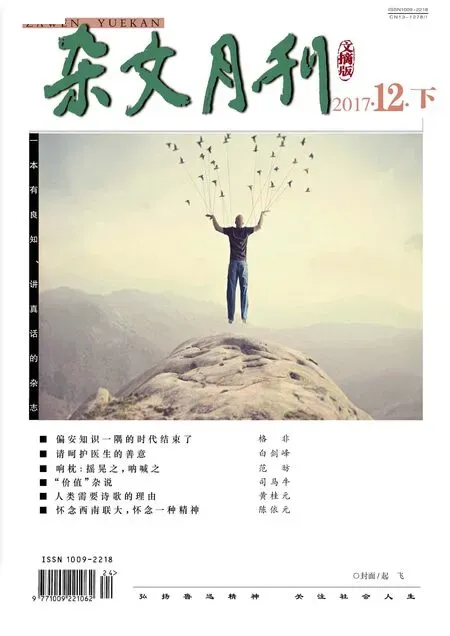石黑一雄:『內臟感到對』
□ 張秋子
諾貝爾文學獎結果的公布,令國內的出版社與讀者群體又一次陷入集體陣痛或集體狂歡中,當年沒有買下石黑一雄版權的出版社陷入哀嘶長鳴,讀者們則紛紛在網絡社交平臺發布狀態,花式展現自己與石黑一雄的“書緣”。同時,人們又都“瞎操心”地開始心疼石黑一雄那位長期跑步、想與諾獎時間競賽的本族人——村上春樹。
當然,石黑一雄只是“萬年陪跑者”村上春樹的同族人,而非同國人。早在1960年,石黑一雄的父親石黑鎮男就被供職的英國北海石油公司派往英國,石黑一雄和母親、姐姐也由此移居英國,從此,居住在倫敦附近的小鎮吉爾福德。那時,石黑一雄只有六七歲。雖然與奈保爾、魯西迪同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但石黑一雄身上那種由身份認同以及族群認同帶來的困惑感并不明顯,他顯然把自己當作地道的英國人,只有在平靜、克制甚至有時顯得乏味的文字風格以及繚繞不散的淡淡哀傷中,我們才能依稀辨別出他的“日本氣息”。而他筆下所書寫的世界圖景同樣展現出一種具有“世界文學”意識的宏闊視野。“世界文學”的概念來自于歌德,這位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一直期待著一個超越民族文學的世界文學的時代降臨。在與他的秘書艾克曼聊天時,歌德說起了正在讀的一部中國傳奇,他發現傳奇中的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德國人一樣,由此也歸納出“人同此心”的結論。石黑一雄的創作無疑是在現代語境中對歌德世界文學理想的實現,他的創作非常多元,主題因而五花八門。
有兩種類型的優秀作家,一種是抓住某個核心與主題,就向下不斷勘探下去,比如上世紀50年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莫里亞克,他的小說不斷在婚姻與家庭的復雜關系中開鑿自我,或是近年獲獎的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強烈的女性身份促使她在短篇小說中不斷探討無常世事中女人的處境。但是,我們很難概括石黑一雄的創作主題,他顯然屬于另一類優秀作家:在經驗世界的各個維度向外奮力突擊,在人文圖景的每個角落都留下痕跡。
因而,我們看到,《長日留痕》中英國貴族官邸中管家的壓抑與克制,我們也看到《別讓我走》中發生在未來英國郡縣的那場器官貢獻者的獻祭儀式,在《遠山淡影》中,主角又變成了日本寡婦與女兒對于安定與新生的渴望,而前年新出版的那部《被掩埋的巨人》中,石黑一雄筆鋒一轉,再次穿越時空,指向了中世紀亞瑟王傳說的歷史現場。用既定的“莊園小說”“科幻小說”“歷史小說”等名詞來規約石黑一雄的創作都是不確切的,因為在“世界文學”心理攸同的暗示下,我們多少還是能發現在名目各異的故事背后,流動著的永恒性思考:普通人與特定歷史場景之間的錯層。
渺小肉身與宏大歷史的錯位造成了無窮盡的因果網,每一次的選擇都造就了弦外之音齊鳴,隱隱聽見那里面有深度有闊度,但又是結結實實的人生的悲哀,有學者認為那些看上去很荒誕的西方民間傳統,卻總讓人覺得有根據,所謂“內臟感到對”。石黑一雄的作品表面總是沉默如水,可撥開水簾,總見得一些實在且有根據的生活的悲哀。